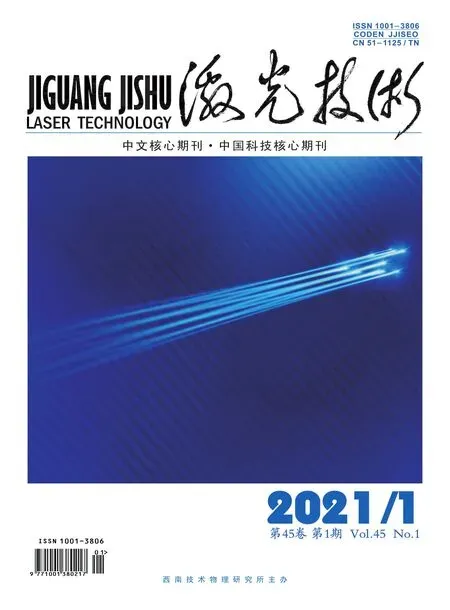激光干擾探測器飽和面積非線性效應研究
郎曉萍,張亞男,李曉英,牛春暉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儀器科學與光電工程學院,北京 100192)
引 言
電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CCD)具有體積小、動態范圍大、抗畸變及靈敏度高等優點,被廣泛應運用在軍事作戰、航天、醫藥診斷和工業檢測等領域。在現代高技術戰爭中,光電對抗作為一種全新的作戰手段在不斷發展和壯大,光電對抗也從傳統軍事力量的一種補充演變為克敵制勝的一種有效手段。在光電對抗中,CCD極易受到激光的輻射干擾,嚴重情況下會導致傳感器無法正常工作,甚至導致傳感器內部結構損壞以及材料的永久性損傷,從而無法再成像。因此,研究不同性能激光對CCD的干擾,對于提高CCD抗干擾性能以及提高我國在光電對抗領域作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外大多數研究集中于紅外脈沖或連續激光對CCD圖像傳感器的干擾和損傷實驗[1-9],部分學者開展了對激光干擾CCD的有限元或其它方式的仿真研究[10-19];其中參考文獻[19]中介紹了“水桶模型”來描述光生載流子的擴散方式,并推導出飽和像元在積分前期數量增長的線性模型,但結果并不能準確描述整個積分過程的非線性關系。
根據激光作用CCD探測器后載流子隨積分時間的非線性增長方式以及載流子在CCD像元間擴散時,超過像元勢阱容量的載流子被CCD特有通道導出的特性,針對已有的“水桶模型”存在的誤差對該模型進行修正,從而獲得符合實際干擾情況的非線性關系,且仿真結果與實驗數據吻合良好,豐富了激光對CCD干擾的研究。
1 CCD工作原理和干擾機理
電荷耦合器件的突出特點是以電荷作為信號,CCD的基本功能是電荷的存儲和轉移,CCD工作過程主要是信號電荷的產生、存儲、傳輸和檢測。CCD的基本單元由金屬柵極、二氧化硅層、半導體硅基底構成,稱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MOS)結構,如圖1a所示。每個MOS單元也就是像素單元,像素單元由P型硅作為基底材料,在P型硅上面氧化極薄一層(厚度約0.1μm~0.2μm),在此氧化層鍍上一層金屬電極,通常稱之為柵極G。將MOS電容接地,與氧化層接觸的硅表面下多數載流子分布基本均勻,如圖1b所示。在柵極與P型硅基底之間施加正電壓V后電勢分布改變,形成一個電子勢阱,用于存儲電荷,如圖1c所示。

Fig.1 Fundamental MOS structure in CCD
當強光照射CCD探測器時,光信號積分時間下,CCD探測器中的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吸收光子,光子能量遠超過帶隙能量從而激發半導體產生大量電子空穴對,稱為光生載流子,載流子中的電子被MOS結構吸引到勢能較低的氧化層與半導體的交界面處,隨著電荷的不斷填充,表面勢收縮,當電荷足夠多時,勢阱被填滿,此時表面勢最窄,束縛的電子達到勢阱容量最大值,于是不再束縛多余電子,電子將產生“溢出”現象。
光生載流子由MOS電容內部產生,MOS電容實際埋溝結構如圖2所示。埋溝的兩邊各有一個比較厚的場氧化物區,形成勢壘溝道。強光輻照CCD,光生載流子在積分初期就可以把勢阱填滿,之后產生的光生載流子則向臨近像元溢流,溢出的載流子向周圍擴散,逐漸填滿周圍勢阱,干擾光斑和串音線由此產生,但是CCD溝道的存在也會排走部分向四周溢流的載流子,從而造成載流子的流失,進而減緩了飽和像元的增長速度。

Fig.2 Buried-ditching structure of MOS capacity
2 CCD干擾的非線性模型建立
2.1 載流子濃度非線性增長理論
可見光激光輻照CCD表面時,CCD將光信號轉化為電信號,理想情況下,如不考慮其它影響因素,若光照不變,光生載流子濃度將隨積分時間t線性增大,但實際上,由于光激發的同時,還存在電子-空穴對的復合,因此實際載流子增長并非完全線性。設t=0時開始光照強度為I。在小注入時,光生載流子壽命τ是定值,被稱為弛豫時間,復合率R=Δn/τ。在光照過程中,單位體積的光生載流子濃度Δn的增加率應為:

(1)
分離變量并積分,利用起始條件t=0,Δn=0,得到方程解為:

(2)
可見,小注入情況下,光生載流子濃度(光電導率)按指數規律上升。當t?τ時,
Δn=αβIτ=Δns
(3)
式中,Q為載流子電荷量,α為半導體吸收系數,β代表每吸收一個光子產生的電子-空穴對數,稱為量子產額,Δn為單位體積的光生載流子濃度,Δns即為光生載流子濃度的定態值[20]。
2.2 載流子擴散模型
根據載流子擴散特點, CCD在受激光輻照時,飽和像元數N滿足如下關系:

(4)
式中,Q0為激光輻照CCD后光生載流子的理想總電荷量,Qth為像元勢阱的電荷量閾值。根據(2)式光生載流子濃度關系式,可以得出理想總電荷量Q0為:
Q0=ΔnSd
(5)
式中,S為CCD受光面積,d為勢阱深度。
把(5)式代入(4)式可得飽和像元數與積分時間有如下關系:

(6)
圖3a為光生載流子擴散分布2維仿真結果。它反映了串擾飽和像元數目分布情況,仿真根據光生載流子擴散速率和載流子濃度成正比的關系,中心光斑處為激光輻射源,為整個積分時間提供擴散的光生載流子,根據CCD像元排布結構特點,即像元在水平方向被溝阻結構隔開,阻礙了載流子在水平方向的擴散速度,因此在仿真過程中載流子在垂直方向上擴散速度大于水平方向的擴散速度,所以可以在仿真結果中看到擴散形成的橢圓光斑和垂直串擾線。圖3a中中心光斑顏色最深,即中心光斑接受的激光能量最高,光生載流子由此被激發出,因此光斑處光生載流子數量最多,CCD的飽和像元最多,載流子填充勢阱并不斷向周圍溢出,距離中心光斑越遠,載流子數目越少,CCD的飽和像元越少,反映到圖3a即遠離中心光斑的位置顏色漸淺;在修正該模型時,考慮到CCD工藝結構中溝道的存在導致一些溢出載流子未來得及擴散到周圍像元便被排出從而使得飽和像元數量增長率降低,進而造成干擾的非線性,因此需要通過對高斯曲線一定通孔半徑范圍內光生載流子積分計算,來補充未參與填充像元勢阱的光生載流子對飽和像元數的影響。

Fig.3 Diffusion distribution of photogenerated carriersa—2-D distribution of carriers b—3-D distribution of carrievs
圖3b 為光生載流子分布3維圖。在圖3a的位置基礎上,對串音線上載流子濃度高低進行形象展現,根據激光能量的高斯分布性質,激光束中心能量最高,占個像素,遠離中心處能量隨距離呈高斯分布,完整的3-D載流子分布圖應各個截面均為高斯分布的鐘形,為了便于計算,這里只截取縱截面進行分析。從圖3b中可以看出,造成“水桶模型”仿真誤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仿真程序中對飽和像元的統計并未考慮CCD溝道排出的載流子,圖3b中大于5000cm-3的部分代表泄露的載流子,因此在模型修正過程中要通過積分方式來計算泄露載流子所占比例。
由高斯分布特性可知,CCD溝道排出的光生載流子電荷量Q滿足:

(7)
式中,w(z)為曲線束腰半徑,A0為高斯分布灰度最大值,k為因子項,g為載流子積分區域損耗,r為束腰半徑。
假設這部分光生載流子總電荷量分布在束腰半徑具體為ρ的區域,則通過積分可以得到損耗掉的電荷量百分比為:

(8)
變量代換,積分區間相應變換為(0,2ρ2),計算積分結果為:

(9)
因為束腰半徑ρ隨t增加而增加,可以認為t∝ρ,即ρ=a×t,a為系數,用積分時間t替換ρ,得:
(10)
綜上所述,結合載流子的產生和擴散,能夠確定一定功率激光作用CCD后,積分時間同飽和像元的關系如下:

(11)
整理后最終得出:

(12)
綜上可知,兩個對激光干擾過程中飽和像元數目的影響因素:光生載流子電子-空穴的復合以及CCD溝道對載流子的泄露共同導致了一定激光功率下飽和像元數隨積分時間的非線性增長。正如(12)式所反映的:理想光生載流子數目乘以這兩個衰減因子后得到實際能夠填充的勢阱數目,即為激光干擾CCD實際飽和像元數。
3 干擾實驗
圖4所示為實驗基本光路圖。所用激光為波長為532nm的連續激光,連續衰減片實現對激光光強的控制;由于激光具有高度的相干性,空中的灰塵、光學元件或激光本身往往有一些散射光會形成光暈等雜散光的干擾,為了改善光束質量,實驗中加入針孔濾波系統:激光先由10倍的顯微鏡物鏡聚焦,再通過直徑約25μm的針孔,使雜散光不能通過,以減少實驗所得數字圖像中非相關光對干擾結果的影響。接著,匯聚的點光源經過透鏡成為各部分光強均勻的平行光,最后輻照CCD相機,通過計算機獲取干擾數據,實驗全程在暗室環境中進行。光路中的分光鏡分光比為1∶1。實驗中采用Basler CCD相機,黑白相機型號為:acA640-120gm Basler ace GigE,采用Sony ICX618ALA芯片,CCD相機像素為659×494,尺寸為5.6μm×5.6μm。

Fig.4 Experimental system diagram
搭建激光干擾實驗系統,并在暗室中展開實驗,調整光束與探測器的靶面位置,通過旋轉衰減片來調整光功率大小。用激光功率計測得光功率值為0μW,13.34μW,18.2μW,70.7μW時,起先沒有激光輻照CCD表面,故并沒有干擾光斑出現,接著小功率激光輻照CCD后,計算機捕獲到CCD干擾圖像,圖像中激光輻照處開始出現一個明亮的小光斑,干擾光斑隨功率的增加尺寸逐漸增大,功率值超過串音閾值后干擾光斑中心出現垂直方向的串音線,并隨激光功率的增強,串音線亮度增強,寬度增大。采集到不同光功率下的干擾光斑圖像,如圖5所示。

Fig.5 Crosstalk phenomenon about laser interfering CCD
不斷旋轉衰減片,使得激光輻照CCD的能量逐漸由弱變強,計算機持續捕獲一系列相應功率下的干擾圖像,通過圖像處理軟件對干擾圖像進行數據處理,最終獲得532nm激光輻照黑白CCD干擾關系曲線,如圖6所示。

Fig.6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interfering area and laser power
圖6可以看出,對于波長為532nm的可見光輻照CCD時,CCD的飽和像數點數隨激光功率的增加呈指數型增長。小功率范圍激光輻照時,飽和點數增長速度快,可以視為飽和點數隨功率呈線性增長;激光功率較高時,飽和點數目增長逐漸趨于平緩,整體來看,飽和像元數隨光強增加呈非線性增長。
4 擬合結果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和公式推導,利用MATLAB建立修正后的CCD光生載流子擴散模型,即(12)式,各個參量值如表1所示。擬合得到飽和像元數隨積分時間的曲線如圖7所示。

Table 1 List of fitting parameters

Fig.7 Varying curve of saturation pixel number to integrating time
圖7是激光干擾3條曲線對比圖。分別為:原有“水桶模型”干擾直線、根據(12)式繪制的仿真修正曲線以及實驗中獲得的實際干擾值。實際干擾實驗中,采用積分時間不變改變干擾激光功率的方法,根據總入射能量E不變,而E=Pt,可以認為改變積分時間t和改變激光功率P兩種方式等價。由圖7可以看出,原有“水桶模型”并不能準確反映對整個的干擾,只能反映積分初期飽和像元的線性增長,而修正后的仿真曲線與實際值吻合良好,說明仿真思路正確,針對原有“水桶模型”誤差的補償方式合理準確,豐富了激光對CCD干擾的仿真研究。
為了驗證本文中提出的非線性模型對于其它波長干擾CCD的有效性,采用4種常用波長(473nm,532nm,632.8nm,1064nm)激光器進行了干擾CCD實驗,根據實驗數據并結合非線性模型進行了擬合,擬合結果如圖8所示。在圖中,點代表實驗數據,實線代表擬合曲線。從圖8可以看到,不同波長激光干擾下,CCD飽和像元數增加趨勢不同,但在初始階段接近于線性增加,隨著積分時間繼續增加,CCD飽和像元數呈現非線性。擬合曲線與實驗數據吻合較好,說明本文中提出的非線性模型對可見光和近紅外波段波長都適合。

Fig.8 Varying curve of saturation pixel number under laser irradiation with different wavelength
定義實驗數據和擬合數據之差與實驗數據的比值為相對誤差,則圖8中對應的473nm,532nm,632.8nm和1064nm 4種波長激光干擾電荷耦合器件實驗數據與擬合數據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7%,5%,5%和7%,證明了本文中提出的非線性模型的有效性。
另外,本實驗中采用的都是連續激光器,根據激光干擾CCD的基本機理,如果采用重頻高(遠大于CCD幀頻)脈沖激光干擾CCD,其干擾像元數變化也可以采用本文中提出的非線性模型進行預測。但是對于重頻接近或低于CCD幀頻的脈沖激光,本文中提出的非線性模型是否有效需要進一步實驗驗證。
5 結 論
根據激光干擾CCD時光生載流子的產生及擴散特點,針對已有的“水桶模型”存在的誤差對該模型進行修正;根據激光作用CCD探測器后載流子隨積分時間的非線性增長方式以及載流子在CCD像元間擴散時,超過像元勢阱容量的載流子被CCD特有通道導出的特性,通過對高斯曲線一定通孔半徑范圍內光生載流子積分,來達到補償未參與填充像元勢阱的光生載流子對飽和像元數的影響,使得飽和點像數隨積分時間滿足實際情況呈非線性增長。針對波長為 532nm 的激光輻照硅基 CCD 探測器而引起的光生載流子的擴散過程,利用修正后的模型在MATLAB上進行了仿真計算,得到了 CCD 探測器受激光輻照時飽和像元隨積分時間的變化曲線,仿真結果與實驗結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