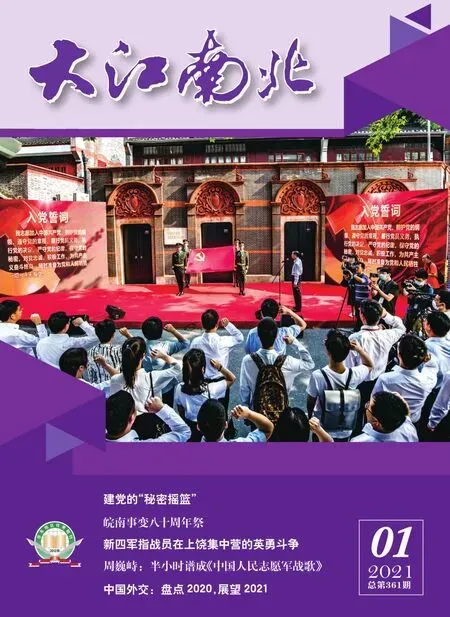皖南事變八十周年祭
□ 童志強
“1941年中國第一件發生的大事件,當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之被取消及皖南部隊之被殲滅。這事震驚了全世界。”上引這句話是皖南事變親歷者、時任新四軍戰地文化服務處處長錢俊瑞,從烽火皖南突圍抵達上海后,于1941年2月20日寫就數萬字《皖南慘變記》序言的起首語。
一
新四軍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的。為配合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抗戰,新四軍奉命挺進大江南北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不斷以積小勝為大勝,取得不少戰績。位于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臺北“國史館”中,保存有新四軍各支隊伏擊日軍呈蔣介石和第三戰區的大量戰況電報,以及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關于新四軍戰績的周報、年報和嘉獎電文。
然而,國共兩黨經過短暫的“蜜月”,國民黨1939年1月和11月,先后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和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處理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的秘密文件,從政治限共發展到軍事限共。從1939年秋天開始,國民黨在其內部文電中便逐漸出現對新四軍“制裁”、“剿辦”、“以遏亂萌”等用語。容不得中共武裝在敵后日益壯大,是國民黨“制裁”新四軍的根本原因,其主謀就是蔣介石。1940年1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抗倭剿共,盡可雙管齊下。”

安徽涇縣皖南事變烈士紀念碑
在蔣介石、何應欽主持下,軍令部于3月22日制訂出《剿辦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非法活動之異黨指導方案》。計劃在3個月內“剿滅”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新四軍。
國民黨第三戰區也有“制裁”江南新四軍之預案。1940年2月27日,蔣介石向顧祝同發出手令:“上饒顧長官:第三戰區內之新四軍以及共黨之行動,應嚴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軌行動,應不稍留情,從嚴制裁。”
4月2日,顧祝同致電蔣介石,提出“預防并準備制裁”江南新四軍的3項辦法:“一、第五十二師應抽集、控置至少兩個團兵力,準備對付該軍主力,以搗毀撲滅其涇縣附近根據地為主目的,并牽制其北渡,鉗制其活動,即預為必要準備,隨時嚴密戒備,免為所乘。二、第一四四師必要時由績溪進駐旌德,預密為制裁之準備。三、電冷副總指揮及另派員,確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設法牽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轉移。上三項除飭遵照妥密準備外,必要時擬斷然予以制裁,以遏亂萌。”
蔣介石于4月5日復電:“查所擬3項辦法尚屬可行,仰切實督令遵照,并將實施情報續報。”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現顧祝同與蔣介石密謀部署軍隊“制裁”涇縣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檔案實證。
當時新四軍軍部孤懸皖南,面敵背頑,如羊在虎口,處境極為不利。然而在新四軍發展方向以及統一戰線等問題上,中共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做法與中共中央的精神并不合拍:對中央的批評以辭職對抗;對葉挺和南方局提出新四軍皖南部隊和軍部分批移到皖北的建議置若罔聞;對陳毅主動將蘇南茅山根據地讓給軍部,促其“放棄挺進皖東南的下策”的意見患得患失。陳毅當時激憤地說:“項英既不去皖北,又不來茅山,竟這樣目無中央!他賴在皖南,按兵不動,猶疑不決,到現在還五心不定,將來一定會輸得干干凈凈!”正如《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題注所指出:“項英的思想中存在著嚴重的右傾觀點,沒有堅決實行中央的方針,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對國民黨的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個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間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時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軍九千余人遭受覆滅性的損失,項英亦被反動分子所殺。”
二
1940年10月上旬,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蘇北指揮部以少勝多,粉碎魯蘇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德勤的多路進攻,取得黃橋戰役勝利。周恩來指出:對黃橋兵敗,“蔣介石捏住鼻子沒有說話,但他是要復仇的。在蘇北戰爭結束后,王懋功就到顧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變。”
因擔心國民黨報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于10月8日致電新四軍:“蔣令顧、韓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戰將在蘇北與江南”,并婉轉指出:“最困難的是在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動到三支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10月11日,項英復電中央表明軍部留在原地的態度。10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來電,口吻較10月8日電要嚴峻得多,指出:“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斗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10月18日,軍部以葉挺、項英名義致電重慶周恩來、葉劍英,要他們在同國民黨談判時“萬勿示弱”,“逼他們(蔣、顧)在皖南對我讓步”,仍然流露出不愿放棄皖南的想法。
10月19日,蔣介石授權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要求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黃河以北地區。中共認為“皓電”是蔣介石即將發動全面剿共的重要信號,經過反復考慮,最終決定以退為進,采取皖南新四軍北撤的讓步來緩和雙方矛盾,延續兩黨合作抗日時間,博取中間派的同情,以爭取在全國的有理有利地位。
11月9日,毛澤東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出復何、白“佳電”,表示為了顧全團結抗戰的大局,準備將新四軍皖南部隊移至長江以北。隨即中央采取組織措施,于11月17日宣布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葉挺(在葉挺未到蘇北前由副總指揮陳毅代總指揮),政治委員劉少奇,參謀長賴傳珠,項英到延安參加七大。項英建議由東南局副書記曾山替他參會,未獲批準。
11月中旬,葉挺到上饒與顧祝同、上官云相商談部隊北移事宜,擬定了經皖南宣城、蘇南溧陽到鎮江渡江的北移路線。從12月初開始,皖南軍部非戰斗人員及資材先后分3批向蘇南轉移。
此時,蘇北新四軍和南下八路軍正在曹甸一帶反攻韓德勤部。蔣介石擔心皖南新四軍到蘇北會增厚對付韓德勤的兵力,決定不準新四軍從蘇南北移。12月10日,蔣介石急電顧祝同:“(一)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準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并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12月14日,顧祝同下令皖南新四軍改道“就近北渡皖北”。
與此同時,項英則一再向延安反映長江被日艦封鎖和北岸有桂軍阻擊的困難。其實,偌大的長江,也并非區區幾艘船艦所能封鎖得了的。因日軍占領無為,江北沿江也已無桂軍蹤影。從皖南事變突圍到江北無為的700余名新四軍,沿途并沒有遭遇日艦和桂軍的攔擊,即是明證。
鑒于項英在走與留之間猶疑不決,至12月23、24、25日仍在反復向延安強調困難、請示方針,毛澤東對項英在北移問題上的動搖猶豫,向項英等人發出批評電:“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在中央嚴令督促的背景下,項英才于12月28日主持會議研究部隊北移,最后決定摒棄向東經宣城到蘇南北渡或直渡皖北的原定計劃,下令皖南部隊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繞道蘇南待機北渡。由于這個行動方案之前從來沒有研究與討論過,當晚命令下達后,軍部作戰科的參謀們大嘩。作戰參謀葉超回憶說:“司令部原來對北渡的兩個行動方案,做了將近兩個月的準備,由于改變方向,都用不上了,臨走時把這些材料燒了一大堆,真是前功盡棄。”而葉挺則在29日一早向延安發電要求辭去軍長職務。
當項英在1941年1月1日致電黨中央表示“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后,中共中央于1月3日回電表示支持:“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并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筆者查閱了項英1月1日報告的全文,只是表示了全部移蘇南的決心,并沒有把部隊南走茂林、星潭,繞經國民黨后方的行軍路線報告黨中央。黨中央1月3日的復電只是支持皖南部隊向蘇南轉移,并不等于批準部隊向南行動。黨中央見項英在拖延了這么多時日之后終于決定開赴蘇南,表示了堅決的支持,目的仍是敦促項英及皖南部隊盡快離開皖南險地。
中共中央反對新四軍向南方發展,而國民黨方面最擔心的恰恰也是新四軍到其后方游擊,顧祝同在12月5日致蔣介石電中就表示了擔憂。蔣介石在12月13日復顧祝同電中答曰:“新四軍最后計劃,必如兄五日電所報,其在黃山、天目山與涇縣云嶺一帶化整為零,在我后方對我游擊。故我軍對匪必須先妥籌對策,作一網打盡之計,謀定后動為要,切勿輕易動手,反被其所制也。”
將近年底,顧祝同加緊了迫使皖南新四軍就地北渡的動作,并宣布由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負責統一指揮。上官隨即布置集團軍參謀處于12月29日制訂出《第三十二集團軍圍殲匪軍計劃》,對皖南新四軍待命進剿。國民黨軍7個師、8萬余人,遵照上官云相的命令,從東、西、南3面向新四軍皖南部隊作環形布置,以監視其北渡長江。
三
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軍近萬人隊伍分3路縱隊冒雨南下,因連日大雨,道路泥濘,章家渡浮橋中斷,部隊河中跋涉,一夜行軍不過三四十華里,各部掉隊人員很多,直至5日中午到達各自指定位置。5日下午和晚上,新四軍各部在駐地與群眾舉行同樂會,呈現一派祥和歡樂的氣氛,卻渾然不知危險即將臨頭。
5日早晨,軍部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一通長達千余字的“微電”,除了一再陳述由于餉彈補給不濟和忽令改道,以及周邊友軍的不良企圖,以致造成北移困難外,在電文中明確告之“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隊遵行顧長官電令所定路線轉經蘇南分路俟機北渡”,希望“夾道友軍鑒鬩墻之覆轍,推讓道之高風”。
似乎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坦蕩心跡,這通“微電”罕見地同時發給重慶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上饒顧祝同,徽州唐式遵,寧國上官云相以及遠在桂林的李濟深。本來,皖南新四軍就處在第三戰區8萬重兵的緊逼之中。支日(4日)晚部隊冒雨集結南走茂林,那就應該保守機密,迅速脫離險境,待全軍突過包圍圈后再行告示不遲。然而此電不僅過早暴露自己動向,軍部在5日、6日又下令原地休整,到6日晚上才行動,此時對方包圍圈業已合攏,以致失去了突圍的寶貴時間。
筆者之前在研究皖南事變時,對部隊為何在茂林一帶逗留如此之長的時間深感大惑不解。如果說4日一夜雨中跋涉,疲憊不堪,5日部隊全部到齊后,烘烤衣服、就地休整,再經5日一個整夜的睡眠,應已恢復體力。6日一早就該出動。當時皖南新四軍周圍的數萬虎狼之師已非昔日友軍,如何安全迅速地脫離險境乃是第一要務,此時向對方表白心跡無異與虎謀皮。
及至后來看到這通5日“微電”,方才悟出項英胸中的糾結,即寄希望于對方能承認既成事實,回電同意皖南新四軍轉經蘇南北移。于是在先頭部隊已經交火的情況下,仍因等待回電而躊躇不前,結果回電遲遲不來,以致白白浪費了6日整個白天的寶貴時間,后見回電無望,才決定6日夜間繼續行動。
由于事關皖南新四軍并非直渡皖北的重要軍情,重慶委員長侍從室在這通“微電”收譯后,一定是在第一時間遞送到蔣介石面前。可以想象,原來就懷疑新四軍不肯走皖北的蔣介石在看到“微電”時的震驚程度。1月6日上午,蔣介石認為一網打盡皖南新四軍的時機已到,致電顧祝同,扣響了發令槍的扳機。6日下午和傍晚,顧祝同、上官云相先后發出“進剿令”,從7日拂曉開始,雙方部隊開始了慘烈的拼殺。
新四軍從茂林出發,這條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溝高嶺,部隊分3路縱隊被高山隔開,兵力分散,彼此聯系不暢,在山谷中難以展開,也無法集中優勢兵力。7日中午,新四軍南下部隊在星潭附近遭遇對方2個營兵力的阻攔。當日下午3時,項英在百戶坑主持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下一步行動方案,他既否定了葉挺強攻星潭的布置,卻又拿不出自己的意見。在要不要打星潭這個具體的戰術問題上,居然斷斷續續討論了7個小時仍無決定。最后葉挺忍無可忍地說:“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猶豫不決,不能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即使是錯誤的決定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么辦就怎么辦。”最后項英拍板選擇軍副參謀長周子昆提出的方案:不打星潭,全軍折返,向西南出擊太平,轉入黃山。
8日子夜,部隊折回頭再重翻丕嶺。從6日夜間出發以來,各部一直處在行軍、翻山、作戰狀態,疲勞異常,后撤時秩序混亂,因朝令夕改,冒雨來回翻山,士氣不免受到挫傷。直到8日上午10時方全部撤離丕嶺。
在突圍被阻、形勢不利的緊要關頭,當電臺偵聽到上官云相下達9日發動合擊令后,驚慌失措的項英率袁國平、周子昆等身邊少數人,置大部隊于不顧,于8日深夜擅離職守,致使全軍失去重心,影響非常之壞。此舉使項英多年來在中共黨內和新四軍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喪失殆盡。
9日黃昏,葉挺決定甩開當面之敵,率部向東北方向突圍,再由銅陵、繁昌一帶渡江北上。隊伍與敵混戰一夜,僅行20余里,于10日晨進入石井坑。10日白天,項英等人因突圍不成,也到達石井坑與軍部會合。項英乃以個人名義電告延安,承認自己“臨時動搖”:“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然此時中央已明令部隊“軍事上由葉挺負責,政治上由饒漱石負責”。
11日,葉挺不惜將全部由干部組成的教導總隊也派上前線。至12日,東流山制高點失守,葉挺當晚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分散突圍。夜12時,十幾個號兵以吹開飯號為突圍信號,將所有的機槍在前面集中開火,發出了突圍的命令。最終,有近千名指戰員突圍歸隊。而葉挺、饒漱石等人在沖出石井坑后,連夜翻過火云尖,于13日拂曉抵達西坑后又遭包圍。14日,饒漱石根據中央“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的指示精神,說服葉挺下山談判,結果被扣押。
四
皖南事變中,葉挺談判被扣,袁國平突圍時犧牲,項英、周子昆隱蔽在山洞時被身邊副官謀害,苦心經營3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部被整個摧毀,皖南新四軍除近千人突圍歸隊,其余大部被俘和犧牲。
1月17日,蔣介石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將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頂點。皖南事變的發生,使得在抗戰大局下的國共合作關系瀕臨破裂的危險。如何善其后,便成為國共兩黨和全國政治的焦點,它關系著中國抗戰的命運和前途。
國共兩黨在皖南地區的局部內戰,以及新四軍番號的被撤銷,很快引起全國人民、海外華僑和俄美英等世界反法西斯諸國的震驚。如何善后皖南事變,極大地考驗著國共兩黨的政治智慧。中共發動了凌厲的政治攻勢,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名義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暴行。當天會后,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以此回擊國民政府軍委會關于取消新四軍番號的通令。
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和中共的政治攻勢,蔣介石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其在內部指示中一再強調皖南事變是軍紀問題非政治問題,是局部問題非全面問題,是內政問題非外交問題;始終沒有宣布中共和八路軍叛變,始終沒有下達全面內戰的討伐令;也始終沒有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
由于國共雙方在皖南事變善后處理中都比較冷靜,終于緩解了國共關系的嚴重危機,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繼續維持。
新四軍新軍部的重建,制止了國民黨瓦解新四軍的企圖。從此開始,新四軍完全徹底擺脫了國民黨的種種羈絆,部隊由原來的6個游擊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軍部重建之后,由于更新了領導克服了皖南事變給部隊帶來的消極影響,把全軍的思想統一到毛澤東的路線上來,保證了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能夠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
從此,新四軍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