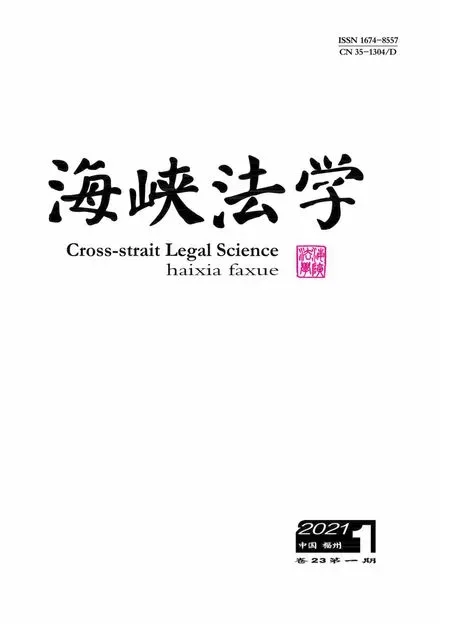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研究:從替代決定到協助決定
張華貴 ,徐晨欣
協助決定也稱支持決策、輔助決定等,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CRPD)第12條確立保障殘疾人自我決定權、尊重人格尊嚴的新理念,響應了成年監護領域“從全面監護到部分監護”范式轉型。反觀我國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為《民法典》)和相關法律規范在成年監護上基本延續完全監護、替代決定等制度,然而其存在不尊重本人意愿、侵害自我決定權利、間接剝奪本人主體資格等缺陷值得關注。因此,為保障被監護人自我決定權、尊重其意愿、響應《公約》新范式,我國成年監護有續法再造之必要。適逢我國《民法典》實施的關鍵時期,為協助決定納入我國成年監護體系提供新契機。基此,本文以協助決定為切點,立足現有成年監護,研究協助決定特點、制度構建的必要性、域外立法經驗,探索協助決定融入我國民法體系的具體路徑。
一、從“替代決定”到“協助決定”范式轉型
替代決定指監護人行使監護職責代替本人決策以實現“本人利益最大”,主要形式是完全監護、保佐等。但是研究發現,替代決定存在否定、剝奪本人行為能力、限制決策自由、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依據“本人利益最大化”而非“尊重本人意愿”等缺陷,而且替代決定的濫用有可能忽視本人意愿,剝奪其獨立決策地位,嚴重時甚至導致民事主體“民權死亡”(Civil Death)。因此,為解決替代決定固有缺陷、保障被監護人權利、強化“本人民事主體地位”,成年監護應當實現“他治式”替代決定到“自治式”協助決定范式轉型。
協助決定研究源于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經聯合國《公約》第12條確立后,在全球范圍得以推廣。制度適用主體是心智殘疾人,包括精神病人、心智障礙者、老年癡呆患者等。關于協助決定概念,目前尚無定論,有觀點認為協助決定是一系列的關系、實踐、安排和協商,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使本人在他人輔助支持下對其日常生活起居做出自我決定的制度。①Robert D. Dinerstein, Implementing Legal Capacity Under Article 12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Difficult Road From Guardianship to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Human Rights Brief,Vol.19,2012,p.10.也有觀點指出協助決定是心智障礙者在第三方幫助下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決定過程等。②N. A. Kohn , J. A. Blumenthal,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for Persons Aging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isa 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 Vol.4,2013 ,p.793.相比替代決定,協助決定核心內容是“他人協助+本人自主決策”,即心智殘疾人在協助者幫助支持下行使自我決定權。
不同時期,協助決定具有特定內涵。協助決定研究的先行者加拿大學者邁克爾·巴赫納指出協助決定是協助者在輔助決策時應尊重心智殘疾人真實意愿,提供翻譯、咨詢等幫助,而非替代本人進行決定。而聯合國《公約》在加拿大學者研究基礎上,豐富協助決定內容,包括保障殘疾人獨立處理日常生活事務、開展基礎的社會交流,重視親屬朋友、社區保護圈等對殘疾人積極影響,營造禁止虐待、剝削、遺棄殘疾人的社會環境。③A. Frank Johns, Fleur Beaupert, Person-Centered Guardianship and Supported Decision Marking: An Assessment Of Progress Made In Three Countries,Public and Private Bricolage-Challenges Balancing Law, Vol.36,2013, p.180.《公約》頒布以后,美國積極探索協助決定研究,如美國學者萊斯利指出,心智殘疾人始終享有自我決定權,可以隨時建立、終止協助關系,承認心智殘疾人行使民事權利具有法律效力。④Leslie Salzman, Guardianship for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A Legal and Appropriate Alternativ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Journal of Hea lth Law &Policy,Vol.4,2011,PP.306-307.又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認為,替代決定與協助決定制度的適用由本人自主決定,而非依據其認知、意思表示能力強制適用成年監護具體措施。協助決定強調心智殘疾人是自己事務的最終決定者,而不是被替代決定人。然而,畢竟協助決定屬“舶來品”,我國對此研究起步晚,與域外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協助決定研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我國應當積極借鑒域外協助決定制度研究,著重考察其協助決定法律法規及政策文本,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協助決定制度,完善現有成年監護,實現“他治”到“自治”的范式轉型。
二、域外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經驗考察
(一)加拿大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經驗考察
正如前文所述,加拿大在協助決定研究、成年監護改革方面屬于先行者,提出生活正常化、公民倡議、尊重心智殘疾人冒險權等理念。加拿大的協助決定存在諸多制度表現形式,包括曼尼托巴省《殘疾人法案》的共同決定、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代表協議法》的代表協議、愛德華王子島省《支持決策與成年監護法案》的支持決策等。協助決定是法院指定、任命監護人的重要替代措施,為聯合國《公約》的制定提供豐富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
為完善成年監護體系,實現替代決定與協助決定良好銜接,加拿大生活社區協會副主席邁克爾·巴赫依據心智殘疾人意思能力的差異,將成年人劃分為3種狀態,包括法律獨立決策狀態、協助決定狀態、促進決策狀態(即替代決定狀態)。法律獨立決策(Legally Decision-Making)狀態下,輕微心智殘疾人能夠理解決策信息、行為后果,依據利益衡量結果趨利避害進行獨立決策,他人侵害民事權利的,可以向公權力機關請求司法、行政救濟。因此,法定獨立決策下無需選任協助者、監護人提供輔助或監護幫助。而協助決定狀態下,心智殘疾人缺乏對復雜事項的認知判斷能力,需要在他人幫助下表達其真實意愿。關于協助者的選任,包括訂立私人協議、訂立公共協議、采取臨時任命或不予直接任命協助者等,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都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①Nandini Devi,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and Personal Autonomy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rticle 12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Law,Vol.4,2013,P.796.而促進決策(Facilitated Decision-Marking)狀態,心智殘疾人完全喪失一切意思表達能力,不可獨立從事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規定司法機關指定監護人,由監護人代理心智殘疾人行使民事權利,但是應當闡明不適用協助決定制度的理由。
加拿大優先適用協助決定,減少對心智殘疾人干預與限制,鼓勵其獨立開展民事活動,從社會生活中鍛煉意思能力。但是如果心智殘疾人完全喪失意思表示能力,應當通過司法程序指定監護人,由監護人代理一切事項,包括日常居住、財產管理、人身保障等。協調好完全監護與協助決定共同發展,對我國協助決定制度的構建、成年監護的范式轉型有積極意義。但是,應當注意是,加拿大采取個案認定心智殘疾人意思能力,當事人權利義務規定不明確,導致協助決定適用成本、權利救濟成本過高。因此,我國應借鑒吸收加拿大協助決定制度時應當積極降低制度運行成本、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提升制度的精準性與科學化。
(二)美國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經驗考察
美國國會雖尚未批準《公約》內容,但承諾保障國內殘疾人的人格尊嚴與自由不受他人歧視。而且美國各州正在積極探索成年監護新范式,如紐約州高級法院在Dameris L.案中撤銷Dameris L.的監護人資格,在第三者幫助支持下自我決策,尊重其人格尊嚴,又如Hatch案中承認Hatch在他人援助下,有權與律師訂立委托協議、與醫生商討治療方案等。②王竹青:《論成年監護制度的最新發展:支持決策》,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3期,第86~87頁。尤其德克薩斯州,在成年監護改革與協助決定組織(簡稱為GRSDM)推動下,2015年第84屆立法會議通過三項法案,包括《協助決定協議法》(以下簡稱為《協議法》)《德克薩斯司法委員會監護權改革條例》(以下簡稱為《條例》)《沃德權利法案》(以下簡稱為《法案》),率先構建協助決定制度,成為美國協助決定研究的先鋒。③Eliana J. Theodorou, Supported Decision-Marking In The State Lone-Star,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4,2018, pp.995-996.
德克薩斯州的《協議法》規定了協助決定協議的適用范圍、訂立條件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等必備條款,為當事人提供協議范本、程序規則等。但是,該法案并未明晰協議的生效要件、如何履行、有無抗辯權、情勢變更事項、解除條件等,使得法案實施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在《協議法》基礎上,《條例》明晰了協議的生效條件、協議履行抗辯權等。當發生協議糾紛時,一方面明確心智殘疾人的訴訟地位、尊重其真實意愿等;另一方面要求法院裁判時審慎考察協議的成立條件、生效要件及有無履行可能等,若判決適用替代決定而非協助決定,應當充分論證適用替代決定的原因、不適用協助決定的理由。此外,《條例》還考慮到法官、律師等司法從業人員有可能存在欠缺協助決定辦案經歷、不了解心智殘疾人的真實意愿的情況。因此,建議對本案律師、法官及協助者等開展4小時以上培訓服務計劃,培訓內容包括協助決定協議的履行、監督、管理、特殊信任的獲取等。但是《條例》卻未詳細闡明心智殘疾人基本權利,因此,《法案》第24條列舉心智殘疾人參與訴訟、自我決定、享受社會福利等權利。
美國規范當事人協助決定協議經驗,包括明晰當事人權利義務、監督者職責、協議履行、司法培訓等,能夠給我國成年監護立法提供域外經驗。但是,美國協助決定缺乏專業人才、專項資金等協助決定配套措施,使得協助決定的實施欠缺社會基礎。因此,為構建我國協助決定制度、實現成年監護改革,應當培育一批高素質、專業化協助決定工作人員,由民政部門提供專項財政撥款,提高制度的實用性與可操作性。
(三)澳大利亞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經驗考察
依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初次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尚未建立起協助決定法律框架,但是南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新南威爾士等協助決定試點經驗值得借鑒,如南澳大利亞2010-2012年協助決定試點項目,又如新南威爾士州司法部(簡稱為NSW)為加強協助決定制度宣傳,制定多元文化計劃、殘疾人融入行動規劃,錄制協助決定普法教育視頻“你不得不去法院”,頒布《能力手冊》等,實現協助決定理論與社會實踐相結合。
澳大利亞強調個別地區先行先試,積累協助決定理論與實踐經驗,加快養老產業、康養產業等發展,發揮試點經驗項目優勢,實現理論研究、政策導向、制度實施的統一。例如,新南威爾士州司法部制定《殘疾人融入計劃》,規定從2015年到2018年,司法部圍繞對殘疾人的行為態度改變、宜居社區構建、雇傭體系與服務體系完善等層面,強調心智殘疾人脫離原封閉式醫療管理,投入社區生活,從社會生活中鍛煉恢復認知判斷能力,探索殘疾人融入計劃,為我國協助決定服務人員培訓、專項資金供給、協助決定制度實施等提供了新思路。又如協助決定專業人才培養,新南威爾士州司法部利用法院服務部門業務培訓、戰略人力資源——領導力與能力發展培訓等資源,強制要求審理監護案件的司法從業人員參加為期12個月的“殘疾與靈活的服務提供”項目活動,綜合培養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與服務能力。①NSW, Disability Inclusion Action Plan, https://www.cityofparramatta.nsw.gov.au/community-care/disability-access-and-inclusion/ disability-inclusion-action-plan, 下載日期:2019年10月22日。例如,協助決定專項資金的提供,司法部不是直接進行財政撥款,而是創立協助決定專項服務管理基金,當心智殘疾人生活困難、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時,可以安排臨時住宿服務,平等享受國家基礎設施與社會福利,此外,司法部還與就業辦的培訓機構合作,將殘疾人就業問題納入到勞動力計劃與規劃流程,定期公布殘疾就業指標分析,支持協助殘疾人融入工作與社會,增強其自食其力的榮譽感。②同上。
澳大利亞協助決定政策經驗,能夠優化成年監護制度,完善協助決定配套措施,為澳大利亞成年監護范式轉型、協助決定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但是,澳大利亞協助決定缺乏系統性協助決定法律法規,政策倡導僅規定公權力機關職責,尚未落實到當事人的具體權利義務。因此,我國應當通過成年監護專項立法,構建協助決定制度,方可最大程度保障心智殘疾人利益。
三、我國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分析
構建協助決定、實現成年監護范式轉型,已逐漸成為我國監護改革的基本目標,例如廣州殘障融合組織、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等,發起了一系列自創自倡協議,倡導心智殘疾人自我決策,掌握自己生活。③杜生一:《成年監護決定范式的現代轉型:從替代到協助》,載《北方法學》2018年第6期,第143頁。然而實施協助決定時發現,我國成年監護范式轉型同樣存在與域外立法相似的困境。筆者擬采用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制度變遷理論,從正式拘束、非正式拘束與制度實施3個層面④[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理解經濟變遷過程》,鐘正生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論述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
(一)從正式拘束以觀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
正式拘束是人們自覺、有意識地創造出一系列法規、政策與規則,包括憲法、法律法規及社會政策等制度。⑤王躍生著:《制度、文化與經濟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49頁。我國以《民法典》為主的成年監護體系基本延續替代決定,未能吸收協助決定新理念。而替代決定極易忽視被監護人的人身權益、過度干預本人決策自由、不尊重本人的真實意愿,導致監護人不履行、怠于履行監護職責的侵權現象時有發生。
《民法典》第35條規定的最大利益原則,模糊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認知、判斷能力的區別。因為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未成年人因社會經驗不足、價值觀尚未成型,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時,應當嚴格遵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則。比較未成年人,成年人生活經驗豐富、價值觀基本成型,監護人履行職責時應尊重本人真實意愿,不能以監護人的價值觀、利益衡量標準隨意干預本人行使權利。雖然我國《民法典》第35條第3款、第30條等規定了應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但是事實上我國成年監護是建立在《民法典》第21條第1款、第22條民事行為能力宣告制度上,心智殘疾人喪失部分、全部行為能力,其獨立實施的法律行為范圍非常有限。此外,我國《民法典》第35條第3款前提是本人利益最大原則,依據法律規定邏輯順序可知,我國尊重本人真實意愿是建立在最佳利益原則上,如果依據本人的意愿決策不符合“最佳利益”,則監護人代理民事法律行為不會遵循本人的意愿與偏好,而是依據監護人價值觀、利益衡量標準直接做出決策。因此,我國《民法典》規定的“最佳利益原則”直接架空“尊重本人的真實意愿”,使得該原則的實施陷入困境。
我國成年監護延續傳統禁治產制度,同樣重視財產利益保護、忽視人身利益保障。雖然《民法典》第34條監護人監護職責的列舉,將人身保障放置于財產保障之前,表明立法者優先保護人身利益的態度,但是縱觀整個監護制度,規定財產權利的法條數量遠多于規定人身權利的法條數量,而且法律賦予監護人代理權、追認權、同意權、撤銷權、財產管理權等,這些都屬于保護心智殘疾人的財產權利,立法對心智殘疾人的預先醫療指示、配偶權、生育權等都未予以明確。而且在權利限制方面,我國成年監護規定監護人代理本人一切事項,遠比禁治產的權利限制更廣。雖然,有觀點認為我國將人身保護依附于財產保護符合“無財產則無人格”“無財產則無自由”等理念,人格尊嚴的維護必須建立在財產權利的保護上,方可實現“財產的人格屬性”“人格的財產要素”,保障被監護人的權利。①尹田:《無財產即無人格——法國民法上廣義財產理論的現代啟示》,載《法學家》2004年第2期,第49頁。然而不同于“財產法中無財產即無人格”論證邏輯,成年監護更能體現人身權利保障屬性,法律本意是補全本人行為能力,尊重其獨立決策地位,而不是本末倒置,過度推崇“人格之財產要素”,違背本人真實意愿與選擇,由監護人進行替代決策。
(二)從非正式拘束以觀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
非正式拘束是指一個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的、不依賴于人們主觀意志的社會文化、行為規范、行事準則及其慣例。②[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杭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1頁。在我國成年監護領域中,法律家父主義決定具體制度的構建,超法律家父現象時有發生,自我決定理念缺乏社會文化基礎,具體內容包括:
成年監護適用法律家父主義,有如下積極意義:因為社會生活發展多變,人類認知存在局限,法律家父主義可以彌補心智殘疾人行為能力、意思能力的欠缺,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民事行為進行二次確認,可以保障本人免于承擔他人行為的不利益,維護社會交易秩序同時保障被監護人利益,最終實現實質正義。③宋遠升:《精神病強制醫療中的法律父愛主義》,載《政法論叢》2016年第2期,第38~39頁。但是實踐發現,成年監護中超法律家父現象時有發生。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為《精神衛生法》)規定的心智殘疾人應當接受精神病院、療養院、康養中心提供的強制醫療服務,采用封閉式醫療監管模式,將其隔離于社會生活之外,剝奪其獨立從事民事活動的機會。又如《精神衛生法》第28條第2款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給他人或自己造成傷害的,監護人有權對其進行強制住院、就診并接受醫療,但是現代醫學理論認為,醫療權屬自我決定權的一種,是否住院、接受治療應當由本人決定。又如《民法典》第34條第1款規定,監護人的職責是代理被監護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替代本人做出決定。因此,有觀點認為,全面監護是剝奪公民權利最徹底的民事懲罰制度,被監護人地位與“民事死亡”無異。①李霞:《論預先醫療指示》,載《東南法學》2018年第1期,第6~8頁。
此外,協助決定的自我決定權理念,不符合我國“積家以成國”“國之本在家”等家庭本位傳統。社會普遍認為個人隸屬于家庭,心智殘疾人因殘疾等不能行使民事法律行為的,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可以代理本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家庭行為就是個人行為,家庭行為效果就等同于本人行為效果,自我決定權理念缺乏適用空間。此外,自我決定也有違于“心智殘疾人是被動的救濟對象”社會認知,即心智殘疾人因生理、心理缺陷導致民事行為能力不足,不具有獨立參與社會生活的資格,需要監護人事無巨細,替代本人決定一切事務。若不考慮前述家庭本位傳統、社會認知等,強行將協助決定融入成年監護體系,極易產生排異反應,增加法律實施與運行成本。因此,協助決定制度的構建、成年監護改革應充分考慮家庭本位傳統,改變心智殘疾人是被動救濟對象的認知,完成法律家父主義向尊重本人自我決定權、生活正常化理念轉變。
(三)從制度實施以觀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
諾斯指出,僅依賴非正式約束與正式約束,我們社會并不能產生有效的、低成本的契約實現機制,只有制度的全面實施,才能實現“制度變遷結果”。但是研究發現,因為當事人權利義務約定不明確、協議未經公證、配套措施的欠缺,我國成年監護的實施存在如下困境:
意定監護、協助決定作為完全監護的替代措施,對成年監護的改革起關鍵性作用。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為《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意定監護制度,《民法總則》第33條吸收了意定監護,擴展成年監護的適用對象,《民法典》基本予以延續。雖然立法強制要求訂立書面意定監護協議,但是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立法都未予以明確,協議是否需要公證也不置可否。實踐表明,當事人具體權利義務不厘定、協議未經公證存在如下危害,包括意定監護、協助決定協議欠缺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不能按照行為人的意思表示發生法律效力。此外,當事人訂立的協議未經公證人員的確認,對臨終治療、不動產管理、遺產分割等約定不明、有歧義,發生監護糾紛時,當事人需要消耗大量時間、精力證明協議成立生效與否、有無履行等,增加訴訟成本,不能及時救濟心智殘疾人。②徐晨欣、李勃:《公證介入意定監護協議的路徑研究》,載《行政科學論壇》2019年第7期,第30頁。因此,協助決定構建需要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予以明晰,采取書面協議,并對協議進行公證登記,防范協助者的道德風險,糾正協助者怠于履行監護職責、侵害被監護人等不當行為。③王竹青:《論成年監護制度的最新發展:支持決策》,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3期,第86~87頁。
此外,我國成年監護范式轉型還欠缺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社會支持網絡、醫療護理輔助、日常生活照料、財產管理處分等。依據措施的功能,可分為如下兩類:一是積極防御措施,如社會支持網絡、日常生活起居協助等;二是消極救濟措施,如醫療護理協助與財產事務管理協助等。前者能夠給心智殘疾人提供物質保障,促進其融入社會,鍛煉認知判斷能力、恢復其精神狀態等,后者是當事人喪失、完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在協助者幫助下自我決策,獨立行使民事權利。而這些措施能夠給心智殘疾人帶來支持服務,鼓勵本人從事民事活動,通過實施民事法律行為鍛煉認知能力,增加個人重返社會的機會。④陳圣利:《預防性監護監督制度的構建——基于社會正義與制度成本的均衡考量》,載《北方法學》2018年第2期,第80~81頁。因此,在了解心智殘疾人需求類型后,還應當建立協助決定的配套措施,給心智殘疾人提供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滿足心智殘疾人對成年監護制度提出新要求、新期待。
四、協助決定融入我國成年監護制度的建議
協助決定與意定監護成為世界范圍內成年監護改革的標志性成果。適逢我國《民法典》實施,結合域外立法經驗,將協助決定納入我國民法體系,解決成年監護范式轉型的困境,可謂恰逢其時。
(一)從正式拘束以觀協助決定融入我國成年監護
依據被監護人年齡,監護制度劃分為未成年人監護、成年人監護。未成年人監護秉持《兒童權利公約》本人利益最大原則,而成年監護則更需要尊重本人意愿與選擇,強化其獨立決策地位,行使權利免受他人過度干預。依據心智殘疾人的意思能力不同,將法定監護劃分為替代決定與協助決定2種,理清協助決定在成年監護中位置。心智殘疾人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存在障礙,需要他人提供法律咨詢、財產管理、健康醫療等輔助支持,適用協助決定制度。心智殘疾人完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監護人與其溝通仍無法了解其內心真意,適用替代決定制度。但是替代決定的適用應滿足如下條件:一是法院在裁判過程中,應當說明不適用協助決定、必須適用完全監護的原因與理由;二是完全監護的適用需要在尊重本人真實意愿基礎上,秉持本人利益最大原則。因為即使被監護人基本喪失一切事項決定能力,但是對日常小額消費、符合其認知范圍的事項仍可單獨決策,當然對于一些復雜、超越本人認知范圍事項決定,監護人應當代理本人實施民事行為,實現本人利益最大化。①張巖濤:《殘疾人權利保護的“范式轉變”——<殘疾人權利公約>概覽》,載《人權》2015年第5期,第122~124頁。
成年監護立法應當完善心智殘疾人的人身權益保障,在專項監護立法中規定日常生活起居、疾病護理、醫療方案選擇等內容。協助者向心智殘疾人提供人身權利輔助服務前,應當在醫生、心理專家指導下,給心智殘疾人提供自測健康評定量表全面了解其人身權益保障需求,重點考察生活習慣、健康自評、日常生活行為、生活滿意度、認知判斷、抑郁程度等指標,依據生理、心理健康評價結果,向其提供專業化、復合型定制服務,給予心智殘疾人不同層次的生活照料服務、醫療護理服務、精神文化娛樂服務等。例如,生理、心理健康自評商數數值越高則代表心智殘疾人的身體狀況、生活自理能力越好,對醫療護理服務、生活照料服務要求越少,對精神文化娛樂服務需求則越多。反之,生理、心理健康自評商數數值越低,當事人對醫療衛生護理、生活起居照料需求越多,對精神文化娛樂服務需求反而越少,當然也不排除例外情形。
(二)從非正式拘束以觀協助決定融入我國成年監護
成年監護立法應明確尊重本人的自主決定權,雖然心智殘疾人因身心障礙不可獨立從事部分復雜民事活動,但是對純獲利益、小額交易行為,監護人對本人提供協助決定服務應當控制在有限范圍,不可過度干涉本人決策。不同于古羅馬法 “浪費人”、近代禁治產制度,現代成年監護承認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享有平等權利、承擔平等義務,行為能力的喪失與否與尊重本人自我決定權并無必然聯系,因為自我決定權屬于天賦權利、自然權利、應然權利,法律不可進行不必要的限制。此外,針對心智殘疾人專屬事項的決定,如捐贈人體器官、生育權行使、與他人締結婚姻關系、接受絕育手術、放棄生命維持設施等,這些具有人格、身份專屬事項的決定,監護人不可依據自己的價值理念、思維邏輯、利益衡量標準替代本人進行決策,而是應當聽取本人意愿與偏好,輔助心智殘疾人行使民事權利。②李國強:《成年意定監護法律關系的解釋——以<民法總則>第33條為解釋對象》,載《現代法學》2018年第5期,第189頁。
而且成年監護立法應認識到心智障礙者是社會結構有機組成,殘疾屬于人類進化不可避免的現象,殘疾對個人而言是偶然,但是對社會而言卻是必然,身心障礙所帶來的后果應當由社會承擔,而非心智殘疾人自己來承受,社會在享受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時,應當共同分攤心智殘疾人產生的額外社會成本。①李霞:《成年監護制度研究》,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2頁。同時,我國成年監護立法還應鼓勵心智殘疾人脫離封閉式醫療監管模式,投身于社區生活,在民事法律活動中鍛煉個人價值、恢復行為能力,享受權利、履行義務、承擔責任。采用協助決定制度,給予心智殘疾人社會物質幫助,消除因身心缺陷、殘疾導致的物質生活、教育就業、醫療服務、交通出行、文化權利等偏見與隔閡,取消浪費人、精神病人、智障等歧視性語言,采用尊重人格尊嚴與平等的中性化法律術語,營造良好的、反對歧視的社會環境。同時,還應當將“家庭互助文化”融入協助決定制度,實現個人自主與家庭穩定、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協調融合。例如,預先醫療指示中,應當將醫療行為、醫療結果通知其家庭成員,優先選任共同生活的親屬作為共同協助者,甚至發生協助者侵權、協助利益發生沖突時,其他家庭成員可擔任臨時協助者,協助本人提起撤銷監護資格訴訟。
(三)從制度實施以觀協助決定融入我國成年監護
成年監護范式改革,協助決定主要條款的確定,應當參照《公約》第1號一般性意見,包括當事人的基本信息、權利義務、監護職責及權限范圍、糾紛解決措施等。除前述主要條款,其他條款的確定,包括處分財產類型、約定當事人報酬請求權、協議內容的公證等,應當充分聽取本人真實意愿與喜惡偏好,由當事人協商確定。此外,還應當鼓勵當事人就協議內容進行公證,要求公證機關在協助決定協議成立、生效與履行全過程,發揮保障心智殘疾人利益的作用,包括:一是協助決定尚未成立之前,公證機關依據當事人需求,向本人提供專業性法律咨詢意見,輔助本人在近親屬、親朋好友、工作單位、村(居)委會、社會組織中選任協助者,全面審查協助者主體資格,記錄心智殘疾人對協助決定的認知與意思表示,擬定協助決定協議。②李辰陽:《老年人意定監護的中國公證實踐》,載《中國公證》2017年第6期,第26頁。二是協助決定協議成立后、生效前,公證機關對當事人的主體資格進行持續性關注,持續性向心智殘疾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協助辦理協議公證登記、輔助制作被協助者的財產清單、定期審查財產清單內容等。三是協助決定協議生效后,公證機關可以承擔部分監督職責,定期審核心智殘疾人的意思能力、行為能力,監督協助者職責履行情況,定期考察心智殘疾人的人身、財產權利有無受到侵害。
關于協助決定配套措施的完善,應當從人身事務、日常生活居住、財產事務協助三方面進行論述。財產事務輔助應當秉承“尊重本人意愿”與“意思自治”,即使按照其意愿決策并不符合“本人利益最大化”,只要該決定不嚴重損害本人利益,協助者就應當支持本人決策。日常生活照料輔助應劃分為正式決定與非正式決定。非正式決定指雖然法律將心智殘疾人劃分為輕微、中度、重度、嚴重四個等級,但是無論是輕微還是嚴重心智殘疾人皆可獨立實施日常生活消費、小額交易等民事法律行為。因為《民法典》規定對于本人有能力獨立處理的事項,監護人不得干涉。然而正式決定指對于購買不動產、履行不動產租賃契約、簽訂保險合同等與生活品質提升、風險規避相關事項,協助者應向本人提供適當的輔助支持服務,包括輔助本人與不動產中介公司訂立居間合同,幫助本人指定保險合同受益人、依據受保財產的價值選擇保險標的額等。而人身權利輔助,則建議加強醫療協助者隊伍建設,培養一批高素質、復合型、專業性醫護人員,開展定期職業技能培訓活動,提高專業醫護人員的薪資待遇,給予相應財政補貼。真正做到多方面、多層次解決心智殘疾人權利保障問題,為心智殘疾人營造一個不會因身心障礙而歧視他人、和諧穩定的社區生活環境,實現從他治式到自治式,替代決定到協助決定的成年監護范式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