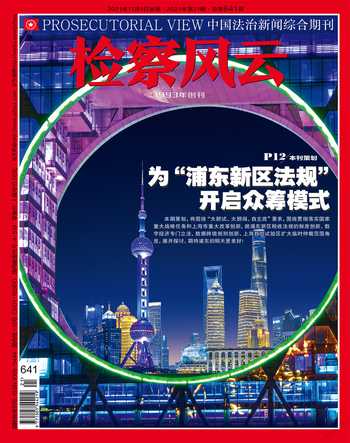場外配資非法經營案遭密集打擊
梁思遠

傘形信托通過高杠桿的場外配資成為“股災”的重要誘因
2015年的股票行情,人們依稀記得傘形信托通過高杠桿的場外配資助推了一輪牛市,而這也成為“股災”的重要誘因。當年7月,曾大力開展傘形信托的信托公司,經過一輪行業整頓,不少機構受到了處罰。
2021年2月19日,河南省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判決了一起非法經營案。這起案件即發生于2015—2016年間。結合當時行政處罰案例來看,本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或為取道傘形信托進行場外配資的首批非法經營刑事案件之一。
2013年4月1日,大專學歷的李國院籌集資金與女友施盼盼開設了河南默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雅阜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默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共計三家公司(以下簡稱“河南默名等三家公司”)。這三家公司既無中國證監會頒發的證券、期貨經營許可證,亦無中國人民銀行頒發的金融許可證,實際控制人為李國院、施盼盼。據查,河南默名等三家公司,系一套人馬、三塊牌子,實際辦公地址均在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內環路2號某大廈內。河南默名等三家公司內設總經理、執行董事、人事行政部、業務部、風控部、財務部等職務和部門。施盼盼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等職務,實際控制相關關聯公司;孫莉莎(已判決)歷任公司風控部負責人、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等職務,負責公司的全面工作;鮑啟亮(已判決)擔任公司風控部主管;黃冠軍、柴獻卓(均已判決)擔任公司業務部負責人。
2013年12月至2015年11月期間,李國院、施盼盼、孫莉莎、鮑啟亮、黃冠軍、柴獻卓等人(以下簡稱“李國院等人”)在上述三家公司的登記注冊經營范圍均不包括經營證券、期貨業務,不具有經營證券、期貨業務資質的情況下,未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相關主管部門的批準,先后以上述三家公司的名義,開展場外配資業務,招攬“融資方”與“資金方”,即為客戶高杠桿融資。技術上,李國院等人與恒生公司開展合作,接入了恒生HOMS系統第三方交易終端軟件,進而實現為客戶提供開立證券交易子賬戶(匿名傘形分倉子賬戶)、接受證券交易委托、查詢證券交易信息、進行證券和資金交易結算清算以及強制平倉等證券交易服務目的。這樣一來,李國院等人即可通過繳納保證金以放大1倍至10倍不等的比例為客戶提供融資融券服務,吸引客戶投資,收取保證金、利息及交易費等相關費用。
根據河南中財德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計并出具的《鑒定意見》: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19日期間,河南默名等三家公司共開立2390個子賬號,為1604名客戶提供配資業務,經營總額為逾41億元。
那么,為什么李國院選擇采用嵌套傘形信托的形式來實現業務目的,信托公司又為什么會選擇與李國院合作呢?這要從以下兩個背景原因說起——
眾所周知,場外配資從業者的目的在于獲取利潤。但信托公司作為持牌的金融機構,為何會與無資質的公司合作,進而衍生出利用傘形信托進行場外配資的違法活動呢?這就“得益”于信托公司的一類業務,名為事務管理類業務(又稱:被動管理、通道業務)。中國人民銀行2014年10月16日發布的《信托業務分類及編碼》這樣區分:主動管理信托是“信托機構在信托財產管理和運用中發揮主導性作用、承擔積極管理職責的信托業務”。與之相反的,事務管理信托則是“信托機構根據委托人或其指定的人的指示,對信托財產進行管理、運用和處分不承擔積極管理職責的信托業務”。
在事務管理的模式下,場外配資經營者將劣后資金(屬于一個安全墊的資金,意思是在資金遭到風險時,劣后資金優先償付風險,在獲得收益的時候,其收益將會在優先級的收益之后支付)交付至信托專戶,簽署投顧協議,通過扮演“委托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的角色,對信托經理下達投資指令,進而實現管理資金的目的。至于提供杠桿的優先級信托份額則一般由銀行等機構或者個人投資者來認購,資金可以借助結構化達到1:3的比例。信托公司將配資業務視為“通道業務”,僅關注形式合規。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委托人(李國院)取道形式合規,而信托公司卻因為“通道”項目而回避責任,形成了實質上的監管套利與監管盲區。
取道傘形信托為何是監管套利的“必然選擇”?這主要取決于信托的靈活性。首先緣于傘形信托的設立過程十分便捷;其次緣于傘形信托所投資標的范圍大大超過融資融券業務,傘形信托可以參與兩融賬戶無法觸碰的ST板塊,亦可以參與封閉式基金、債券等投資品種的交易。 此外,信托公司既能為融資方提供資金,同時又是代客理財的管理者,是一個標準的資金撮合者。從金融牌照的“營業范圍”來看,信托作為橫跨證監、銀保監體系的非銀金融機構,早年曾經被視為“萬能”牌照,幾乎可以參與除證券發行以外的絕大多數金融應用場景。從這個角度看,取道傘形信托幾乎是監管套利的“必然選擇”。
場外配資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
那么,本案場外配資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呢?就證據及事實方面,本案還是存在一定爭議的:即場外配資不構成犯罪。據不完全統計,國內目前涉案有數千家公司,數萬億資金涉及場外配資,而被列為犯罪的似乎僅有本案。
那么,本案中,借助傘形信托進行場外配資的營業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呢?傳統上認為,經營配資業務,“無資質+無資質=無資質”。即不具備證券期貨業務許可證或金融許可證的主體不得從事配資業務。如a公司(假定為貿易公司)借助b公司(私募基金)開展配資合作,這種即a與b均無金融牌照,則當然構成非法經營罪。
但2015年,很多經營配資的企業主考慮到刑事風險,通過與持牌機構合作,變相“租借”牌照從事相關業務。也即有“無資質+有資質=有資質”。換言之,非金融機構主體通過借助信托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的正常業務間接開展配資業務是否違法?
盡管2015—2016年股票市場劇烈震蕩曾被歸因為傘形信托的濫用,但經檢索裁判文書網,筆者始終沒有找到其他將“非金融機構主體通過借助信托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的正常業務間接開展配資業務”的模式認定為非法經營罪。該罪名的案例常見于“無資質+無資質=無資質”這類情形。本案的辯護律師也認為,“涉案期間有數千家公司,數萬億資金涉及場外配資,其中嵌套了一層金融機構的配資行為被列為犯罪的僅有本案”。
從歷史上看,認定“無資質+有資質=有資質”似乎是金融監管默認的事實。但沒有判決并不代表司法層面一直允許。隨著近年來金融監管的趨緊,結合《資管新規》及其配套細則的精神,包括信托計劃在內的資管產品應進行穿透審查,也就意味著“無資質+有資質=有資質”本身也是可能存在問題的,持牌機構起碼沒有鎖死審慎監管的義務。而對于委托人,即配資經營者,也是在明知自己沒有特許資格的情況下,意圖通過“繞監管”“嵌套”等方式進行違規配資,鉆“無資質+有資質=有資質”的空子。配資經營者的行為本質上就是監管套利,這是近年來監管機關不能允許的。
最終法院判決,被告人李國院伙同施盼盼等人違反國家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業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根據判決,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最終還是認定了爭議模式存在違法性,系非法經營行為。
2021年5月11日,證監會公布了《2020年場外配資違法犯罪典型案例介紹》,這一批包括10起通過各種手段規避監管違法配資的案件。發生時間多在2017年以后,均為各地公安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密集的打擊態勢既表明違規配資仍然屢禁不止,也表明了官方監管部門的態度,即未來將出現越來越多的非法經營刑事案件。行政處罰一經罰款就“一了百了”的監管套利黃金期結束了。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