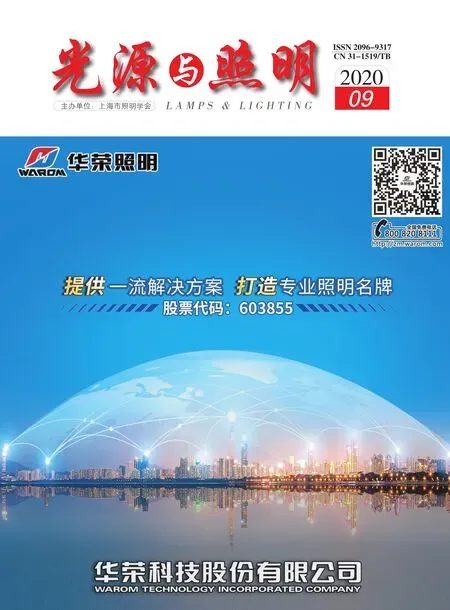色彩與光影在交互性照明中的應用研究
楊 健
常州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0)
0 引言
在過去的光環境設計中,照明功能性占主要地位。隨著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科技的迅速發展,照明設計逐漸轉向新的方式,即光的藝術性。其是通過色彩和光影對比拓展空間立體感的照明手法,使身處其中的人們的思想和情緒達到一種以光傳情的藝術境界。費伯?比倫曾在《照明、色彩與環境的科學化》中提出:“在設計現代環境時,必須充分了解顏色對人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人無意識的注意領域中,總是先注意到所視對象的顏色,然后再是它的外形。”[1]在創造照明環境的過程中,不可忽視色彩這一重要因素。美國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在《藝術與視知覺》中表示,“光影具有很強的模糊性,這種模糊體現在人們影子造型邊界的感知模糊和對影空間的范圍模糊。模糊會對視覺產生一種獨有的吸引力,可以產生一種未知感。”[2]
1 光藝術中的色彩與光影
照明中光藝術是多種藝術表現與文化體系的綜合體,其匯集了聲樂、表演、展示,乃至互動等多種藝術表現與多元文化,在發展歷程中也逐漸演變成了舞臺燈光影戲的戲劇形態、建筑立面光影的繪畫、光雕藝術品展示、互動裝置的光感體驗以及投影燈光秀中的照明技術創新與應用等[3]。光藝術經歷著從簡單傳統的光藝術形態到獨立復雜藝術形態的轉變。早期色彩與光影大多應用在教堂采光中,彩繪玻璃在陽光照射下形成教堂內部斑駁的光影與絢麗景象,這些光貼合著宗教思想,讓表達的想法與意境營造更加深厚。真正將色彩與光影引入照明藝術領域的是20世紀初期包豪斯燈光藝術先驅路德維克?赫希菲爾德?馬克。1912年,其作品《色彩-燈光-音樂調節器》中五顏六色的燈光透過模板印射圖像,和樂曲組合形成變幻光影,才使色彩與光影在照明中得到充分體現。后來美國托馬斯?威爾弗雷德并用“Lumia”一詞命名該種燈光藝術的表現形式,指營造和表現各種色彩流動、緩慢變化的光影形態[4]。直到1930年,造型藝術家拉斯羅?莫霍利?納吉設計的燈光藝術裝置《光-空間調制器》讓光的表現形式產生了各種視覺形態,色彩與光影作為光藝術的表達形式受到更多的關注。1984年,比爾?莫格里奇提出的交互設計概念,使交互性照明成為燈光、互動者、設計者三部分之間信息雙向傳遞反饋的活動。
2 照明色彩與光影對環境、心理的影響
2.1 色彩對氛圍、情感的影響
照明色彩能給人最直觀的感知,視知覺會隨著色彩變化產生相關適應性,其直接影響人對視覺信息和視覺造型的判定。純度越高,色彩的性格越明顯、積極,在視覺上趨向前進;純度越低,則越含糊,視覺上趨于后退[5]。不僅如此,面積、彩度、明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色彩的對比效果,面積小、彩度高、明度高的色彩更突出。從環境心理學方面看,光的色彩物理特性與心理知覺有關,在紅色光源環境中,人的心跳、脈搏、血壓會加快,情緒緊張或焦慮;相反,處在藍色光源環境中,脈搏減緩且情緒冷靜,呈現放松的狀態[6]。在TUNDRA團隊設計的照明藝術裝置《離境之日》中,就很好地利用了該種色彩心理,以自然環境的色彩和其在現代城市景觀中的地位,讓自然中的綠色草葉成為“主角”,在音效播放下,將模擬的自然場景植入燈光藝術中。倒置的光幕色彩漸變,由綠色到紅色、白色的過渡,形成了一幅如同超現實主義繪畫一樣的浮動草地,仿佛在經歷著四季循環往復。體驗者心境也由開始的平靜放松,變得焦慮不安,最后又歸于平靜(見圖1)。

圖1 《離境之日》
2.2 光影對視覺感知的影響
照明光影作為空間的一種參與因素具有靈活性,其能讓空間中的照射載體物質要素多變,光影關系呈現的肌理效果也更加豐富和復雜。事實上,由于空間要素的多樣性,光影與照明結合更具感染力與沖擊力,形成的虛擬場景會讓空間性質和人們心理認知發生改變。從空間性質上看,是形成具有意義的場所,是意境形而上的;從心理認知上看,是主觀的、抒情的、藝術的。
3 照明色彩與光影對視覺空間秩序的重構
視覺空間有開敞、閉鎖和縱深三種類別,在照明的視覺中心,人的視線容易將空間中的要素定位成近景、中景、遠景,如果視線受阻或視線相對狹窄,會重新判定空間要素的關系。因此,利用色彩與光影表現視覺空間的主次關系,易于建構更有秩序的視覺空間。
3.1 “圖-底”反轉的主次秩序建構
在照明的視覺空間中,視覺要素往往交織穿插、復雜多變,沒有明確的分界。該種場景環境要表現視覺輪廓,用色彩與光影表現主要事物,讓被照的構筑物從黑暗的背景中跳脫出來,表現為“圖”的形式。為了吸引更多的人群參與燈光互動體驗,空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和最需要強調的部分,也是最需要用特別方式設計的部分,就是用色彩、光影強化或弱化以打造一個接近于理想狀態的照明空間,讓它們帶來明顯的目標感,同時也讓人從心理上產生凝聚力、向心力乃至吸引力等感受。
3.2 “點、線、面”多形式的空間建構
“點”是視覺空間區域的重要標志物,需要特別強調空間的主體物,可利用照明色彩與光影重新構造視覺焦點和中心;“線”是縱深的視覺空間,有明確的方向性、指示性以及時間性,線性照明方式可以利用色彩與光影進行有序的、無序的交替照明;“面”是視覺空間的節點,集中了比較多的功能與人流,相對于其他區域而言,照明光線范圍大、密度大、光通量強、色彩飽和度大。
為了使視覺空間與光空間形態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讓照射區域的表現形式呈現多種效果。一般采用“光組織”進行設計,使光序列、光造型、光動態、光分布等呈現出高低錯落、有序排列、無序排列、虛實、漸變等。為了很好地達到燈光的互動性,設計師通常利用色彩與光影設計空間照明的節奏,或側重照明色彩,或側重照明光影,或變成了標準的幾何圖形,或變成了抽象的視覺中心,其中的任何一種照明方式,抑或任何一種藝術形態都在強調空間上的組織性。由于設計形式的不同,它們擁有了自身的獨特性,并與周圍環境形成了強烈的對比[7]。日本設計師千田康弘設計的《布洛肯5.1》燈光裝置就很好地利用光組織強調空間中光影與色彩的關系,60 000個孔洞相交的交互式物體,光線材料形成交織、重疊、疏密、虛幻的光影效果,隨著顏色變化漸淡漸出。置身其中,仿佛背對太陽站在山脊上,巨大的彩色薄霧將自己包圍,從而讓主題效果更鮮明,體驗更具趣味性(見圖2)。TUNDRA團隊也很好利用光組織在節奏上的設計,在其《序列》燈光裝置中,由LED全息屏幕陣列組成動態圖式,作品形態自由變換。生成的聲音驅動視覺的變化,序列是使數據結構化的一種基本方式,顏色組合成字符,字符合并為文字,作品原本的視覺圖像與略有延遲的空間光影反饋形成了有趣的二次對話(見圖3)。

圖2 《布洛肯5.1》

圖3 《序列》
3.3 “視錯覺”效應的虛實空間建構
“視錯覺”在照明設計中的運用是比較出彩的方法之一,其是視覺的加工過程,結合平面幾何圖形構成的視錯覺運用,可將有序、狹窄的水平面視覺空間塑造成寬擴感、立體感、以及剪影關系等,形成亦真亦幻、虛虛實實的景觀效果。
為將該種虛擬場景和實體場景完美融合,一般采用“光拓展”的形式進行設計,利用光的物理特性,即光源的反射、折射、散射、漫反射、衍射、色散等照射方式,給人最直觀的視覺感受,同時結合照明色彩與光影營造視覺空間形態。由于照明色彩、光影的真實效果與空間實際材料有關,材料本身的特性和構造形式對原本的光源進行二次加工,借助這樣的影響有時會出現如同視錯覺、視覺殘留等視覺現象。如果場景中加入其他感官感知形式,空間體驗就會發生新的轉變,讓光拓展出新的效果,借助這些特質運用到交互性照明設計中,主體空間的互動形式就會存在多種可能[8-9]。2015年,由尼克?維斯塔德設計的《ANIMA》在梵 ?高博物館展出,其是一個實體的發光雕塑裝置,懸掛在天花板上,仿佛停在半空中,在黑暗的環境下,充當了空間唯一的光源,吸引著觀眾。其能對他們的存在做出反應,通過一個強大的廣角投影儀和魚眼鏡頭從球體內部實現,在光束中產生圖像,讓照明的色彩與光影產生實時變化,投影出的效果布滿整個球體,似光花一樣極具視覺沖擊力的水波紋,仿佛紋理扭曲并圍繞球面流動(見圖4)。

圖4 《ANIMA》
4 照明色彩與光影對感知空間的意境營造
色彩與光影是極具意境的物質,其在主題照明上營造是非現實、神秘的,夢幻和趣味性的。照射方式的不同會讓空間氛圍變得不同,人的情緒很容易配合這些空間屬性立刻做出回應,結合特定的時間、空間結構、故事情節產生特有意境。設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主題性。色彩能營造空間性格,光影能調節空間氛圍。照明色彩能營造室內溫感的效果,使人產生聯覺效應,運用照明的色彩與光影實現可視化的空間,讓營造的氛圍吻合當下體驗者的心境,可以產生更好體驗效果。藝術大師詹姆斯?特瑞爾就從空間和視覺感官感知的基礎上,著重于色彩與光影對主題空間的營造,在他的《光與空間》系列作品中,將漸變色以及互補色與感官實踐結合,緩慢地將一種顏色變為另一種顏色,從而激發出一種超然的體驗感,讓人們時刻感受空間因光照帶來的變化(見圖5)。

圖5 《光與空間》
(2)游戲性。基本通過對人的行為、心理而設計。光作為空間的虛體構成要素,需要通過其他實體要素作為載體呈現自身的特性,并結合游戲體驗與照明互動表現。如阿姆斯特丹的互動裝置《Periscopista》,在湖面上有一片巨大全息云團,參與人群可以通過聲音和動作控制它。視覺效果隨著人們的動作而變化,云團色彩與光影隨著幾個麥克風接收到的人群噪音的增加和減少,這種效果是一種令人困惑的迷幻效果,吸引人觀賞,也刺激人參與其中(見圖6)。

圖6 《Periscopista》
5 總結
隨著現當代藝術照明的需求轉為多元化與多層次,不僅在視覺上有所體驗,更包括精神需求。色彩與光影特有的物理屬性使使用的光線在構造陰影同肌理、質感和色彩方面,與人的知覺和心理綜合形成一種獨特的體驗,傳遞著豐富視覺信息和感官性,給人以更深層次的情感表達,不再只是呈現光的視覺效果,也能讓光藝術表現形式在互動性上有更好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