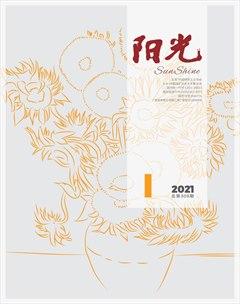塑命:李志正的摶土夢
馮海
神創世紀。
締造了宇宙萬物,造了人。
這是兩件最偉大不過的事情。
在志正老師看來,就雕塑而言,他是要匍匐于神的腳下的。神的動手能力太強,連太陽地球都是他太小的作品。他一開口,就讓光布滿這個世界。還將水和空氣分開,有晚上,有早晨;有陸地,有海洋;有菜蔬,有果子;有晝夜,有節令;有雀鳥,有大魚。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昆蟲各從其類。最后照著他的形象造人,將生氣吹在土人的鼻孔里,就成了有靈的活人。神稱他為亞當,將他安置在伊甸園,看園子。怕他孤單,神又動了惻隱之心,從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做他的配偶。亞當稱她為夏娃。
神話總是誘人。
不過,因本土始祖之故,志正老師似乎更仰慕盤古,用遺體捐獻的方式創造宇宙。其景狀,“丹華灼烈烈,璀璨有光榮”。將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將淚水灑向天空,變成萬點繁星。陽根化為伏羲,雙乳化為女媧,汗珠變成湖泊,血液變成江河。就連毛發也不剩,變成森林草原。最為悲壯的,是最后一口氣,變成清風云霧;最后一聲嘆息,變成響雷轟鳴。即便在倒下的時候,仍不忘保持體態的莊重神圣——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頭化作東岳泰山、腳化作西岳華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腹部化作中岳嵩山的五岳雄姿。
其蕩氣回腸,令人嘆為觀止!
但如果現在讓志正老師選擇一位雕塑大師作為鼻祖的話,他認為非女媧莫屬。摶土造人,無論材料還是工藝手段,幾乎就是現代人類照搬的原始模型。唯一差別就是產品的能量等級,一個是神造的,叫天賦生命;一個是人造的,叫藝術生命。
還有讓志正老師頂禮膜拜的、離他最近的一位雕塑大師,是無論遠近都無法看清的一件神秘東西——時而有形,時而無形,教人渾然不覺,還自覺領從。這個東西就是:歲月光陰!
李志正1942年出生的時候,伊甸園和他沒有半毛錢關系,他根本不知道園子里的事情,更不可能時空轉移受蛇的誘惑,吃了園子里的果子,而背負他不該背負的苦。
然而,歲月,能是個什么東西呢?
河北泊頭,運河古驛。1912年,時任民國代總統的馮國璋以四萬元現洋入股,在此創建火柴公司,從此泊頭火柴天下聞名,一改國人依賴洋火的歷史。據說火柴公司就有李志正家的一小部分股份。如此說來,李家當是對中國工業發展有貢獻的家族。誰承想,當年,他父親在縣政府供職,后來加入傅作義部隊赴綏遠任文職官員,就為其后的結局埋下了伏筆。雖然1949年和平解放,李志正的父親隨部起義,成為進步人士,但1951年劃定成分為地主,人生就此斷送。受其累及,之后李志正的姐姐和母親相繼病逝。
沒有家的完整架構,李志正的童年是靠兩個哥哥供養的。
那時,雕塑走進過他的夢嗎?
志正老師只記得八歲時大同城拆毀鐘樓的場面,他好奇,問圍觀的大人:“挺好看的,為什么要拆了呢?”大人告訴他:擋害。
還有一個場景,讓他至今都不能忘懷。1951年,剛在大同西城賜福庵小學上一年級的李志正,在老師辦公室里看到擺著不少高年級同學做的手工作品,遂引發興趣,便和小伙伴們去御河挖膠泥,用買來的陶范脫泥人玩。岸邊是一大片菜園,片石堆砌的方臺上有一尊鎮河鐵牛,黑亮黑亮的肚子上不知什么時候被人砸開了一個鍋大的破洞。不遠處有棵大柳樹,樹下有一口井,水面距離井口很近,毛驢拉著水車發出咔噠咔噠的響聲。看護菜園子的老農坐在大柳樹下吃飯,莜面窩窩和稀飯,是家人提著黑釉瓷罐送來的,罐上扣著一個粗瓷碗……這幅充滿鄉間田園氣息的生動畫面,如雕塑般,連同古城的城墻、城樓、四牌樓、鐘樓、鼓樓,以及宏大富麗的琉璃九龍壁,一下子刻印在腦海,揮之不去。如今七十年過去了,幻想著長大后重做一頭鐵牛,以替換那個肚子破了個大洞的鐵牛,始終是一個縈繞不去的夢。
1952年大年初三,家住忻州窯礦的李志正跟著礦上一伙打著一面彩旗還背著一面大鼓的隊伍,翻山越嶺蹚水過河到了云岡。第一次看見大佛,他興奮異常,天色很晚了才回家。而那一天,冥冥之中竟成了母親的祭日。
大佛。母親。
母親。大佛。
一組讓他無法釋懷的符號對應。
…… ……
雕塑,三度立體的空間藝術和視覺藝術。如果讓志正老師回答是哪三度,他一定會答:上天,歲月,還有造化。想成為一個雕塑家之前,那得看你自己在這三度空間中被雕造成什么。志正老師崇拜魯迅,一個偶然的事件改變了魯迅,從此手術刀換成了筆。至于手術刀和筆哪個更鋒利,那要看其作用的對象。
家庭的慘痛遭遇,讓李志正自覺不自覺地自塑為柔弱、敏感、內斂的性格取向。他在哥哥的家里度過了少年時期,會吹口琴和畫畫的大哥影響了他。及后入大同三中讀書進美術組,參加勤工儉學廣告社,都受到大哥潛移默化的影響。1962年元旦,《大同報》發表了他以剪紙形式創作的“鳳凰城五谷豐登”的宣傳畫。當他拿到一塊五毛錢稿費收入的時候,其喜悅,如沐春風,如飲甘露。
1962年,李志正高中畢業。
當時他二哥希望他能參加高考,以改變人生的命運。然而災荒年,大學招生少,像他這樣的家庭成分,會不會被錄取還是一個疑問。在志正老師看來,那時迫在眉睫的是肚子問題。不知為什么,那個時期的他,飯量出奇的大,以至于每當肚子餓的時候,都如同一場殊死搏斗的戰爭。他放棄了高考,獨自跑到城市人口壓縮辦公室和勞動局辦理了招工手續,然后義無反顧地背著鋪蓋卷兒爬上拉煤的火車,到雁崖礦當了一名采煤工。
口泉溝深處,幾萬名礦工家屬,各種各樣的機構、民居、辦公樓、宿舍、學校、醫院等,好像被一根扭曲的長繩穿著,擠壓在干河、鐵路和公路兩邊的狹窄地帶。這里沒有龍、鳳、麒麟,更沒有大衛和斷臂維納斯,有的只是一群群一隊隊頭戴膠殼帽、身穿勞動服、頭頂礦燈、腳踏膠靴的“當代普羅米修斯”和高高矗立的飛輪、旋轉的井架罐籠。那時,李志正每天要在只有一米來高的回采工作面爬進爬出,和鉆洞的動物沒有什么區別。最不能忍受的是綁著護膝的雙腿始終要保持對自然敬畏的跪姿,伏著身子用短把大頭的鐵鍬鏟煤,再運上煤溜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三個班倒來倒去,不知不覺就是11年。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李志正不敢自比。是不是天將降大任于是,也不敢希冀。倒是心志苦了,筋骨勞了,體膚餓了,身空體乏了,一點兒不假。盡管如此,李志正從未叫過苦,他壓根兒也沒把這當作苦,只要每月能得到58斤全國最高工種糧,就是他最大的滿足。
人生可能真有上半場和下半場之分;歲月對人的塑造,也可能真有心情好和心情不好之分。1967年,礦上搞革命宣傳,搞階級斗爭教育展覽,搞“三忠于”活動,就讓李志正寫標語、畫毛主席像和各種宣傳畫。就這樣,李志正由采煤工變成了工人畫家。這期間得到的最大鍛煉,就是和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的曲乃述老師一道,在大同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創作《礦工淚》雕塑。受其言傳身教,李志正對雕塑藝術有了醍醐灌頂般的開悟。
被歲月塑造,也追逐歲月的塑造。人生的能量場離不開歲月這個軌道。就像地球是太陽的附屬,就像雕塑是宗法制度下的附屬,體制之下,李志正的手藝怎么可能不附屬于某個相關聯的事業需求?
1973年,煤峪口礦區一個街道辦陶瓷廠誕生,急需懂美術會造型的設計人才,礦區工業局的一位朋友便推薦了李志正。李志正興沖沖地去了,但實地一看,心就涼了半截。口泉火車站西山坡上,幾間磚廠留下的房子,就是所謂的廠房。陶瓷工藝看似簡單,但對環境要求極為嚴格,無塵是起碼的條件。李志正抬頭上望,長長的塵網在頭頂晃來晃去,目光所及,其破陋之象,睹之多有不忍。
但朋友的動員還是讓李志正留了下來。還有一個私念,就是再也不用下井了。然而,搞陶瓷設計,不熟悉工藝怎么行?李志正到遼寧錦州、河北宣化等陶瓷廠進行了考察,對比而言,就陶瓷廠廠房的現有條件和人員,走同樣的路幾乎沒有存活的可能。那么,何不發揮繪畫、雕塑的強項另辟蹊徑呢?李志正很快投入設計,搞出了可愛的兔子造型的儲錢罐以及花瓶和臺燈的產品模型。誰也沒想到,在第二年的廣交會上他們的產品一炮走紅,創出了兩萬件外貿訂單的驚人業績!
兩萬件,對于現在來說,多嗎?但請記住,上世紀70年代初,人民生活是個啥水平?小白兔儲錢罐出口6角5分,內銷4~6角不等,平均價約5毛錢,20000件就是10000塊錢的收入。10000塊,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煤峪口街道陶瓷廠一下兒火了,隨即改名為煤峪口藝術瓷廠。作為廠里唯一的設計師,11年間,李志正從設計畫圖到機械造型,從原模到胎具,全都親自動手完成。動物造型,三塊模具一次注漿成形,相對于茶壺需要11塊模具分四組成形的成本,效率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其悟性和動手能力,連他自己都佩服自己。有一年,山西省二輕廳陶瓷專家水既生工程師到陶瓷廠考察,看到李志正設計的產品和模型工藝,大為驚奇,問他是哪個陶瓷學校畢業的?李志正回答他是礦工,沒學過陶瓷工藝,剛干這一行。人家不信:“你哄我呢吧!”
在那個“紅寶書”“偉人像”遍布、興趣極度乏味的時代,散發著濃郁生活氣息的瓷塑小動物,一下子風靡了煤海,攪動了全國的工藝品市場。隨著《一只小白兔救活了一個廠》的新聞報道見諸報端,他們的產品在廣交會上的訂貨量逐年翻番,第一年20000件,第二年40000件,第三年80000件,最多一年訂出300000件。日用瓷、玩具瓷、禮品瓷,有近百個花色品種,遠銷至歐、美、澳、日等多個國家及東南亞地區。11年間工藝瓷國內外銷售量總計約一千萬件。一時間,煤峪口藝術瓷廠在省內二輕行業聲名鵲起,成了遠近聞名的開放單位,來廠參觀的領導和外賓絡繹不絕。陶瓷廠也成為礦山青年們的向往,員工由最初的二十幾人壯大到鼎盛時期的三百二十余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行各業都呈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局面。1979年8月,全國工藝美術藝人和創作設計人員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全國參會代表共565人,山西代表團12人,李志正為其中之一。那年他37歲。8月16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胡耀邦、徐向前、紀登奎、余秋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同參會代表們親切見面,合影留念。至今想起,他都激動不已。
企業的成敗取決于一兩個領導人,這是體制之弊。離開,是李志正必然的選擇。昔日的輝煌漸行漸遠,正一步步淪為傳說。1982年8月,李志正獲輕工業部工藝美術百花獎優秀創作設計一等獎,這榮譽和廠子的即將倒閉放在一起,多少有些諷刺的意味,但事實就是如此。一紙榮譽,仿佛是他離開陶瓷廠實現華麗轉身的最后告白。
特殊的年代,每個人的經歷都具有紀念性和被雕塑的性質。這種紀念性和被雕塑,因為具有某種“意義”,而迫使每個個體都成為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是生命活動的投影,而其行進軌跡只不過是符號下的注釋和對應。
對于時間,佛經有多種闡述,比如一天以內的時間可分剎那、坦剎那、臘縛、牟呼栗多和時晝夜。人間五十年,為四天王天一晝夜;人間一百年,為忉利天一晝夜……如果是很長的時間,就用“劫”表示。劫又分小劫、中劫、大劫、無量劫、塵點劫等。這個東西算起來比較麻煩。就用《華嚴經》所說的最小劫做一個比照吧:娑婆世界的一劫,于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才僅僅是一晝夜。這一晝夜是多長呢?一千六百八十萬年。
志正老師算了算,當采煤工人11年,干陶瓷11年,加起來也就是22年,相對于娑婆世界的一劫,人的個體,不就是一介微乎其微、渺乎其渺的塵埃嗎,有什么不能釋懷的呢?
回頭西望,祥云飛天。
美好的上天造物,令人急切向往之。
離開陶瓷廠,給了李志正一個再次拜謁云岡的善愿。
其實在此之前,這個善愿就已經埋下了種子。1977年,陶瓷廠一片興旺景象,來廠參觀的客流一撥接著一撥,其中不乏國際友人。一天,云岡石窟研究所所長陪著客人來陶瓷廠參觀,向李志正建議,希望能搞一點兒云岡題材的旅游紀念品。李志正一下子心動了。云岡石窟,夢魘般在他的腦海里縈繞了多年——大佛忘不掉,母親也忘不掉。
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在云岡石窟,一住就是三個月。李志正選擇了幾尊有代表性的造像,白天在洞窟臨摹,晚上對照照片資料進行比對研究,每天工作都在12個小時以上。原本以為憑自己的造型能力,臨摹幾個程式化的佛像是很輕松的事。但隨著時間的推進,越來越覺得這事兒遠沒那么簡單。
事后的結果也確如之前他的擔心和判斷,三個月努力塑造的五尊佛頭造型,拿給北京的一位佛學專家看,給出的評價就五個字:“還不夠深入。”
這件事讓李志正掛懷了多年。就如同兒時看到御河鐵牛肚子上破的那個大洞,期望能夠修補殘缺成為一個縈繞不去的夢一樣,讓云岡佛頭造型“風范氣韻,極妙參神”“使人懔懔,若對神明”,在冥冥之中締結為一生的交付。
遙想1600年前的宏大場景,云岡石窟,將一個王朝的盛大刻進了石頭。那鏗鏘的斧起錘落之音,是何等的震撼人心。而今北魏遠去,歷史已經悄無聲息,面對云岡,任何贊嘆都顯得太浮太輕。就連冰心看過云岡都感言“方知文字之無用”。李志正檢視自己理解的膚淺,以一顆俗心去面對線條典雅、悠游、流暢、圓潤、華滋、靜穆的佛像,以及面的開相、表情的慈悲、手相的程式,和由此形成的整體氣象而傳達出的“大自在”,無論哲學理解還是學術準備都太嫌不足。誠如柏拉圖所說,“荷馬培養了整個希臘。”換句話說,不了解荷馬史詩也就無法理解希臘文明。同樣的,云岡佛像必然涉及到佛教思想,如果不了解佛教思想,也就無法鑒賞佛教藝術,更無法創造佛教藝術。
大凡每條河流在其源頭都是清澈的。
開鑿于1600年前的云岡石窟,發端于清凈光明的佛國世界,是生機勃勃的沒有污染的凈土藝術。
李志正認識到,洗凈自己的分別心、是非心、得失心、執著心,以一個工匠的身份重新審視云岡,把情感以及心靈交付給這座由佛像、壁畫、雕刻等藝術形式共同組成的一個綜合性視覺語匯的偉大建筑,是一個虔誠的拜謁者禪修的必要前提。
一念放下,萬般自在。
李志正再次和佛像對視。
時空悠悠,這一對視就是43年。
這對視,也將自己雕塑為78歲高齡的老人。
252個窟龕,五萬余尊雕像。錯落有致的洞窟,像一個個幽玄的門,明暗分明。門外是熙攘紛擾的世俗世界,門內則是超然物外的精神家園。由內向外望,幽玄的入口就是明亮的出口,而每一次的一入一出,就是一次從超然物外的精神家園回歸熙攘紛擾的世俗世界的時空調度。
一公里的石窟群,在志正老師看來,就如同視覺感召,每走過一次,心理轉換便經歷多次,自在和知見便獲得數重。佛、菩薩、弟子和護法諸天,神態各異,栩栩如生;佛陀的手指,優雅、曼妙,意味深長;箜篌、排簫、篳篥和琵琶等古代樂器,豐富多彩,琳瑯滿目。這其中,尤以第二十窟唯一的露天大佛最為撼人心魄。體量、神態的巨大,有頂天立地之磅礴氣勢,既是佛,又是至高無上的皇權象征——放眼望去,一派勝利者的浩然氣象,讓誰人不發出“頂天立地奇男子,照古騰今大丈夫”的千古贊譽呢?
李志正感佩工匠們“其形依意而設,其意依形而存,形意相溶,大而化之”的藝術感悟。雖然大佛的肩寬和身長遠遠超出人的正常比例,但雙腿單盤氣勢開張,橫如千里陣云,把幾何形的概括、夸張和變形以及簡潔就是豐富的美學妙理運用到了極致。神態慈祥而不軟弱,剛正而不生硬,偉岸而不傲慢,平和中透著鮮卑人強悍、豪放的尚武精神。前傾的體態,體現出對眾生的觀照。仰望之,有巨大勢能的震撼。唯美、端莊。只要目光與之對接,就教人一生一世無法釋懷。
43年,目光與之對接,心靈重建的同時,也讓李志正對佛像造型有了全新的感悟。從古至今,佛像造型不計其數,但形象氣質好的卻在少數。這是事實。石刻雕塑不似泥塑,多了少了可以彌補,石刻的一斧,下去便是永恒。此外,佛像的雕琢還取決于石刻匠人的文化素質和雕刻技藝以及傳承關系。這讓他的視點又轉向對大同華嚴寺遼塑佛像造型的關注。與剛勁雄健的云岡石窟造像不同,大同華嚴寺的佛像造型雍容典雅。綜合就是創新,嘗試著將兩個風格融合在一起塑造出具有時代氣息的更具魅力的覺者形象,就此成為他多年探討的課題。
43年,呈現在眼前的似乎還是那五尊佛頭,但卻是43年隨著覺悟的深入,在入門之作上多次改進的全新造型。并且絕對稱得上是中國目前最美的覺者造型,而沒有之一。
“慈悲不等于軟弱,莊嚴不等于兇惡”。這個分寸在佛形象的刻畫上極難把握,但志正老師做到了。
什么是“氣厚則蒼,神和乃潤”?融合了大同兩種風格的佛頭造型,“不豐不腴,不刻不雋”,堪稱是當代佛像造型的一個偉大突破,其表現手法與美學風貌,以及簡潔、和諧、適宜、對稱、比例、對比、呼應、重復、停頓、再現、強調、節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無不給人以境界的崇高、時間和空間的優游恰適以及瀟灑超邁的審美享受。
佛國如此,人間亦然。
這便是那種“有意味的形式”。
藝術家王頌對此評價道:一千六百年前先人塑造的佛像,充滿莊嚴、肅穆、神圣之氣。今神筆再造,愈加超凡脫俗,化入神妙仙境!這些雕像儼然已脫盡人間俗氣,觀其氣度、神態、眉目、表情等,大有定力無邊之感。沒有挑剔,只有膜拜!這分明是神不是人。是佛!是大圣先知先覺先悟之神佛!只有讀懂了佛學,大徹大悟了禪宗佛道之高僧信徒,才能塑造出此等至尊佛像,真所謂心中有佛佛自生!
藝術的永恒標準是美而不是新。
什么是高手?就是能把作濫了的題材脫塵去俗。
1991年,李志正出席大同市優秀人才表彰會。在會上見到了剛剛擔任礦務局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張枚同先生。張枚同對他說:“還是回礦務局吧,工作需要你。”于是,李志正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大同礦務局,擔任文委培訓部副部長,并被推選為大同礦務局美術書法家協會主席。
1996年,李志正應雕塑家苗新田之邀,參與五臺山五頂文殊菩薩銅像的塑造。在大連鑄造廠見到了中央美院教師給大連和美國佛羅里達州做的兩尊千手觀音像,他大受刺激。覺得這兩尊千手觀音像既缺乏傳統又缺乏美感,明顯地暴露出現代美院教學輕視傳統,而熱衷于創新、搞怪,標新立異的傾向。從那時起,他就發誓一定要為大同古城雕塑一尊天下最美的千手觀音。因為他覺得,作為“中國佛教雕塑之都”,大同應該有一座具有時代氣息的千手觀音造像。
之后還有一件事讓志正老師大受刺激。無錫靈山原本是太湖邊上的一個小漁村,只因1997年建成了一座通高88米的大佛像,而很快成了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并極大地帶動了江蘇旅游經濟的發展。說實話,這尊佛像雖然體量巨大,但形象、神態之俗不可耐,根本無法與云岡大佛相提并論。本可屬于中國佛教雕塑之都——大同的機遇,就此流失掉了。
大同,“中國雕塑之都”。準確地講,應稱作“中國佛教藝術雕塑之都”。為了展示古城璀璨的佛教文化底蘊,圓滿佛教文化園區的建設,留下古城盛世復建的標志,抒發大同人“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情懷,2008年市政府擬定以社會集資的形式在云岡石窟以東的開闊地帶選址建一尊高33米的千手觀音銅像。要求是:具有大同經典佛造像特征并適當融入一些現代審美取向。大同市政府把這項設計任務交給了李志正。李志正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從古至今這類造像不計其數,若想從眾多的造像中脫穎而出,談何容易?為了能虔誠靜心地投入創作,他謝絕了合同約束和資金支持,他說:“請允許我靜下心來投入設計。”日以繼夜八個多月,小稿終于出臺,并一炮走紅,在入選2010上海世博會的同時還榮獲山西省首屆文博會金獎的最高榮譽。
然而,把小稿變成建筑,錢是問題。
項目擱淺,古城保護復建,千手觀音最終成為泡影。
2017年,一家公司老總自愿岀資贊助建造千手觀音并召開了專家研討會,然而報上去之后也沒了下文。
對于志正老師來說,時間等不起。上蒼有幾個四十三年讓他伴祥云之浮移,共明月而潮生?
2019年12月,李志正又一件最具代表性的驚世之作《女媧補天》誕生。
那是怎樣一幅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闊圖騰啊!
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五彩石。
那其中一塊,被女媧高高舉起,直指蒼穹。
僅僅是一個神話故事的再現嗎?顯然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能源被大量消耗、環境污染、物種銳減、臭氧層破壞、核戰威脅等生存危機日趨嚴重,因此,拯救賴以生存的地球成為全人類最為緊迫的任務。談到創意,志正老師說,天怎么會塌下來呢?補天,意在警示事態的嚴重性。之所以將雕塑的結構以靜態的千斤頂的形式呈現,則完全是“斷鰲足以立四極”,一種頂天立地、勇于擔當的精神寫照。
與許多女媧補天的雕塑作品不同,志正老師塑造的女媧形象,面容姣好,身材修長,著一襲拖地長裙,立于三層圓形的基座上。“三”為陽數,萬物之母,寓意生命的循環往復。發髻斜綰,頎頸削肩,戴金翠之飾體,綴明珠以耀軀。鮮明的豐乳,強化了女媧作為女性的生育能力。兩只形似翅膀的寬大衣袖,款款搖風,為補天的姿態增添了無窮的動感。而補天的石塊,也與多數不規則的造型有質感的區別,是經緯縱橫的矩形狀,寓意科學補天,精準補天。一眼看去,貫通天地之大勢,與現代時尚之風情渾然一體,令人拍案叫絕的同時,也令人肅然起敬,注目致意。
在此之前,李志正還創作了多件雕塑作品。包括齒輪廠標志雕塑《運轉》、云岡賓館雕塑《天歌》和云岡賓館浮雕壁畫《云中伎樂圖》。《天歌》入選第二屆全國城市雕塑優秀設計方案展覽,《天歌》與《運轉》入選2011大同·國際雕塑雙年展。另有《北大校鐘》,三亞《南山佛鐘》,大連《千禧吉祥鐘、吉順鐘》《香港回歸紀念鐘》《澳門回歸紀念鐘》《大同鐘》《5·9事故警示鐘》,華嚴寺、善化寺、觀音堂香爐等。其中,大同鐘是為2000年8月舉辦大同首屆云岡旅游節而鑄造的,現懸掛于云岡二十窟大佛前的鐘亭里。大同鐘的銘文《大同賦》由著名北朝研究學者殷憲(1943—2015)所撰:
桑干泱泱,武周蒼蒼,偉哉大代,在此立邦。
開邊拓土,大業煌煌,改革漢化,華夏隆昌。
鑿窟造像,佛法光揚,其力無極,直追羲皇。
其功何著,承漢啟唐,大同之大,雄踞朔方。
唐置節度,嘉名乃彰,遼金西京,王氣堂堂。
明清重鎮,威被八荒,大哉大同,古韻新章。
紀元復始,虎步龍驤,民族大同,國裕無疆。
世界大同,天道滄桑。
宿世謬畫客,前身應畫師。
面對云霞川流、清溪淺波、漁歌唱晚、煙寺暮鐘這些詩意的符號,第一時間我們會想到王維。同樣,面對鼻高堅挺,目深細長,肩膀展闊,胸廓寬厚這些佛像的符號,我們會想到云岡石窟,也會想到李志正。因為它們都是運用符號的方式,把情感轉變成訴諸人的知覺的東西。誠如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所言:“它們好像年年常春的神物,能夠擺脫歲月的折磨;在它們的結構之中,似乎蘊藏著某種永生的活力和不死的精神。”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李志正的雕塑情懷,與體積、材質、手法無關,只有超拔于形質之上的本真的精神境界,與之關聯。
雕塑,摶土之技也。如果說五尊覺者佛像是他43年反復修成的正果,那么重新塑造“千手觀音”,又讓他回到“有意味的形式”的修行中,終日拜謁。他相信,中國雕塑之都需要這樣一座千手觀音,而這座城市也容得下他李志正的千手觀音。他堅信,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這不是夢。
這是塑命,也是宿命。
李志正(1942.3—)河北泊頭人。雕塑家、高級工藝美術師,山西省工藝美術大師,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大師。擅長雕塑、陶瓷工藝。歷任大同礦區煤峪口藝術瓷廠美工、副廠長,大同市美術設計院副院長,大同礦務局美術書法家協會主席,山西省雕塑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馮 海:供職于同煤日報。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理事。有文章見于多種報刊,其中報告文學《無字的碑記》《今日天歌》,中篇小說《夢語惶惶》,散文《思維的跡象》分獲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