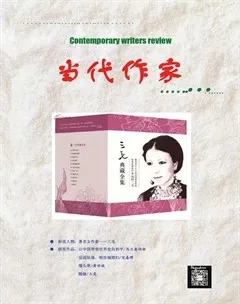遙遠的外婆
嚴行星
外婆于我來說,非常遙遠,非常遙遠。我三歲進幼兒園時,外婆就離開了我們家,直到母親去世前的一個月,外婆病逝,我都沒有見到過她。對外婆的印象都是停留在母親斷斷續續的描述里,但外婆卻在我心里扎下了根,盡管影像模糊。成年后,我一直都有想去看外婆的沖動,內心想感恩的積淀越來越厚重。
我生于六零年,適逢三年自然災害,也可以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饑荒嚴重,食品短缺,是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現在國家已全面脫貧進入小康社會。我常常慶幸自己能夠活到今天,已是賺大了,且現在衣食無憂,頤養天年。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前醫學院校畢業生且是進步青年。解放前夕,他們沒有象其他同學那樣,遠走國外或港臺,而是選擇留在了缺醫少藥的家鄉城市醫院,父親擔任外科主任,母親擔任內科護士長。
六十年代初,國家每月給予高級知識分子特供20斤大米、白糖、牛奶等食品。而我患上了嚴重的佝僂病等疾病,出現乒乓頭、雞胸、O型腿等典型癥狀,近3歲還不會走路,氣若游絲,特別需要營養。是國家當時的高知政策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可以說,沒有特供,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
據母親后來告訴我,第四任保姆時常將我放在下端放有痰盂的兒童椅上,喂稀飯時,太燙,我扭頭,保姆就會拿來縫衣針,用背面刺我的嘴唇,痛但不出血,然后吹吹稀飯,自己喝掉大半碗。當時保姆非常難請,她們常常不但自己吃我碗里的食物,還悄悄拿回家享用。許多的事都是鄰居路見不平后悄悄地告訴父母的。后來,父母選擇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輪流給我喂食物,我才得以勉強活下來。
那時,母親時常非常擔心我能否活下去,挺過來。便建議從老家請外婆來帶我,但父親三緘其口,擔憂外婆地主的身份會影響他的仕途。其實,號稱縣里“一枝花”的外婆在大學讀書時就是進步青年。解放后,外婆跟身為公安人員的小舅在城市生活過一段時間,然后就一直在農村老家獨居,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甚清楚,但只知道是靠母親每個月寄錢度日。
母親常常勸解父親說,自己是自己,父母是父母,自己的每一次進步都沒有受到父母成份不好的影響。父親無言以對。
外婆來了后,全力以赴地帶我,我的營養迅速跟上了,不但長胖了點,臉上也有了點血色。外婆沒日沒夜地時常給我按摩,上夾板,訓練走路,并將我順利地送進了機關幼兒園。至此,外婆回老家直到去世,我和外婆就再也沒有機會見過面。有關外婆的趣事,都是母親臨終前告訴我的,這讓我倍感溫馨。可以說,外婆給了我第三次生命,如果沒有外婆,也許就沒有現在的我。
我退休后,就向二十余年沒有回過家鄉的小舅打聽清楚老家弄底村路線后,在今年清明節時攜愛人及妹妹妹夫駕車前往。
八十三歲的表哥方木帶著我爬上屋后郁郁蔥蔥的山上找墳,一臉疑惑,他指著一處黃土坎說道,外婆的墳應該就在這里。當初修建G60高速路時,他親自將外婆的墳從山腳遷到這半山腰的。記得當時遷墳時,墳里什么東西都沒有找到,于是,他就鏟了一盒黃土,拿上來埋在這半山腰了,立沒有立碑,就記不得了,他疑惑怎么找不到了呢?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可以肯定地說外婆就在這座山上,她已然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這也許是外婆最好的歸屬。我從懷里拿出外婆泛黃的照片,仔細地端詳,在一塊空地上,點上香燭,心中默默地祈禱:感恩有你,希望你在另一個世界一切安好!并保佑我們家族的所有人平安順達。
臨別時,表哥方木帶我來到外婆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他說外婆當初住在這里時,他任生產隊長,給予外婆不少關照,特別是外婆去世時,喪事都是由他帶領族人一手操辦的。原本想看看外婆的墳是否需要重修或加固,但已然不用了。于是,我便將一個大信封交給了表哥,一是感謝他幾十年來對外婆的照顧;二是希望他能夠繼續尋找外婆的墳墓。
當車離開弄底村時,看到村里一座座樓房別墅矗立林間,鄉間柏油馬路四通八達,村前屋后的竹林和果林交相輝映,油菜花開滿田間地頭,一派興旺發達的新農村景象印入眼簾,我感慨萬千。外婆泉下有知,也會感到非常欣慰,非常欣慰。
作者簡介:
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閃小說專業委員會會員。從1995年起在《健康報》《環球時報》《貴州日報》《貴州都市報》《微型小說月報》《荊楚閃小說》《傳奇故事·閃小說》等報刊雜志上發表散文、隨筆、小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