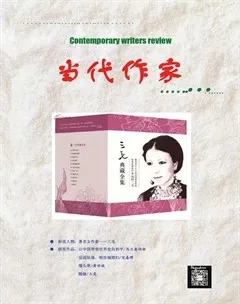母親塑造我人生底色
丁慶月
1933年3月14日,母親韋節福出生在石門山鎮石泉莊,家境殷實。小時曾跟著本家二叔上了近一年的私塾,讀過《女兒經》,接受過舊時的傳統教育。在那個年代,女孩上學讀書是很少見的,所以母親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女性中的一員。
母親17歲嫁給了做教員的父親,來到三面環山的美麗鄉村—石門山鎮丁家莊,與老祖母、爺爺奶奶及父親的兄妹七人一起擠在三間土坯正房與矮小的東西配房里,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不到17歲的母親過早地擔起了不該屬于她的生活重擔,做飯、洗衣、種地、伺候長輩和三個不滿10歲的小兄妹。就是這樣辛勤勞作,稍有不慎,有時也要受到指責。聽父親說:有一次攤煎餅,母親勞累了一天,收拾好鏊上鏊下的物品后就早早休息了,可不知半夜起風,把鏊內的余火星吹了出來,造成廚房被燒,為此,長輩們生氣地斥責母親干活不利索。看著燒掉的茅草廚房,母親也是心疼不已,但委屈只能往心里去。聽到此事,我明白了什么是負重前行。
母親是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型婦女,樂善好施,見不得別人苦,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寧愿自己苦與累,也愿意幫助別人。記得小時候一日午飯時間,全家人在默默地喝著玉米面的糊涂,吃著碗里兩三片高粱餅。一位要飯的老伯來到我家門口,輕輕地說道:“行行好吧,給點吃的。”母親看了一眼穿著破舊衣服的年老乞丐,不假思索,隨手拿起一個煎餅(那時每頓能吃上煎餅就是美味了)走到外面,遞給要飯的老伯,說:“你把飯碗給我,我給你盛碗糊涂喝。”老伯眼看了看飯桌上的碗猶豫著說道:“能不能給我一個碗?我的碗在前一家要飯趕狗時,沒注意打壞了。”母親為難地看了看他,因為她知道家里沒有多余的碗,如果給了要飯的老伯,我家就會有一個人沒有飯碗。可母親還是拿了個碗,盛上滿滿的一碗糊涂端給他,老伯千恩萬謝地端著碗走了。我看在眼里,知道了善良的意義。
解放前,爺爺是當地有名的生意人,走南闖北地把附近幾個鄉鎮的水果、干果賣到黃河北或江淮流域。由于做事仗義,不拘小節,生意做得雖大,但獲利并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對個人商業的限制使一向會做敢做生意的爺爺沒有了用武之地,家庭生活主要靠爺爺上山打石頭和種十幾畝薄地生活,加之爺爺在教育孩子上十分舍得投入,日子過得比別家清貧許多。聽父親說:生我的那年,兩間矮小的東配房對我們六口之家已顯得十分狹小,擇地蓋新房成了母親揮之不去的心事。好強的母親經與外祖父商量后,從娘家借來了蓋房的木料。父親當時在本村擔任校長,深得大隊干部的認可。書記丁慶義得知我家蓋房后,表示由村負責義務派工,免費供應所有石料。為劃塊好地基,母親還狠狠心買了二斤燒餅送給當時負責批地的本家大爺。一切具備,就等來年動工蓋新房。可爺爺卻把我家準備蓋房子的木料、石料自作主張,私下送給了他認為更需要蓋房的兒女,這讓母親很是生氣,因為靠父親那點工資重新蓋房已沒有任何希望,要面子的母親更是不愿意再麻煩娘家的兩個弟弟。為此,母親生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多日不起。聽老人講,當時都把母親的送老衣服準備好了,后來幾經治療,命雖保住,可落下終身病根。即使這樣,在我的記憶中,每到春節,母親總是攆著我們給爺爺、奶奶去拜年。平時,上了歲數的爺爺愛吃油炸馓子,母親就省吃儉用,只要有食油,就給爺爺炸好馓子送去。為了防止我們吃,她常常都是等我們睡下后,獨自一人搓面條、炸馓子。了解了這些往事后,我懂得了寬容、孝敬。
母親經常告誡兒女“望人好自己才好”、“太陽不會總在西邊”;看到或聽到不仁不義之事時,她會提醒我們“許他們不許咱”;當我們長大參加工作后,她會叮囑我們“好好工作,聽領導的話”、“在外勤快點,倒茶端水、掃地擦桌子小不了自己”、“馬大值錢,人大不值錢”……長大了,我才深刻感到:母親樸素的言語其實真的很深邃。
母親平常的衣服總是一身的簡單,一年能有二三套就算好的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等我們長大想讓母親穿好些時,母親總是笑著說:“千萬不要給我買衣服,我的衣服夠穿了。”我知道母親的心事,她認為心愛的兩個兒子沒有房子,沒有多余的財物,生活過的還不如別人,她是為兒子省一分是一分啊!后來,為了讓母親安心穿上相對好些的衣服,我總是換個角度說:“您現在穿衣不是為您穿的,我們都已成家立業了,您穿的不好,別人會笑話我們不孝順的。”聽了這些話,一心為兒女著想的母親,這才舍得穿上好些的衣服,盡管不高檔,可母親已經很滿意了。再到后來,我們家境已經不錯了,姐姐、兒媳常常會給母親買些衣服,可多年養成的節儉習慣,她總是舍不得穿。從母親的著裝中,我理解了美麗、慈愛的真正內涵。
我們兄妹成家立業后,為兒女操勞不盡的母親,與父親一起又為公益活動操持。2004年,并不富裕的父母在新修村柏油路時捐資200元,為建曲阜市北部唯一一座懿行碑亭捐資1000元,整修村西大街時捐資600元,同時動員在外的四叔、五叔贊助3000元,重建村西三神廟時捐資200元,發動兄妹先后為我的高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立碑紀念……點點滴滴的凡事中,我看到了做社會公益的幸福。
2005年12月16日13點左右,當家鄉的五哥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母親病重讓我快點回家時,一種不祥的感覺縈繞心中,我期盼著母親能平安,可回家看著躺在客廳用棉被蓋著的遺體,我頭腦轟然一下,就像個木頭人,不知哭泣,沒有哀傷。站在母親靈柩前,我漠然無淚,只是輕輕掀開蓋在母親臉上的白紙,靜靜地看看她熟悉而慈祥面容,安詳地閉著眼睛……我清楚:從此我已沒有喊娘的機會了。
從我懂事到母親去世,我從沒聽到母親說長輩和小輩的一點壞話,有的只是對去世長輩的無限懷念和對小輩的真誠贊美和期盼;從沒看到母親與妯娌、兄妹、鄰里之間打架、吵罵過,有的只是對親人鄰里的理解、寬容和無私的幫助。從母親去世后親人、鄰里的哭聲、感言中,我感受到了平凡母親在親人、鄰居中的位置。
昨天已經逝去,母親,永遠是我心中最懷念的人。
今天正在進行,母親,永遠是我修身踐行的航標。
明天將要到來,母親,永遠是我前行的源生動力。
202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