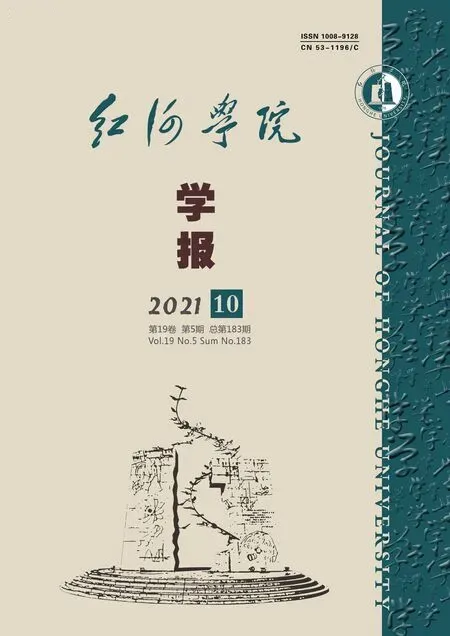哈尼族古歌《窩果策尼果》的比喻藝術研究
王 馨
(紅河學院音樂舞蹈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哈尼族神話史詩《窩果策尼果》屬于口傳史詩,最初主要由氏族首領來演唱,后來慢慢地出現了專門的傳唱者——莫批(祭詞)。莫批是哈尼族的祭司,精通哈尼族宗教、文化、歷算等方面的知識,同時也是哈尼族史詩的主要演唱者。《窩果策尼果》的最初漢譯版本,主要由元陽縣哈尼族莫批朱小和演唱,盧朝貴、史軍超等人翻譯、整理而成。本文依據的正是這一個版本。
一 《窩果策尼果》比喻的豐富性
據筆者統計,《窩果策尼果》中的比喻數量驚人,多達兩百多個。《窩果策尼果》中的比喻大部分是明喻,亦即陳望道所說的“用另外事物來比擬文中事物的譬喻。正文和譬喻兩個成分不但分明并揭,而且分明有別;在這兩個成分之間,常有‘好像’‘如同’‘仿佛’‘一樣’或‘猶’‘若’‘如’‘似’之類的譬喻語詞綰全它們。”[1]59
這些明喻大部分是物與物之間的比喻,少部分是意與物之間的比喻。據分析,這些比喻的喻體十分豐富,涉及了哈尼族熟悉的大量事物。植物類或與植物有關的有大樹、金花、鮮花、老林、老藤、棕樹、樹葉、蘑菇、竹樹、花瓣、桃子、樹皮、棉花、樹枝、雜草、竹篷、蘑芋葉、神樹、芭蕉心、芝麻、姜、生芭蕉等。動物類或與動物有關的有天鵝翅膀、花魚、牯子、燕、螞蚱、黑鴿、白龍、駿馬、牛脖、虎、象、牛蹄、馬尾、虎眼、牛屎、螞蟻、八哥、牛皮、蠶、老牛走路、芻雞、牛犢、大蛇、小黑蟲、牛腰、瘋狗、豺狗、雞虱、鴿、蝴蝶、畫眉、紅尾鳥、家燕、泥鰍、喜鵲、點水雀等。與人體或衣物有關的有包頭、打瞌睡的女人、醉漢、手掌、臉蒙上黃罩、胡子、衣褲、頭發絲、手心、腰帶、手桿粗、姑娘梳頭、小手指甲、姑娘眼睛、指頭、新衣等。與食物、生活用品、生產工具有關的有蜂蠟、金銀、篩、擺子、銀制鑰匙、金鎖、背籮、金針、銀針、花布、黃金、水碗、水缸、煙筒、床、稀飯、鏡子、籮篩、蒸糕、鐮刀、鋤頭、大刀、干柴、飯豆、麻袋口、鴨蛋、蘿卜、蜂蜜、筷子、鍋底、火塘等。自然界無生物類如霧露、春雨、水塘、海上、湖水、云彩、雷、天地、大水、電閃、彩霞、大雪、河沙、流水、星星、風、崖、石、大江、山河、太陽、罩霧的半山等。
由此可見,《窩果策尼果》中的喻體包羅萬象,凡是哈尼族生活中所見、所聞、所嗅、所觸、所味的事物,都成為被選對象。《窩果策尼果》是口傳神話史詩,演唱者必須引起聽眾的興趣才能夠完成追述傳統文化歷史、布傳倫理道德、述說生產技術等重任。因此,以這些事物作喻體,一方面是因為聽眾比較熟悉它們,知曉它們與本體之間的相似點,從而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則是熟悉的事物容易使人們產生一種親切感,這種親切感會使人們的注意力更為集中。通過這種方法和方式,史詩演唱者才能勾起聽眾們的興趣、注意力。
二 《窩果策尼果》比喻的新奇性
《窩果策尼果》中的比喻,也極富新奇性。這種新奇性,不僅表明了哈尼族豐富的想象力,也反映了他們對世界萬事萬物的深刻認知。古歌中的比喻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對事物的深刻認知,比喻就會顯得怪誕,甚至荒謬。因此,縱然想象力豐富,也必須以深刻認知作為主旨,比喻才能既新奇又深入地表現事物。這是因為“修辭格本身是思維的產物。是人類思維規律的一種表現,于是它也就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許多修辭格是建立在相關關系相相似關系之上的,而相關關系和相似關系正是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方法。人類認識世界的活動,基本路線是從已知向著未知領域進軍,基本的辦法是把未知的東西納入已知的范圍之中,把未知的東西同已知的事物進行對比,從相關相同相似的地方開始,尋找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用已知的東西來解釋還未知的東西。”[2]
例如“彎扭的天梯象九山的老藤,先祖們順著它上下來往”[3]的比喻句。它將天梯比喻為九山的老藤,這就表現了天梯本身與九山老藤之間的相似點:既彎曲又堅韌。天梯本身也是哈尼族想象力的產物,哈尼族認為祖先們能夠順著它上下來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有了哈尼族認為天地之間可以相通,他們對大自然的認識,才會出現九山老藤這樣的比喻。“天笑是天上的雷鳴,地笑是山頂的電閃。”將雷鳴比喻為天的笑,將閃電比喻為地笑,由此我們也能夠深切感受到哈尼族以豐富想象力創造出來的新奇比喻。這種天馬行空、自由奔放的想象力,其實也不是沒有認識作為導向,不是完全信馬由韁的。天笑與地笑表明哈尼族將天與地擬人化。而之所以將天與地擬人化,其實是因為哈尼族認為萬物有靈。因此,歸根結底我們會發現,前述的比喻其實建基于哈尼族萬物有靈的觀念上。
這種建基于萬物有靈論上的新奇比喻還不少。如“高能的大神梅煙啊,又拿出金刀劃了七十七道臺階,這就是太陽走的路了。她又拿出銀刀劃了七十七道臺階,這就是月亮走的路了。”古時候的哈尼族先民觀察到日升月落這種自然現象,但還沒具備足夠精確、豐富的科學知識去解釋它們。因此他們便發揮了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構織了一種可以自圓的、新奇的說法。萬物有靈論之所以是這種想象力、比喻的基礎,是因為它使人們與所有事物都具備了可比性。也就是說,在哈尼族看來,人與自然界的所有事物其實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有生命的、有靈的。又如“大神俄嬌把牛血抹上天空,抹出滿天鮮紅的彩霞。穿上彩霞的衣裳,光漉漉的天也不光了,穿上彩霞的褲子,害羞的天也不害羞了。”這個比喻中的牛指的是“查牛”。哈尼族認為,古時候,天由于某些原因出現了裂縫,必須用“查牛”才能修補。因此,他們請求神靈把“查牛”殺了。“查牛”身體的每一個部分就變成了彩霞、云朵、天柱、湖泊、高山等。這個比喻中,將彩霞比喻為牛血,可謂新奇,不同于平常的比喻。而這個比喻其實也涉及到哈尼族對世間萬事萬物起源的認識,涉及到他們解釋這個世界的知欲。這種未知欲產生的結果即是神話,神話是由于人們試圖解釋自然或解釋自然中呈現出的種種力量,進而使人們實現征服自然的目的。因此,這時的人們已擁有一定的想象能力(雖然這些想象并不一定能夠解釋自然的真正奧秘和規律),并逐漸達成一定的共識。“他們為了共同認識‘自然力’而作的互相交流,為了培養后代所作的教育促使了當時已經產生的‘神’(神的觀念)與‘話’(語言)的結合,于是最原始的‘神話’也就出現了。”[4]
除了建基于萬物有靈論上的新奇比喻,《窩果策尼果》中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新奇比喻。這些比喻涉及到哈尼族對日常生活中事物的認識,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如“哈尼的草排象天鵝的翅膀,高高地飛上蘑菇房”。按照一般的思維,應該很難將草排與天鵝的翅膀聯系起來。但哈尼族豐富的想象力卻往往能夠出人意料地創造出新奇、獨特的比喻。草排與天鵝的翅膀,在形狀上有著相似之處。其實,天鵝并不屬于哈尼族非常熟悉的事物。因此,將草排比喻為天鵝的翅膀,以不熟悉的事物作為喻體,意味著哈尼族想象力的跨越空間大、跳躍性強。概言之,即想象力豐富。也正因想象力豐富,才能夠創造出如此新奇獨特的比喻來。這個新奇獨特的比喻,也與哈尼族樂觀天性有關。草排本是哈尼族主動地、辛辛苦苦地織好并蓋上房頂的,但史詩演唱者卻說草排是自己飛上蘑菇房的。很顯然,這體現了哈尼族不畏艱苦、克服艱苦,乃至與艱苦嬉戲的樂觀、勤奮精神。又如“烏也拔森啊,你的智慧象你的胡子一樣多”“日子像榕樹一節節過去”“穿毛衣的老熊也生啦”“它的家譜實在多,七十只背籮也背不下”“爐煙燒得象黑老鴿飛”“老虎像石頭一樣滾進寨子”等比喻,都表現出了哈尼族對日常生活事物、周圍事物觀察與認識的細膩、深入,也透露出他們詼諧、樂觀的天性。
三 《窩果策尼果》比喻的形象性
作為一種重要的修辭手法,比喻可以形象生動地再現,描述事物與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經驗。在比喻修辭過程中,“一個比喻的作比事物與表現對象是否彼此復合、相互印證,即它們之間貼切不貼切的問題,是這個比喻能不能成立的根本前提。從這種意義上說,貼切是比喻的生命。”[5]所謂貼切,其實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形象性。在文學比喻修辭手法中,形象性主要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指喻體通常是具象的,有著一定的形態結構或者聲色香味,人們比較熟悉,如將殘陽比喻為血,血有著具體的紅色;另一層則是指喻體與本體具有性質上的相似點,如“試問閑情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這里的本體與喻體就不是形態結構上的相似,而是性質上的相似。也就是說,“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都具有一種迷蒙、模糊、無以名狀、恍惚的性質,而閑情本身也具有這樣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性質。可以說,文學藝術文本之間千差萬別,各具特色,每一文本中的形象都有其特殊的創作原則。不過,“文學藝術的形象性畢竟源于生活世界,它與生活世界的形象性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一致性或同構關系,這種一致性或同構性關系正是隱喻性關系或象征性關系。”[6]
在《窩果策尼果》中,形象性的比喻俯拾即是。如“茶壺冒出的大脛骨的熱氣,像霧露纏繞著山崗”“霧氣像口大鍋,蓋在平平的海上”“四周還有長長的圍墻,就象包頭盤在頭上”“俄瑪生下的千千萬萬個地神,象密密的老林把大地站滿了”“哈尼的寨子在哪里?在駿馬一樣的高山上。哈尼的寨子象什么?象馬尾耷在大山下方。大山象阿媽的胸脯,把寨子圍護在凹塘”“她們把太陽和月亮,被得象篩子一樣圓”“太陽的金針啊,攆散了世上的寒冷,月亮的銀針啊,攆散了世上的黑暗”“樹果少得象白日的星星”“半山再去看一看,上面系著腰帶一樣的好地,半山再去望一望,上面擺著手板心一樣的好地”“我的身子雖然小,肚子卻象裝不滿的葫蘆”“頭人坐上了高位,講出的理象天地一樣大。貝瑪(莫批)站在祭桌旁邊,咒鬼的聲音象打雷一樣響。工匠站在鐵匠房里,化鐵的爐火象鮮花一樣開放”,等等。除了這些本體與喻體在形態結構上具有相似性的比喻外,還有一些在性質上具有相似點。如“遠古的先祖已經去世,留下的窩果象春雨播在哈尼心上”“先祖的窩果是粗直的大樹,巨大的蔭涼蓋住四面八方”“他們的心象湖水一樣平”“哈尼的惹羅大寨,名聲像流不盡的泉水四處流淌”“杰羅的嘴像石頭一樣笨,這個人的嘴像八哥一樣靈”“我的智慧只有他的小手指甲那樣大”“福氣像七月的洪水淌進家來了,好運象九山的石頭堆進家來了”“他們的本領象太陽和月亮一樣亮眼”,等等。
四 《窩果策尼果》比喻的夸張性
在文學與藝術中,許多作者都會采用夸張的手法。陳望道認為,“說話上張皇夸大過于客觀的事實處,名叫夸張辭。說話上所以有這種夸張辭,大抵由于說者當時,重在主觀情意的暢發,不重在客觀事實的記錄。”[1]104也有研究者認為,“作為修辭的夸張,則是以想象為載體的思維的夸張在審美創造實踐中的具體運用。”[7]具體地說,創作者可以通過描述事物或對象的數量、體積、程度、狀態等方面進行修飾,這樣,對象的特殊性通過夸張的手法更加鮮明立體,也可以反映出創作者對于此一事物敏銳的感覺和其獨特的審美體驗、感知能力。而讀者也可以在其中進一步獲得獨特的審美體驗和享受。因此,夸張并不是目的,主觀情意的抒發才是目的。比喻中的夸張性自然不能等同于作為修辭格的夸張,但兩者畢竟還是具有共性。也就是說,比喻的夸張性與夸張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事物的真實樣貌,使特征或擴大或縮小了許多倍,從而達到表情達意的效果。
《窩果策尼果》中多處采用了夸張性的比喻。如“煙沙的名聲像天地一樣大”,煙沙是大神梅煙所生,具有很高的本領,生下了司管風、雨、雷、土、籽種、水、田、地溝等九位大神之后,還生了金、銀、銅、鐵、錫等五位大神祗,給哈尼族帶來了福祉。因此,在哈尼族的心目中,煙沙的名聲很大。但無論如何大,都不可能像天地一樣大。在這里,夸大煙沙的名聲,其目的是為了表達哈尼族對煙沙大神的崇敬、愛戴。又如“他們踢起的黃灰,把三層天的臉蒙上黃罩”,這個比喻中的“他們”是指幫忙造天的日神、月神、雨神等。踢起的“黃灰”再多,也不可能把三層天的臉都蓋住,因此,這個比喻并不是實指,而是夸張,目的是為了表現天神們幫人造天的熱情與勤奮。同樣,“大群地神走出宮門,象大水從巖洞里噴出來了”這個比喻也不是實指,而是為了表現地神們幫人造地的熱情。又如“須根象牛腰樣粗,主根象老崖樣大,細枝象山河樣長,粗枝象大江樣長”。這幾個比喻描寫的都是哈尼族神話中的遮天神樹。很顯然,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樹的須根像牛腰粗,主根象老崖一樣大,細枝象山河一樣長,粗枝象大江一樣長。通過夸張,神話作者要傳達的是哈尼族克服種種困難最終砍倒了這棵遮天大樹的大無畏精神與堅韌的意志。這種夸張性強的比喻還有很多。如“愿秧苗長大結出鴨蛋樣大的谷子”“割倒的谷桿象山包一樣堆高”“拿手摸一下,皮肉象棉花一樣軟”“大田耙得鏡子一樣平,只等待秧姑娘來嫁”,等等。
五 結語
“好詩是一棵樹,而比喻是青蔥的枝葉;詩歌的發展是一條不竭的河流,比喻是其中光彩閃爍變幻的浪花”[8]劉繼業先生的這種詩意比喻表明,比喻能夠使作者所要表現的事物更加形象、生動、斑斕多彩,帶給人們以美的享受。如前述,好的比喻并不僅僅指作者觀察到的事物與事物之間形態結構的相似,還指作者認識到了事物與事物之間性質的相似。哈尼族口傳神話史詩《窩果策尼果》中,運用了大量蘊含豐富性、新奇性、形象性、夸張性特征的比喻。這些比喻,既有具象帶來的美感,也蘊含著哈尼族族對世間萬事萬物的深刻認識,當我們重溫這部口傳神話史詩時,不僅可以得到美的享受,也可以從中感受到哈尼族族面對生活挑戰所展現出的不屈不撓、堅強樂觀的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