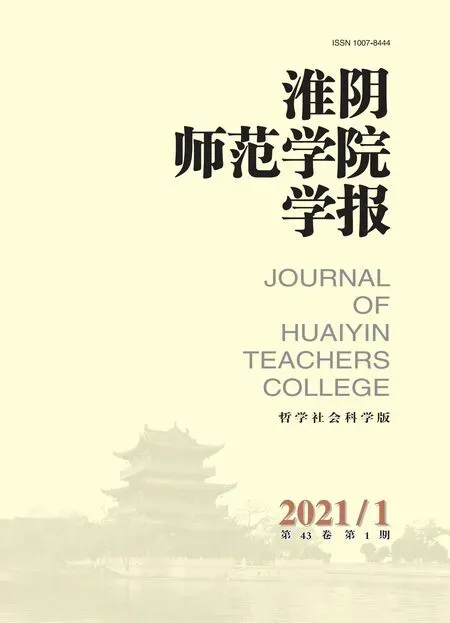《唐音癸簽》周本淳校勘本評騭
郭殿忱
(北華大學 文學院, 吉林 吉林 132013)
1981年夏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當代著名學者周本淳先生的力作——明末鴻儒胡震亨所著《唐音癸簽》之校勘本。40年后的今日,此書仍為研究唐詩者案頭必備之書。何以如此?現從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三方面略加評騭。
一、從目錄學角度看周先生校勘《唐音癸簽》之成就
目錄學,乃治學路上之津梁。舍此,便無由到達理想之彼岸。相隔四百年的胡氏、周先生兩位學者薪火相傳,使重視目錄學的傳統不斷發揚光大。
(一)從校勘《前言》看目錄學之應用
《前言》開宗明義:“在明朝后期研究唐詩幾位成就較高的學者中,胡震亨可稱巨擘。他的貢獻遠在楊慎、王世貞兄弟乃至胡應麟之上。成績主要表現為一千多卷的巨著《唐音統簽》,其中尤以《唐音癸簽》為突出。”[1]這不刊之言,無疑是在認真研究了《楊升庵詩話》及其《拾遺》、王世貞《藝苑卮言》、王世懋《藝圃擷余》、胡應麟《詩藪》與《少室山房筆叢》之后得出的結論。
1.從地方志史志中鉤沉胡震亨家世、生平等情況
古人讀書講究知人論世。然而受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所限,許多杰出人物并未見諸經傳。明清“四大名著”中的三位作者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就被《明史》“漏收”。我曾在拙文《論學術研究中的方志利用》(《中國地方志》1991.5)中提及此事。胡震亨亦被《明史·列傳》所“遺漏”,更未見諸傳世的行狀、志銘。欲知其家世、生平等情況,只有到地方志中搜尋。地方志,向稱一方之百科全書。《海鹽縣圖經》就載有胡氏父祖事跡。《海鹽縣志》載其本人“數上公車不遇”。《故城縣志卷二·教諭》(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歷本)載:“胡震亨,浙江海鹽縣人。由舉人萬歷三十五年任。博綜經史,富有詞章;文學可振一方,行誼足模多士。升直隸合肥縣知縣。”《合肥縣志卷三十五》載有其論述改革益處的《興革鉅務議》一文,后經上司批準,“立石縣前,永為奉行”。又,崇禎十年胡氏任定州知州。《定州志·名宦》載:“胡震亨,海鹽舉人,崇禎十年以薦舉知定州。在任廉明,惠政多端。……其文詞古峭,亦擅名天下。”胡氏終官兵部職方員外郎。此亦為其仕途中的最高官職,故后世稱其為“胡職方”。其孫與曾孫在所撰《刻戊簽緣》后還用了一方“郎官后裔”的圖章,足見重視之程度。按:《歷代職官表》載:“唐、宋職方郎中在兵部為第二司,職掌與明、清同,源出《周禮》的職方氏,北周仿《周禮》建此官,隋因之,屬于兵部。”[2]199而《新唐書·百官志》稱:“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奏之,副上于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3]1198
可惜,任職不久的胡震亨便“乞歸,藏書萬卷,日夕搜討”,過起了賦閑治學的生活。何至如此?細心的周先生從親友的詩文中發現了端倪:“危言曾痛哭,任事終引肘。”“限于資格,未盡展其用。”復又從康熙《嘉興府志》中找到“是跟當時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合不來而告老”的說法。
2.從《明史·藝文志》等著述中錄出胡震亨的著述成果
目錄之作,濫觴于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與《七略》。而正史中首事之功則應歸譽“漢書”。《漢書·藝文志》保存了古代書目和圖書分類法,是我國現存最早、內容亦較完整的目錄學著作。此后600多年間,自《后漢書》迄《周書》10部正史,目錄之作闕如。直至唐人修《隋書》才以《經籍志》之名重現。清人所修《明史》,《藝文志》之名雖遠承《漢書》近續《宋史》,但一改前例,只錄有明一代之著述。于胡震亨名下列有:
《靖康盜鑒錄》1卷(史部·雜史類)
《讀書雜錄》3卷(子部·小說類,按原書實只上下2卷,有康熙刻本,又見于《豫恕堂叢書》,《明志》訛。)(今按:周先生雖只著一“訛”字,已屬校勘學中的他校成果。下文將詳加論列。)
《秘冊匯函》20卷(子部·類書類)
《續文選》14卷(集部·總集類)
《唐音統簽》1 024卷(同上。按:《統簽》甲至壬為1 000卷,《癸簽》33卷,合1 033卷。《明志》總數既訛,又以《癸簽》為36卷,亦非是。)
此外,周先生又將寓目之書列目補闕:
《通考纂》24卷(經世元學),今按:括號內文字為時人評語,下同。
《赤城山人稿》(摛藻如淵、云),今按:漢代著名辭賦家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云。又,赤城山人為胡氏之自號,學者稱為赤城先生。
《李詩通》21卷、《杜詩通》40卷。今按:后合稱《李杜詩通》。
《海鹽縣圖經》16卷(見《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
周先生爬梳諸多前人著作所得出的胡氏“可謂著作等身”之論,絕非泛泛溢美之詞。
(二)從《癸簽·集錄(1—4卷)》看唐人集本之著錄
《集錄·一》稱:“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者:一曰《舊唐書·經籍志》(今按:集部只收開元以上);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今按:較《舊志》多出500多家);一曰《宋史·藝文志》(今按:15種志書中質量最差,重復、遺漏較多);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略》(今按:鄭樵不應科舉,苦讀30載,復又外出訪書10年,遇藏書之家必借住,閱盡乃去。故其著錄書中之珍稀孤本、善本彌足珍貴);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今按:尤袤自號遂初居士,藏書家,與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號稱‘南宋四大家’);一曰馬端臨《文獻·經籍考》(今按:馬氏,字貴與。積二十年的功力撰成《文獻通考》一書,多補杜佑《通典》之闕失),端臨所引書又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今按:晁氏,字子止,家富藏書24 500多卷,任職榮州時校勘同異,論述要旨,撰成私家目錄學之名著《郡齋讀書志》),一曰陳直齋《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家藏書50 000余卷,繼承發展晁公武,所著《直齋書錄解題》,為宋代著名的提要目錄)。此數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今校除重復,參合有無,依世次先后,具列卷目左(下)方備考。”[1]307今按:這結末一句看似簡單的話,業界中人深知:這可是件耗時、費力的工夫活!
1.別集類。帝王:自太宗,迄濮王泰,8人,306卷。初唐:自陳叔達,迄王助,152人,2 655卷。盛唐:自王維,迄劉方平,49人,560卷。中唐:自元載,迄來澤,164人,2 445卷。晚唐:自杜牧,迄養素先生,137人,769卷。閏唐(即五代十國):自李琪,迄失姓名的《蘆中詩集》作者,143人,1 229卷。方外(釋子、羽流):自僧惠頤,迄杜光庭,33人,304卷。宮閨:自上官昭容,迄薛濤,5人,24卷。總計691人,8 292卷(內晚唐許郴,閏唐孟貫、劉兼3人,出宋刻《百家唐詩》,嘉靖中云間朱氏重刻。集之晚出而非偽者,故并附)。
胡氏結語稱:“自宋嚴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后人傅會,謾云千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如此,即七百亦不滿,其中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概稱集者,亡佚寖遠,難可悉稽。約略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大抵為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簽唐音,在亡之數,其猶幸相半也乎!”[1]315
今按:1 000卷之《唐音統簽》與錢謙益、季振宜遞輯之《全唐詩稿本》,即為今人所見之《全唐詩》主要來源。誠如康熙本人所撰《御制全唐詩序》中云:“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簽》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4]3
值得一提的是:胡氏還將同人倡和之《珠英學士集》等25種,餞送詩之《朝英集》等6種,題詠勝境之《九華山詩錄》等12種,一方人士詩之《丹陽集》等5種,家集詩之《李氏花萼集》等4種,省試詩之《前輩詠題詩》等5種,僧詩之《五僧詩集》等3種,道家詩有《洞天集》1種,婦人詩有《瑤池新集》1種,全部列入“別集”之中,實為打破傳統目錄分類之法,因上列諸書在《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今按:北宋國家圖書總目,不知何故,胡氏未加引用)及《郡齋讀書志》中,均歸入“總集類”。
周先生于此卷后,出校記28條,其中涉及人名10處,地名1處,均為他校,多加按斷。古人云:“讀書有三難:人名、地名、職官名。”加以按斷更見功力!又,本校、理校各一處,說詳下文校勘部分。
2.選集類。此為胡氏獨創。自南朝梁阮孝緒撰《七錄》,至《宋史·藝文志》,上引10部目錄學名著中無一部列“選集”類目[5]附表。當代學者有主張:別集,對應總集而言;選集,對應全集而言。竊以為舉凡冠“全”字者,很難搜羅畢至。以《全唐詩》為例,日本江戶時期漢學家市河世寧(1749—1820,字子靜),就將流傳至該國的唐詩纂輯為《全唐詩逸》3卷,今已附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唐詩》之卷末。[6]2193更有當代學者王重民輯《補全唐詩》,孫望輯《全唐詩補逸》,童養年輯《全唐詩續補遺》。[7]1可見,用“全集”一詞要慎之又慎。
胡氏于選集又細分:唐人選唐詩、五代人選唐詩等類目。其中,合前代選者,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等5種。選初唐者,有《正聲集》等3種。合選初、盛唐者,有《閨秀集》一種。選盛唐者,有《河岳英靈集》等2種。選中唐者,有《南薰集》等4種。合選初至晚唐者,則有《唐詩類選》等3種。五代人選唐詩,則有《國風總類》等14種。
今按:當代學者輯《唐人選唐詩》時,已接受胡氏“閏唐”之說,將五代人韋莊所編《又玄集》、韋縠所編之《才調集》(即胡氏所錄《名賢才調集》)收入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人選唐詩(十種)》中的《搜玉小集》[8]687,即胡氏所錄《搜玉集》。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中的《珠英集》[9]47、《瑤池新詠集》[9]883,即胡氏上卷所錄之《珠英學士集》與《瑤池新集》。
胡氏又云:“自宋至今,唐詩總集,有選家,又有編輯家。唐詩至后代多亡佚(今按:難逃兵、蟲、水、火四大厄運),故有編輯家也。茲錄其稍著者。”[1]323宋代有《文苑英華》(太平興國中,學士李昉等奉詔撰。1 000卷,內詩230卷,六朝人居其一,唐人居其九)、《樂府詩集》(鄆州郭茂倩輯自漢、魏訖唐樂府)、《萬首唐人絕句》(洪邁編,五言25卷,七言75卷。每卷百首,共百卷),國朝(今按:即明代)有《百家唐詩》(華亭朱警刊,分初、盛、中、晚四期,共100卷)、《初唐詩紀》(黃德水編,16卷。吳琯補成60卷)。《盛唐詩紀》(吳琯編,110卷)。
復列宋至明的唐詩選集,宋代兩種:《唐百家詩選》(王荊公選,20卷)、《文粹》(今按:即《唐文粹》,姚鉉選,內詩13卷,又皆古體也);金、元四種:《唐詩鼓吹》(金代元好問選唐七言律95人,580余篇,10卷)、《瀛奎律髓》(元初歙人方回撰,收唐宋五、七言律詩并分門類加注釋,共49卷。以十八學士登瀛洲,指代唐;以五星聚奎,指代宋)、《三體唐詩》(元人周伯弼選唐人五律、七律、絕句,成20卷)、《唐音》(元人楊士弘選,15卷);國朝有《唐詩品匯》(洪武中新寧高棅選,90卷)、《唐詩正聲》(高棅從《品匯》所收近6 000首中,精選1 010首而成)、《唐詩選》(李攀龍選,13卷)。
胡氏總結云:“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士弘)始揭盛唐為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為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1]326
周先生出校記8條。其中據他書改“季善夷”作“李善夷”,“李元採”作“李元操”,頗是。理校,逕改“詭異寢盛”作“詭異寖盛”,更見諟證之功力。
3.詩話類。亦為胡氏所獨創。他認為:“詩話在集部,與文史同類(今按:自《崇文總目》集部設“文史類”,尤袤、陳振孫、馬端臨、《宋史·藝文志》皆仍之),用以標成法,搉往篇,備瑣聞,一切資長吟功,此焉在,不可無錄。”[1]329
唐人詩話,自李嗣真《詩品》1卷,至盧瑰《抒情集》2卷,共26種。胡氏評曰:“以上詩話,唯皎師(然)《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余如李嶠、王昌齡……諸撰,所論并聲病對偶淺法,偽托無疑。張為《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宋元人詩話,自丘昶《賓朋宴語》3卷,至劉會孟《七家詩評》(評王維、李白、孟浩然、杜甫、韋應物、孟郊、李賀七家詩),共74種。胡氏評曰:“宋人詩不如唐,詩話勝唐。南宋人及元人詩話,又勝宋初人。”
國朝詩話,自瞿宗吉《詩話》3卷,至胡應麟《詩藪》20卷,共16種。胡氏評曰:“明興,說詩者以博推楊用修(慎),以雅推徐昌榖(禎卿),以俊推王弇州(世貞)。……吾嘗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應麟)。”
今按:括號內之名字為筆者所加。誠如周先生《前言》所云:“胡氏此書博稽群集,成一家之言,三十三卷部帙井然,綱舉目張,可謂體大思精。然亦有可指摘者:引用他書,漫無體例,或居條目之前,或注條目之后;或舉書名,或稱字號,如王世貞或稱《藝苑卮言》,或稱元美、弇州、長公等。推原其始,或由展轉引用,隨手編錄,未能畫一。”[1]14
胡氏又云:“唐人詩集,多出后人補編,故多遺漏。其編次之序,又各人自為政,故本多不同。至注釋尤難言之。他不暇縷舉,即李、杜二大集,經多手改編并注(今按:世傳“千家注杜”),可商者正夥,附志后以例其余。”[1]333-334既談目錄,又及版本,留待下文論列。
周先生于此卷出校記26條,除刪衍文,補奪文,正手民之誤外,更指出徐衍《風騷要式》等8種宋人詩話,竟被《詩藪》訛作“唐人詩話”,尤以第十七條最得校勘要旨:在不憚瑣細地轉引《詩藪·雜編》卷五的一段“全文”后,按段:“胡氏(震亨)撮引,已覺失中,而以《漁隱》與《總龜》《玉屑》并列,更與元瑞(胡應麟)本文相左。”[1]341今按:周先生另有力作——校點《詩話總龜》前、后兩集。《前言》開篇即云:“今存宋人編輯的詩話總集,主要有三大部:《詩話總龜》、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和魏慶之的《詩人玉屑》。”[10]1至于三者之間的關系,兩位胡氏的意見并不相同。
4.傳世真跡與金石類:前者亦為胡氏始創。后者在《隋書·經籍志》中,入經部小學類;至《直齋書錄解題》才入集部文史類。胡氏認為:“唐人詩見于金石刻及自有真跡傳世者,至宋尚多。如宣和內府所收藏載在書譜者,真跡班班可考。而金石刻收藏之富,無如歐陽文忠、趙明誠兩家,目錄備在。”[1]343
《宣和書譜》真跡,自太宗《禊宴詩》(行書)起,迄釋靈該《種柳歌》(八分書),計48件。尚包括明皇隸書,李白、懷素草書,褚遂良、顏真卿正書等彌足珍貴之作品。
歐陽修《集古錄》,自《流杯亭侍宴詩》起,迄《浮槎寺八紀詩》,計16件。其中存于寺廟者居多,除浮槎寺外,尚有玄元廟、神女廟、道林寺、善權寺、法華寺等。
趙明誠《金石錄》,自天后《少林寺詩(正書)》,迄沙門湛然《題井陘山壁詩(正書)》,計65件。內中有與《集古錄》相重出者。書體又多出篆書1種。
王象之《輿地碑記》,自袁高《茶山詩》,迄《流杯十四詠》,計37通。逐一注明碑所立州府名。間有刻、立(復立)年代者。
周先生于此卷出校記38條,多“以信傳信,以疑傳疑”。如對《流杯十四詠》(在巴州西龕寺流觴亭……蓋取羊士諤流杯十四詠,以自序為證云爾)的“十四詠”[1]350生疑,遂引《全唐詩·羊士諤卷》之載記:“乾元初,嚴黃門(武)自京兆少尹貶牧巴郡。以長才英氣,固多暇日。每游郡之東山,山側精舍有盤石細泉,流為浮杯之勝。……士諤謬因出守,得繼茲賞,乃賦詩十四韻刻于石壁”,得出:“羊詩為五言排律共二十八句(即十四韻),‘詠’字誤”之結論[1]355。又如對《楠木歌》(嚴武、史俊。行書,無姓名)出校云:“‘嚴武’下,《金石錄》有‘撰’字,末無‘無姓名’三字,意為嚴武詩史俊書也。按之下文……有‘史俊寄嚴侍御楠木詩’”,《全唐詩》卷七十五史俊有《題巴州光福寺楠木詩》得出,“疑《金石錄》誤”之結論,更有“‘閬州’,《輿地碑記》作‘閬中’,全詩已佚,無從考定”的學術坦誠。
二、從版本學角度看周先生校勘《唐音癸簽》之成就
今人嚴佐之導讀錢基博《版本通義》稱其“主要看點有二端:一是‘會通古今’的‘義例’,二是‘重在校勘’的‘義理’”[11]2。明季大儒胡震亨與當代著名學者周本淳先生于此學問,亦是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一)從校勘《前言》看版本學之應用
胡震亨生于明代嘉興府海鹽縣。有明一代府志即有正統前、弘治、正德、嘉靖、萬歷等六修。府屬七縣,縣縣修志,海鹽縣志五修。其中就包括胡氏參與修撰的《天啟海鹽縣圖經》,以上均用年號分辨版本。周先生不僅引《康熙嘉興府志》《康熙廬州府志》《乾隆定州志》等鉤稽胡氏事略,更據上文所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歷故城縣志》,考定《嘉興府志》《海鹽縣志》《西庫全書總目》所記“固城”為“故城”之訛。
1.對《唐音統簽》版本的考定
清代大學者王士禛撰《分甘余話》云:“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音統簽》,自甲至癸,凡千余卷。卷帙浩汗,久未板行。余僅見其《癸簽》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于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板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周先生評論曰:“王氏此言雖為一些方志所引用,而實為誤記。曹寅所刻為《全唐詩》,《統簽》迄無全刻。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統簽》全帙,甲(今按:帝王詩)、乙(初唐詩)、戊(晚唐詩)、癸四簽為刻本,丙(盛唐詩)、丁(中唐詩)兩簽刻而未全,其余均為范文若鈔配本。”[1]9今按:范氏其人,詳見下文。
2.對《唐音癸簽》版本的考定
清代通儒邵懿辰認為:此書為明刻本。周先生云:“就我所見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天一閣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各本板式全同,其中以南京圖書館所藏前幾頁鈔配者印時最早。”復據卷七、卷八末有“戊戌秋刻”字樣,推論道:“明末清初以戊戌紀年者有三:萬歷二十六年(1598)、順治十五年(1658)、康熙五十七年(1718)。《癸簽》萬歷時尚未成書,此不特胡夏客《李杜詩通識語》可為佐證,且書中引用程良孺《讀書考定》為萬歷四十一年刊本,徐炯 勃《筆精》則為崇禎四年刊本,更足發明。而此簽于‘玄曄(今按:應作燁)’不避諱,不改字,不缺筆,與《戊簽》之刻于康熙時者迥異,故必刻成于順治十五年之后,康熙之前。”[1]16邏輯謹嚴,適足可信!筆者20世紀80年代作為訪問學者,曾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善本庫見過所藏此書,惜未嘗留意版式、行款。今翻看編者所贈《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得見:“唐音癸簽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 清順治(1644—1661)刊本(六冊)。”[12]288可謂得圖書館專家之旁證。
周先生又云:“《統簽》各本板式均為半頁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黑魚尾,可知原有統一計畫,但《癸簽》每板注大小字(今按:即大字正文與小字注文)數,猶存明末書板格式,他簽則否。長期誤認為明刻,或由于此。然此或刻工由明入清而致,不足為明刻之根據。”[1]16細心探求致誤原因并給出合理解釋。可惜的是該首頁所記“金陵劉鳳鳴刻”之刻工劉鳳鳴,難覓其生平也。
結末,周先生又指出:“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曾加標點排印,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今按: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加訂正再版。然校點方面訛誤尚多,北京師范學院齊治平同志曾指出多處,頗有啟發。”對新中國的兩種版本而言,周先生此校勘本,正可謂“前修未密,后出轉精”之作。
3.對《唐音癸簽》版本(兼及目錄)之補充
周先生于書末又輯《唐音癸簽敘錄》,收書兩種、記文兩篇,涉及目錄、版本事體,茲分錄如次:
四庫總目提要
《唐音癸簽》三十三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明胡震亨撰。……舊無刊版,至國朝康熙戊戌,江寧書肆乃得鈔本刊行(按:周先生已考定順治朝已有刊本)。……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盡為定評,而三百年之源流正變,犂然可按,實于談藝有裨,特錄存之,庶不沒其蒐輯之勤焉。(今按:此評價堪稱公允)
四庫簡明目錄
《唐音癸簽》三十三卷 明胡震亨撰。……縷析條分,元元本本,唐三百年詩派之源流,已約略備具矣。(今按:唐祚不足三百載,而加胡氏所稱“閏唐”,又過三百載。“三百”,略稱之謂)
鄭振鐸《劫中得書續匯》
《唐音癸簽》三十六卷(今按:周先生出校記訂正為33卷)十六冊
明末刊本關于胡震亨……搜集唐詩之評論成《癸簽》一書,其用力之劬,不下于計有功之《唐詩紀事》、尤袤之《全唐詩話》;而于明人詩話,所收尚多;盡有今日不易得見之本……清人刊《全唐詩》,其詩人傳僅寥寥數語,不足為知人論世之助。季輯全唐詩底本(今按:即上文所言錢、李二氏遞輯之《全唐詩稿本》),雖傳語較詳,然亦不甚完備。故重輯之功,仍當以此《癸簽》為主而再加以展拓也。”[1]357
今按:鄭振鐸先生抗日戰爭時期堅守在淪陷區上海,克服種種困難孜孜搜求保存古籍,事后撰寫的《劫中得書記》就收有《離騷圖》《古文品內外錄》等88種。包括《唐音癸簽》在內的《續記》又收《中州集》《國朝詞綜補》等60種。[13]417后編進《西諦書話》,葉圣陶先生《序》中稱:“振鐸講究版本,好像跟一般藏書家又不盡相同。他注重書版的款式和字體,尤其注重圖版——藏書家注重圖版的較少,振鐸是其中突出的一位。”[13]2
俞大綱《紀〈唐音統簽〉》 《唐音統簽》1 033卷,明海鹽胡震亨纂,輯錄有唐一代詩,卷帙浩繁,網羅宏備,為私家總集纂輯之冠。《統簽》卷帙既繁,未嘗全部鋟版,歷來通行易得,僅戊、癸二簽刻本。故宮所藏《統簽》,全帙無遺闕,刻本外,鈔本皆題邢村范希仁文若鈔補。考文若,清初海鹽人。故宮藏帙,書端間鈐范氏藏書印記,其為文若自藏本無疑。文若與胡氏子孫,同時同邑,《統簽》之有刻本者,自易得之,不認識本未刻者,亦可借錄鈔補,故此帙傳世獨備耳。”其中注文有云:“《癸簽》崇禎時已先有刻本(又按:周先生考定為順治十五年后始有刻本),《四庫總集存目》著錄康熙五十七年刻本,仍謂舊無刊版者,實誤。”今按:誤則誤矣,但言有崇禎刻本,亦復誤也!
(二)從《唐音癸簽》前29卷校記看版本學之應用
在唐代中期發明雕版印書之前,書籍以簡、牘形式出現。前者以竹片為材質,如2019年9月22日,《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新書發布會上所公布的“安大簡”《詩經》,就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量最多的古本,同時也是未經后代改動過的較原始本子。”[14]牘的材質為木板,后世稱文書為文牘,稱書信為尺牘,均為其遺響。又有以縑帛為材質的書卷,如本世紀初年在湖北隨州孔家坡出土的《日書》、歷譜,就被科學鑒定為西漢早期的卷本。[15]15620世紀初年,敦煌石窟洞開,除大量佛教經卷面世外,唐詩寫本卷子亦為國家文化珍寶(詳見張錫厚編《全敦煌詩》)。惜胡震亨未及得見。《癸簽》只能從雕版論起。
1.體凡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體凡”1卷,論詩之體裁變遷(周先生用他校法指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本,即作“體裁”)兼及聲病舉要。周先生校記四條,其一便云:“原刻版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黑魚尾(今按:同上引《統簽》版式);目錄騎縫作‘唐音統簽 癸’,正文騎縫作‘唐音癸簽’;作者均另行,目錄無‘著’字。文津閣本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作者另行題‘明 胡震亨撰’。”今按:因親自過目,故記載頗為詳盡。
2.法微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法微”3卷,論詩之“比、興”體格及字句、對偶、用典之利弊。周先生出校記42條。如胡氏于“雜詩”條下云:“自孔融離(今按:省略了詩字,下同),鮑照建除,溫嶠回文,傅咸集句而下,字謎、人名、鳥獸、花木,摹仿日煩,不可勝數。至唐人乃有以婢仆詩登第,孩兒詩取禍者。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夜致功,猶懼弗窺奧眇,暇役志及此?皆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胡元瑞《雜俳諧體》)”[1]26周先生引《詩藪》外編卷二原文:“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奧妙,而以游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回文,傅咸集句,亡補于詩,而反為詩病。自茲以降,摹仿實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兩相比較后,得出“胡氏顛倒改竄過甚”之結論。今按:周先生實事求是、不為尊者諱的精神值得稱許。
再如:“蘇長公(軾)論詩,有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元瑞《詩藪》)”周先生引古香齋《施注蘇軾》本卷二十六稱:“此詩為《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集作‘定非知詩人’。詩話引用多誤倒,應從原集義長。《詩藪內編》卷五,首句原作‘蘇長公詩無所解,獨二語絕得三昧’對東坡輕加抹殺,胡氏刪改,大勝原作,可為元瑞掩疵。”周先生對胡氏引文,憑不同版本校勘有貶有褒,堪稱公允。
3.評匯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評匯”7卷,分別依時代、詩歌體裁、題材、風格、評論重要詩人、詩作。周先生出校記122條。如:“虞永興(世南)師資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擬浣宮艷之舊。故其詩洗濯浮夸,興寄獨遠;雖藻彩縈紆,不乏雅道。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徐獻忠)。”校記云:“‘慕’,初印本亦較模糊,據明翻宋本《唐百家詩》前附刻《唐詩品》補。”[1]50此條原文為:“虞監師資野王,嗜慕徐、庾,髫丱之年,婉縟已著;琨玙之美。綺藻并豐。……其詩在隋,則洗濯浮夸,興寄已遠;在唐,則藻思縈紆,不乏雅道。殆所謂圓融整麗,四德具存,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今按:“在唐”二字,乃治世先聲之前提也。
又如:“云卿詩祖述沈千運,調氣傷苦,怨者之流。”校記云:“四部叢刊本《中興間氣集》逸去孟云卿評語。孫毓修據何義門校本補者,與此小異,此二句作‘漁獵陳拾遺,詞意傷怨’。”[1]52今按:上文所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人選唐詩(十種)》正同此。[8]314
另如:“大概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漢、魏至唐,詩家能事都盡,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導源,為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歷系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1]55(元瑞)”對這段盛贊杜甫力克“三難”,成就“三功”的文字,周先生用本校法出校記二條:一在“漢、魏至唐”下,校記云:“《詩藪·內編》卷五作‘子建以至太白’,胡氏妄改,與下文‘杜后起’句矛盾,當從《詩藪》原文。因杜接李后可通,杜承唐后則謬矣。”(今按:此又用理校法)二在“系興”下,校記云:“《詩藪》作‘繼興’。”今按:“繼興”,更文從字順。
“長卿自稱‘五言長城’(高仲武)”條下,《校記》云:“《中興間氣集》無此句。《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六: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秦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胡氏誤記為高仲武語。”今按:“五言長城”下之52字,確為高仲武評劉長卿之語。
“劉文房:‘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而劉為蘊藉。(楊升庵)”[1]109《校記》云:“《升庵詩話》卷十三‘劉文房詩’條,此句原作:‘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胡氏改為‘而劉為蘊藉’,失原意矣。”[1]116今按:周先生依本校法匡謬正誤,令人佩服。
4.樂通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樂通”4卷,分別論列詩與樂曲、詩與舞曲的種種關聯。周先生出校記87條。如:“《唐書·樂志》云:旋宮之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周先生于《唐書·樂志》下出校記云:“應為《新唐書·禮樂志》。”今按:兩唐書之“樂志”,《舊唐書》沿襲《隋書》作《音樂志》,而《新唐書》的《禮樂志》則是遠接《漢書》而來。《樂》在先秦,與《易》《詩》《書》《禮》《春秋》合稱“六經”,經秦皇一炬不復存在,僅在《禮記》中保存一篇《樂記》。司馬遷撰《史記》“八書”中有《禮書》《樂書》兩種,班固在《漢書》中合為《禮樂志》。其后,《晉書》《宋書》《齊書》《魏書》又分為《禮志》與《樂志》。周先生厘清新、舊唐書的兩種《樂志》,極是。
又如:“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中源乾曜作;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顯慶中李義府作。”《校記》稱:“《唐會要》卷三十三《昭和》下注云:‘撿撰人未獲’。胡氏與《舒和》《休和》同歸之李義府,蓋未細參故也。”今按:周先生用他校法,可謂縝密細致。
另如:“德宗 定難樂(河東節度馬燧作以獻。《本紀》:貞元三年、上御文德殿,試定難樂曲。)”,周先生于“文德殿”下,出校記云:“《舊唐書·德宗紀》及《唐會要》均作‘麟德殿’,本書卷三十三亦有德宗‘麟德殿宴群臣詩’,當以‘麟’為是。”今按:短短一條校記,兼用他校、本校之法,甚佳。
“《永遇樂》(杜秘書工小詞,鄰女酥香能諷才人歌曲,悅而奔之。事發,杜流河朔,述此訣別。女囗附持紙三唱而死。見《錦繡萬花谷》,云唐人。)”,《校記》云:“南京圖書館藏嘉靖本一百二十卷《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三十七‘妓妾·酥香’條云:‘唐杜秘書工于小詞。鄰翁有女,小字酥香,凡才人所為歌曲,悉能諷之。一夕,逾墻而至,杜始望不及此。鄰翁失女所在。后半年,仆有過,杜笞之,竄而聞官。杜流河朔,臨行,述《永遇樂》一詞訣別。女持紙三唱而死(并《白樂天集》)’,按:白集實無此事,故胡氏不取而止云唐人。四庫本無‘云’字。文中‘囗附’二字均為衍文,當刪。又會通館一百卷本《錦繡萬花谷》未見此則。”今按:周先生先后引三種版本將故事說得更清楚,衍、奪文字已指明。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辭書出版社又據錫山秦氏繡石書室翻宋刻本,將此書影印出版。[16]716
又如,“笛曲 紫云回(明皇游月宮,聞上清樂曲,歸而以玉笛寫之,因名。載樂章,令太常刻石。)”,《校記》云:“《太平廣記》引《開天傳信記》云:‘明皇夢游月宮’,義似長。下文‘舞曲’此條亦有‘夢’字。”今按:李隆基自然是在夢中游月宮,他校準確,本校“此條”二字換成“霓裳羽衣舞”則更佳。[1]157
另如,“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倚聲制詞,起于唐之季世。(《困學紀聞》)”《校記》云:“《困學紀聞》卷十八原文作:‘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聲填詞,起于唐之季世。’胡氏刪去胡、陸二名,遂使王應麟轉述之語,成為自創,失卻原意。”今按:“致堂”,為南宋著名學者胡寅(1098—1156)之號。他官至禮部侍郎(文化教育部副部長),著有《讀史管見》《斐然集》。
再如,樂通卷二校記末云:“按原刻此卷僅于本頁末行尾注‘卷終’二小字,與他卷異。”今按:足見周先生對版式之關注。
5.詁箋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詁箋”9卷,從訓詁及解釋典故角度,將唐詩中相關詞語(包括生僻字詞與方言俚語)加以解釋。周先生出校記101條。如解“重三”云:“張說《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曰重三。’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曰重三也。(鄭良孺)”[1]177周先生校記曰:“‘鄭良孺’應為‘程良孺’。”今按:此結論來之不易。周先生長子周先民教授從潘榮生所撰《厚積薄發,嘉惠士林——懷念一代宿儒周本淳先生》一文中得知:《唐音癸簽》引用鄭良孺之說十四條,依據內容可推知其為明代人。于是爬梳《明史·藝文志》見有《茹古集》作者“程良孺”之名,音韻功底深厚的周先生知道“鄭、程”二字乃“一聲之轉”。憑借學術敏感,“再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查得程良孺著有《讀書考定》三十卷,遂前往上海圖書館查閱(此書的萬歷四十一年刊本),將其全文通讀一過,《唐音癸簽》所引十四條果然盡在其中,遂訂正了傳抄過程中出現的一大謬誤。”[17]149今按:即化解了古人所云“讀書有‘三難’”中的首難——人名。
周先生又于“亥市”條后、“金潾”條前,出校記云:“南京圖書館藏順治刻本前有‘雙與堂藏板’扉頁者,于第八頁第九頁之間,補刻一頁,板心高于他頁一公分,較他本多三條,照錄如下”:
“二庭”,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缽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東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鄭良孺)”
《校記》稱:“《讀書考定》卷三,‘東庭’作‘南庭’。‘界’下尚有:‘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注唐詩者云:二庭未詳。如此未核,何以注為?’”
今按:問得極好!記得20世紀80年代,山西大學靳蒼璧教授就在《光明日報》撰文直言:“古籍整理工作不能提倡‘干中學’,必須具備一定基礎后再來干。”這是很需要膽識才敢表達的真知灼見。
“瓠蘆河 苜蓿烽”,岑參《寒上》詩:“苜蓿烽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按:上六字原刻漫漶不可識,據《讀書考定》卷三校補)玉門關,即西域之咽喉矣。”
今按:玉門關外五烽(烽火臺),常被誤書為山峰之峰。此條指明烽與郵驛相關聯,訛誤不再歟!
“拂云祠”,唐朝萬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岸有拂云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后料兵度而南。事見張仁愿傳。李益:“漢將新從虜地來,旌旗半上拂云堆。單于每近沙場獵,南望山陰哭始回。”山陰即所謂北岸者是也。君虞正以拂云在虜地,吾兵奪之,虜望而哭,故足雄耳,豈浪用漢事哉?古人作邊詞,未許不知地理者輕讀。(遯叟)
《校記》云:“四庫文津閣本,亦無此三條。”今按:胡氏強調讀唐人邊塞詩需有地理知識儲備,即克服“讀書三難”中第二難(地名)之意也。
6.談叢卷校記論及版本事略評
“談叢”5卷,專門搜羅唐代詩人的奇聞軼事(《學海類編》收有單刻本,僅10數字小異)。周先生出校記39條。如:“黃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至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黃巢比武王’之誚。”[1]279《校記》云:“事見《唐摭言》卷十三:‘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胡氏原刻及四庫文津閣本均作‘至仁伐不仁’,《全唐詩》同。然《孟子·盡心下》原有‘至’字,故據《唐摭言》校補。”[1]280今按:寓目之《唐摭言》[18]《孟子》[19]2773均如周先生所言。另,《登科記考》載:“乾符五年戊戌(878)進士三十人: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知貢舉:中書舍人崔澹。”[20]可以為佐證。
又如:“玄宗天寶二載,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暐還鄉。”《校記》云:“《舊唐書·玄宗紀》: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道士還鄉。天寶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別賀知章于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又《唐詩紀事》卷十七載御制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投歸老之《疏》,……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據此,‘二載’當作‘三載’。”[1]287今按:唐玄宗天寶三年正月,君臣大發思古之幽情,依《爾雅·釋天》所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19]2608于正月丙申,改“年”為“載”(見《新唐書·玄宗紀》)。所以二年不會稱“二載”,正月庚子日,《唐詩紀事》稱“天寶三年”,“年”字則應改作“載”。
三、從校勘學角度評價周先生504條校記之成就
學界公認校勘學濫觴于西漢劉向《別錄》中的“校讎”一詞:“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而“校勘”一詞則始見于梁代《沈休文集》:“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民郎、左民尚書,專共校勘。”至于校讎學專著則首推南宋鄭樵所撰《通志·校讎略》。古代集大成者,當推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所著《校讎通義》。其開篇即云:“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后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詞、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于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21]
此言一出,后世學者于“校讎”一詞便分別有狹義(如王叔珉《校讎學》、阮廷焯《校讎通論》為代表)、廣義(如張舜徽《廣校讎略》、程千帆等《校讎廣義》為代表)之兩種解讀。中山大學趙仲邑先生的詮釋較為通俗:“狹義的校勘,專指同一部書,用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互相核對,比較其文字的異同,以訂正錯誤;或只比較文字的異同。廣義的校勘,則包括古書的辨偽、輯佚及書目的校理,如張心澂《偽書通考》、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宋代的《崇文總目》、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等。”[22]
從上文對周先生校記的略評可以得出他廣、狹二義兼而用之的結論。下面再從幾種校勘方法入手,評價其校記的成就。
(一)對校法。即以同一部書的各種版本互相比勘之法。從所得結論看,此法又可細分為二:
1.述而不作之法。“述而不作”,典出《論語》,朱熹注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這頗類似《全唐詩》的做法,只一一列出版本之間的異同而不加是非優劣之按斷。竊以為此風不可長!因為這扼殺了學者們的創新能力。
2.宜各從長之法。“宜各從長”,語出《國秀集》所載屈同仙詩《燕歌行》后的毛晉校記:“‘習戰’作‘血戰’,‘不復和’作‘尚不和’,‘春輝’作‘光輝’,‘厭向’作‘厭得’,‘愁聽’作‘但聽’,宜各從長也。”[9]333竊以為此作法,既是對校勘唐詩水平之檢驗,亦是閱讀唐詩的積極取向。據周先生考證,胡氏“和明末大藏書家、刻書家汲古閣主人毛晉又是極好的朋友,他刻的《秘冊匯函》就是和毛晉一同校刊的”[1]7。彼此影響甚大。周先生校胡氏書取毛晉之法,亦適用下文本校與他校各條。
如卷四的17條校記中只有1條屬于“述而不作”類:“劉勰云:‘兩韻輒易,則聲韻微燥。’”《校記》云:“‘燥’,《文心雕龍》作‘躁’。”[1]33未加是非按斷(二字極易混淆,筆者先后在《羊城晚報》〔1984.9.9〕、《語文知識》〔2012.2〕發表《燥與躁》與《說“燥、躁”辨“枯燥”》二文,可資參考),其余16條皆屬“宜各從長”類,如(胡元瑞)云:“用事非詩正體,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只供厭吐。”《校記》云:“‘厭吐’,《詩藪·內編》卷四作‘厭飫’,義似長。”余如:“萬里”當作“萬井”;原刻“隱”字必誤;“粧”,原刻誤“籹”,逕改;“數十”,原刻作“二十”,據《藝圃擷余》校改;“從此”,原刻作“此從”,依《藝苑卮言》校乙;胡氏刪改,大勝原作,可為元瑞掩疵;“神韻為上”,《詩藪》原作“神韻為主”,義長;“姓字”,《詩藪》原作“姓氏”,義長。一一加以按斷,充分體現周先生才、學、識俱佳!
(二)本校法。即以本書的前后文字互證,比較其異同,從而斷定出舛錯訛誤之法。具體分析,此法亦可二分:
1.就《唐音癸簽》一書的本校。如卷二十三“張籍‘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校記》云:“二句見王維《老將行》,非張籍詩,本書卷二十一亦置《老將行》于王維條下,可證此處為抄胥之誤。”[1]250再如卷二十八“(賀)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臣,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于上京。朝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校記》云:“(‘朝’下)原刻衍‘萬’字,據本書卷二十九校刪。”今按:據本條亦可知:賀朝萬之“萬”字,乃齊融之姓。讀古書白文(無標點)常犯之錯誤。
2.他校時所引書,內中出現矛盾處的本校。如:“元微之詩‘光陰三翼過’。《越絕書》及《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舟名,蓋戰船之輕捷者。張景陽《七命》:浮三翼,戲中沚。梁元帝:‘白華三翼舸’‘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三翼木蘭船。’并用此。(鄭良孺)”[1]209《校記》云:“‘鄭’當作‘程’(今按:已見上文)此則見《讀書考定》卷二十七,節錄于下:‘《文選(張景陽)七命》“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艦也。……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白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之者。’又按:梁元帝詩見《全梁詩》卷三,題為《別荊州吏民》,此聯為‘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以‘日’對‘風’,字當作‘日’,胡氏沿程書之誤。”今按:周先生音韻學功力,又派上用場。又如卷二十三:“唐宦官多出閩中小兒私割者,號‘私白’,諸道每歲買獻于朝,故當時號閩為中官區藪,備載《唐書·宦官傳》。”《校記》云:“《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上)》云:‘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后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胡氏誤記為《舊唐書》。”今按:五代人劉昫所撰《唐書》有《宦官傳》。宋祁、歐陽修等所撰《新唐書》行世后,為加以區別才稱前者為《舊唐書》。上引文字在《唐書·宦官傳》中找不到,周先生翻檢《新唐書·宦者》卷上,才在《吐突承璀傳》中查獲。[3]5870此亦本校法、他校法并用之例。
(三)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之法。按他書成書年代,又可分為3類:
1.以前人之書校本書。如卷二:“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校記》云:“‘綮’,原刻誤‘棨’,依《唐詩紀事》校改。”今按:《唐詩紀事》為宋代計有功輯撰。
2.以后人之書校本書。如卷七:“朱慶余學于張籍,其體而微。‘旅雁捉孤島,長天下四維’。猛句亦水部(今按:即張籍)所少。(遯叟)”《校記》云:“‘捉’當依《全唐詩》作‘投’。”今按:周先生可能受‘治史學,孤證不立’說之影響,往往是前人書連引。如卷十八:“詩家詠登第多用淡墨榜事,指榜頭‘禮部貢院’四字也。或曰:文皇(今按:即唐太宗)以飛帛書之。”《校記》云:“‘飛帛’,《唐摭言》卷十五‘雜記’同。‘帛’,疑當作‘白’,書體有‘飛白’無‘飛帛’也。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上‘論飛白法’條,可參考。”今按:撰《唐摭言》的王定保為五代人,撰《東觀余論》的黃伯思為宋代人。《校記》中亦有前人書、后人書并用者,如卷四:“初稹以詩投賀,賀誚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校記》云:“《劇談錄》此說不足信。元稹年長于李賀十一歲。而又早達:‘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制下,除右拾遺。’(《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其時李賀尚未成年。《唐摭言》卷十云李賀:‘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今按:指韓愈)特著《諱辨》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劇談錄》之說純屬無稽,胡氏亦失之深考。又清人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辨此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于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轉引自《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錄以備參。”今按,《劇談錄》為唐人康駢所撰,現已有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鉛印本。又,清代王士禛之書,明人胡震亨無由見也。
3.以同時代之書校本書。如卷三:“七言絕語半于近體,同其句格宛順;節促于歌行,倍夫意味長永。(胡元瑞)”《校記》云:“此節胡氏剪截《詩藪·內編》卷六之文,晦澀難解。《詩藪》原文節錄如下:七言短歌始于《垓下》……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于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于歌行,而詠嘆悠永倍之。遂為百代不易之體。”[1]27今按:周先生將這段文字揭載于校勘《前言》,以示重視。
他校之法亦有綜合利用前人書、后人書、同時代人書之例證。如卷二:“摯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過;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校記》云:“此段引文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嚴可均輯《全晉文》卷七十七,又見《藝苑卮言》卷一。原文‘相過’作‘相遠’,按‘過’字與上文重復,作‘遠’為是。‘逸辭’,《藝苑卮言》作‘造詞’。”[1]13今按:晉人摯虞所撰《文章流別論》之語,被唐人歐陽詢等選入《藝文類聚》。此二人均為胡氏前代人。復又被清人嚴可均輯入《全晉文》,嚴氏為胡震亨后世之人。《藝苑卮言》為明人王世貞所撰,王氏與胡震亨為同時代人。又,《全晉文》“相悖”下,尚有:“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23]可補全摯虞之題旨。
(四)理校法。即以常理(包括文理)推斷正誤之法。上文已談有個例,茲再舉4例:
1.卷八:“唐彥謙詩律學溫、李,‘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回腸’,何減‘春蠶’‘蠟燭’情藻耶?”《校記》云:“此指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燭’似應作‘炬’。”今按:能燃盡成灰者,必為炬之木芯而非燭之繩芯也。
2.卷九:“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之類,對偶未嘗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校記》云:“‘嘗’,原刻作‘常’,依文義逕改。”今按:此為古籍整理中常犯之訛誤。
3.卷二十四:“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俗謂何物為底,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直云等物耳。”《校記》云:“‘刊謬正俗’,通稱‘匡謬正俗’,宋人避趙匡胤諱改。”今按:識辨避諱字是鑒定古代書畫真偽的重要方法之一。
4.《唐音癸簽·敘錄》:俞大綱《紀〈唐音癸簽〉》:“(胡震亨)時年七十四,復盡卷竄訂焉。旋遘改革,頻囑小子夏客(今按:震亨之子)藏稿本山寺,行遁(疑為僧名,或下有脫字)不懌而卒。”《校記》云:“‘行遁不懌而卒’即指胡震亨死于避難中,非有脫誤。俞氏夾注云云,蓋未細繹原文,不足憑信也。”今按:古人云“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信然!
最后,借用南京師范大學郁賢皓教授《學術深厚和治學嚴謹的學者——記周本淳先生》中的一段話作結語:
我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拜讀了周本淳先生校勘的《唐音癸簽》,非常佩服他知識的淵博和治學的嚴謹。……覺得無論在校勘、標點、分段、校記等各個方面都做得非常精當,從未發現有什么失誤之處,而且還有不少發明,使我深受啟發。
今按:吾更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