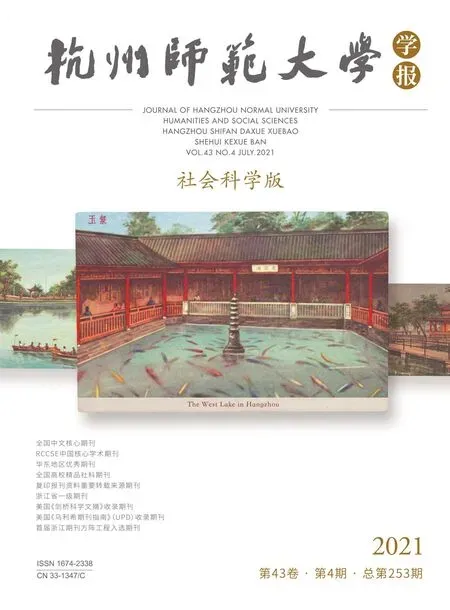比較倫理學:意義與方法
——黃勇教授訪談
黃 勇,陳喬見
上篇:中國哲學如何走向世界
陳喬見(以下簡稱“陳”):《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策劃了“21世紀前20年中國學術思想的展開與前景”專題,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通過訪談的方式,來對21世紀前20年各自所在的領域做一個回顧和前瞻。他們委托我對您做一場有關“比較倫理學”的專訪。確實,21世紀已經(jīng)走過了五分之一,回首20世紀的前20年,那真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來自西洋的堅船利炮和思想學術都對中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陳獨秀主掌的《新青年》,對東西方倫理都有不少比較,比如“中國重私德輕公德”“中國重義務輕權利”“中國重家族輕個人”等等一些觀點,都是在與西方相互比較的視野下得出的結論。不過,由于“救亡壓倒啟蒙”,那時的東西方比較更多地指向社會改造,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批判和否定居多。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都大為不同,如果說上世紀前20年是中西“倫理比較”,那么我們最近二三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則更加回歸學理,確屬“比較倫理學”了。在此方面,黃老師無疑是一位重要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注意到您在世紀之交(1999-2001)擔任“北美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主席時,于2001年在美國創(chuàng)辦了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較哲學雜志》)。我們就從這個協(xié)會和期刊談起,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協(xié)會,當初創(chuàng)辦這份雜志的初衷是什么?
黃勇(以下簡稱“黃”):先說協(xié)會,最早的時候是一些中國大陸到美國讀書的學生成立了一些留學生協(xié)會,學歷史的成立了“中國留學生歷史協(xié)會”,學政治的成立了“中國留學生政治協(xié)會”,等等。我們這個實際上就是學哲學的中國留學生的協(xié)會,不過我們協(xié)會用的名字比他們更專業(yè),叫“北美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雖然我們這個協(xié)會成立的時間相對晚點,大概是在1995年美國東部哲學學會年會上成立的。當初最早去美國讀哲學博士的一些中國學生已經(jīng)畢業(yè),開始在美國的一些大學任教,包括李晨陽、倪培民、姜新艷等,他們是第一屆理事會的成員。我自己是在國內(nèi)獲得博士學位后出去的,而且一開始并沒有打算再在美國讀書,只是陰差陽錯又在哈佛大學神學院讀了一個學位(因我在復旦做的博士論文主要涉及中世紀哲學家阿奎那,所以在神學院旁聽了一些課,其中的一位教授鼓勵我再讀一個神學博士),所以當初還在寫論文找教職(我是1996年開始在美國正式任教的,但事實上當初還沒有完成博士論文;論文是在1997年夏天完成并在秋天答辯,不過聘任我的學校說我已經(jīng)在中國獲得了一個哲學博士學位,所以一開始就以正式的助理教授職位聘我)。我記得當初選協(xié)會第一屆主席時,李晨陽和倪培民獲得同樣的最高票,后來是用扔硬幣的方式?jīng)Q定由李晨陽任第一任主席,兩年后換屆時倪培民被選為第二任主席,而我是第三任主席。“北美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的英文名稱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North America”(ACPA),這里的“中國哲學家”指的不是做中國哲學的學者而是研究哲學的中國人,因為至少在當初,我們中的大多人主要做的都是西方哲學。當然后來由于我們這批人的研究興趣大多轉(zhuǎn)向中國哲學,這個協(xié)會的性質(zhì)也不知不覺中逐漸有了變化,看起來更像是做中國哲學的學者的協(xié)會。一方面,它開始吸收一些研究中國哲學的非中國人,而另一方面,后來有些國內(nèi)來美國讀哲學博士的學生由于做的完全是西方哲學,他們也就并沒有太強的愿望加入我們這個協(xié)會。
陳:看來這個協(xié)會起先是“在北美的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似乎有點海外游子抱團取暖的意思,后來逐漸走向了“中國哲學在北美”的協(xié)會,更接近關于中國哲學的協(xié)會,較之于種族認同更為側(cè)重文化認同。這份雜志跟這個協(xié)會有關系嗎?
黃:有。這份雜志從一開始到現(xiàn)在,都掛著“北美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說起來,創(chuàng)辦這份雜志有些偶然。在任協(xié)會主席時,我當初認識的一位朋友,叫Parviz Morewedge,在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Binghamton)校區(qū)任教,主要研究中世紀伊斯蘭傳統(tǒng)中的神秘主義哲學,但同時又熱心出版事業(yè),成立了一個小型出版社,叫全球出版社(Global Publications),附屬于他所在的學校。后來他離開了這所大學,便將它重新注冊為全球?qū)W術出版社(Global Scholar Publications)。有次開會時跟他見面,他知道我在負責北美中國哲學家協(xié)會,就說他愿意為我們協(xié)會出一套叢書。我就跟我們協(xié)會理事會的其他兩位成員倪培民和王蓉蓉商量了一下,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可以順便增加我們這個年輕協(xié)會的曝光率,所以馬上決定了下來,將該套叢書命名為ACPA Series ofChineseandComparativePhilosophy,并馬上準備該叢書的第一卷,即由姜新艷主編的《經(jīng)由省察的生活:中國的視野》(TheExaminedLife:ChinesePerspectives)。
就在這第一卷出版之前,我的這位喜歡出版事業(yè)的朋友又建議我為我們的協(xié)會出版一份中西比較哲學的雜志。由于我們當初協(xié)會的規(guī)模不大,會員不多,而且在中西比較哲學方面已經(jīng)有《東西方哲學》(PhilosophyEast&West)、《中國哲學雜志》(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和《亞洲哲學》(AsianPhilosophy)等成熟刊物,擔心我們新辦一個刊物可能沒有優(yōu)質(zhì)的稿源,甚至擔心我們的會員也不愿意將最好的文章給我們自己的雜志,于是我發(fā)電郵征詢會員意見,雖然有個別的有我上述的擔心,但絕大部分認為應該辦一份雜志。為了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負責這個刊物,我就讓倪培民負責那套叢書。在他負責下,這套叢書迄今出了大概有近十本書。除了姜新艷編的一書外,還有Ewing Chinn和Henry Rosemont, Jr.編的《元哲學與中國思想:解釋郝大衛(wèi)》(MetaphilosophyandChineseThought:InterpretingDavidHall),Marthe Chandler 和 Ronnie Littlejohn編的《擦亮中國之鏡:祝賀羅思文》(PolishingtheChineseMirror:EssaysinHonorofHenryRosemont),伍安祖(On-Cho Ng)編的《理解的命令:中國哲學、比較哲學和本體解釋學》(ImperativeofUnderstanding:ChinesePhilosophy,ComparativePhilosophy,andOnto-hermeneutics),Jay Goulding 編的《中西跨文化:走向世界整合的哲學》(China-WestInterculture:TowardthePhilosophyofWorldIntegration)以及安延明的專著《中國哲學史上的誠的概念》(TheIdeaofChengin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等。
這樣我就開始籌辦這個新的中西比較哲學的刊物。首先是要確定刊物的名稱。我們在協(xié)會會員的電郵群中展開討論,最后覺得商戈令提出的 Dao 比較好,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涵括整個中國哲學,但考慮到這個名稱對不知道中國哲學的西方人聽起來有點神秘主義味道,我就堅持加了一個副標題,這樣我們的刊物的完整名稱就是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較哲學雜志》)。在一開始,我們邀請了一些名人寫稿子,比如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南樂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黃百銳(David Wong)、柯雄文(A.S.Cua)、安樂哲(Roger Ames)等,都曾經(jīng)為我們供稿。過了兩年,我們的稿子就很多了,我自此開始也不再邀稿了,而所有的稿子都需要經(jīng)過匿名評審(在此之前邀稿不送外審),每篇兩個評審,即使來自有名的作者也是一樣。這樣我們這個刊物逐漸成熟,特別是在第六卷(2007年)由比較正規(guī)的Springer出版(不久便收入A&HCI)以后,成為與上述幾家中西比較哲學的成名刊物不相上下、并駕齊驅(qū)、甚至有所領先的刊物。例如在2019年的刊物影響因子的排名中,在收錄的528種哲學刊物中,我們刊物是進入第一區(qū)(最高的25%)的刊物中唯一一種非西方哲學刊物。
陳:這份雜志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績,實屬不易。想必您也知道,這份雜志現(xiàn)在國內(nèi)也很吃香,因為很多大學激勵老師英文寫作,在海外刊物尤其是在收入A&HCI的刊物上發(fā)文。您之前也曾私下說起,因為堅持匿名評審,有可能為此“得罪”了國內(nèi)一些學者。能否談談您辦這份雜志所堅持的原則。
黃:在編這個雜志的過程中,我堅持幾點。第一,我非常尊重匿名評審的意見。如果他們建議不錄用一個稿子,即使我自己認為這個稿子不錯,我也都不會錄用。一方面,經(jīng)常不尊重評審的意見,以后就很難有人愿意為我們的刊物作評審(你可能知道,在英語世界為刊物評審文章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這會讓我自己在面臨熟人、朋友的被評審者拒絕的稿子時很為難,因為他們知道我可以推翻評審者的看法。當然這樣做的一個可能弊端是一些真的優(yōu)質(zhì)稿件也會流失,但我覺得如果一篇稿子真的是優(yōu)質(zhì)的,作者可以將其投給其他刊物,而遲早會有其他刊物的評審者推薦發(fā)表的。第二,我決定不在自己編的這個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因為我們發(fā)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經(jīng)過匿名評審,而很顯然我作為主編無法為我自己的文章安排匿名評審。與此相關,我讓兩位書評編輯全權負責書評,一個負責英文著作的書評,一個負責中文著作的書評(我們的刊物從很早開始就每期發(fā)表三篇中文著作的書評,三篇英文著作的書評,在有規(guī)律地發(fā)表中文著作的書評方面,我們這個刊物是非常獨特的)。盡管如此,我要求兩位編輯不要安排發(fā)表我自己所寫、所編的書的書評。第三,自從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后,培養(yǎng)和接受了不少博士生。我鼓勵他們用英文發(fā)表研究成果,經(jīng)常幫助他們修改文章,一直到我認為可以發(fā)表為止。這時我就會讓他們投到別的刊物上。我跟他們說,至少他們開始的四、五篇英文文章在別的刊物上發(fā)表以后才可以考慮投到我編的刊物上。結果由于他們在別的刊物上不斷發(fā)表文章,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發(fā)表過我自己的學生的一篇文章。
陳:確實,要辦好一件事,甫一開始就要把基本原則或者說某種類似“憲法”的東西確定下來,而且,重要的是主事者以身作則,率先遵守。學術刊物乃天下公器,在中國這樣一個所謂的人情大國,主事者確實需要把“憲法”寫在心中。以我的觀察,國內(nèi)一些重要哲學刊物也愈來愈走向和信賴匿名評審制度了。從長遠來看,這必將有利于學術的健康發(fā)展。
黃:后來我又做了一套叢書,現(xiàn)在還是很有影響的。你知道,國外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有指南(Companions)系列叢書,其中包括的題目會很具體。例如不僅會有《亞里士多德指南》(CompaniontoAristotle),還有《尼各馬可倫理學指南》(CompaniontoNicomacheanEthics)等,但往往不包括任何關于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家的指南,或者最多是籠統(tǒng)的《中國哲學指南》一本。因此我就跟Springer出版社說,我們能不能做一套叢書,叫SpringerCompanionstoChinesePhilosophy,整套書的每一卷都是關于中國哲學的,他們很樂意,并說這套書也不用出版社的名字,就叫DaoCompanionstoChinesePhilosophy,以便與已有的同名雜志相配套,相互促進。這是所有英語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眾多指南叢書中唯一一套關于中國哲學的指南叢書。我的計劃是,這套書可以包括一些比較廣的題目,也可以包括一些比較具體的題目,希望在若干年后能夠為中國哲學中每一個哲學流派、每一部哲學經(jīng)典、每一個重要哲學家都出一本,基本采取成熟一本出一本。到現(xiàn)在為止已經(jīng)出版了十五卷,包括有沈清松編的先秦儒家哲學、梅約翰(John Makeham)編的宋明儒家哲學、David Esltein編的當代儒家哲學、劉笑敢編的先秦道家哲學、David Chai編的魏晉玄學、王友如編的中國佛教哲學、馮耀明編的中國邏輯哲學、黃俊杰和John Tucker編的日本儒學、Ro Youngchan 編的韓國儒學、Gereon Kopf 編的日本佛教哲學等。這些都是較為一般的指南叢書,還有一些則比較具體,如有Amy Olberding編的《論語》、陳慧編的郭店楚簡、Paul Goldin編的韓非子、Eric Hutton編的荀子和我跟吳啟超合編的朱熹等。另外莊子和孟子兩卷很快會出版,還有老子卷、梁漱溟卷、易經(jīng)卷、法家卷都在編輯過程中。我覺得細水長流,每年出一到三本,長期下來應該比較有規(guī)模。
陳:做這個“Dao”系列的中國哲學指南叢書確實很有必要,很有意義。我到牛津大學訪學一年,就發(fā)現(xiàn)他們那邊類似的叢書非常多,有TheCambridgeCompanionstoPhilosophy,BlackwellCompanionstoPhilosophy,RoutledgePhilosophyCompanions,OxfordHandbook等系列,還有幾年前您給我介紹的SEP(StanfordEncyclopediaofPhilosophy,斯坦福哲學百科)網(wǎng)站,后來我經(jīng)常使用這個哲學百科查詢一些自己感興趣、想了解的哲學概念或理論等,很方便,也很權威,也曾多次向?qū)W生推介。我就在想,中國大陸現(xiàn)在不缺錢,也應該來做類似的事業(yè),由某幾個名校哲學系及其出版社來推進,當然,主事者非常重要。現(xiàn)在反而是在您的主事下,憑一己之力,用英文先做了,很有必要向大陸學者推廣這套以海外學者為主撰寫的中國哲學指南叢書,它應該成為研究相關人物或領域的必備參考書。
黃:是的,現(xiàn)在復旦大學已經(jīng)開始著手將我編的這套中國哲學指南叢書翻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一直在想,以你上面提到的《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為樣板,中國學者可以至少做兩件事情:一是出一套類似的包羅萬象的中文版的哲學百科全書;另一個是出一套英文版的中國哲學百科全書(雖然《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也收一些中國哲學的條目,但畢竟有限)。因是網(wǎng)絡版,不受字數(shù)限制,每一個條目可以有上萬字甚至數(shù)萬字長。而且如你注意到,在《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中,對于重要的哲學家,不僅有一個全面的條目,而且還對這個哲學家的哲學的各個重要方面另安排獨立的條目。以康德為例,除了“康德”這個條目外,還有“康德的道德哲學”“康德的哲學發(fā)展”“康德與休謨論道德”“康德的超驗唯心論”“康德與休謨論因果”“康德的超驗論證”“康德的數(shù)學哲學”“康德的科學哲學”“康德的宗教哲學”等,差不多有20個獨立條目(很可惜的是,里面沒有一個中國哲學家享受這樣的待遇,這也說明我們有必要出一套英文版的《中國哲學百科全書》)。另外,這個百科全書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這些條目的作者都是這個領域公認的學者,而且雖然條目的作者都是邀請的,但寫好的每個條目跟雜志文章一樣都要經(jīng)過匿名評審,一般都需要修改以后才能發(fā)表。不過,如你所說的,雖然中國現(xiàn)在不缺錢,但我無法想象誰會發(fā)起做這樣的事,而且即使有人發(fā)起做這樣的事,國內(nèi)頂尖的學者是否愿意為它寫條目都是一個問題。
陳: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與文化要走出去,這項工作確實很有必要。但是,想必您也有所了解,國內(nèi)現(xiàn)在都是“項目化生存”,果真有一天國家開始出資推動此項工作,我擔心研究很可能陳陳相因,東拼西湊,即便做出來也很難有公信力和權威性。而且,如果撰寫類似詞條不在各種評價體系之內(nèi),有多少人愿意為之努力確實很難說,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對培養(yǎng)學者的學術榮譽感似乎并不有利。就此而言,有時候一人主事反而辦得好,就像您一二十年來所堅持的那樣。
黃:最近還策劃了一套叢書,因得到復旦大學哲學院的支持,起名為FudanStudiesin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由Bloomsbury 出版。這套書中的每一本都以某個重要的當代西方哲學家為焦點,我會邀請十來位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要求他們?nèi)プx這位西方哲學家的著作,然后試圖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對這個哲學家思想的某個方面提出挑戰(zhàn)、批評,然后再邀請這位西方哲學家對這樣的挑戰(zhàn)做出回應。雖然這樣的西方哲學家一般不懂中國哲學,但由于我們是用中國哲學的資源來討論他們自己哲學中的問題,因此也可以從理論角度作出恰當?shù)幕貞N覀円话阆乳_一個討論會,然后再要求會議的參與者回家修改論文,再將它們連同西方哲學家的回應一起編輯出版。到現(xiàn)在,該叢書的第一卷,MichaelSlote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已經(jīng)出版, 第二卷ErnestSosa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將在年內(nèi)出版。第三卷討論英國哲學家Simon Blackburn,但由于疫情,會議幾經(jīng)延遲,到現(xiàn)在還沒有開成。很多在英語世界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往往抱怨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不感興趣,但如果他們對中國哲學一無所知,他們怎么可能對中國哲學感興趣呢?所以本叢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讓西方哲學家知道,中國哲學中有很多資源直接涉及他們所關心的西方哲學問題,從而使他們對中國哲學產(chǎn)生一定的興趣。而且由于這些都是有影響的當代西方哲學家,其他一些受這些哲學家影響或者研究這些哲學家的學者也可能因此產(chǎn)生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本書的另外一個目的則是通過要求每一卷的參與者認真閱讀有關西方哲學家的著作,鼓勵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盡可能多地了解當代西方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或者把自己對古代中國哲學的研究與當代西方哲學中所關心的問題掛鉤起來,看看前者是否能夠?qū)笳咦鞒鲋匾呢暙I,而這就涉及我自己所從事的研究中國哲學或者中西比較哲學的方法論問題。
陳:經(jīng)由您的引介,斯洛特于十年前就多次來國內(nèi)開會,并且于2013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做了系列講座,這些年他與中國學界的交往交流比較頻繁。據(jù)我所知,國內(nèi)做美德倫理學或情感主義的幾乎言必稱斯洛特,而他自己也很樂意從中國哲學比如孟子、王陽明和陰陽思維中汲取思想資源。我對于索薩的“美德知識論”略有所知,布萊克本的書也略有翻閱,但都了解不深。當您邀請當代有影響的西方哲學家參加這種比較特別的哲學對話時,他們有何反應,事后他們覺得如何?
黃:如你所說,斯洛特在我們開會討論他的著作之前,已經(jīng)關心中國哲學了。他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最早應該是他有一個中國學生跟他寫博士論文,用他的道德情感論解釋孔子的思想。我跟他最早認識大概是在2009年溫哥華召開的美國哲學學會西部分會的年會上。當初我參與組織了“宋明理學與道德心理學”的會議,得到美國哲學學會的支持和資助,作為這次年會上的小型會議,記得有三場討論。我們做宋明理學的學者發(fā)表宋明儒學中涉及當代西方道德心理學的文章,由西方的道德心理學家做回應。雖然我的文章是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霍卡(Thomas Hurka)回應的,而斯洛特回應的是另外一位學者的文章,但我們在會上做了比較多的交流。你上面提到的他在華東師大的系列演講也是我安排的,當初的設想是做一個系列能夠長期堅持下去,每次請一個西方哲學的名家做三到四個講座,然后請一些做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對這些講座做評論,再請這個哲學家做回應,并最后將這些講座、評論和回應結集出版。但由于種種原因,斯洛特的講座成了這個設想的系列中的獨唱,書也沒有出版,有點遺憾。所以我那次組織從中國哲學的角度討論他的哲學,他當然非常樂意,事后也開始花更多的精力研究中國哲學。相對來說,我們第二次會議、叢書第二卷的主角索薩事先對中國哲學的了解不是太多,不過他也曾經(jīng)在我主編的雜志上發(fā)表過一篇短文,通過對《論語》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句話的解釋來闡發(fā)他的美德知識論思想,或者說用他的美德知識論對《論語》中的這句話做出了一種獨特、有啟發(fā)性而又不無道理的解釋。因此,當我跟他談起我的這個計劃時,他也欣然接受。后來在讀了我們從中國哲學對他的美德知識論提出的各種挑戰(zhàn)的論文后,他說看來中國哲學家,特別是莊子、荀子和王陽明(因這三個哲學家在我們的論文中出現(xiàn)得最多)確實在美德知識論方面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為了回應我們從這些哲學家的角度對他的美德知識論提出的批評,他說他不得不要超出甚至修改他在已經(jīng)發(fā)表的著作中的觀點。他非常支持我將這個計劃做下去,并說如果我在聯(lián)系西方哲學家時遇到困難,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切身經(jīng)歷給他們做說明。至于我們計劃中的第三次會議、叢書第三卷的主角布萊克本應該對中國哲學也有些了解,因為他自己單獨編寫過一本哲學詞典,其中也有不少中國哲學的條目。因會議還沒有開始,我當然不知道他對我們這個計劃的反應,但當我跟他聯(lián)系時,他也是馬上答應的。當然并不是我所聯(lián)系的西方哲學家都愿意參與我的計劃,我曾經(jīng)聯(lián)系過好幾位這樣的哲學家,但他們都以這樣那樣的理由婉言相拒。不過,另一方面,當我邀請一些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參與我的這個計劃時,也有不少人婉拒。盡管如此,我看到,兩方面還是有不少的學者愿意參與這個在我看來非常有意義的項目,因此我還是會堅持做下去。目前只希望疫情趕快過去,讓我們把這個計劃中的第三個項目盡快完成。
下篇:比較倫理學的意義與方法
陳:您說當初辦《道:比較哲學雜志》事出偶然,但是后來做“道”系列指南和西方哲學家遭遇中國哲學系列叢書時,恐怕更多地是出于計劃,我相信在您內(nèi)心深處,一定是有某種雄心和抱負,認為這是一樁值得付出的事業(yè),一旦認準了,不急不躁,持之以恒,“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三年一小成,九年一大成。相信中國哲學在西方哲學界的尷尬處境一定會因黃老師的努力而有所改觀。讓我們轉(zhuǎn)到比較倫理學的話題。說到比較倫理學,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值得提起,即1993年在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孔漢思(Hans Küng)起草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自此后,“全球倫理”的提法日漸增多,而與此相關的一個話題則是有關“道德金律”的討論火了一陣子。在2000年前后,國內(nèi)很多有分量的學者都對此有所討論,而我第一次知道您,也與此有關。2004年7月,您和理查德·羅蒂造訪復旦大學,羅蒂做了題為《哲學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國、美國與世界》,您做了關于“道德銅律”的講座。您于2010年在臺大出版社出版了“全球化時代”的宗教、倫理與政治三部曲,對以往有關“全球化”的研究算是一個階段性匯集。能否介紹一下“全球化倫理”在西方的一些情形?
黃:“全球化時代”三部曲的出版跟臺灣大學的黃俊杰有關系。當初他邀請我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做訪問學者,并希望我為他們高研院所編的叢書供稿。我就將我那段時間發(fā)表的有關全球化的論文匯編成一冊叫《全球化時代的倫理、宗教和政治》,但因篇幅太大,他就決定將其分為三冊:《全球化的倫理》《全球化的宗教》《全球化的政治》(后來上海交大出版社用了別的書名出了這三本書的簡體字版),并專門搞了一套“全球-在地化”叢書,我的這三本成了這個系列的前三本。說起全球化,我們可能首先會想到全球化的食物如麥當勞、全球化的飲料如可口可樂等。但是,我想真正具有全球化意義的應該是最有地方性的。就此來說,越是全球化,越是要講地方性。
你上面提到的1993年的全球倫理大會,西方學者都強調(diào)“己所欲,施于人”的所謂金律,而認為儒家講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能是銀律。但以杜維明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堅持消極表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金律,在全球化時代更有價值,因為它強調(diào)不要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別人。但是,對儒家“金律”的一個主要批評是,不用做任何事,就能遵守此規(guī)則。但在我看來,無論是道德金律還是銀律,無論是肯定表述還是否定表述,有一個共同點,即假定我與人是相同的:我所欲一定也是人所欲、我所不欲一定也是人所不欲。所以,我提出“道德銅律”這一概念,其積極表達是“人所欲,施于人”,消極表達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英文版2005年發(fā)表在《東西方哲學》。我的提法主要是受了莊子的啟發(fā),比如他所講的“混沌”的寓言,以及魯侯養(yǎng)鳥是“以己養(yǎng)養(yǎng)鳥”而非“以鳥養(yǎng)養(yǎng)鳥”的寓言。這兩則寓言充分表明,我之所欲不一定為他人之所欲,因而也隱含著我之所不欲不一定是人所不欲。我的“道德銅律”跟“道德金律”或“道德銀律”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它關注行為主體與行為對象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行為對象之間的差異。我認為道德銅律古往今來都是適用的,但其意義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更顯突出。
陳:從主體視角向他者視角的轉(zhuǎn)化,以及人們有各自的善觀念,除了莊子的啟發(fā)外,是否還有羅爾斯的影響。我知道您在哈佛大學讀書時,聽過羅爾斯的課,彼時正是羅爾斯由《正義論》走向《政治自由主義》。晚期羅爾斯有個基本看法,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存在大量合理而又整全性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他稱之為“多元論的事實”,道德或政治規(guī)范不能建立在任何一種整全性學說的基礎上,否則就會造成對其他整全性學說的排擠和打壓。
黃:我剛到哈佛時是訪問學者,旁聽了羅爾斯的兩個課:一個是他給本科生開的課,記得是近代倫理學史;另一個是他和斯坎隆(Thomas Scanlon)和阿瑪?shù)賮啞ど?Amartya Sen)三個人為哲學系和政府系合辦的一個博士項目開的課,每次其中一個人主講,其他兩個人做評論。但說實話,去這些課堂有點追星的味道,我真正對羅爾斯思想的理解還是通過讀他的著作而獲得的。我的道德銅律思想跟羅爾斯對宗教、文化和形而上學多元性(在他看來多元性不只是個事實,而且也是一個價值)有關,但至少在兩個方面也有不一樣:一個是關注點不同。他主要是在政治哲學角度討論多元性這個事實和價值。由于存在著宗教、文化和形而上學關于好生活的多元看法,羅爾斯就認為,一個社會在確定其政治原則時,不能用其中的任何一種看法作為理由,因為這樣做意味著對在好生活問題上持不同看法的公民不公。而我的道德銅律則主要是從倫理學角度關注多元性這個事實和價值;更重要的一個差別是我們對這個事實和價值的關注程度不同。在羅爾斯那里,在我們討論政治問題時,要表示我們對在好生活問題持與我們不同看法的公民的尊重,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用我們自己的有爭議的好生活觀作為理由,我們唯一能用的就是他所謂的公共理由,即我們作為公民(而不是作為教會成員、家長、工會成員等等)提出的、為所有公民能夠接受的理由。在這一點上,即使是在政治哲學范圍內(nèi),如我在后來出版(先是英文版后是中文版)的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政治之公正與宗教之善:超越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爭》所表明的,我也不同意羅爾斯的看法。由于為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所謂公共理由(如科學、數(shù)學、邏輯的理由)往往不足以解決大多數(shù)政治問題,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的不同公民伙伴的、與我們不同的好生活觀中是否有我們能夠接受的、同時又可以支持我們所倡導的政治原則的理由。這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真正顯現(xiàn)了我們對自己的公民伙伴的尊重。要尊重我們的公民伙伴,光是不把我們的好生活觀強加到他們身上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力圖了解、理解且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他們的好生活觀。這一點在倫理學方面就顯得更加重要。我的道德銅律要求我們的行動必須適合我們的行動對象的獨特性,而要實現(xiàn)這一點,我們首先就必須要了解我們的行動對象的這種獨特性。這種了解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對特定的行動對象作出恰當?shù)男袆樱硪环矫嫠旧砭捅硎玖藢ξ覀兊男袆訉ο蟮淖鹬亍?/p>
陳:確實,了解他人才能真正尊重他人。在此方面,您寫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些理論和觀點,比如Ethics of Difference(差異倫理學)、Patient-Centered Relativism(對象為中心的相對主義),以及莊子是 patient-centered relativist等,極富啟發(fā)意義。2004年作為碩士生的我第一次聆聽了您的相關講座后頗不以為然,后來閱讀您的文章多了,也比較了解您的思路和想法,對此越來越贊賞。我相信您提出的“差異倫理學”一定會具有持久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我認為這是對莊子思想的一個極好的闡釋和現(xiàn)代發(fā)展,中國哲學真正要對現(xiàn)代世界貢獻思想與觀念的力量,需要更多的這樣的研究,而不是困在歷代浩如煙海的注疏中。不過,我也一直有點疑惑,道德銅律似乎不再相信儒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倫理觀念。我們能感受到莊子“以人養(yǎng)養(yǎng)鳥”的寓言就是沖著解構儒家道德原則的,在孟子的心學普遍主義與莊子的以對象為中心的相對主義之間,您似乎更傾向認同莊子?人與人之間真的無法達成道德共識嗎?這也是莊子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黃:我們也可以說,“道德銅律”就是一種道德共識,可以說人人相同的“心”和“理”就是要根據(jù)我們的行動對象的獨特性來行動。當然你也可以說儒家講的這個人人相同的“心”“理”是仁,但這也與我講的道德銅律不矛盾。仁者愛人,但如何去愛一個人則取決于我們的愛的對象的獨特性。我們對父母的愛、對子女的愛、對妻子丈夫的愛是不同的,我們對好人與壞人的愛也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對父母,在他們年輕的時候與在他們年邁的時候,我們對他們的愛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么程頤用“理一分殊”來說明張載《西銘》中講到的不同種類的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程子認為,雖然我們這里所謂的道德金律或銀律是“近于仁”,是“入仁之門”,是“仁之方”,“然未至于仁也”。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知以己之好惡處人而已,未至于無我也”。相反,如果我們能夠“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所以,雖然我的道德銅律主要源于莊子的思想,但與儒家的基本立場也是一致的。
陳:很受教益。我相信程子的“以物待物”或“物各付物”可能吸收了莊子的一些思想。讓我們轉(zhuǎn)向您前面已經(jīng)提到過的比較哲學方法論的問題。您最近20年來主要從事美德倫理學的研究,我知道現(xiàn)在已為國人所熟知的斯洛特、赫斯特豪斯等美德倫理學家及其著作,最早都是從您那里獲悉的。莊子之外,近十余年來,您更多地還是做一些儒家與美德倫理學相互發(fā)明的工作。記得2018年,您到華東師范大學做了幾場關于二程和王陽明的講座,我發(fā)了一條微信廣而告之,提前“劇透”了您的思路,名之曰“西方倫理學的問題,理學家更好的回答”。確實,有人會認為您的比較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取徑是“西方的問題,中國的回答”。國內(nèi)有不少人對此做法頗有異議,認為問題是西方哲學設定的,而我們不能總是跟著西方哲學設定的議程或問題走。這貌似是一個很嚴厲的批評,因為它暗含了某種“原罪”,意味著這樣做本質(zhì)上就是錯的。您新近出版的《當代美德倫理:古代儒家的貢獻》(2019年)和即將出版的《美德倫理學:從宋明儒的觀點看》,兩部書名都表現(xiàn)了這一取徑,而且書名也頗有意味,比如您不是從美德倫理學的視域來看宋明理學,而是從儒家(包括宋明理學)的觀點來看美德倫理學。能否借此機會詳細談談您做比較倫理學的方法。
黃:事實上,我并不是在先確定如何做中國哲學以后、或者說對做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有一個明確意識以后才開始做中國哲學的,可以說我做中國哲學的方法是在做中國哲學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你知道,無論是在華東師大、在復旦還是在哈佛的學生時代,我雖然也學中國哲學,但主要學習的都是西方哲學,前后加起來四個學位論文都是西方哲學。而且我在美國教書時教的主要也是西方哲學課(我當初應聘的職位是政治哲學),最初發(fā)表的五六篇英文期刊文章也都是關于西方哲學的,另外我在美國的哲學系的所有同事也都是做西方哲學的。所以當我開始將研究重心轉(zhuǎn)到中國哲學后,很自然地,跟很多國內(nèi)的中國哲學的學者不同,我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具有一種比較獨特的中西比較的視野:一方面,在思考中國哲學問題時,我就在想西方哲學家有沒有思考這個問題;而另一方面,在思考西方哲學問題時,我就會考慮中國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會持什么看法。如果經(jīng)過進一步的研究我發(fā)覺,西方哲學家在其中的某個問題上的看法存在著缺陷,而中國哲學家的觀點恰好可以克服這樣的缺陷,我就開始構思論文,說明中國古代哲學家如何可以比西方哲學家更好地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
陳:這種意識會不會跟您在西方接受學術訓練有關。您上面提到您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是有關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的,聚焦宗教之善與政治正義展開論述,您既不是單邊地贊同自由主義,也不是單邊地贊同社群主義,而是看看“兩造”各有什么好的觀點,還存在什么問題,然后在分析綜合的基礎上,提出您對此問題的觀點和主張。只不過那種比較主要是在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內(nèi)部,而后來關于美德倫理學與儒家倫理學的比較則擴展到兩種文化和兩種思想傳統(tǒng)之間,但基本方式似乎還是一樣。
黃:順便提一下我在別的地方說起過的,事實上,我在構思博士論文時,也在上杜維明先生的幾個研究生討論班,其中一個是關于朱子的。當時我覺得朱子的一些思想可以用來超越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各自的偏頗,但后來我的指導老師認為這樣一個題目太大,鼓勵我博士論文集中在當代西方語境中討論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爭,而在博士論文寫完后可以再研究朱熹,這事實上也確實就是我后來的大致研究路向。關于你講到的我討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關系的方式與討論中西哲學關系的方式,是有一點類似,可以說都是廣義的分析哲學的方法。分析哲學一般是以問題為出發(fā)點的。寫一篇論文就要在這個問題提出一種獨特的看法。要做到這一點,你就必須說明你的看法與其他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既有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樣,為什么人家的看法有問題,你自己的看法如何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而且你還要設想人家對你的看法會有什么樣的反對意見,你如何回應這樣的反對意見。分析哲學要求你的論證一定要清楚,如果你無法把自己的觀點寫清楚,大概是因為你自己還沒有將自己的觀點想清楚,而不是因為你自己的觀點有什么深不可測。但在我的這兩個研究之間也有一點不同:我在做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問題時力圖提出一種超越兩者的立場,而在做中西比較哲學時我主要是要說明中國古代哲學對當代西方哲學的貢獻。當然有時也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即在研究中國哲學時發(fā)現(xiàn),在中國哲學家討論的一些問題上,西方哲學家的解決思路更獨特,或者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提出了一些在我看來中國哲學家無法很好回答的問題,或者我發(fā)現(xiàn)西方哲學家的某些看法有問題,但中國哲學家也無法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我就放棄這樣的研究計劃。為什么這樣做呢?還是因為我當初在英語世界以英文寫作寫給西方哲學家看。有些西方哲學家認為中國沒有哲學,我覺得對這種看法的最好回答不是抽象地、一般地去論證中國有哲學,而是去論證即使是在西方哲學家最關心的一些哲學問題上,中國哲學家也有可能提出比他們更有道理的看法。而這樣的做法同樣也適合對中國哲學有同感或者好奇心但由于語言的限制而無法自己去做中國哲學的一些西方哲學家,因為他們對中國哲學感興趣,很顯然不是要證明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高明,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中國哲學家是否持一些與西方哲學家類似的立場,而是想知道中國哲學家對于他們解決他們自己的西方哲學中的問題是否能夠提供什么幫助。因此如果你的研究只是表明,(例如)孔子有很多與亞里士多德類似的美德倫理思想,那么這些西方哲學家就不會有動機去讀《論語》,因為他們已經(jīng)熟知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思想,而孔子只是有些類似的思想而已。
陳:確實,如果中國古代思想家也關注和討論一些西方哲學家(無論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所關注和討論的一些哲學問題,這較之訴諸philosophy或ontology等詞源學或概念的比較來確證中國古代有無哲學更為有效,也更為實質(zhì)。在我看來,西方哲學上討論的很多問題是普遍性的,中國古人也討論這些問題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您的比較倫理學研究主要不是意在尋求相同或相似的東西,而是探討哪一方對相關問題解決得更好。
黃:是的。由于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做中國哲學研究,很自然地我跟國內(nèi)中國哲學學者的一些做法會有明顯不同,盡管我當初對自己的這種方法論沒有明確的意識。我真正有意識地思考中國哲學研究(特別是在西方哲學語境中)的方法論問題與劉笑敢教授有關。劉笑敢認為雖然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眾多,但主要有兩種,一種以歷史的客觀性研究為主的導向,一種是以理論發(fā)展創(chuàng)新為導向。后來他看到了我寫的一些文章,覺得有些特別,不太容易歸入這兩種方法之中。我記得他問我是否可以用一段話說明我的這種做法。當初我思考了一下,寫了一段話電郵給他,但現(xiàn)在找不到這個電郵了。不過我看到他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發(fā)表的《中國哲學妾身未明?——關于“反向格義”之討論的回應》一文中就這樣描述我的中國哲學研究方式:“兩種導向的說法反映的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現(xiàn)狀以及應該注意的問題。這并非要將所有的關于中國哲學的研究一律納入兩種導向之中。純粹客觀的哲學觀點的比較式研究就不必列入兩種導向之中, 純粹哲學問題的討論可以兼及中國和西方哲學內(nèi)容,也不一定要納入兩種導向中的某一方。中國哲學的研究大可在扎實深入的思考探索中開拓新的方法和角度。比如黃勇討論意志軟弱是否可能以及討論人為什么要有道德的課題時都以二程的資料為主, 卻擺脫了平行比較、或以西釋中、或援西入中的既有模式, 完全集中于對哲學問題本身的討論。這既不是純粹將二程當作研究對象,又不是利用二程的資料建構自己新的思想體系, 而是不分中西的哲學理論的探討。這應該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一種模式, 或許是一種值得提倡的模式。”在該頁的注釋中他又說:“或許有人認為黃勇的做法是援中入西, 但筆者認為這樣說未必恰當, 因為他是以程頤的思想資料回答西方哲學中的問題, 并不是將程頤的思想納入某個西方哲學的體系或框架之中。”我覺得他對我的做法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確的。
劉笑敢在討論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即“反向格義”。大家知道“格義”主要指的是中國哲學史上當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人們用大家熟悉的中國本土哲學特別是道家和儒家的概念來解釋當初大家不熟悉的外來的佛教概念,在這種意義上格義這種方式還是有其肯定意義的。而劉笑敢說的反向格義主要是指在當代中國哲學的討論中一些學者用外來的特別是西方的(因而至少在某種意義上是大家不熟悉的)概念來解釋大家熟悉的中國哲學概念,這就有些奇怪。由于我自己做的工作主要不是解釋工作,而是用中國哲學的資源去解決西方哲學中的問題,無論是在中國哲學研究的語境中還是在西方哲學的語境中,都沒有反向格義(或者格義)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研究的語境中,我不是在用西方哲學的概念來解釋中國哲學,所以對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來說,我不是在做反向格義;在西方哲學研究的語境中,我不是在用中國哲學概念來解釋西方哲學,所以對于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來說,我也不是在做反向格義。
由劉笑敢的問題激起的我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的思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因為差不多這個時候我已經(jīng)完成了關于二程哲學的專著(WhyBeMoral:LearningfromtheNeo-ConfucianChengBrothers)各章的寫作,正需要寫一篇導言,而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要說明我在該書各章中體現(xiàn)的方法論。所以你看,我并不是預先確定了某種方法論,然后再根據(jù)這種方法論來撰寫全書各章。相反我是在撰寫全書各章的過程中,由于我所處的環(huán)境(在西方哲學界)中所設想的主要讀者群(不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而是對中國哲學不甚了解甚至不感興趣的西方哲學家)而自然形成的。順便說一下,該書的中文版已經(jīng)由華東政法大學的崔雅琴翻譯成中文,年內(nèi)將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中文書名現(xiàn)在暫定為《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道德哲學的當代啟示》。
關于我在該書的導言中所歸納的我從事中國哲學或者比較哲學研究的一些主要思想,實際上已經(jīng)在你幫我翻譯的《如何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做中國哲學:以儒學研究為例》(《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一文中介紹給國內(nèi)的學者了。雖然上述劉笑敢講的兩種導向主要是指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本身而言的,而我做的應該算是比較哲學,但在比較哲學領域,就方法論而言,主要也是這兩種導向。一方面,有些從事比較哲學的學者之所以從事比較,主要是為了通過比較對所比較的哲學家獲得更好的理解。例如通過跟孔子的比較,可以看到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我們原先看不到的方面,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有些從事比較哲學研究的學者在從事比較研究時主要關心的不是他們在比較的哲學家(如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本身,而是想在這樣的比較中得到某些啟發(fā),為他們自己的哲學構造服務。南樂山在我所編的刊物(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第一卷的第一期上所發(fā)的文章《比較哲學的兩種形式》(“Two Form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就詳細闡明了這兩種比較哲學方式的不同。大多數(shù)比較哲學學者認為他們在從事的是第一種意義上的比較哲學,南樂山則明確承認自己在做的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比較哲學。相對而言,雖然很多學者認為安樂哲所從事的也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比較哲學,但安樂哲自己并不認同,認為他所講的是真正的中國哲學。
陳:誠然,大概很少有作者寫一本書或研究一個主題,會先把方法論寫好,然后按部就班做研究,一般都是在寫完后覺得有必要再來一個方法論的總結作為導論,當然一開始必定也有某種未曾明言或概念化的方法論在其中。我在這里要為您的“如何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做中國哲學”的方法論辯護和擴展一下。首先我認為方法隨主題和對象而定,討論不同的主題,面對不同的對象,會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也認為一些看似比較特殊的方法也有其普遍性。比如您所講到的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如何做中國哲學的方法,其中一些同樣適用于在中國語境中做中國哲學,沒有這些方法論的自覺,中國哲學的當代發(fā)展很難走出陳陳相因、浮泛空疏的困境。
黃:是的。我自己所從事的比較哲學跟南樂山講的這兩種都不同,或者說是介于這兩者之間。一方面,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哲學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中國哲學對重大哲學問題的貢獻,而且由于我在英語世界從事這樣的工作,很自然地我會選擇那些歷史上和當今西方哲學家在我看來存在缺陷的重大哲學問題上的有關觀點,然后看中國歷史上的哲學家如何能在這些問題上提出更為合理的看法。所以我有點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研究是讓西方哲學家確定(他們無法很好解決的)問題,讓中國歷史上的哲學家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所以很顯然這不是南樂山所講的第一種比較哲學研究方式。但同時,由于我要向西方哲學家所表明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哲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當然一定是我認為是恰當?shù)囊蚨彩俏宜邮艿目捶?,我的研究也不同于南樂山講的第二種比較哲學研究方式。因為我需要表明我所講的中國古代哲學家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確實是這個古代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而這就要求我對有關的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文本做仔細的客觀的研究。
在這種意義上,你將我的比較哲學研究方式概括為“西方的問題,中國的回答”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當然也可能引起誤解(就像我自己關于這種方法論的說法會引起誤解一樣),而如果有人進而認為我實際上在做的不是中國哲學,而是西方哲學則更有問題。當然我也不會反過來辯護說,我在做的是中國哲學,而不是西方哲學。實際上我在做的既是中國哲學,也是西方哲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中西哲學家共同關心的哲學問題。當然我迄今的研究還是單向度的,還沒有反過來做,即選擇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討論的、其代表性的觀點存在嚴重缺陷的問題,然后再看西方哲學家在這樣的問題上如何能提出更有道理的看法,即讓中國哲學家設定(他們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而讓西方哲學家提出定論(如果我這樣做,會不會有人認為我在做的不是西方哲學而是中國哲學呢?)。不過,無論是在中國哲學研究的語境中,還是在西方哲學研究的語境中,這種相反向度的研究,至少在目前看來,還沒有很強的迫切性。
陳:我記得您曾私下談論過,當您談論這種雙向度的比較研究時,國內(nèi)一些學者建議您不要做后面那一種研究,即中國哲學家設定問題,西方哲學家更好的回答。因為中國哲學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弱勢,近代一百多年來大家都說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不行,一直處于被否定的狀態(tài)。而且,在我看來,這種否定很多時候是成見偏見所致,并無多少學理性。如果有人真心誠意從學理上研究中國哲學的不足,我以為還是很有意義的。
黃:是的。在某種意義上,在中國做中國哲學也是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做中國哲學。雖然跟美國大學不一樣,中國大學的所有哲學系都會有人做中國哲學,但還是西方哲學占主導。不僅做狹義上的西方哲學的人往往比做中國哲學的人多,而且做邏輯學、倫理學、科學哲學等的基本上都是在做西方哲學,如果你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算作是西方哲學的話,那做中國哲學的人在一個哲學系中真的是少數(shù)派。現(xiàn)在回到我上面的話題。在何種意義上,我從事的這種比較哲學研究也是一種中國哲學研究呢?表面上看起來,我用中國哲學資源來解決西方哲學的問題,很顯然我真正關心的是西方哲學而不是中國哲學。但其實不然。這可以從幾個方面看。首先,為什么我們可以用中國哲學資源來解決西方哲學問題呢?這不正表明西方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也正是中國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嗎?這里,很顯然我不同意一些學者的看法,他們強調(diào)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因此絕對不能與西方哲學掛鉤;但我也并不假定,所有中國哲學家討論的問題也都是西方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或者只有西方哲學家也討論的問題才算是哲學問題,反之亦然。我認為不要作這樣的一般的事先假設。相反,我們應該從我們關心的具體問題出發(fā)。如果我們首先關心到的是西方哲學中的某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去看看中國古代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有什么看法,特別是有啟發(fā)性的看法,反之亦然。我自己的比較哲學研究經(jīng)驗告訴我,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哲學傳統(tǒng)中看到關于相應問題的討論。
這就涉及我的做法與其他比較哲學的不同,我的比較側(cè)重的是問題,而不是概念。當然中西哲學中有些類似的哲學概念可以比較,但這樣的比較可能性比較狹小。中西哲學中可能缺乏相應的概念,但可能有相應的問題。例如在西方哲學中從蘇格拉底到戴維森都討論意志軟弱這個問題,提出過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國古代哲學家中有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的呢?如果我們?yōu)榇硕谥袊糯軐W典籍中去找“意志軟弱”這個概念,則要么根本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但跟西方哲學中的“意志軟弱”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作為一個問題,按照戴維森的看法,意志軟弱就是:你經(jīng)過綜合考慮知道你應該做一件事情,而且也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但是你還是沒去做。這實際上就是知行問題(比如,知而不行),而關于知行問題,在中國古代哲學家中有廣泛的討論,因此很顯然也是中國哲學的問題,而不只是西方哲學的問題。
陳:您剛才提到的兩個要點,一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比較研究,一是質(zhì)疑所謂中國哲學獨特性,我完全贊同。講中國哲學特殊性的一些學者,往往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們自己的理解),然后說中國哲學是另一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其實較之通常所謂“以西釋中”還更加變相西化,因為你逃避不了人家的陰影,雖然你明面上可能有意地避免使用一些西方哲學的詞匯。
黃:我的看法是,也許中國哲學確實具有他們所說的獨特性,但這應該是大家深入廣泛地研究以后得到的結論(如果真會有這樣的結論的話),而不應該是我們從事這樣的研究的前提。現(xiàn)在我要講一下在何種意義上我所做的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第二點。雖然我試圖用中國哲學的資源去解決那些在我看來西方哲學家沒有很好解決的哲學問題,但在此過程中,我也始終從西方哲學家的角度對我闡述的中國哲學家的思想發(fā)問,看他們是否能夠回答這樣的問題,而這會促使我們看到我們之前往往會忽視的中國哲學家的一些洞見。例如宋明儒承襲先秦儒特別是孟子的性善論,但西方哲學家就會問,你有什么根據(jù)認為人性善呢?我們都知道程朱的回答是由惻隱而知仁,或者說由情知性。性是形而上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情是形而下的,是可以經(jīng)驗到的,因此我們可以從可經(jīng)驗到的善的情來知道經(jīng)驗不到的善的性;這里善的性是用來解釋善的情的:沒有善的性怎么能有善的情呢,就好像沒有根怎么會有苗呢?但是站在西方哲學家的角度,我們又不能不進一步發(fā)問,既然程朱也承認人的情不總是善的,也有不好的情,那么為了解釋這些不好的情,我們是否也必須假定人一定也有不好的性呢?當然我們可以回應說,好的情一定要有好的性來說明,但壞的情不一定來自壞的性,就好像從好的苗我們可以推知一定有好的根,但從壞的苗卻不能斷定其根一定不好,因為苗之不好有可能是別的原因引起的。但這樣的回應無法完全排除壞的情來自壞的性這種可能性,就好像我們無法排除壞的苗是由于壞的根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程朱的由情知性無法證明人之性善。但這是否就表明儒家性善論有問題呢?我?guī)е@個問題進一步閱讀朱子的文本發(fā)現(xiàn),他的這個由情知性論證是跟另一個論證緊密相連的,這就是人禽之辨。當人做了傷人的事情以后,我們會說這個人不應該傷人,但當一只老虎傷人時,我們不說老虎不應該傷人。為什么呢?因為應當隱含著能夠。我們從經(jīng)驗的觀察和研究可以知道老虎不能不傷人,而人可以不傷人。我們可以讓傷人的人不去傷人,但無法讓傷人的老虎不去傷人。從這樣的觀察我們可以知道,傷人不屬于人的本性但屬于老虎的本性。當然這樣的論證也不一定就對人性論做了完美的證明,但這個事實說明,我們做中國哲學的學者時刻想著西方哲學家對我們討論的觀點的可能挑戰(zhàn),有助于我們關注我們沒有關注的方面。我這里不是說我們先前忽略了程朱哲學中關于人禽之辨的討論,而是說我們沒有把它與由情知性一起來論證性善論。
再舉一個相關的例子。我們上面談到了宋明儒講人性是形而上的。事實上宋明儒在西方一般被稱為新儒學,而宋明儒較之先秦儒之“新”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也許就是其形而上學,但在當代西方哲學中,特別是英美哲學中,出現(xiàn)了一種反形而上學潮流,認為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后形而上學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如羅蒂所指出的,“宗教和形上學共有的律令——給思想找一種非歷史、超文化、跨時空而無物不適的基質(zhì)——已經(jīng)死去,不復存在。在后形上學的文化中,人們會認為,人類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對上帝或‘實在的本性’負責,不是由上帝或‘實在的本性’告訴我們生活·世界是什么”。因此用宋明儒學來幫助當代西方哲學家解決他們的哲學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回應他們對宋明儒學的形而上傾向的可能批評。在此過程中,我就發(fā)現(xiàn),當代西方哲學家所反對的是一種特定的形而上學,我稱之為基礎主義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認為,我們首先要確立一個超經(jīng)驗、非歷史的真理作為基礎,它獨立于我們的經(jīng)驗信念與實踐信念,并可以推導出我們的經(jīng)驗信念與實踐信念或者確定這些經(jīng)驗信念或?qū)嵺`信念之真假。但如我們上面看到,宋明儒關于人性的形而上學不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首先假定了一些經(jīng)驗事實,人有惻隱之心,惡人能變善而動物則不能,等等,然后試圖解釋這樣的事實,認為如果不存在由仁義禮智構成的人性,我們就無法解釋這樣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這里,雖然在本體論上,形而上的人性是在先的(沒有作為性的仁就不可能有作為情的惻隱),但在認識論上,這些經(jīng)驗現(xiàn)象是在先的(離開了惻隱這樣的情就無法知道仁這樣的性)。我稱宋明儒的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為解釋性的形而上學,它可以避免當代西方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的批評。
陳:確實,儒家人性論的研究和當代發(fā)展,如果沒有源自外來思想的批判或援助,我覺得很難講出新意,也不太具有說服力。
黃:現(xiàn)在我再講第三點。雖然我的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解釋中國哲學,但由于我強調(diào)用中國古代哲學家本來的思想來解決西方哲學家的問題,這就需要認真研讀文本,從而對中國哲學的某些方面可以提出一些獨到的解釋。例如為了說明程頤對西方哲學中討論的意志軟弱問題的貢獻,我們不能不關注他在由張載提出的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問題上的看法。學界一般都認為,聞見之知是像關于雷鳴電閃這樣的經(jīng)驗知識,而德性之知是一種理性的道德知識。可是我做了仔細的研究,發(fā)現(xiàn)張載、程頤講的聞見之知主要也是指道德知識,只是這些知識是從老師那里聽來的或者從儒家經(jīng)典中看到的,因此是一種間接知識,而不是一個人通過自己內(nèi)心體驗而獲得的知識,而后者才是德性知識。因此,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往往具有相同的形式,如我們對父母要孝。如果一個人只是從書本上或從老師那里知道應該對父母孝,甚至理解為什么應該對父母孝,但沒有從內(nèi)心體驗到這一點,這個人并不會有動機去對父母孝,而這就是聞見之知。而如果這是一種通過內(nèi)心體驗而獲得的知識,是一個人的自得之知,這個人就自然會有孝父母的動機,而這就是德性之知。所以在這種意義上,一方面你可以說聞見之知是間接知識(從別人那里獲得的),而德性之知則是直接(自得)之知;而在另外一種意義上,你甚至可以說聞見之知是理智之知,而德性之知反而是經(jīng)驗之知(只是通過內(nèi)在經(jīng)驗而不是外在經(jīng)驗獲得的知識),即杜維明所謂的體知,雖然它也包含了理智的成分。關于對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這樣一種理解,我在去年發(fā)表于《哲學分析》第3期上的《作為動力之知的儒家“體知”論:杜維明對當代道德認識論的貢獻》一文中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
陳:黃老師關于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這個發(fā)現(xiàn),很受教益。可見,當我們試圖從中國哲學資源中尋求對西方哲學問題的解答時,不只是對一些觀念做一些去脈絡化的大而化之地提取,也需要我們從中國哲學固有的脈絡中認真研讀中國哲學家的文本,準確理解他們所講一些概念的涵義。總之,從西方哲學問題出發(fā),也能加深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而且往往能發(fā)人所未發(fā)。就此而言,所謂“以中釋中”未必比“以西釋中”(姑且如此名之)對理解中國哲學家的文本更準確。不過,是否也存在這樣的情形,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中的一些問題也構成了嚴肅的挑戰(zhàn)?
黃:當然。上面提到,雖然我試圖用中國哲學中的資源來解決西方哲學中的問題,我也始終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對我所用的中國哲學中的觀點立場提出責疑和挑戰(zhàn),而為了回應這樣的責疑和挑戰(zhàn),我往往會在中國哲學中發(fā)掘出以前不太為人關注的方面。但并不是在所有場合我都能對西方哲學的責疑和挑戰(zhàn)提出令人滿意的回應。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我們知道儒家中的人性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事實上,我在試圖為西方哲學中的問題提出儒家的解決方案時也往往使用儒家的人性概念。但我們?nèi)绾我?guī)定人性概念呢?我們從儒家的角度也許會說,人性并非就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把人與其他存在物區(qū)分開來的東西,即人性就是人所獨有的特性。上面提到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家霍卡認為這樣的觀點有問題。他說把人性理解為人所獨有的特性會把人類與其他存在者共有的所有東西排除在人性之外,不管它對于人來說多么重要,同時也會把人所特有的東西都視為人性,不管它對于人來說多么微不足道。另外,當我們說某種(些)性質(zhì)是人所獨有的時,事實上我們不光是在說人,而且是在說人以外的存在物:這些別的存在物沒有人所有的這種(些)性質(zhì)。這里的問題是:我們無法斷定什么是人性,除非我們已經(jīng)考察了迄今存在的所有別的存在物并確定它們都沒有人所有的這些性質(zhì)。即使這種工作實際上是可能的,但如果一百年后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的存在物也具有人所特有的東西,我們是否就必須否定這些性質(zhì)屬于人性呢? 那么我們把人性理解為人所必不可少的東西、即無之不足以成為人的東西是否可行呢?這種觀點的一個好處是,要了解什么是人性,我們只需要研究人,看什么是人所必不可少的性質(zhì),而無需研究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但他認為這也有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的人性概念就太泛了。像自我同一、占有空間這樣的特性對于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們對于與人很不相同的其他存在物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人性的第三種理解是把上述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即人性是人所特有的而且是人必不可少的性質(zhì)。霍卡認為,雖然這種人性觀可以克服上述兩種觀點的一些弊病,但是上述兩種觀點的其他一些問題,特別是第一種觀點的一些問題還是存在。例如,說人性是人所特有(并且必要)的特性,我們還是得研究人以外的存在物,這使我們的人性概念至少部分地取決于我們關于所有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本性的概念。他自己提出了他認為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的一種人性觀,我這里就不加討論,但我認為既然人性概念對儒家哲學特別是儒家倫理學這么重要,儒家必須認真考慮,我們到底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人性概念,并使這樣的人性概念避免霍卡提出的問題。
陳:這確實是一個在儒家人性論傳統(tǒng)中不曾留意的問題,值得認真對待,好好思考。您特別強調(diào),您運用中國哲學資源來解決西方哲學問題,要對中國哲學有細致深入的理解,您可能對它們做出了某種獨到的解釋,但仍然是其原意,并不是在做一種所謂“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這涉及到文本解釋學的問題。我在翻譯您的論文時學到兩個原則:一個是principle of charity(厚道原則或?qū)捄裨瓌t),大致是說解釋者對被解釋者要盡力做出最厚道的解釋;一個是principle of humanity(人性原則),大致是說解釋者也應該認識到,被解釋者哪怕古代的圣賢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犯錯,因此對其明顯的矛盾之處或有問題的觀點不能一味回護。這兩個原則對我很受用,也經(jīng)常會給我的學生講。我以為如果我們很多研究者都懷有這兩個基本原則,我們的研究會大為改觀。我想問的是,這兩個原則有沒有一種優(yōu)先關系,比如厚道原則優(yōu)先于人性原則;關于厚道原則,有沒有錢穆先生所謂“溫情的敬意”或“同情的理解”的意思。人性原則,有沒有最近幾年哲學界很喜歡講的“批判性思維”在里面?
黃:事實上,這兩個原則差別沒有這么大。奎因和早期戴維森的厚道原則要求我們在解釋他人(特別是古人和其他文化中的人)的文本時,要盡可能假定這個人的講話是合理的甚至是真的。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古人和其他文化中的人與我們的背景很不相同,因此如果我們不深入研究他們講話的背景和假定,我們可能將其講的許多話看作是假的甚至非理性的。后期戴維森接受的、最初由葛然蒂(Richard Grandy)提出的人性原則實際上差不多,只是他試圖糾正在使用厚道原則時可能有的極端化現(xiàn)象,即把古人和異文化的人講的明明是錯誤的話也看成是真的。之所以被稱為人性原則是因為它假定人是理性的,因此我們在解釋他人的話時,也要假定這是理性的,如果我們覺得不合理,我們也許還沒有真正理解他講的話,這與厚道原則沒有什么兩樣。但人性原則也假定人是人,而人是有可能犯錯的,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古人或異文化的人講的話有可能是錯的甚至不合理的。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人性原則包含了厚道原則并試圖避免其誤用。同樣,在這種意義上,他們都類似于你上面提到的 “溫情的敬意”或“同情的理解”。人性原則可能沒有批判性思維那么強,批評性思維可能與左派或女權主義所倡導的懷疑的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類似,解釋者往往懷疑古人的著作講的是不是真的,例如有些女權主義《圣經(jīng)》學者認為《圣經(jīng)》中關于婦女在早期基督教中的地位的描述是不對的,受到了男權至上主義的影響。左派和女權主義喜歡用“懷疑解釋學”,比如左派會說某某經(jīng)典就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等。
陳:我想我大致理解“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是怎么回事了。我想這個概念可用來形容國內(nèi)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儒學的解釋心態(tài)和方法,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批判(更準確地說是“批”),在一本名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總批判》的著作中,一位老一代的學人得出孔子“為少數(shù)惡人之師表、集片面謬說之大成”的結論。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種心態(tài)和方法至今在國內(nèi)學界并不少見,這愈發(fā)突顯厚道原則和人性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您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歌德說: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其實不懂語言。宗教學研究之父德國學者繆勒(Max Mueller,1823-1900)認為這同樣適用于宗教:只懂一種宗教的人其實不懂宗教(He who knows one[religion],knows none)。您自己進而說:只懂一種哲學的人其實不懂哲學,只懂一種倫理學的人其實不懂倫理學。王國維說“學無中西古今”,現(xiàn)在國內(nèi)有不少學者從事比較倫理學或更一般而言的比較哲學研究,您能否對這些博士生或青年學者提供一些建議和良言,作為本次訪談的結束語。
黃:首先我想說的是,雖然我認為我所采取的這種研究中國哲學或者中西比較哲學的方法具有它的獨特意義,但很顯然它只是而且應該只是研究中國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的眾多方法中的一種,因此我并不主張大家都采取這種方法。事實上,可能很多人認為這種方法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很少有人愿意采取這樣的方法。對于想用這樣一種方法研究中國哲學或者中西比較哲學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如博士生,雖然沒有良言,但我會鼓勵他們?nèi)プ觥N衣牭揭恍┎┦可f,要用我這種方式做研究、寫論文,需要有扎實的中西哲學的訓練,而這不是在博士階段可以完成的。我覺得這里最關鍵的是選題,這方面確實需要導師的建議或者把關,確定這樣一個題目是有意義的,而且是做得出來的。而一旦題目確定,即使這個學生先前的中西哲學訓練不是很全面,問題也不會很大,只要他愿意花力氣。例如,你的題目是王陽明如何可以幫助美德倫理學回應來自情景主義(situationism)的批評,你要閱讀研究的主要就是這兩項,當代道德心理學和倫理學中情景主義對美德倫理學的批評和王陽明哲學的有關內(nèi)容,而即使你以前對這兩個方面都沒有深入研究,在博士生的幾年中還是可以完成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好幾位博士生都在這方面有成功的嘗試。在博士畢業(yè)之后再做幾個題目,那么你在中西哲學兩方面的訓練就更加扎實。所以這里似乎也存在一個類似循環(huán)的解釋學的東西:你在中西哲學方面的訓練越扎實,你就越能做中西比較哲學;而你的中西比較哲學做得越多,你在中西哲學方面得到的訓練就越扎實。
- 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其它文章
- 杭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師新作選:董春雷《無塵(三聯(lián)畫)》(2021年)、許建春《日暮結局村》(2021年)、孫爾、鄭怡艷《痕》(2017年)、朱珺《絕學之路·中國壁畫藝術展》(2020年)、徐清《沙孟海先生集易林聯(lián)》(2021年)、斯泓《霓裳羽衣曲(系列之一)》(2017年)
- 杭州師范大學名賢篆刻錄:樂石社社刊《樂石第二集》篆刻選刊:陳兼善/邱志貞/陳偉(1914年)
- 杭州師范大學名賢書畫錄:孫智敏《閬苑畫屏行書七言聯(lián)》(約1940年代中期)
- 張涌泉《<金瓶梅>詞語校釋》手稿
- 蘇元老撰并楷書《龍洞記碑》
- 基于文化遺產(chǎn)的“結構—功能”變遷,推動歷史文化名城的內(nèi)源性可持續(xù)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