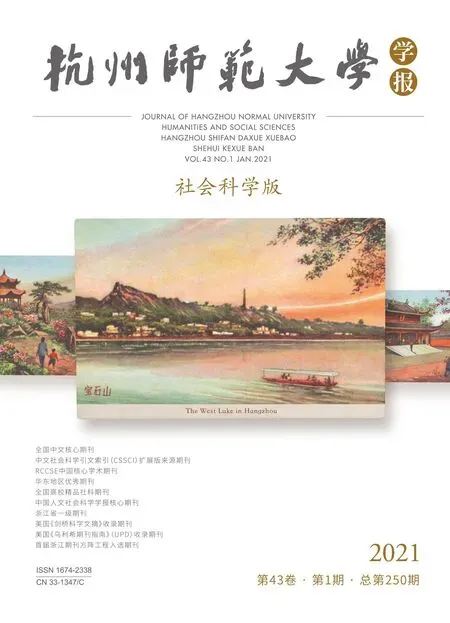試論史前時代至新王國時期古代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
劉金虎
(西北大學 中東研究所,陜西 西安 710069)
縱觀整個法老時代的歷史,位于尼羅河下游的古埃及人曾長期與尼羅河中游的廣大地區保持著密切的往來。盡管現代埃及學家往往將這一區域統稱為“努比亞地區”,(1)“努比亞”的地理范圍大致涵蓋了現今從埃及南部至蘇丹中部的廣大地區,參見D. K. Welsby, “Nubia”,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51。不過古埃及人曾對該地區有多種稱呼。從早王朝開始(約公元前3000年—前2686年),古埃及文獻中曾用“弓之地”(古埃及語 tAstj)(2)然而該地名有時也指古埃及傳統疆界內從阿斯旺(Aswan)至伊德夫(Edfu)之間的地區,即上埃及第一諾姆,參見J. Roy, The Politics of Trade: Egypt and Lower Nubia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p. 3。、“南部的土地”(古埃及語tA nHsj)等指代尼羅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地區[1](P.39),其居民也曾被統稱為“南方人”(古埃及語nHsjw)。例如第四王朝(約公元前2613年—前2494年)的一篇銘文中提到古埃及人某次軍事行動中曾“抓獲17000名南方人”[2](P.113)。到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550年—前1085年),古埃及人在向南擴張中一度控制了從尼羅河第一至第四瀑布沿岸的廣大地區。他們將其控制的區域大致分為兩部分:從第一瀑布至第二瀑布間的區域被稱為瓦瓦特(古埃及語wAwAt),或下努比亞地區;從第二瀑布以南至第四瀑布的地區則被稱為庫什(古埃及語kAS),或上努比亞地區。[3](PP.234-235)新王國之后,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似乎對這一地區也較為熟悉。例如荷馬史詩[4](P.4)和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常將該地區稱為“埃西歐匹亞”(古希臘語Aithiopia)(3)例如希羅多德曾提到一位名為塞索斯特里斯的國王曾同時統治了“埃及和埃西歐匹亞”,參見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82頁。,而此地的居民“埃西歐匹亞人”的字面含義是“臉部被灼黑的人”[5](P.37)。現代學者常使用的“努比亞”(Nubia)一詞最早出現于公元前3世紀,其詞源可能來自古埃及語“黃金”(nb)一詞,抑或是源自古典時代晚期(公元4世紀—7世紀)曾經生活在該區域的努拜人(Noubai)。[6](P.2)
作為曾經與古埃及文明往來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西方學者十分關注努比亞地區與埃及文明間的交往歷程。整體而言,西方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西方埃及學家通過在本地區的考古發掘初步構建起古代努比亞歷史發展的框架,并對其與埃及的關系進行了初步的論述;至20世紀60年代,隨著對努比亞地區新一輪考古發掘的廣泛開展,各國學者不僅進一步修正了努比亞地區歷史發展的分期,還從更客觀的角度審視了兩者在交往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間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西方學界從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等視角,嘗試分析被埃及控制之下的努比亞地區在文化、經濟、宗教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以及其對埃及文明發展所產生的影響。(4)20世紀以來西方學界的代表性成果包括:G. A. Reisner,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1908, 2 Vols., Cairo: Government Press, 1910; M. C. Firth,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Cairo: Government Press, 1927; W. B. Emery and L. P. Kirwan, The Excavations and Survey Between Wadi es-Sebua and Adindan 1929-1932, 2 Vols., Cairo: Government Press, 1935; T. S?ve-S?derbergh, gypten und Nubi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alt?gyptischer Aussenpolitik, Lund : H?kan Ohlssons Boktryckeri, 1941; H. S. Smith, “The Nubian B-Group”, Kush, Vol. 14, 1966, pp. 69-124; B. G. Trigger, Nubia under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W.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D. O’ Connor, “The Location of Ire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73, 1987, pp. 99-136; W. V. Davis ed., Egypt and Africa: Nubia from Prehistory to Isla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R. G. Morkot, “Economy of Nubia in the New Kingdom”, Cahiers de Recherches de l’Institut de Papyrologie et Egyptologie de Lille, Vol. 17, 1998, pp. 175-189; S. T. Smith, Wretched Kush: Ethnic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Egypt’s Nubi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 AD 5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L. Ross, Nubia and Egypt 10000 B.C. to 400 A.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eroitic Period, Lewiston, Queenston and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13; K. Howley, “Egypt and Nubia”, in P. P. Creasman and R. H. Wilinson eds., Pharaoh’s Land and Beyond: Ancient Egypt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19-227,等等。此外,雖然埃及學在我國開展較晚,但在古代埃及與努比亞關系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5)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包括:郭丹彤《古代埃及對外關系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郝海迪、孫異《試析古王國時期埃及與努比亞關系的演變》,《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6期;葛會鵬《古埃及與努比亞關系研究——以努比亞總督為中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馬一舟《從他者到我者: 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對外交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徐昊《古埃及文獻中的外族人及其形象構建研究》,《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等等。
不過,從史前時代至新王國時期的2000多年中,古代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實際經歷了由和平轉向暴力,由單一的經濟往來變為在文字、藝術、宗教等多層面交往的復雜演變。而西方學者在對這一過程的研究中,由于受文獻及考古資料的限制,將兩者間的關系簡單地界定為“先進文明”對于“落后文明”的征服與改造。因此,本文嘗試結合現有的研究成果,嘗試從整體性視角分析埃及與努比亞地區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交往方式的變化,以期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古代文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交往模式。
一、和諧與沖突:從史前時代至古王國時期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約公元前4000年—前2181年)
從史前時期至古王國時期,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經歷了從和平往來變為暴力沖突的過程。現代考古證據表明,由于地理位置相近,發源于上埃及的涅加達文化(約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和相鄰的下努比亞地區文化群A(A-Group,約公元前3700年—前2800年)[7](PP.92-111)在公元前4000年存在著直接的貿易和文化往來。在這一時期,下努比亞地區的史前居民們不僅曾居住于尼羅河第一瀑布以北的庫巴尼亞(Kubaniya)(6)目前考古學證據表明,該史前文化曾廣泛分布于從第一瀑布以北至第二瀑布以南的塞拉斯(Saras)之間的廣大區域,參見D. N. Edwards, The Nubian Past: An archaeology of the Sud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69。,他們也多從埃及進口陶器、各種石制、骨質和銅制的手工制品,以及谷物、啤酒和葡萄酒等農業產品。而涅加達時代的埃及人則可能更青睞努比亞人販賣的象牙、黃金、寶石、鴕鳥蛋、獸皮等原產自南部非洲的珍稀物品,導致掌控貿易線路的下努比亞部落首領們從中獲利頗豐。[8](P.36)此外,上埃及諸如希拉康波利斯(Hierakonpolis)和阿布希爾·艾爾·馬利克(Absuir el-Meleq)等地的埃及人也沿用了下努比亞地區的一些喪葬習俗。[9](P.176)而當社會結構更復雜、政治權力更集中的原始國家(Proto-State)出現在涅加達文化III期(約公元前3200年—前3050年)的埃及時,毗鄰的下努比亞地區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至少從該地區墓地出土的陪葬品推斷,該時期下努比亞地區的社會中不僅有貧富差異,而且存在享有特權的統治者。例如,在第二瀑布以北的庫斯圖爾(Qustul)地區的一座貴族墓葬(L 24)中不僅發現了眾多珍貴的陪葬品,在一個石制的香爐表面還出現了一位頭戴白王冠的不知名的努比亞統治者。(7)S. Wenig, Africa in Antiquity: The Arts of Ancient Nubia and The Sudan, Vol. II, New York: Brooklyn Museum, 1978, p. 117.不過,這可能并非說明象征古埃及王權的白王冠起源于下努比亞地區,而是下努比亞地區的統治者借用了此類象征權力的符號,參見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 AD 500, p. 43。而在同時期其他努比亞貴族的墓葬中發現的滾筒印章和印璽,似乎也表明某種形式的行政機構和原始文字正在孕育之中。[8](P.44)
然而,隨著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國家的最終統一,古埃及人在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中開始變得更具侵略性。除了出于邊境安全的需要,古埃及的統治階層對于奢侈品需求的不斷增長可能也促使埃及人試圖徹底控制下努比亞地區,以便與尼羅河中、上游的南部非洲地區直接進行貿易往來。[10](P.5)關于埃及與努比亞沖突的最早證據來自第二瀑布附近的謝赫·蘇萊曼山(Gebel Sheikh Suleiman)石壁上的兩幅巖畫。這些圖畫無一例外都描繪了前王朝或早王朝時期(約公元前3050年—前2686年)的古埃及統治者,對某些努比亞部落的殺戮。(8)J. Roy, The Politics of Trade: Egypt and Lower Nubia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pp. 217-220;葛會鵬《論古埃及文獻中的努比亞人》,《古代文明》,2013年第7卷第3期,第36頁。其中一幅巖畫中所描繪的巨蝎攻擊努比亞人的場景,則可能暗示此次軍事行動是由前王朝時期的統治者“蝎王”所發動的。[11](PP.88-91)至早王朝時期,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軍事活動可能變得更加頻繁。例如第一王朝(約公元前3000年—前2890年)法老阿哈統治時期的一塊木板上就描繪了法老對于努比亞地區的軍事行動,其中首次出現了表示“弓之地”的象形文字符號(伽丁內爾符號表Aa 32)。(9)T. A. H. 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p. 178;該象形文字符號參見A. H. Gardiner, Middle Egyptian Grammar, 3rd editio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Publications, 1957, p. 512。而相似的場景也出現在第二王朝(約公元前2890年—前2686年)法老哈塞海姆威統治時期的一塊石灰石石碑上,其中匍匐在地上的努比亞俘虜頭上標有相同的符號。[12](P.100)同時,第一王朝法老至少在第一瀑布附近的艾利芬提尼(Elephantine)建立了一座要塞,其主要目的可能是為了保護南部邊界的安全,同時也可為埃及人向下努比亞發動的軍事行動提供后勤補給。[13](PP.112-113)或許正是由于埃及人頻繁的軍事掠奪,加之對尼羅河貿易線路的掌控,最終導致下努比亞文化群A在早王朝時期被徹底消滅,或被驅離該地區。[3](P.230)
至古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時期,持續的經濟往來與間歇性的暴力沖突仍是埃及與努比亞地區交往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一時期,古埃及法老一方面通過軍事掠奪繼續獲取努比亞地區的勞動力及動植物資源。例如第四王朝法老斯奈弗如(約公元前2613年—前2589年)就曾“對努比亞地區進行攻城略地,帶回7000個(活著的)俘虜、20萬頭綿羊和山羊”(10)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p, 66; 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上卷,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8頁。如果這一數字沒有被夸大的話,斯奈弗如的軍事行動可能發生于較為富饒的上努比亞地區,因為同時期的下努比亞地區應該不存在如此眾多的居民和牲畜,參見R. G. Morkot, The Black Pharaohs: Egypt’s Nubian Rulers, p. 46。。另一方面,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活動可能更多聚焦于貿易往來和資源開采,而不是對該地區進行徹底的征服。[14](P.165)尤其是從第五王朝(約公元前2494年—前2345年)開始,古埃及文獻中常提及與“蓬特地區”的貿易往來中可以獲得烏木、象牙、沒藥、金銀礦石和各種原產自南部非洲的動物等珍稀物品。然而,除了沿紅海航行,埃及人若想從陸路到達“蓬特”則必須經過努比亞地區。(11)目前學界對于“蓬特”的所在地存在爭議,但大致認為該地可能處于埃及東南方的蘇丹、埃塞俄比亞或索馬里一帶的某個區域,參見K. A. Kitchen, “The Land of Punt,” in I. Shaw ed., 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 Food, Metals and Tow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587-604。同時,埃及人還在下努比亞的數個地區開采礦產和巖石。例如下努比亞地區的托斯卡(Toshka)在第四和第五王朝時期是重要的閃長巖礦場,胡夫、杰德夫拉、薩胡拉等法老都派人在此開采巖石,用以制作法老的雕像和石碑。[6](P.46)而位于阿拉克干涸河道(Wadi Allaqi)入口處的庫班(Kubban)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節點,埃及人還在此開采了大量的銅礦。[8](P.57)此外,位于尼羅河第二瀑布的布亨(Buhen)還成為了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第一個重要據點。從第四王朝開始,布亨便成為了古埃及人在本地的軍事和貿易重鎮,城中還有相關設施供埃及人熔煉銅礦。[14](PP.172-174)此外,努比亞人在古王國時期也開始被吸納入埃及社會中。例如法老斯奈弗如在戰爭中俘獲的戰俘會作為勞動力被安置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東部地區。[8](P.56)古王國的軍隊中也開始征召努比亞人,盡管他們只是作為輔助部隊伴隨埃及人作戰。(12)R. O. Faulkner, “Egypt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39, 1953, p. 33. 例如,第六王朝大臣烏尼在對亞洲地區進行作戰時從“伊爾柴特的努比亞人中、邁扎的努比亞人中、依瑪的努比亞人中、瓦瓦特的努比亞人中和卡阿烏的努比亞人中”征募軍隊,參見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p, 142;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中卷,第494頁。最后,此時期埃及人可能與上努比亞地區還存在和平的外交往來。例如臨近艾利芬提尼的塞拉(Shellal)就埋葬了一位死于第二或第三王朝時期的努比亞人。此人極有可能是一位來自上努比亞地區、且地位較高的“貿易代表”。[15](P.27)
然而,從古王國第五王朝后期開始,古埃及人似乎在下努比亞地區逐漸失去了立足之地。在這一時期,盡管埃及人對努比亞地區的軍事掠奪還時有發生,且仍能獲得當地部落首領的效忠,但下努比亞文化群C(C-Group,約公元前2400年—前1600年)[4](P.54)和上努比亞的克爾瑪文明(Kerma Culture,約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8](P.63)的興起似乎都對古埃及人在下努比亞的統治地位構成了挑戰。[16](PP.1125-1127)最后一位在努比亞地區留下銘文的古王國法老是第五王朝的法老尼蘇拉(約公元前2445年—前2421年),而布亨和托斯卡地區的采礦活動在第五王朝結束后也停止了。[17](P.23)第六王朝法老派皮二世統治時期(約公元前2278年—前2184年)的古埃及官員派皮納赫特(Pepinakht)仍有能力攻擊努比亞地區的部落,“殺掉部落首領眾多的子女和優秀的士兵”,同時還將俘獲的眾多戰俘送往法老的宮廷。(13)而且在他的第二次努比亞“遠征”中,派皮納赫特可能采用了更為平和的外交手段,參見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p. 163;葛會鵬《古埃及與努比亞關系研究——以努比亞總督為中心》,第26-27頁。派皮二世的前任法老美然拉(約公元前2287年—前2278年)甚至親自到艾利芬提尼地區接受了努比亞地區的瓦瓦特和伊爾柴特(古埃及語irTt)部落首領的效忠。[18](P.111)同時,為該法老效力的官員烏尼在受命去努比亞地區采集木材的過程中也得到了伊爾柴特、瓦瓦特、依瑪(古埃及語imA)及邁扎(古埃及語mDA)部落首領的幫助。(14)參見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 p. 22;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中卷,第498頁。實際上,此時的埃及法老可能已無法直接控制下努比亞地區。[6](P.49)因此,在更多情況下,面對實力不斷增長的努比亞部落,埃及法老不得不采取和平的方式以維持與南部地區的貿易。例如生活在美然拉和派皮二世統治時期的另一位官員哈庫夫不僅沒有提及埃及與努比亞部落進行交往時曾使用武力;在他的第三次遠征中,哈庫夫甚至還需要“實力強大的伊瑪(努比亞)軍隊”的護送才能穿過伊爾柴特、撒柴烏(古埃及語sATw)和瓦瓦特控制下的努比亞土地。(15)見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中卷,第512頁。一般認為,古王國時期的伊爾柴特、撒柴烏和瓦瓦特均位于下努比亞地區,而伊瑪可能就是上努比亞地區的克爾瑪文明,參見R. G. Morkot, The Black Pharaohs: Egypt’s Nubian Rulers, p. 49;也有學者認為,伊瑪可能位于第五瀑布以南的非洲內陸地區,參見D. O’ Connor, “The Location of Irem”, pp. 100-102。這或許也說明埃及人在該地區的活動并非都受到本地居民的歡迎。最終,隨著第六王朝(約公元前2345年—前2181年)的終結,埃及的中央政權土崩瓦解,古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軍事和經濟活動一度處于停滯狀態。
二、擴張與防御:從第一中間期至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181年—前1650年)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
隨著第一中間期(約公元前2160年—前2055年)法老政權的衰落,埃及在努比亞和西亞等周邊地區的軍事和貿易活動大大減少。正如中王國時期的文學作品《伊普味陳辭》在描繪這一時期的社會情形時說道:“今天沒有人前往巴比羅斯,(以獲取)制作木乃伊的雪松……黃金匱乏,合金耗盡。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王宮被掠奪了。”(16)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 Berkeley, Los Ang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p. 152;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下卷,第796-797頁。巴比羅斯(Byblos)是古埃及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重要的貿易伙伴,埃及人通過貿易從此地獲取諸如黎巴嫩的雪松、葡萄酒等珍稀商品。不過仍有證據表明,這一時期努比亞人經常作為雇傭兵在埃及軍隊中服役。通過位于上埃及地區的努比亞士兵墓地中的銘文和壁畫可知,有些努比亞士兵甚至迎娶了古埃及婦女作為妻子,并雇傭埃及人作為自己的仆人。[19](PP.44-80)而該時期上埃及的底比斯人也曾試圖控制相鄰的下努比亞地區,并向下努比亞地區的一些部落征收稅賦。[20](PP.288-289)
不過,從底比斯第十一王朝重新統一上下埃及開始,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055年—前1650年)古代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頻繁交往首先仍表現為激烈的暴力沖突。該王朝法老孟圖霍特普二世(約公元前2055年—前2004年)不僅在北邊擊敗了敵對的赫拉克里奧波利斯王朝,還一度向南進攻至第二瀑布的布亨地區。[21](PP.23-37)雖然該王朝并未在努比亞地區建立永久的據點,但孟圖霍特普二世仍在埃及南部邊界的艾利芬提尼修建堡壘并駐扎軍隊,同時重新開始與努比亞地區進行貿易。從第十二王朝(約公元前1985年—前1773年)開始,埃及人對努比亞地區的軍事行動變得愈加頻繁。經過長期的準備,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約公元前1985年—前1956年)憑借武力再次推進至尼羅河第二瀑布地區。(17)例如阿蒙尼姆海特第29年的《庫爾烏斯庫銘文》,參見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p. 228。而引發埃及人再次征服這一地區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此時建立于下努比亞地區的敵對王朝,參見B. Williams, “Three Rulers in Nubia and the Early Middle Kingdom in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72, pp. 1-10。之后繼位的數位法老在統治期間都發動了針對努比亞地區的戰爭,而且過程可能十分慘烈。(18)例如塞索斯特利斯一世(約公元前1956年—前1911年)統治時期的一位大臣曾說:“瓦瓦特余下的地區都遭受了屠殺。之后我勝利地順流而上,將努比亞人殺死在河邊;然后我又順流而下,掠奪谷物、砍倒他們剩下的樹木……”參見Z. ?ába, The Rock Inscriptions of Lower Nubia,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1974, p. 99。例如塞索斯特利斯三世(約公元前1870年—前1831年)在其統治的第10年、12年、16年、19年發動了多次針對努比亞的軍事行動[6](P.57),將埃及人實際控制的區域拓展至第二瀑布以南約60公里的塞姆納(Semna)和庫瑪(Kumma),使該地區成為中王國時期埃及在努比亞地區的最南邊界。有鑒于此,該法老在碑文中夸耀自己“俘虜了他們(即努比亞人)的婦女,奪走了他們的仆人,抽干了他們的水井,殺掉了他們的牛群。我踐踏了他們的谷物,并將他們點燃”[22](P.296)。法老同時貶低努比亞人“(聽見)一聲大吼,努比亞人就會潰敗,這是在警告他并迫使他退卻。對他(即努比亞人)勇猛無畏,他就會轉身離去;對他退讓,他就會前來掠奪。他們不是受尊敬的人,他們是卑鄙、懦弱的人”。(19)M. V.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p. 111;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上卷,第55頁。
然而,僅僅憑借短期的軍事掠奪似乎并不能完全滿足該時期埃及人對于控制貿易線路和維護邊疆穩定的需求。因此,中王國時期的法老采取了一系列全新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在下努比亞的戰略要地建立了“古代世界最偉大的軍事要塞體系(之一)”[14](P.176)。根據相關文獻記載,中王國時期的埃及法老曾在從第一瀑布至第二瀑布以南超過400公里的尼羅河岸邊建立了17座要塞。[23](P.186)這些要塞均沿尼羅河而建,或是處于地勢平坦但位置重要的河道附近,或是建造于河岸的峭壁之上,甚至有幾座要塞隔河相望。[24](P.127)每座要塞不僅充分利用當地的地勢,而且防御設施完備,并長期駐扎有古埃及軍隊。這些要塞的作用不僅限于監視本地區努比亞人的動向,也可支援埃及人在附近地區的貿易和采礦活動。其中一些要塞甚至是古埃及人與努比亞人進行貿易往來的指定場所。正如塞索斯特利斯三世時期矗立在塞姆納的界碑中提到:“南部的邊界……用來防止任何努比亞人跨越此處,無論水路或陸路,乘坐船只或是驅趕牲畜;除非他將前往依肯(即第二瀑布以南的梅爾吉薩要塞)進行貿易,或是擔負外交使命(才可通過)。”(20)界碑內容參見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pp. 293-294。此外,第一瀑布以南的要塞庫班不僅守衛著通向努比亞地區重要金礦產地的入口,同時還負責將金礦石熔煉后運往埃及本土;而第二瀑布以南的要塞如塞姆納和烏爾奧納提(Uronarti)也負責金礦的稱量工作。[25](PP.66-67)由此,中王國法老在努比亞地區修建的多座要塞都既可作為固定的軍事防御設施,監視周邊的努比亞部落;同時也可支援埃及軍隊在努比亞地區發動的軍事行動,保護尼羅河貿易線路的暢通;此外還兼具多種經濟職能,直接參與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商貿活動。[26](P.132)
此外,為了更好地管理埃及人控制的努比亞地區,古埃及法老還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例如整個努比亞地區的要塞都由名為“南部地區的總管”的埃及官員所監管,其職權范圍還包括了赫爾墨波利斯(Hermopolis)以南的上埃及地區。[8](P.86)要塞中不僅駐扎著各級將領和士兵,還配有專門的糧倉、金庫、武器庫等行政管理部門,甚至還有專門負責懲戒努比亞人的“監獄”。(21)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 AD 500, pp. 91-92, 95-96.此外,各要塞之間的沙漠中還有由古埃及士兵和邁扎部落雇傭兵組成的巡邏隊,定期沿主要道路進行巡視。[27](PP.8-9)同時,整個下努比亞地區應該也被分成了若干行政區域,并由各級埃及官員進行管理。[8](P.95)
盡管如此,中王國時期的埃及人似乎并未尋求徹底吞并努比亞地區。即使在要塞林立的下努比亞地區,考古證據也表明,本地的下努比亞文化群C居民并未像古王國時期那樣被驅趕走,而是與古埃及人相鄰而居。而當中王國后期,埃及人開始逐步放棄一些努比亞地區的要塞時,本地居民還在原有建筑規模上將其重新改建為居民點。[28](PP.158-159)同時,上努比亞地區以克爾瑪城為核心的克爾瑪文明不但從未被中王國的法老所征服,而且當第十三王朝時期的埃及政權再次陷入衰落時(22)中王國最后一位在努比亞地區留下銘文的法老可能是第十三王朝的法老涅菲爾霍特普一世,參見B. Porter and R. L. B. Moss,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75, Vol. VII, p. 139。,處于“古典時期”的克爾瑪文明(約公元前1750年—前1500年)還將勢力范圍從上努比亞地區一直擴展至埃及的南部邊境。
三、征服與融合:從第二中間期至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650年—前1085年)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
第二中間期時期(約公元前1650年—1550年),隨著古埃及王權的再次衰落,埃及不僅再次面臨內部的政治分裂,同時還要面對外來的敵人。一方面,從中王國后期開始進入埃及北部的“亞洲人”(古希臘人所說的“希克索斯人”)逐漸占據了三角洲地區的阿瓦利斯(Avaris)等城市,并一度統治了埃及一半以上的土地。[29](PP.174-190)與此同時,上努比亞地區的克爾瑪文明(古埃及人稱為庫什王國)也變得十分強盛。盡管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記錄,但有考古證據表明,該時期克爾瑪文明已具備了較為復雜的宗教和行政體系,并由一位具有絕對權力的國王所領導。克爾瑪城本身不僅存在行政、宗教、民事等功能區域的劃分,其外圍還環繞有高達10米的泥磚城墻和防御壕溝。[4](PP.80-83)與此同時,克爾瑪文明還控制了從尼羅河第五瀑布以北的庫爾古斯(Kurgus)至第一瀑布沿岸超過1200公里的區域,甚至下努比亞要塞中的埃及人也都臣服于上努比亞的統治者。例如布亨要塞中的一位埃及官員塞佩德赫爾(Sepedher)稱自己“是布亨要塞勇敢的指揮官……我為荷魯斯、布亨之主修建了神廟,以此來取悅庫什的統治者”[30](P.55)。另一塊出土于該地區的石塊上甚至描繪了一位頭戴白王冠的不知名的努比亞國王。[6](P.68)此外,努比亞人很可能還與尼羅河北部三角洲地區的第十五王朝(即“希克索斯王朝”,約公元前1650年—前1550年)有直接的貿易和外交往來,同時與底比斯的埃及本土王朝時常發生沖突。例如第十七王朝時期的一位埃及官員提到克爾瑪王國曾經聯合其他努比亞部落進攻上埃及。[31](P.52)而克爾瑪統治者的墓地中大量來自埃及的陪葬品很可能也是戰爭所得。因此,當埃及人再次試圖統一“兩土地”之時,南邊的克爾瑪王國對埃及人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從第十七王朝(約公元前1580年—前1550年)晚期開始,古埃及法老再次利用戰爭手段控制了努比亞的大部分地區。盡管曾一度臣服于尼羅河三角洲的希克索斯王朝,但從第十七王朝的埃及法老賽肯奈拉·陶開始,底比斯人試圖重新奪回對于整個埃及的控制權。而賽肯奈拉的繼任者卡摩斯(約公元前1555年—前1550年)意識到埃及人在戰略上處于南北敵人的夾擊之中。正如法老對他的大臣說:“讓我們分析現在的形式,一個統治者在阿瓦利斯,一個統治者在庫什,而我則在他們中間,他們與我共享埃及的領土。”[32](上卷,P.64)而在向北進攻希克索斯人之前,卡摩斯在其統治的第1至第2年先征服了下努比亞地區,并在其統治的第3年重創了希克索斯王朝的軍隊。然而,由于他的早逝,徹底驅逐希克索斯人的任務則由他的弟弟阿赫莫斯(約公元前1550年—前1525年)完成。隨后,埃及法老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征服更南的上努比亞地區。曾服役于阿赫莫斯、阿蒙霍特普一世(約公元前1525年—前1504年)及圖特摩斯一世(約公元前1504年—前1492年)統治時期的將領埃巴娜之子阿赫莫斯(Ahmose, son of Ebana)曾多次提及跟隨法老乘船沿尼羅河進攻努比亞地區。(23)參見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I, pp.8, 17-18, 33-34;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中卷,第551-553頁。而圖特摩斯一世不僅洗劫了克爾瑪文明的都城,其軍隊最遠甚至進攻至第五瀑布以北的庫爾古斯地區,并在此地樹立界碑稱“任何膽敢逾越此界碑的努比亞人,(我的)父親阿蒙神會將他押送給我,他的首領將被屠殺……”[33](P.50)盡管如此,努比亞人在他的繼任者圖特摩斯二世統治時期(約公元前1492年—前1479年)仍然掀起了反叛。法老嚴厲鎮壓了反叛者,并將一位反叛的努比亞部落首領的兒子帶入王宮中,他由此成為第一位接受“埃及化”教育的努比亞人。[8](P.162)在哈特舍普蘇特女王(約公元前1473年—前1458年)和圖特摩斯三世(約公元前1479年—前1425年)統治時期,埃及人也曾多次發動針對努比亞地區的戰爭。其中,女王本人可能親自領導過數次針對努比亞的軍事行動[34](PP.52-53),圖特摩斯三世則徹底摧毀了克爾瑪城,并模仿其先祖在庫爾古斯樹立了另一塊界碑。在此之后的約300年中,尼羅河第一至第四瀑布之間的土地基本都處于埃及人的掌控之中。阿蒙霍特普二世(約公元前1427年—前1400年)之后的第十八王朝法老在努比亞地區進行的軍事活動主要針對尼羅河兩側金礦分布較為集中的沙漠地帶,且次數逐漸減少。[3](P.234)第十九王朝的統治者如塞提一世(約公元前1294年—前1279年)和拉美西斯二世(約公元前1279年—前1213年)等在努比亞地區的對手多是南部邊界之外的其他部落,且規模可能較為有限。美棱普塔(約公元前1213年—前1203年)也曾殘酷鎮壓過一次努比亞人和利比亞人聯合的反叛行動。而第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約公元前1184年—前1153年)則可能是最后一位在努比亞地區指揮過軍事行動的新王國法老。[35](PP.214-225)
同時,為了更好地掌控努比亞地區,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550年—前1085年)的統治者在中王國時期的政策之上又有所發展。首先,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建立了一套更為有效的行政管理機制。除了不斷進行軍事征服,從阿赫莫斯開始的新王國法老將處于埃及控制之下的努比亞地區交由一位高級官員統一管理。這位“努比亞總督”的頭銜最初為“國王之子”(古埃及語sA nswt,圖特摩斯四世時期改稱sA nswt n kS“國王的庫什之子”(24)關于新王國時期歷任努比亞總督的列表,參見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 AD 500, pp.171-177;葛會鵬《古埃及與努比亞關系研究——以努比亞總督為中心》,第84-93頁。),地位與古埃及行政體系中最高階的文官——維西爾相同。直至第十九王朝時期,該官員的常駐地均在新王國的首都底比斯,并通過定期巡視的方式進行管理;該職位一般任期為10至20年,但并非終身授職。[8](P.178)總督的人選一般來自高級別的行政或軍事官員,并直接向法老匯報有關事務,其家族成員也可在努比亞地區的官僚機構中任職。作為掌管努比亞地區最高級別的埃及官員,努比亞總督的主要職責包括監管本地區的國家建筑工程,控制金礦的開采,本地部落的稅收和貢賦的征繳,以及這一切的運輸工作等。例如圖特摩斯三世統治時期的總督奈赫的自傳中就提到他為法老“帶來了南部地區的貢賦,包括金子、象牙和烏木”[22](P.261)。而大約也在同一時期,努比亞總督的轄區被分為兩大部分:瓦瓦特(即下努比亞地區)和庫什(即上努比亞地區)。總督向兩個地區各指派一名“國王之子的副手”(古埃及語idnw n sA nswt),輔助他進行管理。這些“副手”往往來自努比亞地區的行政機構,很多還是本地部落的高級別成員。[36](P.7)在他們之下,努比亞地區的城鎮或軍事據點分別由“市長”(古埃及語HAty-a)和“軍事官員”(古埃及語Tsw,Hry pDt或imy-r mr xtm)進行管理,其中一些官員還在努比亞地區的神廟中任職。[37](PP.262-263)而更下級的書吏、仆役等則會負責行政機構的日常運轉。此外,很多本地部落的首領及其家族成員也被納入這一行政體系當中,并常常負責稅賦的收集和運送工作。
其次,新王國時期的埃及也通過其他手段試圖將努比亞地區“埃及化”(Egyptianization)。從中王國開始,下努比亞地區就已經被視為埃及領土的一部分,盡管該時期的埃及人從未試圖改變本地居民的身份認同。[38](P.79)然而,新王國時期的埃及人除了使用軍事和行政手段之外,其在努比亞地區施行的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對當地部落高級成員的“同化”(Acculturation)。從第十八王朝早期開始,努比亞部落首領的子嗣在幼年時期就被帶到埃及,甚至是在王宮當中,與其他埃及兒童一起接受語言、文字、宗教、社會習俗等方面的教育,最終使他們完全認同埃及人的“價值觀念”。這些努比亞人在成年后可以在埃及或努比亞地區的行政機構中為法老效力,部分人甚至可以身居高位。[39](PP.35-37)例如,曾經活動于下努比亞泰赫海特地區(古埃及語thxt,大致相當于現今第二瀑布以北的布亨至法拉斯地區)[39](P.35)的部落首領家族在第十八王朝時期就是深受埃及文化影響的努比亞人。[37](PP.266-267)根據現存的考古及文獻資料記載,該家族已知的第一代男性成員曾是該地區的一位部落首領,而第二代男性成員瑞烏伊烏(古埃及語rwiw)已經在埃及接受過教育,因為他具有“書吏”的頭銜。[8](P.266)瑞烏伊烏的兩個兒子除了具有相似的頭銜,還都被賦予了“埃及化的”名字:長子名為杰胡提霍特普(古埃及語DHwtj-Htp),次子名為阿蒙尼姆海特(古埃及語imn-m-HAt)。同時,從兩人所具有的其他頭銜判斷,他們還與當時的古埃及王室甚至哈特舍普蘇特女王存在緊密的聯系。[34](P.54)在杰胡提霍特普位于戴畢拉地區(Debeira)的陵墓的墻壁上,不但他的膚色、發型和衣著與古埃及人完全相同,其上所描繪的各種日常活動,如駕戰車狩獵、欣賞努比亞舞者和樂師帶來的表演、巡視自己的田產和花園等也與新王國時期的埃及貴族并無兩樣。[36](P.187)而他的弟弟阿蒙尼姆海特的陵墓的頂部不僅坐落著一座小型的泥磚金字塔,其墓室中陪葬品的樣式和種類也與同時期古埃及貴族的毫無差別。此外,另一位生活在阿蒙霍特普二世統治時期的努比亞人赫卡姆撒森(古埃及語HqA-m-sA-sn)不僅成長于底比斯的王宮中,同時還具有“國王右手的持扇者”和“南部土地的總管”等高級別職位;而生活于圖特摩斯四世統治時期(約公元前1400年—前1390年)的某位努比亞年輕貴族甚至在死后被埋葬于底比斯的“帝王谷”之中。[6](PP.84-85)
同時,新王國時期的埃及人也試圖從努比亞地區盡可能地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盡管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潛力似乎不及埃及本土,但努比亞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及沿尼羅河的貿易線路從古王國開始就是埃及人所青睞的對象。至新王國時期,努比亞地區為埃及帶來的經濟利益對維系整個王朝內政外交的穩定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38](PP.93-95)除了農產品與勞動力,努比亞地區儲量豐富的黃金不僅充實了埃及法老的國庫,還被作為供品慷慨地獻祭給了古埃及的神廟。例如,圖特摩斯三世在他的“年鑒”中就曾記載:在他統治的第38年從上努比亞地區得到了約100德本(25)古埃及語dbn,重量單位,新王國時期的1德本約等于91克。黃金的貢賦,從下努比亞地區獲得了2844德本;第41年從上努比亞獲得了黃金超過94德本,從下努比亞則獲取了3144德本。(26)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I, pp. 211, 214.而該法老在位期間以金塊、金環等形式向底比斯的阿蒙神神廟共贈予黃金約13840千克。[3](P.77)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古埃及的對外交往中,從努比亞地區獲取的珍稀物品常通過“禮物交換”的形式,成為法老在外交活動中有力的籌碼。[40](PP.42-44)其中,黃金仍然是西亞各國的統治者最為青睞的“外交禮物”。正如米坦尼國王圖什臘塔(Tushratta,約公元前14世紀)在寫給埃及法老的信中說:“在我兄弟(即埃及法老)的國度,黃金多如塵土……(如果)我的兄弟愿送給我大量未經加工過的黃金。無論我兄弟房屋(即國家)中缺少什么……我都愿意支付十倍于他所需要(的數量)。”[41](PP.43-44)此外,埃及人還將努比亞地區大量的耕地以及在其上耕作的農民都劃歸國家或神廟所有。[25](P.129)第十九至第二十王朝時期,古埃及神廟占有的大量土地中有不少就位于努比亞地區。(27)該時期整個埃及約三分之一的可耕地都歸神廟所有,參見D. O’ Connor, “New Kingdom and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1552—664 BC”, p. 227。這些歸屬神廟的土地往往是免于征稅的,其產出的各種產品也要上繳給神廟,侵吞或挪用這些物品的人將受到嚴厲的懲罰。(28)例如新王國時期的一篇銘文提到不論何人如果“拿取……任何(應)作為收益上繳給神廟的努比亞產品,他將遭受被(棍棒)擊打一百下的刑罰,并向神廟上繳相當于這些物品價值八倍(的罰金)”。參見B. J. Kemp,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3, p. 238。
最后,第十八王朝前期對努比亞地區的軍事征服也促使埃及人在該地區興建了眾多神廟和城鎮,使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和社會習俗在本地區廣泛傳播。尤其是自圖特摩斯三世統治時期開始,新王國時期的埃及法老開始在努比亞的庫班、阿尼巴(Aniba)、卡塞爾·伊布瑞姆(Qasr Ibrim)、布亨、塞姆納等地興建了多座神廟。[8](PP.184-185)這其中,圖特摩斯三世本人在上努比亞的博爾戈爾山(Gebel Barkal)下修建的神廟,不僅是整個地區最重要的一座阿蒙神神殿,同時也促進了其后1000年中阿蒙神崇拜在努比亞地區的廣泛傳播。而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修建的神廟至今仍是古埃及精湛的建筑藝術的重要代表。[42](PP.87-90)另外,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建造的神廟不僅在布局上與埃及本土的神廟完全一致,而且同樣造價不菲。例如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他建造于索勒布(Soleb,位于第二與第三瀑布之間)的神廟銘文中說:“我為你(即阿蒙神)建造了你的千秋萬世之所(即神廟)……它由白色的砂巖建造而成,從里到外都鑲嵌著黃金;它的地板由白銀打造,所有的通道都由黃金裝飾……我要為他(即阿蒙神)獻上不計其數的公牛……我讓那些令人鄙夷的庫什首領都(來)朝拜你,背上都背著他們的貢賦。”[22](PP.360-361)此外,由于本地區的威脅逐步被解除,很多中王國時期的要塞被改建成為以神廟為核心的城鎮,并同時兼具行政和經濟職能。這些城鎮在布局上基本與同時期埃及本土的城鎮相似,包括被圍墻環繞的神廟、與普通民眾隔離開的官員住所以及分布于它們周圍的農田耕地。[43](P.94)然而,埃及人在這些城鎮中只占少數,其他居民大多是本地的努比亞人。到新王國時期結束時,生活在下努比亞地區城鎮中的努比亞人,無論是部落首領,還是普通民眾,大都接受了古埃及人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37](PP.263-264)
余 論
從早王朝至新王國時期,暴力沖突似乎時常成為古代埃及人與包括努比亞等周邊地區交往時的重要表現形式,但這一切主要源于古埃及人對世界的認知。從文明之初,古埃及人就認為宇宙中同時存在秩序(古埃及語mAat)與混亂(古埃及語isft)兩種永恒對立、相互爭斗的力量,而他們所生活的秩序和諧的土地時刻都被周邊野蠻和混亂的勢力所覬覦。只有法老——這位由神所選定的統治者能維護世界的秩序,消滅一切混亂和邪惡。[44](P.11)正是基于這種“二元化”的世界觀,古埃及人構建了出“我”與“他者”的身份差異,有意將自己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區分開來。(29)對于古埃及人來說,世界上存在四個族群:埃及人、努比亞人、利比亞人和亞洲人,參見A. Leahy, “Ethnic Diversity in Ancient Egypt”, in 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 New York: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5, pp. 226-228。這種差異一方面反映在埃及壁畫或雕塑對于不同民族的描繪中:“文明的”埃及人(男性)往往有紅褐色的皮膚,長及肩部的黑色頭發,臉上蓄著精心修剪過的胡須,身穿由白色亞麻布織成的短裙;而來自“異國土地”(古埃及語xAst)的努比亞人則往往皮膚較黑,鼻子寬而扁平,頭發被編成一縷縷下垂的發辮,耳朵上佩戴大耳環,雖然下半身穿著埃及式樣的亞麻短裙,但上半身往往還佩戴著獸皮肩帶。(30)古埃及人對于不同族群的描繪雖然基于一定的實事基礎,但大部分都是一成不變的“刻板印象”,參見S. T. Smith, Wretched Kush: Ethnic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Egypt’s Nubian Empire, pp. 21-23;徐昊《古埃及文獻中的外族人及其形象構建研究》,第84-90頁。更重要的是,這種差異的存在直接影響了古埃及人與周邊地區交往中的態度:交往中的一方即“我”常居于核心的地位,而另一方即周邊的“他者”則往往被貶低,成為被征服和鎮壓的對象。[45](PP.126-127)這也導致古埃及人對包括努比亞人在內的其他民族常常抱有“蔑視”和“敵意”的態度。例如在新王國時期的古埃及文獻中除了常把努比亞人描繪為“鄙夷的”“懦弱的”“野蠻的”族群外[46](PP.34-41),還認為他們可以操縱危險的“魔法”。正如阿蒙霍特普二世告誡他的努比亞總督時說:“絕對不要對努比亞仁慈!小心那里的人和他們的魔法!”[47](P.6)甚至在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30年—公元641年)的世俗體埃及語文學作品中,仍然將努比亞人與魔法聯系在一起。[48](Vol. III,PP.142-150)因此,為了保證世界秩序的安全,“我”需要不斷征服和控制這些代表“混亂和野蠻”的“他者”。[47](P.8)這就導致暴力成為大多數歷史時期埃及與努比亞地區交往時的首要特征。
然而,在實際交往過程中,古埃及人與努比亞人之間并非簡單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或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盡管在數千年間,埃及與努比亞地區的交往模式很難稱之為“利益互惠”(31)古代東地中海地區的“利益互惠”是“對稱(或地位相等)的群體相關部分的交互運動……互惠需要在群體間對等的背景下進行……”,參見郭丹彤《埃及與東地中海世界的交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23頁。,但長期存在于埃及和努比亞地區之間物質或非物質層面的交流,逐漸在兩者間建立起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動態關系(32)“文明交往是一個雙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各個文明之間既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又相互沖突、相互抗爭,其常態是相對的靜態平衡和動態平衡。”參見彭樹智《文明交往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頁。。對于古埃及人來說,從早王朝時期不定期的軍事掠奪,到中王國時期規模龐大的防御體系,再到新王國時期從行政、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全面“同化”,古埃及人對努比亞地區的政策經歷了從單一到系統、從局部到整體的發展與變化。其中,除了意識形態和邊界安全的需要,獲得努比亞地區豐富的礦產、動植物和勞動力資源,以及占有經過該地區直達南部非洲的貿易線路,顯然也是歷代埃及法老不斷試圖掌控這一區域的重要動機。由此,下努比亞地區的部落成員從古王國時期開始就長期被征召入埃及的軍隊中;中王國時期由眾多要塞保護的尼羅河貿易線路,使法老在與上努比亞地區的貿易往來中獲得了眾多珍稀的原材料;東部沙漠中干涸河道(如阿拉克和卡布卡巴干涸河道)中的近百個金礦則為新王國時期的埃及法老提供了數量龐大的黃金[14](P.233);該時期的埃及人還從努比亞人那里直接購買無花果、椰棗、蜂蜜、葡萄酒等日常食品和飲品[49](P.101)。因此,與努比亞地區的物質交往,不僅滿足了古埃及統治者維護自身權威和統治的需要,同時也促進了埃及自身的經濟發展,并且為提升埃及在整個東地中海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了物質方面的保障。
同樣,從長期來看,努比亞地區的歷史及社會發展也得益于其與埃及在物質及精神層面的交往。涅加達文化III期時,隨著埃及開始向文明時代過渡,臨近的下努比亞文化群A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趨勢。這一方面得益于正在興起的埃及貴族對于象牙、烏木、獸皮等珍稀物品需求的不斷增長,下努比亞地區的部落首領們利用過境貿易積累了不少財富,并促使本地區社會分層變得更加復雜;另一方面,在與埃及人的交往過程中,這些首領也借鑒了埃及人在行政、經濟、宗教方面的創造,最終在尼羅河第二瀑布附近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原始國家”。(33)該時期以努比亞地區的庫斯圖爾為核心的原始國家與上埃及涅伽達、希拉康波利斯、阿拜多斯等地的原始國家在社會層級和經濟結構方面十分類似,參見M. C. Gatto, “The Nubian A-Group: A Reassessment”,Archéonil, Vol. 16, 2006, pp. 71-73。而上努比亞的克爾瑪文明在“古典時期”的崛起則與古埃及文明息息相關。此時的克爾瑪統治者在維持其統治時,依然需要依靠與埃及的貿易獲利及進口的埃及器物和制造技術。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克爾瑪統治者也有選擇地模仿古埃及人的觀念和做法。例如克爾瑪國王也接受了古埃及王權的概念,包括對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對祖先的崇拜;克爾瑪城中的神廟也與古埃及神廟的職能類似,其中就包括負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工作。[50](PP.266-269)最后,盡管新王國時期埃及人曾控制努比亞地區長達500年之久,但當地部落社會的結構并未消失。只要表現得順從和臣服,那些接受“埃及化”教育的部落領袖及其子嗣不僅可以在努比亞和埃及的行政機構中任職,其在本地的統治地位同時也受到埃及人的認可和維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兩者間的“互惠”。[8](P.273)
更重要的是,在埃及與努比亞地區和平或暴力的交往過程中,人為構建的差異和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我”與“他者”在相互影響中也逐漸走向融合。[51]至第三中間期時期(約公元前1085年—前664年),興起于上努比亞涅巴塔(Napata)地區的統治者不但將古埃及文明的要素與自身的傳統進行了有機結合,而且一度同時統治了努比亞和埃及,并與擴張中的新亞述帝國發生了激烈的沖突。[52](PP.133-136)作為深受古埃及文化影響的努比亞統治者,涅巴塔的國王在很多方面都繼承和發展了古埃及人的傳統。現代考古證據表明,位于涅巴塔以南艾爾·庫如(el-Kurru)的王室陵墓中從約公元前10世紀開始就出現了以埃及象形文字符號書寫的人名。從公元前9世紀開始,努比亞國王的陵墓結構都由上層的金字塔和下層的馬斯塔巴組合而成。[8](P.308)至公元前八世紀中期,努比亞國王卡什塔(約公元前760年—前747年)不僅在銘文中使用了諸如“上下埃及之王”“拉神之子”“兩土地之主”等埃及法老常用的頭銜[53](P.45),還將他的女兒培養為底比斯的高階女祭司,并可能以此逐步控制了上埃及地區[6](P.158)。他的繼承人皮亞(約公元前747年—716年)不但模仿新王國時期的埃及法老,公開宣稱自己的王位是由阿蒙神所欽定[53](P.55),還通過一系列軍事行動迅速征服了眾多分散于埃及各地的利比亞統治者,終結了古埃及土地上的“混亂”。而由他開創的第二十五王朝(約公元前747年—前656年)的統治者不僅再次將埃及和努比亞地區融入一個統一的王國之中,還同時任用埃及人和努比亞人共同管理尼羅河兩岸廣大的土地,并試圖從文字、藝術、宗教等方面“復興”古埃及文化。[52](PP.136-137)由此,曾經被征服的“他者”變為了維護秩序世界的“我”,而曾經相互敵視和對抗的兩種文明最終也走向了更大范圍的理解和包容。
- 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其它文章
- 何來勝《李白憶東山(其一)》
- 黃印凱《聽風》
- 崔水良《龍井方向》
- 顧致農《高山流水》
- 徐境懌《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 林浩浩《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