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電影的中國氣韻生成
——以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為例
劉毅青,廖芝林
(南昌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自“萬氏兄弟”于1941年拍攝國內(nèi)第一部長篇動畫《鐵扇公主》開始,由傳統(tǒng)題材改編而來的動畫電影產(chǎn)量非常豐富,收視與口碑屢創(chuàng)高峰,被國際評論認(rèn)為“達(dá)到世界第一流水平,在藝術(shù)風(fēng)格上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中國學(xué)派”[1]。但之后的中國動畫并未隨著國家經(jīng)濟的崛起迅速成長,反而在國外動畫的沖擊下,淪為“洋動畫”的加工廠。動畫人才斷層,加上長期機械地模仿國外動畫,使觀眾已經(jīng)習(xí)慣了以美、日為代表的動畫藝術(shù)風(fēng)格,這也促使中國動畫界一再以國外的動畫模式作為創(chuàng)作標(biāo)準(zhǔn),久而久之國產(chǎn)動畫不僅在制作技術(shù)與視圖觀感上極盡效仿之能事,連內(nèi)容與價值意涵都帶入了美、日經(jīng)驗。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jīng)濟騰飛,文化期待復(fù)興,國產(chǎn)動畫作為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重要一環(huán),開始意識到回歸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對國外動畫長達(dá)數(shù)十年的效仿使得中國動畫界仍然存在思維慣性,即便想要創(chuàng)作獨具民族特色的原創(chuàng)作品,也因無法找準(zhǔn)發(fā)力點而顯得后勁不足,以至于一度呈現(xiàn)出文化焦慮和技術(shù)掩蓋故事的局面。長此以往,獨具想象力、靈動感的動畫電影十分稀有,更不用說觀眾能從中獲得民族性審美感受與精神共鳴。
近年來國產(chǎn)動畫一改90年代以來的發(fā)展頹勢,向著質(zhì)與量齊頭并進(jìn)的方向踏步前進(jìn)。以《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以下簡稱《大圣歸來》)《大魚海棠》《白蛇·緣起》《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哪吒》)為代表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將先進(jìn)的技術(shù)與深厚的文化底蘊相結(jié)合,帶著好口碑與高票房重新奪回本土市場。取材于文化經(jīng)典、神話傳說的國產(chǎn)動畫為何能在市場瓜分漸成定局的情況下開疆拓土?這在于創(chuàng)作者與觀影者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創(chuàng)作者利用動畫電影這種藝術(shù)形式將傳統(tǒng)文化作了當(dāng)代呈現(xiàn),觀影者也從審美感知層領(lǐng)略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然而,這些作品與曾經(jīng)的“中國學(xué)派”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這種距離表現(xiàn)在由動畫作品形式到內(nèi)容所呈現(xiàn)出來的民族藝術(shù)特性與文化價值的缺失:即堅持手繪的中國學(xué)派,形式上將氣韻生動的畫稿作為影片構(gòu)圖設(shè)計的基礎(chǔ);內(nèi)容上,將民族精神之“氣”與民族文化之“韻”相融合,形成獨樹一幟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同時從精神上引起觀眾共鳴。反觀當(dāng)前國產(chǎn)動畫電影,不乏有將“中國”作為一種元素,鑲嵌在外來美學(xué)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觀念之中的表達(dá),無論是形式還是內(nèi)容都很難具備“氣韻”之審美狀態(tài)。本文以近來中外動畫電影的對比分析指出國產(chǎn)動畫(尤其是傳統(tǒng)題材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從形式到內(nèi)容尚未具備“氣韻”的美學(xué)品格,接著以《哪吒》為例,探討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電影生成“中國氣韻”的可能性路徑。
一、氣韻與動畫電影的雙層關(guān)聯(lián)
將氣韻引入動畫電影理論研究,需要對氣、韻二字做分解性理解。“氣”在魏晉南北朝以前多綜合性地指稱為“生命力”,其本身具有貫通性、流動性與形而上的哲學(xué)審美意味。將“氣”引入個體生命,則源自孟子,孟子將道德內(nèi)涵注入氣論思想,“氣”成為個人意志與生理互為表里的一種生命力。后被引用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生命力,正如曹丕《典論·論文》中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徐復(fù)觀先生認(rèn)為“一個人的觀念、感情、想象力,必須通過他的氣而始能表現(xiàn)于其作品之上。同樣的觀念,因創(chuàng)作者的氣的不同,則由表現(xiàn)所形成的作品的形相亦因之而異”[2](P.137)。以繪畫為基礎(chǔ)形式的動畫電影同樣灌注著創(chuàng)作者之“氣”,當(dāng)動畫創(chuàng)作者將“氣”裝載到其觀念、情感、想象力上去,傾瀉于動畫作品中時,“氣”便成了有力的塑造者。“韻”字起用于漢魏之間,最初意與音律相關(guān)。后被用于藝術(shù)的人倫鑒識,指一個人外在流露出來的清逸、放曠等情調(diào),即從“第一自然”進(jìn)而把握神形合一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即“氣韻”的萌芽性說法。顧愷之畫論中所謂“‘傳神’,正是在繪畫上要表現(xiàn)出人的第二自然,而氣韻生動正是傳神思想的精密化”[2](P.150)。“韻”由繪畫引入到文學(xué)領(lǐng)域始于劉勰《文心雕龍》中“異聲相和謂之和,同聲相應(yīng)謂之韻”。所以“韻”無論是從音樂、人倫鑒識、繪畫還是文學(xué)角度,都指向?qū)徝缹ο蟮膬?nèi)在和諧,是與形式對立的,側(cè)重于審美對象內(nèi)在的精神特質(zhì)。動畫電影之韻就是指其“第二自然”,即超脫熒幕之外的精神層面的意義傳達(dá)。
“氣韻”一詞的合成運用最早出現(xiàn)于謝赫的《古畫品錄》,后世多作為畫論出現(xiàn),將氣韻引入動畫電影研究有其理論關(guān)聯(lián)性。“動畫,最早外國人管它叫卡通,但是現(xiàn)在歐、美、日,許多動畫藝術(shù)家也稱它為動畫了。之所以有這樣的名稱,是因為動畫實際上是‘活動著的畫’。”[3](P.40)津堅信之認(rèn)為“在包括實拍電影在內(nèi)的所有影像藝術(shù)中,動畫片最獨特的點是它的影像是運用“繪畫”表現(xiàn)出來的,因此能夠?qū)⒎彪s和多余的信息排除在畫面之外,從而使表達(dá)內(nèi)容更為直接或抽象”[4](P.2)。也就是說無論是手繪動畫還是CG動畫(計算機動畫),均以繪畫為基本形式,且對畫稿有超越寫實的訴求。羅宗強在《論“氣韻”與“神韻”》一文中指出,“氣韻”是畫作與鑒賞家共言,畫作提供客觀條件而鑒賞者在審美素養(yǎng)與能力的前提下提供理解力,是二者的合成。以“氣韻”論動畫電影,同樣在于動畫作品本身與觀眾共同作用下產(chǎn)生的一種審美感受,基于民族精神文化之“氣”是連接創(chuàng)作者、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紐帶。高超、孫立軍以“神韻”引入動畫電影研究,在《“中國學(xué)派”動畫電影中的東方神韻及其現(xiàn)實意義》中指出,“神韻”成就了“中國學(xué)派”在國際上的地位。文中對神韻的定位是“具有動態(tài)生成性的美學(xué)特質(zhì)”,但從傳統(tǒng)美學(xué)來看“神韻”,它側(cè)重于審美對象自身形而上的狀態(tài),不注重與欣賞者之間的溝通。即便萬籟鳴說“我是主張要致力于人物形象特征和神韻的描繪”[3](P.25),這里的“神韻”也是針對畫稿本身究竟應(yīng)該寫實還是傳神這一問題。動畫長片以“第七藝術(shù)”——電影為承載,其傳播媒介的性質(zhì)決定了溝通的必要性,具有流動、貫通特質(zhì)的審美范疇“氣韻”相較于“神韻”有其超越性。
“氣韻,就是宇宙中鼓動萬物的‘氣’的節(jié)奏、和諧。”[5](P.89)宗白華先生以生命精神來詮釋氣韻,進(jìn)而強調(diào)其“動”的美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氣韻”引入國產(chǎn)動畫理論研究,嘗試做這樣的定義:“中國氣韻”是基于民族性精神文化的一種審美經(jīng)驗,它由內(nèi)而外地體現(xiàn)在動畫作品的藝術(shù)美感中,通過創(chuàng)作者、作品、觀者之間的循環(huán)溝通,在共同的“呼”與“吸”之間,以共鳴的方式感受著動畫電影中蘊含著的內(nèi)在韻味。為便于作品分析,姑且從兩條路徑著手:一是形式層,以“氣韻”引入畫稿標(biāo)準(zhǔn);二是內(nèi)容層,主題要以民族文化為背景,根植民族精神之“氣”,創(chuàng)作者與觀影者才能以共鳴的方式烘托動畫電影之“韻”。
二、國產(chǎn)動畫從形式層還未走向“氣韻”
以“氣韻”論動畫電影,一是指畫稿本身呈現(xiàn)出來的“氣韻”。動畫電影的基本形式——畫稿,是為主題與內(nèi)容服務(wù)的,所以不僅對繪畫技術(shù)有要求,還需要創(chuàng)作者在對作品整體理解后將個人觀念、情感與想象力投注其中。
當(dāng)前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的畫稿,受國外動畫影響嚴(yán)重,極力追求高科技特效而忽視文化特性,使得動畫構(gòu)圖缺乏民族獨創(chuàng)性。以“神”“妖”形象為例,作為傳統(tǒng)題材動畫電影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反映在當(dāng)代動畫電影中很難找到本民族的審美定位。《大圣歸來》中,體格健壯、身形魁梧的大圣不再是傳統(tǒng)審美下靈性十足的美猴王,更像是以美國漫威系列為藍(lán)本、以孫悟空為原型塑造的中國英雄。《白蛇·緣起》中身著低胸裝、袒露大長腿的狐貍精形象與傳統(tǒng)審美下的妖怪形象相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無論是神還是妖都是一種無法說明的精神觀念的投射,更注重投射對象身上散發(fā)出來的“氣”,正如《搜神記》中言:“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而不是體型之怪與肉體欲望。這些基于模仿而非在觀念、情感、創(chuàng)造力支配下融入“氣”的動畫形象,是無法呈現(xiàn)神形兼具之“韻”的。由無數(shù)仿作畫面構(gòu)成的動畫電影從形式層也難以呈現(xiàn)其“第二自然”。那么,動畫電影如何在形式上生成氣韻呢?“中國學(xué)派”做出了卓越示范。以“狐貍精”為例,《鐵扇公主》中的玉面狐貍 “倒掛八字眉,高鼻梁,櫻桃嘴,具有國畫寫意畫的風(fēng)格韻味”[5]。片中并未過多袒露玉面狐貍的身體,但無論是對鏡變臉還是曲意逢迎,舉手投足間都讓觀者感受到這是一個賣弄風(fēng)騷的女妖怪。再如《鹿鈴》中的惜別片段,小鹿從見到父母的疑惑與興奮,到對小孫女的不舍,再到分離,整個片段沒有一句對白,全靠鹿的“眼神”來完成情感轉(zhuǎn)換。橢圓形的眼神意味著疑惑與迷蒙,五邊形的眼睛傳達(dá)著驚訝與不安,半圓形的眼神透露著無辜與不舍,最后以月牙形的眼睛傳遞出釋然與深情。中國學(xué)派的創(chuàng)作者們始終看重畫稿的內(nèi)在韻味,認(rèn)為“人物形象的特征和神韻恰如山中之仙,水中之龍,有了它,插圖中的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神采流動,沒有它,人物就會顯得平淡呆滯,黯然失神”[3](P.25)。這里所謂的“神采流動”即創(chuàng)作者運用“氣”將文化觀念、民族情感、想象力等通過畫稿的方式進(jìn)行的具象表達(dá),從而在動畫形象中呈現(xiàn)超脫于畫稿之上的“第二自然”即“氣韻”,由無數(shù)以“氣韻”為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畫稿剪輯而成的動畫電影自然能有生動之美感。
以氣韻融入畫稿的創(chuàng)作理念不僅成就了中國學(xué)派的輝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日本動畫界的創(chuàng)作。日本的第一部彩色動畫長片《白蛇傳》改編自中國神話。日本動畫開山鼻祖手冢治蟲在自傳性動畫電影《手冢治蟲物語:我的孫悟空》中明確表達(dá),《鐵扇公主》中“孫悟空”就是激發(fā)他走向動畫創(chuàng)作之路的根源。當(dāng)代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成功更是離不開其堅持手繪的創(chuàng)作理念:“全世界的動畫都在向 CG 發(fā)展,宮崎爺爺卻與之背道而馳,執(zhí)著于手繪,哪怕短短4秒的動畫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1)參見紀(jì)錄片《永無止境·宮崎駿·夢與狂想的王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914399/。即便是宮崎駿在2018年首次采用CG 技術(shù)制作的動畫短片《毛毛蟲菠蘿》中,就菠蘿出生時的一個轉(zhuǎn)頭動作便做了兩個多月,宮崎駿認(rèn)為動畫師做出來的效果并沒有將菠蘿初次看到這個世界的天真表現(xiàn)出來,“基本上就應(yīng)該比較遲鈍,世界對它而言還是陌生的,這個動作全都是文化”(2)參見紀(jì)錄片《永無止境·宮崎駿·夢與狂想的王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914399/。,這里所說的“文化”便是創(chuàng)作者之“氣”在畫稿中的投注。CG動畫通過數(shù)據(jù)測算固然能做出仿真式的畫面,但技術(shù)側(cè)重于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再現(xiàn),而缺少手繪賦予畫面的藝術(shù)靈動感。基于此,將氣韻引入動畫電影理論研究,它不局限于國別,以民族文化與藝術(shù)特性為要;也不局限于古典審美范疇中形而上的審美內(nèi)涵。它可作為一種方法論而存在,在動畫電影形式層知識性地分解為創(chuàng)作者基于對作品的理解之上,傾注于畫作之上的情感、觀念、想象力,和觀賞者基于創(chuàng)作者之“氣”上,產(chǎn)生“韻”的心靈脈動與氣質(zhì)情調(diào)。所以,國產(chǎn)動畫電影尤其是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電影從形式層引入“氣韻”的審美,無須以一個又一個的懸念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甚至無須過多的對白與音效,僅從一張張氣韻生動的畫稿中就能將觀眾拉入故事情境,這便是“氣韻”在動畫電影形式層中運用的魅力。
三、從“氣韻”的內(nèi)容層觀照動畫電影
將“氣韻”引入動畫畫稿,它從形式層連接著創(chuàng)作者、作品與觀影者,在視圖觀感層將觀者帶入一個特定的民族場域。那么,內(nèi)容層如何走向“氣韻”?這關(guān)涉到“氣韻”在動畫理論中的第二重路徑,也是動畫電影生成“中國氣韻”的根本,即以民族文化之“氣”為精神根基烘托動畫電影之“韻”。主題是氣韻之根,文化為氣韻之魂,而當(dāng)前動畫電影在主題表達(dá)非中國化的同時,也沒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
(一)主題非中國化
拋開審美素養(yǎng)與鑒賞能力,觀眾觀影之后最直觀的感受便是主題。基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主題可以將形式層中“氣”的連接效用發(fā)揮到最大,繼而在無意識層面與觀影者達(dá)成交流。“無意識”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雖然包含著一些難以用言語表達(dá)的,不被社會、道德、審美所接受的人性原始欲望的內(nèi)容,但顧明棟在此基礎(chǔ)上認(rèn)為“文化無意識現(xiàn)象,不僅是一種心理功能和被壓抑的記憶和情感的表現(xiàn),更是一個以不知不覺的方式產(chǎn)生有意識的認(rèn)識、觀念和價值判斷的思想機器”[7]。動畫電影作為新時期文化無意識的載體之一,其價值觀念往往以民族文化為基礎(chǔ)。所以,透過《料理鼠王》《冰雪奇緣》或是漫威英雄我們能從中看到美國文化中對夢想與自由的追求,哪怕是改編自中國題材的《花木蘭》《功夫熊貓》,也折射出美國夢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在日本動畫中,從《懸崖上的金魚姬》到《千與千尋》再到《天氣之子》,對青春之愛的贊頌是永遠(yuǎn)繞不開的情節(jié)。回到中國動畫,早在“中國學(xué)派”時期,動畫電影極力建構(gòu)民族風(fēng)格之外,也在情節(jié)之中融入了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1941年上映的《鐵扇公主》傳到日本后不久便被禁止播放,原因就在于“這是一部體現(xiàn)了反抗精神的作品,粗暴地蹂躪中國的日本軍,遭到了中國人民齊心協(xié)力的痛擊”[3](P.91)。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動畫電影主題就像是無意識層面的一個觸角,通過精神層面的交感,與觀眾無意識層面的文化觸角產(chǎn)生共鳴。
然而,當(dāng)代中國傳統(tǒng)題材動畫電影,在國外藝術(shù)創(chuàng)作觀念與價值意涵的嚴(yán)重侵襲下,民族性主題表達(dá)已十分罕見。2015年上映的《大圣歸來》,看似是對《西游記》的創(chuàng)造性改編,但單線式的故事與個人英雄主義式的結(jié)局,與美國動畫電影《花木蘭》的主題極其相似。同樣以傳統(tǒng)題材作為改編對象,影片中的木蘭替父從軍,在大軍潰敗之際,既無體力又無武力的她以智慧為武裝力挽狂瀾,以一己之力救百姓于危難,一舉成為人人崇拜的民族英雄。這是美國英雄的經(jīng)典模式:心懷夢想的凡人——強烈的戲劇沖突下發(fā)掘個人潛力——怯懦自我與夢想自我的對話——夢想戰(zhàn)勝怯懦——正義戰(zhàn)勝邪惡個體拯救集體。以此模式來套用《大圣歸來》,大圣就是美國故事中的“凡人”,旅途中與江流兒之間的情節(jié)發(fā)展就是“自我與內(nèi)心”的對話,“山妖”作為片中反派,最后落敗于大圣的腳下。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圣歸來》可以說是以中國動畫的形式塑造了一個美國式的英雄。國產(chǎn)動畫的主題受他國價值觀念的操縱,使得以“大圣”“花木蘭”為代表的傳統(tǒng)題材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元素,鑲嵌在國外動畫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觀念與價值內(nèi)涵中,而中國“氣韻”毫無體現(xiàn)。
(二)價值觀偏離本民族文化
當(dāng)傳統(tǒng)題材改編而來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將中國(故事、民俗、建筑等)作為一種元素在使用時,作品本身就成為了在中國傳播他國價值觀念與藝術(shù)審美的流水線產(chǎn)品。長此以往,此類動畫電影既無法引起共鳴,也失去了民族獨特性,實際上是對文化資源的浪費。2017年上映的《大魚海棠》可作為價值觀偏離本民族文化的典型,影片中“責(zé)任、愛與守護(hù)”的主題一直為人詬病,主人公為個人情愛不惜犧牲集體利益的行為被觀眾指責(zé)為“三觀不正”。主創(chuàng)梁旋堅持“故事的原型,包括設(shè)定的原型,這些完全是從中國文化里來的”(3)參見《中國動漫創(chuàng)造自己的風(fēng)格需要一個過程——〈大魚海棠〉主創(chuàng)訪談》,2016年,中國作家網(wǎng)。。誠然,電影中空靈澄澈、隨順自然的浪漫情懷,舍身救人、善惡分明的情義確實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人公為了個人的“愛與守護(hù)”,進(jìn)行損他利己的行為是無法引起觀眾共鳴的根本原因。即主創(chuàng)者只看到電影主題是屬于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沒有將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更大的背景來衡量主題的表達(dá)方式。
以青春之愛詮釋“責(zé)任與守護(hù)”的主題并非中國的文藝傳統(tǒng)。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男女情感是建立在仁義道德、家國情懷之上的。所以在中國古典文藝作品中,愛情始終無法戰(zhàn)勝綱常倫理,多以悲劇收場。中國普世價值中對純粹的愛與性避而不談;但在日本的文化中,它們卻是生命力蓬勃旺盛的象征,且有其美學(xué)淵源。日本自江戶時代開始便“產(chǎn)生了一種以肉體為出發(fā)點,以靈肉合一的身體為歸結(jié)點,以沖犯傳統(tǒng)道德、挑戰(zhàn)既成家庭倫理觀念為特征,以尋求身體與精神的自由超越為指向的新的審美思潮”[8](P.6)。自由情感、身體美逐漸剝離了世俗的粗鄙定義成為美學(xué)范疇“意氣”的重要部分,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持續(xù)不斷地影響著日本人的精神氣質(zhì)及文學(xué)藝術(shù)。在這種美學(xué)傳統(tǒng)下,日本影視文化中對青春純愛的贊頌遵循其文化歷史,自然能引起日本民眾文化無意識層的精神共鳴。動畫電影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突破一切固有的形式,通過想象構(gòu)建一個既超越現(xiàn)實又合乎情理的理想世界。而《大魚海棠》中,椿為了鯤的生命不惜葬送全族利益,這種情節(jié)設(shè)定與傳統(tǒng)文化中舍己為人、克己奉公的思想相悖。
受儒家文化影響,中國人的社會以倫理為核心,追求的是由家到國而天下的人倫溫情,家國情懷才是傳統(tǒng)美學(xué)的主流。有學(xué)者認(rèn)為《大魚海棠》展現(xiàn)出了一種藝術(shù)之光與人性之美(4)參見賀敏、王寧于《電影新作》2019年第2期上發(fā)表的《大魚海棠:人性之美與藝術(shù)之光》,文章認(rèn)為大魚海棠中是對人性真善美的歌頌。,特指椿、湫、鯤三人之間為了愛不畏犧牲的勇氣。誠然,傳統(tǒng)文化中,愛與善是光輝的人性,但這種人性美遠(yuǎn)沒有與家國利益抗衡的能力。面對質(zhì)疑,主創(chuàng)梁旋將電影主題歸結(jié)為人性在善意的驅(qū)使下做出的抉擇,“很多問題你需要做選擇。所以,椿是一個善良的人,她覺得不管怎么樣要把鯤救活。面對生死問題,其他的東西可以往后排”(5)參見《中國動漫創(chuàng)造自己的風(fēng)格需要一個過程——〈大魚海棠〉主創(chuàng)訪談》,2016年,中國作家網(wǎng)。。生命誠然可貴,但在家國利益面前,君子必然心懷“殺身以成仁”的志氣。《大魚海棠》歷經(jīng)12年的苦心匠造,是肩扛重返“中國學(xué)派”之重任的,在考慮無拘束表達(dá)、展示民族藝術(shù)特色的同時,更要站在民族文化的視野下以主題為牽引搭建與觀眾之間的精神橋梁。正如萬籟鳴先生在歷經(jīng)20年的創(chuàng)作實踐后提出的“美術(shù)片走民族化道路是關(guān)系到我國美術(shù)電影藝術(shù)能否躋身于世界美術(shù)電影之林的大問題”[3](P.129)。
四、《哪吒》——生成“中國氣韻”的嘗試
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電影從形式到內(nèi)容尚未具備氣韻之美學(xué)品格,面對這一現(xiàn)狀,我們很難說明中國氣韻具體包含哪些方面,因為它正需要創(chuàng)作者轉(zhuǎn)變視角,從以往經(jīng)驗性的“仿日趕美”上升為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當(dāng)下的動畫作品,從而進(jìn)行理論的發(fā)現(xiàn)與再創(chuàng)造。這一創(chuàng)造首先要求動畫作品要深植民族文化精神;其次,以繪畫為基本形式的動畫作品,其畫稿需洋溢著一股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給人以 “氣韻”之審美感受。最為關(guān)鍵的是從精神層面引起觀者共鳴的同時,還需體現(xiàn)對當(dāng)下社會問題的反思與對人類生存問題的追問。就此而言,《哪吒》做出了較好的示范,為傳統(tǒng)題材動畫電影生成“中國氣韻”提供了一條可能性路徑。
(一)形式層:以哲思入畫境
“氣韻”在《哪吒》的動畫構(gòu)圖中,以一種方法論的形式存在。“氣韻”與“氣化論”的哲學(xué)思想密切相關(guān),萬物根源于氣,氣在哲學(xué)范疇中既指客觀存在的質(zhì)料之氣,也包含主體在內(nèi)的一切生命存在的內(nèi)在活力與精神性情。然而氣不是靜止的,“動”是其根本屬性,且要按照一定的規(guī)律和方向運動才能具有審美特質(zhì),否則會與期望值相悖而出現(xiàn)錯亂。“韻”的本義是音律的和諧,將“韻”作為“氣動”的規(guī)律,動畫構(gòu)圖必然呈現(xiàn)和諧的美感。
以“氣韻”的哲思引入動畫構(gòu)圖,這在《哪吒》的人物形象設(shè)定中最為直接。混元珠作為哪吒與敖丙的原生之氣,之所以仙氣魔氣纏繞、善惡不分是因為吸收的天地靈氣過于駁雜,原始天尊的煉化過程就是循著內(nèi)在規(guī)律將駁雜之“氣”一分為二,在這個過程中,“韻”是天地靈氣運行的規(guī)律,同時也是力求達(dá)到的審美之境。此外,太乙真人與申公豹作為影片中最具顛覆性的形象之一,他們剝離了傳統(tǒng)思維定式中對仙神的形象塑造,而將性情與外在之氣融為一體,這種由“氣化形、形傳神”的動畫形象還有龍王、長生云、夜叉、坐騎等。以“氣韻”入畫境的創(chuàng)作理念在影片中營造出了萬物皆有靈的動畫效果,極具審美張力。
以“氣韻”為方法論是為了呈現(xiàn)“和之美”。回到造型設(shè)定,太乙真人與申公豹作為魔丸與靈珠的派生形象,并沒有帶給觀眾一種善惡對立的情感沖擊,其審丑化的外在與世俗化的性情中和了觀眾思維定式中仙神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增強影片趣味性的同時極大地提升了觀眾的心理滿足感。其次,《山河社稷圖》的情節(jié)設(shè)計,既是中國畫結(jié)合現(xiàn)代技術(shù)做出的動畫實踐,同時也通過動畫的方式展示了山水畫的精神意涵。歷史上的畫山水觀念起源于文人墨客對修身悟道的追求,正如宗炳在《畫山水序》中言:“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于是畫象布色,構(gòu)茲云嶺。”古典文化中,山水具有與哲學(xué)層形而上之道相連通的意涵,所以在傳統(tǒng)觀念中,畫山水、觀山水畫是現(xiàn)實世界體道、悟道的實踐方式。《哪吒》中《山河社稷圖》的環(huán)境由仙術(shù)構(gòu)建且區(qū)隔于世俗,這與哲學(xué)范疇中與形而上之道連通的自然山水相似。再次,哪吒帶有先天魔性,太乙真人令其進(jìn)入圖中就是為了能讓他在象征著天人合一的圖畫世界中修煉,以中和其身上的戾氣。《山河社稷圖》的情節(jié)設(shè)計,預(yù)設(shè)了山水畫在中國文化中的精神意義,而哪吒以“進(jìn)入”的方式修煉自身與古人畫山水、觀山水畫悟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動畫電影“不只要求有合乎情理的故事、有結(jié)構(gòu)完整的情節(jié)和符合藝術(shù)真實的形象,還必須有戲劇劇本和一般影視劇本所沒有的完全屬于動畫的獨特創(chuàng)意和表達(dá)”[9]。《哪吒》在形式層追求“氣韻”之美的過程即動畫的獨特創(chuàng)意與表達(dá),且與曾經(jīng)“中國學(xué)派”所追求的“詩性”“禪意”等古典美學(xué)品格相比有了進(jìn)一步的超越。它從作品整體出發(fā),以現(xiàn)代化的技術(shù)將傳統(tǒng)哲學(xué)與美學(xué)進(jìn)行動畫實踐,使觀影者能從文化無意識層接受這種創(chuàng)作精神的同時又能直接領(lǐng)略到其生動有趣的表達(dá)。
(二)精神氣韻:“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說形式層往“氣韻”美學(xué)靠攏是創(chuàng)作者自覺走向民族化的體現(xiàn),那《哪吒》中基于美學(xué)傳統(tǒng)傳達(dá)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價值內(nèi)涵才是生成中國氣韻的根本。它以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為指導(dǎo),以民族文化為背景,結(jié)合社會現(xiàn)實生成了《哪吒》之精神氣韻。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帶有民族標(biāo)識的精神性產(chǎn)物,其起源與道教內(nèi)丹術(shù)相關(guān)。張伯端在《悟真篇》中云:“一粒金丹吞入口,始知我命不由天。”內(nèi)丹術(shù)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進(jìn)行性命修煉,通過筑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四個階段的苦修,以期打破虛空,成就不死之身。其“天人合一”的理論根源于傳統(tǒng)哲學(xué)“氣化論”,即天地萬物為一氣流蕩之大生命,“氣”既是萬物之源,又是其生命意義的呈現(xiàn),所以人亦能通過修煉內(nèi)丹達(dá)到天人合一之境。從氣化論理解“我命由我不由天”指向雙重關(guān)系:其一,“我命”與“天命”是兩相對等之物;其二,“我命”不僅指自然生命,還包括個體銳意進(jìn)取的精神,且這種精神可作為天人感應(yīng)的媒介。《哪吒》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表達(dá)與傳統(tǒng)思想十分契合。影片中,哪吒之命與天命始終保持平衡姿態(tài),促使哪吒打破魔丸命定論的是民族文化中“忠孝”的倫理觀念。哪吒何以能逆天改命,其力量無非來源于兩點:一是以“孝”的方式對父親用換命符救他這一舉動做出回應(yīng),哪吒深知李靖希望的無非是陳塘關(guān)百姓的安寧(這也是他對百姓的“忠”);二是從集體的認(rèn)可中獲取精神動力,當(dāng)哪吒以“孝”的方式對父母做出回應(yīng)時,百姓們的態(tài)度由偏見轉(zhuǎn)為尊敬,這也將他“逆天改命”的行為推向了更高的精神境界。
具有精神氣韻的主題表達(dá),向來與民族文化緊密相關(guān)。即便是同樣的題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達(dá)的方式也有差異。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以忠、孝為代表的倫理信念遠(yuǎn)優(yōu)先于個人利益;而在西方文化中,基于自由的個體性構(gòu)建更受關(guān)注。以中國故事“花木蘭”為例,中國文化環(huán)境中的花木蘭是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其女扮男裝為父盡孝、血戰(zhàn)沙場為國效忠、勝仗歸來為光宗耀祖。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迪斯尼動畫電影《花木蘭》,弱化了個體對家、國的責(zé)任與犧牲,而將關(guān)注的焦點聚集在木蘭的個人品格之上。所以我們在迪斯尼動畫電影中看到的是一個堅毅果斷又勇于追求真愛的現(xiàn)代女性形象。不同的文化直接影響著動畫電影中的價值觀念。然而中西文化的差異由何而來?梁漱溟曾言“中西文化不同,實從宗教問題分途,而中國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開發(fā)之早”[10](P.109),也就是說,西方文化受宗教影響深遠(yuǎn),而中國人持有的是非宗教的世界觀。受“氣化論”影響,中國自古以來追求天人合一之道,且占據(jù)中國文化半壁江山的周孔教化,滲透式的將祭天、祭祖等神靈崇拜的內(nèi)容變成了維護(hù)國家統(tǒng)治、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思想武器。沒有宗教的束縛,加上儒道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中國人的文化無意識層中始終趨向理性和自信,思想上的緊箍咒是以家、國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而西方歷史長期受一神教禁欲主義的束縛,使其近代開始了思想上的覺醒,覺醒的首位就是要尊重并肯定人的欲望,恢復(fù)個體自由。由此,西方動畫電影強調(diào)的是一種極具自由精神的奮斗觀,其不受道德倫理的約束而更為關(guān)注完善的個體性人格建構(gòu)。“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價值理念之所以能成為《哪吒》的精神氣韻繼而引起共鳴,正因其從中國民族文化的角度契合了當(dāng)代人的深層倫理意識。
(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當(dāng)代意義
哲學(xué)家張岱年先生說:“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是在占統(tǒng)治地位的哲學(xué)思想熏陶下形成的。” [11](P.22)植根于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之上的“自立自強”的精神即為民族的“共同心理”,“我命由我不由天”即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念。所以,當(dāng)懷有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觀眾去欣賞《哪吒》時,本能地會與之產(chǎn)生情感交流,最終達(dá)成共鳴。當(dāng)然,我們說“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句話帶有民族性標(biāo)識,并不意味著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獨有的,實際上任何一個民族的興旺發(fā)展都離不開這種銳意進(jìn)取的奮斗精神。這在美國的動畫電影中表現(xiàn)尤為明顯,漫威系列中的英雄大多是平凡之軀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才獲取拯救世界的能力;即便是以童話為創(chuàng)作題材,公主和王子也要拼盡全力戰(zhàn)勝邪惡的力量才能收獲幸福。動畫藝術(shù)本就是舶來品,中國動畫電影更是在對國外動畫的效仿與學(xué)習(xí)中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受國外動畫技術(shù)與藝術(shù)審美的影響不可避免。然需指出的是,《哪吒》是中國動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做出的巨大突破,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內(nèi)涵深植于民族哲學(xué),從文化無意識的角度結(jié)合社會現(xiàn)實,展現(xiàn)了個體敘事中的中國故事。影片所傳達(dá)的“自強不息、逆天改命”精神與當(dāng)代社會正面價值觀十分契合,可謂是奮進(jìn)中的中國社會群像。
有學(xué)者指出:“當(dāng)下中國動畫創(chuàng)作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升華故事思想,并積極探索民族化表演與現(xiàn)代視聽語言的結(jié)合方式,從而創(chuàng)作出富有時代風(fēng)貌與民族氣韻的動畫作品,接續(xù)動畫‘中國學(xué)派’的民族化道路。” [12]以民族文化為精神根基,形式層自覺向傳統(tǒng)美學(xué)靠攏,足以體現(xiàn)《哪吒》走民族化道路的自律性。而以藝術(shù)化的方式提煉現(xiàn)實,弘揚與當(dāng)下正面價值觀相契合的精神是《哪吒》展現(xiàn)時代風(fēng)貌、生成中國氣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偏見”作為影片的核心問題,創(chuàng)作者并沒有站在某一個角色的角度去批判,而是從不同的角色視角對其進(jìn)行全面展示。哪吒、敖丙看似一正一邪,實則命運共生,他們都受到個體所在領(lǐng)域內(nèi)倫理道德的支配,竭盡所能的完成倫理設(shè)定下的使命,所以觀眾不僅為哪吒逆天改命的努力而感動,也為敖丙肩扛龍族復(fù)興的使命而心疼。這也是為什么疫情當(dāng)前,當(dāng)全國各省市馳援武漢,發(fā)出“把最硬的鱗給你”這樣的聲音時,能引起強大的社會共鳴。此外,影片中還包含著對父母之愛、朋友之誼、師生之情的贊頌,這都與當(dāng)下中國正面價值觀相契合。
當(dāng)今社會,我們贊揚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更提倡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們的民族精神在百折不撓的奮斗中形成,也成為了我們筑夢、追夢的內(nèi)生動力。正如習(xí)近平同志所說:“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人間萬事出艱辛。越是美好的夢想,實現(xiàn)起來越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無論民族復(fù)興之夢,還是個人幸福之夢,奮斗都是筑夢圓夢的底色。”[13]從民族精神文化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道路,生成了《哪吒》中國氣韻的品格,由它帶來的精神激勵與社會價值也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其作為動畫電影藝術(shù)所承載的功能,這正是我們?yōu)槭裁春魡緡a(chǎn)動畫電影走向“中國氣韻”的根本原因。
結(jié) 語
以氣韻引入國產(chǎn)動畫理論研究并非全盤以古典美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作品,過于形而上的表達(dá)極考驗觀影者的審美素養(yǎng),反而將大量觀眾擋在門外。動畫理論中的氣韻要廓舊創(chuàng)新,走民族化道路的同時體現(xiàn)時代氣韻,精神上立足于民族文化,形式上以符合大眾審美習(xí)慣又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熒屏呈現(xiàn)。《哪吒》就是在古典美學(xué)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社會現(xiàn)實,以一種全世界都能讀懂的方式對“中國氣韻”做出的卓然呈現(xiàn)。這既是對中國精神文化與美學(xué)傳統(tǒng)的傳承和發(fā)揚,也是動畫電影在民族思想、美學(xué)熏陶下對動畫表現(xiàn)形式的突破與創(chuàng)造。動畫電影作為文化自信道路上文化與科技融合的關(guān)鍵領(lǐng)域,創(chuàng)作出具有中國氣韻的動畫電影不僅關(guān)系著國產(chǎn)動畫在國際動畫界的地位,也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側(cè)面體現(xiàn)。“世界美術(shù)片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越是具有民族特點的影片,就越是具有世界意義,越能贏得外國的觀眾。”[13](P.130)反觀當(dāng)下國際動畫領(lǐng)域的發(fā)展,IP創(chuàng)作漸成趨勢。由此,傳統(tǒng)題材國產(chǎn)動畫極占優(yōu)勢,因為在本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大花園中,奇卉異葩,蔚為大觀,題材廣博,風(fēng)格多樣,正等待動畫創(chuàng)作者的深入挖掘。而將“氣韻”引入國產(chǎn)動畫理論研究,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為創(chuàng)作出富有時代風(fēng)貌與民族特點的動畫作品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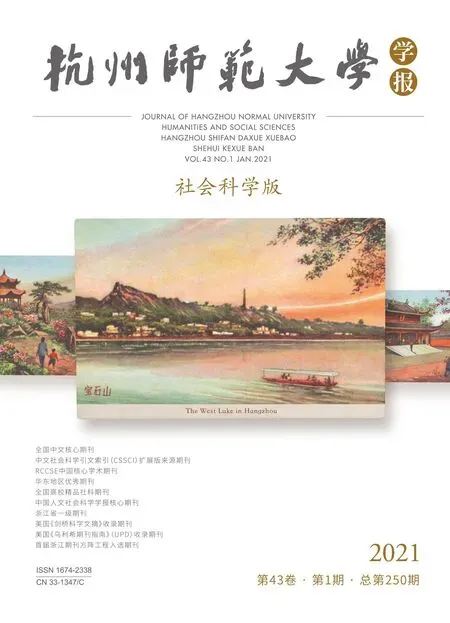 杭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1年1期
杭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1年1期
- 杭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何來勝《李白憶東山(其一)》
- 黃印凱《聽風(fēng)》
- 崔水良《龍井方向》
- 顧致農(nóng)《高山流水》
- 徐境懌《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 林浩浩《寒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