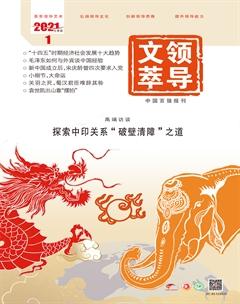“系統過載”,美妄圖以此介入臺海沖突
徐寅
前不久,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研究中心發布第15期“中國戰略視角”系列研究報告——《系統過載:能否在臺海戰爭中分散中國軍力》,對解放軍當前面臨的所謂挑戰和弱點進行分析,并就此提出美國的應對之策。一直以來,對于遏制中國問題,美國政要和智庫大打“臺灣牌”,而對于中國軍力,要么夸大其詞,宣揚“中國威脅論”,要么罔顧事實,把中國軍隊說得不堪一擊。上述報告,美國智庫又會有怎樣的言論?本文僅提供原報告視角與觀點,供讀者批判閱讀。
解放軍的首要任務:對臺作戰
報告認為,數十年來,臺灣一直是推動解放軍現代化的主要動因。解放軍重點發展的彈道導彈、兩棲作戰部隊、空軍等作戰力量,均以臺灣和介入臺海沖突的美軍為目標。解放軍強大的作戰能力,有助于中國實現其在兩岸關系上的近期目標——震懾“臺獨”。
冷戰時期,中國領導人根據可能遭到美國或蘇聯入侵的判斷,多次調整主要戰略方向。自20世紀90年代初,東南沿海——尤其是臺灣海峽——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戰略方向。這標志著一個重大轉變。2008至2016年馬英九主政期間,兩岸關系得到改善,但大陸對“臺獨”和美國干預臺灣的擔憂從未消散。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一直將“臺獨”列為必須阻止的威脅,將統一視為中國的“核心利益”。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2016年當選,島內民眾對統一的支持率持續走低,國民黨作為反對黨勢頭疲軟。這些都強化了臺海作為中國大陸主要戰略方向的地位。解放軍的軍事學說,主要關注幾種能迫使臺灣當局接受“一國兩制”的作戰樣式,如對關鍵目標的聯合火力打擊,封鎖或大規模登島。伴隨作戰概念的開發,是相關作戰能力的迅速發展,如短程巡航導彈和戰術導彈、先進戰機、兩棲部隊及電子和心理戰能力。在解放軍規劃的所有主要作戰樣式中,阻止美國的軍事干預都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因此,中國軍隊強調使用潛艇、轟炸機、遠程反艦彈道導彈,來牽制干預美軍。
中國軍隊的優勢和短板
由于解放軍還承擔著威懾地區對手、維護領土主張、保護海外利益等任務,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臺灣的關注度及資源投入。報告指出,威脅可能會在解放軍應對準備不充分的地區出現,諸如,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60年代的中印邊境沖突及70年代末的中越戰爭,都不是當時中國指定的主要戰略方向。因此,中國的軍事規劃者面臨一個困境:如何在充分做好對臺作戰準備的同時,確保其他國家利益。
報告以其固有思維邏輯分析稱,解放軍仍存在不足,即遠離本土行動的能力較弱。目前,中國軍隊在海外部署的兵力,包括數千名維和官兵、在亞丁灣開展反海盜行動的3到4艘軍艦,以及一座位于吉布提的海外基地。這些部隊能應對小規模的非傳統安全行動,但不足以遂行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如面對美國封鎖,保護中國的海上能源進口。通過推進海上補給線多樣化和建造陸上輸油管道,北京試圖緩解“馬六甲困境”,但如果解放軍不能大幅增強在印度洋地區的海軍存在,中國的對手仍可能在臺海爆發沖突時利用上述弱點。
相比之下,在指揮主要戰略方向上的大規模行動時,解放軍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此類行動涉及來自多個戰區和軍種的部隊。報告指出,任何樣式的對臺作戰,都需要對多個戰區進行廣泛協調。例如,實施導彈和封鎖作戰的部隊將來自東部和南部兩個戰區,登島作戰將需要東部戰區和空軍總部之間協調配合。其他戰區還可能作為戰時備用指揮部,或派遣人員增援東部戰區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報告認為,鑒于臺海沖突涉及不同地區的各類部隊,位于戰區和軍種之上的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可能負責指導對臺作戰。對各參戰部隊的協調工作,事實上很可能通過位于北京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展開。然而,這種作戰決策的集中控制會帶來多種風險。一是,作戰指揮官需要獲得更高層級的授權方能進行戰場機動,這可能貽誤戰機。二是,一旦在另一個戰區出現沖突或局勢升級,專注于處理主要戰略方向上作戰細節的聯合參謀部,可能難以對下級做出有效指導。三是,這種集中指揮模式過于依賴聯合參謀部與戰區部隊之間的可靠通信,戰時,任何干擾都可能癱瘓下級部隊。
美軍如何插手臺海問題
報告也給出建議,目前,美國有關加強臺灣防衛能力的討論,往往集中于向臺北出售防御武器,以及加強美軍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的作戰能力。其實,華盛頓可以制定相應的戰略,使解放軍難以遂行跨戰區作戰,令其“系統過載”。
一方面,應著力加劇中國的“和平困境”。報告建議,在和平時期,美國應制定有效戰略,在其他戰區盡可能地制造麻煩,鼓勵解放軍發展與臺海作戰不相關的能力,以此來削弱解放軍聚焦主要戰略方向的能力。該戰略應尤其注重削弱解放軍地面部隊和東部戰區的作用。為此,美國可采取多種舉措。美國應設法讓中國保持對南海問題的關注,使解放軍投入更多的資源發展海軍和南部戰區,并采購與對臺作戰不太相關的武器裝備。
此外,華盛頓還應加強與中國北部和西部邊境國家的防務關系。例如,美韓以恢復大型軍演等舉動,吸引中國將注意力轉向朝鮮半島,并向北部戰區投入更多資源,加強與印度的合作,將加劇中國對印度挑戰中方領土主張和印度洋航運的擔憂,從而誘使解放軍西部戰區和海軍提出更多的資源需求。此外,與印度等地區大國加強三邊或四邊合作,可引發北京對周邊形成“亞洲北約”的擔憂。
報告提出在整個地區內持續踐行“動態力量運用”作戰概念。該概念由美國前防長馬蒂斯提出,強調美軍軍事行動要變幻莫測,以應對特定戰略的挑戰。此類軍事行動應展現出美軍在中國沿海水域和空域作戰的能力和決心,使解放軍對自身的能力產生懷疑。根據這一概念,美軍將不再被動反應,而是在一系列不斷變化的地點和政治問題上主動展示實力,迫使解放軍在多個方向上保持警惕,例如,可組織航母不定期赴黃海、東海和南海開展行動。
加強美臺防務關系,是針對中國大陸對臺強硬態度做出的“強力回應”,但不應高調升級美臺防務關系。否則,會促使解放軍專注于應對臺海危機。報告建議,美臺軍事接觸應聚焦對提升臺灣防御最為關鍵的領域。
另一方面,沖突爆發后,應增加大陸的決策難度。報告建議,如果威懾失敗,那么美國應試圖延緩解放軍的決策和行動速度,為美軍開赴臺海爭取時間。美國可采取以下舉措:
一是,攻擊中方的指揮和后勤網絡。解放軍對臺作戰很可能由聯合參謀部負責指導,因此,破壞解放軍的統一指揮,是美軍戰爭初期的重點目標。
二是,發動信息戰,在中國高層文官和軍隊之間制造緊張關系。沖突之初,如果解放軍的表現達不到預期,可能導致政府高層文官對軍隊產生懷疑。解放軍的指揮或后勤網絡遭到破壞后,美軍可通過精心發動的信息戰,使中國政府的高層文官了解到相關情況,從而質疑解放軍實現目標的能力,并因中央軍委對相關問題展開調查而導致戰機貽誤。
三是,從多個方向發起常規精確打擊。在臺海戰爭初期,美軍可從在東海和南海活動的海空平臺,以及位于西太平洋縱深地區的設施等多個方向,對大陸目標實施打擊。通過這種分布式作戰,美軍可憑借自身在聯合和兵力協調方面的優勢,攻擊中國戰時指揮體系的弱點。
四是,實施“遠洋”封鎖。美軍還可針對中國的能源進口,威脅實施或實施“遠洋”封鎖。盡管封鎖可能令美國自身的經濟蒙受巨大損失,但可在臺海戰爭的關鍵階段給解放軍中央軍委帶來“意料之外的挑戰”,迫使北京延緩戰爭進程。
(摘自《世界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