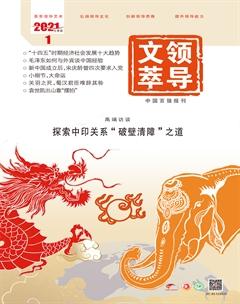殷浩的悲劇
張曉政

在魏晉時期眾多的名士中,殷浩不算最突出的,然而,他在當時所獲得的評價,卻可以說是最高的,甚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
殷浩,字淵源(因唐人避高祖李淵諱,故《晉書》改為“深源”),出身于陳郡殷氏,與王、謝、桓、庾等世家大族相比,其出身不算顯赫。《晉書·殷浩傳》記載,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其擅長解喻《老子》《易經》,因此“為風流談論者所宗”。就是說他年紀輕輕就負有盛名,受人推崇,在眾多玄學名家中亦不遑多讓。有人曾經問過殷浩:“夢見棺材預示著要做官,夢見糞土預示著要發財,這是為什么呢?”殷浩回答:“官位本是臭腐,錢財原為糞土,所以夢見這兩物而升官發財,又有何奇!”此言一出,時人皆深表嘆服,以為至理名言。
或許是因為這番對答過于著名,殷浩雖然名聲在外,但似乎志不在官,他忠實地踐行著自己視官位金錢如糞土的理念。朝廷幾次征召,他都堅辭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安西將軍庾翼接連為其加官進職,他也始終稱病不出,隱居山林幾近十年。就這樣,他辭的官越高,名氣就越大,神秘感也就越多,甚至被人比作管仲和諸葛亮。名士王濛、謝尚專程登門探視,想通過他的進退取舍來預測江東興亡,當猜度他確有避世之心時,相互嘆息道:“深(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意思是殷浩再不出山,天下蒼生可如何是好啊!
永和二年(346),殷浩終于接受朝廷征召,出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坐鎮一方。
殷浩之所以一出仕便獲得如此高位,與當時的政局有莫大關系。時值晉穆帝永和年間,擁兵在外的桓溫羽翼漸豐,不服朝廷節制。由于晉穆帝年幼,朝政由何充主持,何充死后,又由司馬昱(后被桓溫所立,即簡文帝,形同傀儡,憂憤而卒)執掌。司馬昱為牽制桓溫,有意引攬名望正隆的殷浩與之相抗衡。因此,殷浩剛一出仕,便迅速進入了朝廷中樞。
殷浩出仕的這一年,桓溫不等朝廷命令,率軍伐蜀,并迅速平定成漢政權。之后,他挾勝兵之勢,屢次上書要求北伐。永和五年(349),北方因后趙石虎之死陷入混亂,桓溫加緊催迫朝廷北伐。為遏制桓溫坐大之勢,朝廷決定由殷浩主持北伐,并于永和六年任其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永和八年,在經歷了多年內部紛爭之后,殷浩終于領兵開始了北伐征程。
東晉一百余年的歷史,盡管偏安一隅,但從祖逖起至劉裕代晉建宋,亦經歷了多次北伐。然而,由于內部爭權,加之勢不如人,幾次北伐盡管取得過局部勝利,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殷浩這次北伐,同樣是在內有掣肘、外生不測的情形下倉促進行的。在接連遭受嚴重軍事失利之后,殷浩不得不于永和九年(353)匆匆結束了北伐,吞下了又一次北伐失敗的苦果。
殷浩北伐的失敗,對于當時南北分治的格局,或許沒有太大影響;但對于殷浩本人,卻是致命性的打擊。北伐才失敗,桓溫立即向朝廷上書,歷數殷浩“侵官離局,高下在心”“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等行狀,更說他辜負重托,以北伐為名,“外聲進討,內求茍免”“生長亂階,自浩始也”,致使“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總之,殷浩儼然成了禍國殃民、極惡不赦的罪人。因此,縱使不能誅之而后快,也必須將其貶斥流放,“以宣誡于將來”。在桓溫的步步緊逼之下,朝廷不得不將殷浩廢為庶人,并流放至東陽郡信安縣(今浙江衢州)。而殷浩也在兩年之后即永和十二年(356)郁郁而終。
從永和二年(346)出仕到永和十年(354)被貶,殷浩在政治舞臺上只活躍了八年時間。他的政治生命雖已結束,但名士風度卻仍要保持。殷浩被貶后,心雖“愁怨”,卻“不假辭色”,臉上看不出有什么波瀾變化,只是常常用手在空中書劃“咄咄怪事”四字。這也是“咄咄怪事”這一成語的由來。只不過,殷浩心中這份“愁怨”,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承受。殷浩的外甥韓伯曾陪伴殷浩到流放之地,一年后韓伯辭行之日,殷浩送他到江邊,眼望滔滔江水,殷浩情不自禁地念出西晉曹攄的詩句:“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吟罷,潸然淚下,泣不成聲。
殷浩與桓溫,可以說是一對生死冤家。兩人年輕時便雙雙齊名,但彼此都不服對方。桓溫一向輕視殷浩,甚至在殷浩被罷官之后還對人說:“我小的時候,曾與殷浩同騎竹馬,我把竹竿扔到一邊,殷浩卻撿起來繼續玩耍,由此可見,他如何比得上我。”不過,殷浩同樣對桓溫毫不買賬。有一次桓溫曾經咄咄逼人地問他:“你和我相比,誰更出色?”殷浩不慌不忙平靜地回答:“我和你相交一生,還是做我自己更好(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也因此,盡管心知朝廷重用自己乃是為了制衡桓溫,殷浩也不排斥,并斷然拒絕了王羲之勸他與桓溫修復關系的忠告;而桓溫對于殷浩領兵北伐,雖心中惱怒,卻也并不害怕。
事實上,不論是從前的刻意壓制也好,還是如今心態已發生巨變也罷,殷浩對于仕途的牽掛可能比旁人甚至自己所意識到的還要強烈。殷浩被貶后,曾經同他勢如水火的對手桓溫似乎也有些于心不忍了,他向謀士郗超說:“殷浩這個人,德行言談還是頗有可取之處的,如果讓其擔任尚書令或仆射,亦足以為百官楷模。可惜朝廷用非其才,才導致如今的結局。”不僅如此,桓溫還寫信給殷浩,表示有意讓其出任尚書令。否極而泰來,乍落而忽起,桓溫的信無疑在殷浩心中掀起了洶涌波瀾。殷浩迅速回信,“欣然許焉”。但或許是心情太過復雜與忐忑,殷浩對于自己寫的這封回信是一萬個不放心,總擔心其中有什么紕漏或不妥,于是將信折好又拆開,拆開又折好,這樣反反復復幾十回,等他終于如釋重負地將信發出,卻竟然忘了將回信放進信封內。而另一邊,一直等待回音的桓溫發現自己收到的竟是一個空信封,自是怒不可遏,從此與殷浩斷絕往來。圍繞兩人之間的種種恩怨,也自此畫上了句號。
殷浩的失敗,使北伐這面大旗最終還是落到了桓溫手中。殷浩本人也只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一陣微小的漣漪。這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深(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這句話,仿佛成了殷浩悲劇人生的一個反諷注腳。
殷浩的悲劇,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夠正確認識自己。
可惜的是,殷浩本人卻未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深(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這頂帽子固然過于沉重,但事實證明,殷浩本人也沒有將帥之才,因此,當殷浩接受并擔當起北伐重任的時候,其悲劇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更讓人唏噓的是,盡管遭遇了巨大的失敗與恥辱,殷浩仍要竭力維持自己的名士風度,縱使內心痛苦無比,在人前人后也不能有絲毫展現,只有實在無法抑制自己感情的時候才宣泄一二。如果說之前這頂沉重的帽子是別人給他戴上的,到后來,他卻用雙手緊緊地拉住帽帶,不愿、不能也不敢松手。這種戴著面具做人的痛楚,內心深處的無限焦灼和焦慮,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殷浩北伐的失敗,與當時的時代和環境有很大關系,但他的郁郁而終,卻不能不說是自己造成的。
(摘自《月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