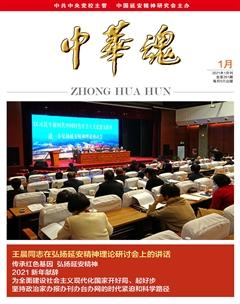自然科學院在延安時期對我黨發展高等教育的有益探索
王民
北京理工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在1986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一書中開頭就寫道:“本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所培養科技人才的理工農綜合性大學——自然科學院,開創了黨領導高等自然科學教育的先河,在中國近代科技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這就非常鮮明地揭示出自然科學院的繼承者——北京理工大學在我黨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
自然科學院于1940年誕生于延安,其前身是1939年5月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誕生背景就是當年的大生產運動。1939年1月初,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號召,要求部隊、機關、學校發展生產。1939年3月3日,中組部副部長兼財經部副部長李富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社論《生產運動》,號召全體人民及黨政軍學全體人員以高度熱忱參加生產運動。1939年4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了《陜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群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從而為大生產運動的全面展開做了提前的準備。
當時李富春同志任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在推動大生產運動逐步深入的過程中深深地感覺到,科技力量的缺失、人才的缺乏是邊區遇到的巨大困難,邊區在生產運動中遇到的種種難題迫切需要有人、有單位來解決。這就需要成立一個科研單位,把科技人才集中起來,提高邊區的科技研究水平,解決實際困難。有了這種設想以后,在1939年3月29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上,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提出成立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建議。中共中央書記處經過認真討論,最后決定:原則開辦。這次會議以后,在李富春同志的具體領導下,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初創工作正式啟動。后來中央決定由李富春兼任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院長,陳康白任副院長,并由陳康白擔任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籌建小組的組長,具體負責研究院的各項籌備工作。
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組建工作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中組部部長陳云和副部長李富春多次討論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人員組成問題,陳云同志對此非常關心和重視,他認為:“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員是后方萬萬不可缺少的,抗戰中需要這樣的技術人員。”所以他專門向中央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央為此明確表示:要求全黨支持這項工作。據當時統計,登記在各機關和部隊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和結業生約300來人,這些科技干部一部分上抗日前線了,還有一部分分散在陜甘寧各個部門。為此中共中央組織部要求各機關、學校和部隊將本單位的科技干部推薦給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并通過中央組織部向國統區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他們采取各種辦法,動員一批科技人員及青年學生到延安參加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工作。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隸屬于中央財政經濟部,辦公地點設在財經部邊區銀行,當時共有近30名行政和研究人員,延安歷史上第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員隊伍就此組織起來。
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以后很快就顯示了其特殊的科技推動作用。首先在延安難民紡織廠的恢復生產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紡織廠在搬遷到永寧山以后迅速恢復了棉紡、毛紡和被服生產,初步緩解了延安軍民的穿衣難題。然后研究院的同志們又來到了離延安城不遠的安塞溝槽渠振華造紙廠,在這里建成了臨時大本營,著力解決延安的造紙難題。在工作過程中,研究院的華壽俊、王士珍夫婦發明了用馬蘭草造紙的新方法,試驗成功后推廣到延安各造紙廠,從而生產出大量的馬蘭草紙,滿足了整個邊區的用紙需求。朱總司令曾為此寫詩贊嘆道:“農場牛羊肥,馬蘭草紙俏。”
在1939年12月25日至31日,黨中央責成中央財經部召開自然科學討論會,對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進行深入討論。參加討論會的除了自然科學研究院的科技人員外,還有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軍事工業局以及其它部門的科技人員,可以說這是陜甘寧邊區第一次科技的盛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大家形成決議:建議黨中央在邊區創辦高等學校,把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招收邊區和敵占區有一定文化基礎的進步青年到自然科學院學習,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培養邊區的科技人才。
這次討論會以后,194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將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李富春仍然擔任院長,陳康白任副院長。此后,自然科學院的籌建工作全面展開,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原有人員成為了自然科學院的第一批工作人員,1940年5月以后,自然科學院在延安杜甫川的基建工作已初步完成,并著手開始了招生準備工作。
從上述自然科學院成立過程來看,這所學校是根據我黨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實際工作的需要和邊區對科學技術和人才培養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首先具備了其政治的先進性。在這之后的實際辦學過程中,每一步都顯示出這所學校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照黨對學校的指引、對人才培養方向的指引,不斷調整自身的發展方向,致力于黨在延安時期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實踐和探索。
二
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學院正式開學。這一天,邊區政府的領導、中央財經部的領導,以及延安各干部學校都派來代表參加開學典禮。朱德總司令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發來賀信,賀信中寫道:“團結起來,艱苦奮斗,掌握科學,為革命斗爭服務。”
自然科學院當時設有大學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此時全院師生不過百余人,其中專業教師20余人,政工人員及行政干部10余人,大學部只有23人,高中部有40余人,初中部40余人。學校開學以后,副院長陳康白赴三邊兼任三邊鹽業處處長,學校的具體工作主要由教務長屈伯川同志負責。大學部開學后統一上基礎課,學一些數學、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外語、政治課等,沒有具體分系教學,打算到第二年再學習專業知識,學制兩年。初中部由延安小轉來的幾十名學生和一些干部子女、進步青年組成,主要補習基礎文化課,學制一年半。高中兩年畢業,并規定高中偏重實際,課程中有農、林、牧、畜科的實際內容,沒有原則性的生物科。應該說此時的自然科學院還并未形成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
1940年12月,徐特立接任李富春擔任自然科學院院長。1941年1月副院長陳康白卸任三邊鹽業處處長,返回學校與徐特立共同負責學校的全面工作。徐特立與陳康白都是湖南長沙縣人,而且徐特立與陳康白有師生之誼,徐特立在陳康白求學、留洋、回國后奔赴延安等人生的關鍵時期,都給予了陳康白極大的幫助和指引。現在師生二人聯手建設這所黨領導的紅色學校,彼此之間就多了很多默契和信任。徐老雖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但主要致力于文化普及、師范教育工作,在正規大學特別是技術學院的興辦上,沒有更多的經驗。而陳康白畢業于廈門大學,因學業優秀留校任教,后又在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在學術上頗有成就。1933年至1937年,陳康白遠赴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化學院任研究員。1937年陳康白為了民族抗戰而回國,在徐特立指引下奔赴延安,來到延安以后成為了當時延安的大科學家。也因為這些,在自然科學院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向上,徐老更多地鼓勵陳康白放手去干,為邊區的科技人才培養闖出一條新路。
陳康白回到自然科學院以后,為了加強學生的理論基礎,提高學生的科學能力,開始了他一直設想的學校正規化建設。陳康白參照國統區及國外大學的辦學模式,經過和大家反復的討論研究,在徐老的支持下對自然科學院的教學安排和學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大學部由兩年改為三年,并分系組織教學,第一年只是補足中學時普通程度的不夠,二三年才開始專門化教學。1941年年初以后,大學部相繼成立了地礦系、化學系、物理系、生物系,培養本科生。高中部改為預科,學制兩年,待兩年后經過考試升入本科。初中部改為補習班,學制三年,主要學習一般中學課程。
自然科學院所有本科生第一學年的主要課程是普通物理、普通化學、高等數學、工程制圖、外語、政治課等基礎課程。由于很多采用的都是國統區正規大學的教材,如談明的《化學》,達夫的《物理學》和克蘭威爾的《微積分》等,因此都有相當的難度。有的老師還采用英文原文教材,講課時也用英語。由于課程安排很緊,進度較快,這讓有些同學吃不消、跟不上,就調到預科班去了。當時學校通過各種方法從邊區外搞到不少實驗儀器、設備、藥品等,一些基本的化學物理實驗也能做。有的課程一時找不到教材,教師們就自編教材和講義,克服困難,保證教學計劃的順利進行。從當時情況來說,雖然各個系的師資力量差距較大,但從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上來看,自然科學院大學部的教學質量已經接近于國統區的大學水平,只是在教學實驗設備方面差距較大。陳康白為了讓自然科學院成為一所真正的大學,一方面絞盡腦汁地挖掘師資力量,制定教學方案,準備教材,添置教學設備;另一方面還要頂住壓力,說服他人,讓自然科學院按照正規大學的模式勇敢地闖下去。也就是從1941年年初到1942年這近兩年的時間里,自然科學院大學部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學校辦學注重理論基礎,并強調在堅實理論的基礎上與實際相結合,為“抗戰建國”服務,培養邊區急需的科技人才。1942年7月22日《解放日報》以《馬雅堂先生參觀自然科學院》為題報道當時西北聯大文學院院長馬雅堂先生參觀自然科學院的情況:
午后參觀自然科學院的物理、化學、生物等系及各種儀器、試驗標本、工場等,馬先生在兩處參觀后深感興趣,當時曾稱:“外面的人以為在延安的人們,總是在開會,做政治斗爭。而不知這延安同樣也有文化,也還有科學。”馬先生又稱:“這種儀器和各種標本等,在大后方各大學里,也是很難得的。”并稱“回去以后當告慰在大后方的自然科學界,使他們也能知道延安的真相。”
由此報道可以看出,當時的自然科學院在高等教育的辦學領域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和規模。
三
要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不是每一個人都贊成把自然科學院辦成正規大學的,從學校創建一開始,就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在激烈地交鋒。這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看問題不同的角度等因素造成的。一種聲音認為:邊區的科學設備太差,教育資源太少,學生和教員的水平不高,辦不好大學。不能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甚至有人認為邊區自己培養不了技術干部,應當到大后方去想辦法,要更多地動員國統區的科技人員到邊區來。另一種聲音認為:邊區的人才和物質條件雖不如大后方,但比起抗戰初期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有了一部分儀器設備,也有了基本的師資和生源。而且,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邊區各方面的支持,有革命的創造性、斗爭性,有良好的風氣和艱苦奮斗的決心。邊區的教育事業決不能向困難和落后投降。而且,我們不能只顧眼前,我們辦大學一方面為邊區培養急需的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為將來的新中國培養建國的人才。共產黨人絕不能長期停留在科技落后的狀態中,不能只注重培養專門技術人才,要培養學生有較為雄厚的理論基礎,能夠有自主科學研究的能力。雖然現在是有一些困難,但就是再難,也要創造條件戰勝困難,按照教育的規律培養出共產黨人自己的人才,就像李富春同志說的:培養“革命通人,業務專家”。
這兩種聲音一直伴隨著自然科學院的發展和建設,其間也遇到了不少來自各方面的阻礙和挫折。但是以徐特立、陳康白為主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敢于面對困難和非議,遵從科學的發展規律,強調基礎理論在科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積極探索正規化辦學,探索用高等教育的理念為今天的邊區、將來的新中國培養又紅又專的科技干部,這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愈發顯得難能可貴。
徐特立在1941年9月24日《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怎樣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一文中說道:
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學,無法跳越其必然階段,人類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據它的必然性來支配。我們今日來談科學建設,首先是對于科學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會變成無原則的主觀主義和無原則的實利主義者。
徐老首先從科學的發展上闡述了自然科學研究的必然規律。然后就提到了自然科學院正規化建設的必要性:
科學家還應照顧到實際條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沒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礎,幻想提高科學是不可能的。如果當抗戰開始時,在邊區即提出學校正規化,不需要軍事和政治的訓練班,是非實際的。如果當沒有中小學生的時候就提出建立自然科學院也是非實際的。但是有了起碼的條件,只等待著條件完全具備,而不愿意在已有條件下加以創造,只知道天定勝人,而不知道還有人定勝天,同樣是錯誤的。可以說,空想主義和實利主義對于科學建設同樣是有害的。
最為關鍵的,是徐特立明確支持陳康白關于正規化辦學的理由,在文中說道:
(學校辦學)過早地專門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創造。在邊區新的環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學基礎不夠的專門家,想把科學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陳康白力主倡導正規化辦學是徐老支持的結果,這話并不全面,就當時延安的氣氛而言,無論是中央高層,還是在各主流輿論中也都是在積極倡導科學自由,希望提高科技水平來改變邊區落后的經濟狀況。這可從當年《解放日報》的兩篇社論為例來說明問題。因為根據我黨宣傳工作的慣例,《解放日報》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起到了黨的喉舌作用,無論社論的起草者是誰,它所發表的社論一般都代表著最高層的意見,也引導著當時的社會輿論導向,實際上也是一種工作方針指南。
在1941年6月10日的《解放日報》社論中曾這樣寫道:
在邊區的經濟建設上,技術科學,尤其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不論是改良農牧,造林,修水利,開礦,工廠管理,商業合作,都必須有專門的知識技能,必須受科學的指導。祖傳的老法已經不行了,必須讓位給科學。自然科學家在這里有最廣泛的活動地盤。……
這樣說,我們歡迎科學藝術人才,就只是為要他們來反映邊區,宣傳邊區,幫助建設邊區嗎?不,我們并不把科學藝術活動局限在啟蒙與應用的范圍,我們同樣重視,或者毋寧說更重視在科學藝術本身上建樹,普及和提高兩個工作,在我們總是聯結著的。雖處在戰爭環境,但估計到戰爭的長期性,中國地大的條件,以及抗戰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必須同時進行,我們不應把科學藝術上的提高工作推遲到抗戰勝利以后。特別是新中國文化的根基尚淺,而民族文化的程度又還十分不夠,我們的責任尤其重大。我們要急起直追,要有決心做長期研究和長期講學工作。要大大發揚樸素切實的埋頭做學問的作風。
我們面前放著的科學藝術的領域如此廣闊,任務如此重大,所以我們雖然已經有不少的科學藝術人才聚集在邊區,然而還覺得必須有更多更多的人來和我們共負艱巨。我們忠實地遵守著列寧的遺教:“沒有在許多不同的范圍中與非共產黨員成立聯盟,任何共產主義建設的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何況,我們今天所著手的還只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國事業。
在1941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社論中曾這樣寫道:
首先我們現在提倡自然科學,是為著改進邊區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技術,發展與提高邊區物質的生產。因為目前邊區在農業和工業所采用的技術是非常落后、原始的,生產量(特別是日常工業用品的生產量)還不能夠滿足自給的要求;另一方面邊區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地區,地下埋藏有很多工業原料,如石油、煤炭、鐵礦等,現在有些寶藏雖然已經開發,但是也有不少仍舊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們要發展抗日的經濟建設,進一步鞏固邊區,保證長期抗戰的物質供給,相當提高人民物質生活的水平,就必需提倡自然科學。……
這就是我們提倡自然科學的最主要的意義。
從這里,可以看出,這樣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全邊區人民以及全國人民之抗戰利益的。提倡自然科學正是發展抗日的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到堅持長期抗戰與增進人民幸福這個目的所必須的、所應有的步驟。
同時,也可以看出,在事實上,也只有在堅持長期抗戰與增進人民的幸福的總目標之下來提倡自然科學,才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
從以上兩篇社論中就可以看到,自然科學院正規化辦學的做法是符合延安當時政治環境的,是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重視自然科學發展 的光輝典范。
自然科學院在正規化辦學和發展高等教育道路上的有益實踐,不僅得到了社會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勵,也在自然科學院的很多教員中引起共鳴。生物系的教師康迪在1942年9月25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寫道:
我同意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經濟建設有密切的聯系,但我不同意辦自然科學院僅僅是解決邊區經濟建設的眼前問題。自然科學院與邊區的職業學校不同,它是中央領導而帶有全國性的東西,它的方針,就不是只看到今天而看不到明天,不是只看到邊區而不能看到邊區以外。如果只是為了目前邊區的經濟建設,不是直接痛快的立刻下工廠做一個工人,就是改為訓練班三個月畢業。如果是要領導技術和把握我黨自然科學前途的話,必須系統的正規的來學習,所以從科學的立場與現有的條件,辦一個自然科學院,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可能。當然是很困難的,但是完備是草創來的,一棵大樹是一粒種子萌芽起來的。我們要拿外國的或國民黨的大學標準比自然科學院,就會成為不實際的教條主義者。但是問題的解決,不在于科學院本身。譬如人力問題,科學院就不能像外面辦大學那樣方便去聘請教員,因為我們不雇傭勞動,人員的調動是有組織的統一支配。物力問題,在封鎖的環墻中,確有困難,但并不絕無辦法,并且在已有的條件來爭取與創造是必要的。
生物系的教師林山也在1942年9月25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關于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教育與工作的我見》,文中指出:
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必須是:除了一面要滿足目前急切的但有限的需要外,一面更要準備著適應到將來發展擴大局面的要求。這兩方面我認為是一致的,不是脫節的。因為在物質條件完備的環境之下執行進步技術,固要懂得較高科學基礎的人材,尤其是在物質困難環境之下,改進落后的技術更要懂得較高科學基礎的人才來創造新的條件和改造舊的條件,不然我們更無法解決許多困難問題。在目前,那就是一種既照顧到目前又照顧到將來的理論與實際一致的科學與技術的教育與研究工作,雖然要把這一工作做得好,我們現有的人力物力還差得很遠,但是如果我們不利用現有的起碼條件(已有一些人才、學生與物力)來培養起一個粗具規模的科學與技術的教育與研究的統一機構——科學院,使得一方面,造就具有一些既可以掌握各部門科學與技術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又可以解決目前的實際問題的基礎的(不是成熟的)干部,一方面可累積許多寶貴的工作經驗(盡管是錯誤的與失敗的)來健全與充實這個統一機構。如果我們不這樣,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一基礎工作,那么,在我們大量需要進步的科學技術來建國的日子,我們將沒有堅強完備的科學技術上的組織中心和支撐骨干,我們就沒有把握來決定科學與技術發展的方向,我們就沒有能力來組織將來更廣泛的科學技術界的力量為我們服務,甚至可能因這一漏洞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和影響。
從康迪和林山兩位教師的文章來看,自然科學院發展高等教育進行正規化建設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得到了延安很多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因為大家知道,只有掌握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在科學的道路上穩步向前,這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規律,這是被太多實驗證明過的普遍真理。
正是由于當時延安上下有這樣一個尊重自然科學、發展自然科學的良好環境,再加上徐特立、陳康白等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胸懷責任,攻堅克難,勇于探索,才使得自然科學院在正規化辦學、發展高等教育、理論聯系實際為邊區服務的道路上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那一時期,自然科學院的師生們在延安的多種刊物上發表了眾多的科普文章,許多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陜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牛頓及其時代背景》《注意邊區的水土保持工作》《談談洋芋》等。另外,自然科學院還結合自身的科技優勢開辦了許多校辦工廠,直接滿足了邊區多方面的生產生活需要,如1941年6月,自然科學院開辦了玻璃廠,建起了酒精廠。1941年8月,自然科學院生物系的師生們和光華農場職工共同努力,試驗成功了“青貯草”,并向邊區各地普及,解決了牲畜冬季的飼料問題,使整個邊區的養殖業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所有這些,都證明了自然科學院在興辦高等教育的同時,還成為了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一個人才培養的紅色熔爐,在這個熔爐中,人人身上都有一股干勁,人人身上都有一種責任。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學知識,想方設法地為邊區解決實際問題,創造著他們心中理想的新生活。
2020年北京理工大學迎來了建校80周年校慶,2021年我們又要迎接光輝的建黨100周年慶典。在共和國日益強大的今天,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人民為早日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我們在此追憶學校在延安時期光榮的辦學經歷,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讓人們體會到我們黨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在尊重知識、發展科學、培養人才的道路上所做出的豐功偉績。作為自然科學院的繼承者——北京理工大學,在繼承和弘揚光榮革命傳統的同時,更應該擔負起時代的重任,為祖國的強盛、為民族的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