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球搬進實驗室
張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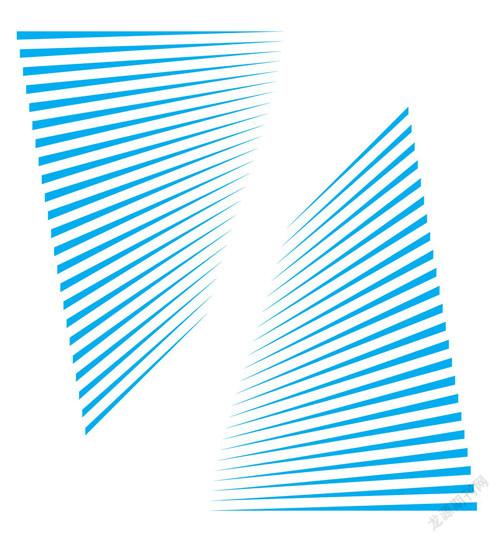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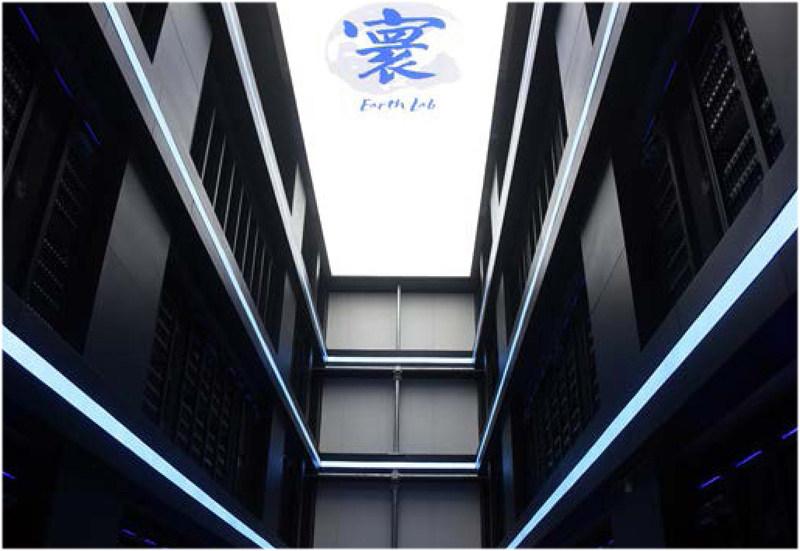
2021年6月23日,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地球系統數值模擬裝置”——寰(EarthLab)在北京懷柔科學城東區落成啟用,這是我國首個研制成功的地球系統數值模擬大科學裝置。
“寰”是我國首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規模及綜合技術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的專用地球系統數值模擬裝置。2018 年經國家發改委批復,項目全面開工建設,其核心軟件是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自主研發的地球系統模式,集成耦合了包含大氣、海洋、陸面、植被生態、大氣化學、海洋生化、陸地生化在內的7 個分系統模式,能夠模擬大氣圈、水圈、冰凍圈、巖石圈、生物圈的演變規律,對地球的過去進行反演、對現在進行觀察、對未來進行預測。這套軟件一天可以計算出地球的大氣圈、水圈、巖土圈、生物圈等多個圈層10 年左右的變化。
在位于北京密云區的懷柔科學城東區,“寰”地球模擬實驗室的科普展廳已經開放。展廳中懸掛著直徑3米、清晰度達到5K 的LED 球形屏,裝置模擬實驗的部分結果會通過球體進行可視化直觀展示。裝置還可以模擬出不同時期天氣氣候、海洋環境、大氣環境、極地海冰、植被生態的情況,時間跨度達到數百年。
“寰”的計算機硬件平臺“硅立方”也已正式亮相。“硅立方”是一個大型機房,2—4層的超級計算機,一層為存貯裝置。以往的超級計算機都是一層平鋪的,這個是垂直放置的,所以叫硅立方。如此一來不僅占地面積小,最遠的兩個機柜之間的距離也小,數據傳輸就會更快。寰的建成將服務于應對氣候變化、生態環境建設、雙碳愿景目標、防災減災(如天氣預報)等國家重大需求,為國際氣候與環境談判提供有力的科學支撐。
地球科學為何要用上數值模擬?
20世紀60年代,國際科學界提出地球科學應該怎樣發展的問題。當時世界上有兩種科學研究方法,一種是理論探討,即理論分析、邏輯推算,理論分析需要實驗去驗證,驗證正確了才是可靠的理論;另一種是實驗分析。
但對地球科學,做實驗是不現實的。做實驗有很多詳細條件,例如需要保證實驗室環境和真實環境一致。要做關于地球的實驗,需要滿足的條件太多,沒辦法做到全部符合。此外,做實驗有時候要破壞一個“環境”,像生物科學可通過解剖來實現,但對全地球卻沒法開展類似實驗,因為地球環境不容破壞。
當時正值電子計算機出現,于是國際上提出了第3種科學研究的辦法,叫數值模擬,或稱數值試驗。
簡單來說,這一方法就是提出一個理論后,要驗證這個理論對不對,就需要建立數學模型并利用電子計算機求解,把經過理論模型計算后的數值和實際對比,來證明理論預測是不是和實際的一致。如果這個數學模型與實際相符,就可用來做模擬實驗。
地球系統模式軟件是復雜的巨系統模型,需要多學科緊密聯系,這是大氣科學、計算科學和計算機技術融合的一個典型。
地球系統模擬裝置是如何工作的?
地球上氣態的空氣、液態的江河湖海、固態的山石冰雪、不斷演化的生命體……這些紛繁萬物,可以簡單地歸為五大圈層:大氣圈、水圈、冰雪圈、巖石圈、生物圈。千百年來,人們在感受著各個圈層中物候變化的同時,也在對自然界的經驗進行總結。
基于科學的進步,科研人員已經能夠總結出一部分自然變化的物理規律,并用數學公式將其定量地表述出來。進一步將這些數理方程編寫成計算機代碼,就得到了對應于各個圈層的代碼集合,也就是常說的“模式”。例如大氣模式本質上就是大氣運動方程、連續方程、熱力學能量方程的代碼集合。
科技人員首先構建起描述單個圈層的模式,再通過“耦合器”將各個獨自運行的模式有機地聯合在一起。耦合器就像一個龐大工廠的交換車間,其中進行著各圈層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從而把大氣、海洋、陸面等模式耦合起來,在最大程度上模擬出自然界的演變過程。
得到了數字化的“地球”后,輸入某一時刻的觀測數據,在超級計算機進行大規模的數值計算,科研人員就能夠推演地球不同圈層的變化,由此重現地球的過去、模擬地球的現在、預測地球的未來,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地球試驗”。
“寰”如何預警極端天氣、助力防災減災?
在全球變暖的氣候背景下,過去30年間有關極端天氣事件及其對人類生活影響的報道不斷增加,這些事件包括強臺風、高溫、暴雨、干旱和寒潮。這樣的極端天氣事件的空間尺度是幾千米,時間尺度在幾小時內。要想準確捕捉這些天氣過程,就需要提高模式的空間分辨率,但也意味著必須承載隨之增加的龐大計算量。
配備高性能計算機硬件的“寰”建成后,利用更加精細和完善的地球系統模式,“寰”能夠捕捉更全面的預測信號,以提高我國防災預警水平、增強防災減災能力。
全球尺度的模擬實驗,是一項具有寬廣時間尺度的超級計算工程。“寰”采用的國產芯片為超復雜的地球系統模式提供了超給力的算力支持。其1分鐘的算力相當于全球72億人同時用計算器不間斷計算4年。
“硅立方”數據庫擁有80PB的存儲空間,可以裝下約13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數據,用來保存各個圈層的觀測及模擬資料。
“寰”如何為碳中和提供支撐?
自19世紀末以來, 地球的平均地表溫度上升了約1.18℃,大多數變暖過程發生在過去40年里,其中2016年和2020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兩年。全球溫度的升高意味著人類將面臨更多極端災害天氣:極端熱浪、極端干旱、極端強對流天氣以及更為猛烈的臺風襲擊等。
2015年,《巴黎協定》提出讓所有國家共同致力于實現相同的長期目標:加強對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威脅做出全球性回應,到21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溫升保持在相對于工業化前水平2℃以內,并為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1.5℃以內付出努力。
無論是1.5℃還是2℃溫升目標,均是基于全球先進的地球模擬實驗室計算出來的——將模擬的“地球”放進實驗室里,看看在不同二氧化碳排放量造成的全球變暖下,“地球”上自然系統的響應程度如何,最終確定一個合適的溫升目標。這涉及對全球碳源匯收支的科學評估,對碳氮循環過程、生物地球化學過程的全球尺度模擬,是一項具有寬廣時間尺度的超級計算工程。
我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寰”具有過程完善的地球系統模式以及面向地球科學的高性能計算機系統,能夠實現高精度的數值模擬計算,以應對寬廣時空尺度上的氣候系統的非線性計算。
“寰”能夠更全面地考慮地球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特別是與地球生態系統和生物地球化學過程的相關模擬及其與氣候系統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生態- 氣溫-二氧化碳濃度-碳排放量”的清晰關系,對溫室氣體核算、未來升溫預估提供有力的模擬支撐。
比如陸地系統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碳匯之一,其作用在制定“碳中和”決策中不可忽視。“寰”使用的新版全球植被動力學模式能對全球植被分布和碳通量進行準確的模擬,從而更準確地把握陸地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的響應和反饋。
因此,“寰”的建成和使用將為我國制定“碳中和”決策和實現“1.5℃溫升目標”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寰”如何應對污染?
“寰”這個“地球模擬實驗室”內有區域高精度大氣污染模式分系統,該分系統擁有國內首個全球多尺度嵌套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大氣復合污染傳輸模式。
它能夠模擬大氣中化學成分的排放、擴散、對流、化學轉化、干濕沉降等過程,模擬臭氧、氮氧化物等5種氣體和沙塵、海鹽、硫酸鹽、硝酸鹽、黑碳、有機碳等氣溶膠成分的時空變化。“寰”能夠為沙塵暴、臭氧、酸雨、灰霾、重金屬沉降等大氣環境污染研究保駕護航,進行空氣污染預報預警、評估污染調控,并進一步探究氣候- 污染排放- 區域空氣質量相互作用。
它還采用全球多尺度嵌套,空間分辨率跨度從幾百千米到幾千米,同時具備重金屬模擬能力、耦合源識別與追蹤技術等特點,能夠做好污染物“溯源”分析。“寰”模擬的中國區域的空間分辨率提升到了3千米,高分辨率模擬融合觀測數據,能夠大大地提高我國大氣污染預測預警的準確性。
目前其他國家是否有地球模擬裝置?
“寰”處于什么水平?
一些發達國家已建成專門的地球模擬裝置,從而在全球氣候和環境變化問題的外交談判中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地球模擬器Cheyenne(夏延)主導IPCC氣候變化預估試驗報告的撰寫等,長期世界領先;日本地球模擬器京K 推動日本地球模擬水平從世界中等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歐盟正在投資10億歐元建設“活地球模擬器”。
“我們要用自己的計算數據作為氣候與環境領域談判的依據,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慶存說。如今,我國面向地球系統專用數值模擬裝置的建成將有利于扭轉這一局面。
我國地球系統數值模擬裝置的大氣模式水平分辨率(實為網格距)可達25千米,海洋模式可達10千米,能夠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寰”建設過程中有何挑戰和突破?
據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朱江介紹,“寰”的建設突破了一系列難題,提前一年半落成啟用,實現“早建成、早服務”。
當時初步設計方案中采用英特爾處理器,在得知我國國產芯片取得重大進展后,為了應對潛在的卡脖子風險,建設單位的科技人員在3個月內對國產芯片進行了密集測試,在兼容性、計算效率等一系列方面取得突破,果斷決策,采用了國產芯片的技術方案。
“國產芯片自主可控,同時也需要不斷優化,當時我們沒日沒夜進行了大量測試。”他說,采用國產芯片避免了因為卡脖子問題導致的裝置建設延期等嚴重后果。
大氣所研究員周廣慶稱,“寰”的軟件本質是用計算機求解最復雜的方程,科研人員在軟件并行計算上也做了大量工作,為此科學家付出了極大的辛勞。
“寰”未來有何計劃?
據中科院大氣物理所介紹,“寰”預計2022年通過驗收后正式建成,實現開放共享與服務。作為懷柔科學城北京國家綜合科學中心首個落成的大科學裝置,將在原始創新、人才匯聚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推動北京市氣象信息產業園的建設。
大氣物理所研究員周廣慶介紹,目前這一裝置更集中在地球表面圈層的研究,因為人類生活在地球表面。未來將耦合更多分系統,研究“入地上天”的深層地球,會把地幔熱力過程、大陸板塊漂移、地震、臨近空間大氣等系統考慮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