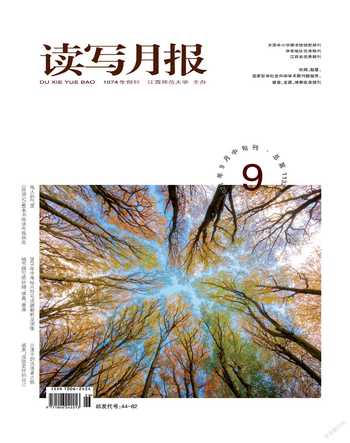沙漠中的流浪者之歌
1.內容簡介
《撒哈拉的故事》是一部作品集,記錄了作者三毛因一本地理雜志的吸引而走進撒哈拉沙漠的點點滴滴。分為七個篇章——《沙漠中的飯店》《結婚記》《娃娃新娘》《我喊荷西回來!回來!》《沙漠觀浴記》《愛的尋求》以及《芳鄰》。
書中主要描寫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時的所見所聞,與當地相識朋友的故事,每個故事都透露出這個隱忍女子對生活的熱愛和面對困難的堅定。三毛用自己的心去適應、關懷這片大沙漠,在她的筆下,那些撒哈拉沙漠的人和物變得豐富多彩。三毛以一個流浪者的口吻,輕松地講述著她在撒哈拉沙漠零散的生活細節和生活經歷:沙漠的新奇、生活的樂趣、千瘡百孔的大帳篷、鐵皮做的小屋、單峰駱駝和成群的山羊。書中無論是荷西把粉絲當作雨來吃,還是他們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婚禮、去海邊打魚、白手起家建立他們沙漠上最美麗的房子,都滲透著彼此間濃濃的溫馨的愛意。“來了沙漠,不經過生活物質上的困難,是對每一個人在經驗上多多少少的損失”,三毛如此說道,而她在生活中也確確實實踐行了這點。物質生活上的極大匱乏并沒有使三毛生出一絲半點的氣餒,她更愿意把這當成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經歷。她永遠像棵不知疲憊的勁草,欣欣向榮。“生命的過程,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青菜豆腐,我都得嘗嘗是什么滋味,才不枉來走這么一遭啊!”人,生下來被分到的階級是很難再擺脫的,但總有這樣一群不安分的生命流浪者,跳出蕓蕓眾生的生活軌道。三毛也以現代文明的視角觀看古老文明與沙漠舊俗,并生動地記錄著她在沙漠的所見所聞,讓我們看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態,領略了異族文化和風土人情。
三毛用細膩的筆觸,真實、詳盡地記下了眾多事件,細節明了,情感真摯,洗凈了夸張復雜的華麗修辭,取而代之的是樸素自然、詼諧幽默的字句,令人耳目一新、忍俊不禁。
2.推薦理由
《撒哈拉的故事》一書中沒有華麗的辭藻,有的只是平實的描述,卻有一種讓人心安的力量。書中描述的撒哈拉沙漠上的異域風情與三毛夫婦在沙漠上情趣十足的生活讓人神往,如此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普羅大眾心中都有卻未有勇氣去追尋的夢。那樣的文字,讓人百讀不厭,難以釋卷。
只因在《美國地理雜志》上看到一組撒哈拉沙漠的照片,她便如感應到前世的鄉愁般義無反顧地奔赴那里去生活。試問這樣的率性,世間幾人能有?
夢,是人心所向的魂牽夢縈,它是戴望舒的雨巷,是惠特曼的草葉,是舒婷的雙桅船,也是三毛的撒哈拉。
3.經典書摘
沙漠為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要瓜分西屬撒哈拉時,此地成了風云地帶,各國的記者都帶了大批攝影裝備來了。
他們都住在國家旅館里,那個地方我自然不會常常去。那時我們買下了一輛車(我的白馬),更不會假日留在鎮上。

恰好有一天,我們開車回鎮,在鎮外五十多里路的地方,看見有人在揮手,我們馬上停車,看看那人發生了什么事情。
原來是他的車完全陷到軟沙里去了,要人幫忙。
我們是有經驗的,馬上拿出一條舊毯子來,先幫這個外國人用手在輪胎下挖出四條溝來,再鋪上毯子在前輪,叫他發動車,我們后面再推。
再軟的沙地,鋪上大毯子,輪胎都不會陷下去。
弄了也快一小時,才完全把他的車救到硬路上來。
這個人是個通訊社派來的記者,他一定要請我們去國家旅館吃飯。
我們當時也太累太累了,推托掉他,就回家來了。這事我們第二天就忘了。
過了沒有半個月,我一個人在家,聽見有人在窗外說:“不會錯,就是這一家,我們試試看。”
我打開門來,眼前站的就是那個我們替他推車的人。
他手里抱了一束玻璃紙包著的大把“天堂鳥”。另外跟著一個朋友,他介紹是他同事。
“我們可以進來嗎?”他很有禮貌地問。
“請進來。”
我把他的花先放到廚房去,又倒了冰汽水出來。我因為手里托著托盤,所以慢步地在走。
這時我聽見這個外國人用英文對另外一個輕輕地說:“天呀!我們是在撒哈拉嗎?天呀!天呀!”
我走進小房間時,他們又從沙發里馬上站起來接托盤。
“不要麻煩,請坐。”
他們東張西望,又忍不住去摸了我從墳場上買來的石像。也不看我,嘖嘖贊嘆。
一個用手輕輕推了一下我由墻角掛下來的一個小腳踏車的銹鐵絲內環,這個環蕩了一個弧形。
“沙漠生活,我只好弄一點普普藝術。”我捉住鐵環向他笑笑。
“天啊!這是我所見的最美麗的沙漠家庭。”
“廢物利用。”我再次驕傲地笑了。
他們又坐回沙發。
“當心!你們坐的是棺材板。”
他們唬一下跳起來,輕輕翻開布套看看里面。
“里面沒有木乃伊,不要怕。”
最后他們磨了好久,想買我一個石像。
我沉吟了一下,拿了一只石做的鳥給他們,鳥身有一抹自然石塊的淡紅色。
“多少錢?”
“不要錢。對懂得欣賞它的人,它是無價的;對不懂得的人,它一文不值。”
“我們——意思一下付給你。”
“你們不是送了我天堂鳥嗎?我算交換好了。”
他們千恩萬謝地離去。
又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在鎮上等看電影,突然有另一個外地人走過來,先伸出了手,我們只有莫名其妙地跟他握了一握。
“我聽另外一個通訊社的記者說,你們有一個全沙漠最美麗的家,我想我不會認錯人吧!”
“不會認錯,在這兒,我是唯一的中國人。”
“我希望——如果——如果不太冒昧的話,我想看看你們的家,給我參考一些事情。”
“請問您是——”荷西問他。
“我是荷蘭人,我受西班牙政府委托,來此地承造一批給撒哈拉威人住的房子,是要造一個宿舍區,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歡迎你隨時來。”荷西說。
“可以拍照嗎?”
“可以,不要掛心這些小事。”
“您的太太我也可以拍進去嗎?”
“我們是普通人,不要麻煩了。”我馬上說。
第二日,那個人來了,他拍了很多照片,又問我當初租到這個房子時是什么景象。
我給他看了第一個月搬來時的一卷照片。
他走時對我說:“請轉告你的先生,你們把美麗的羅馬造成了。”
我回答他:“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人,真是奇怪,沒有外人來證明你,就往往看不出自己的價值。
我,那一陣,很陶醉在這個沙地的城堡里。
又有一天,房東來了,他一向很少進門內來坐下的。他走進來,坐下了,又大搖大擺地起身各處看了一看。接著他說:“我早就對你們說,你們租下的是全撒哈拉最好的一幢房子,我想你現在總清楚了吧!”
“請問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問他。
“這種水準的房子,現在用以前的價格是租不到的,我想——漲房租。”
我想告訴他——“你是只豬。”
但是我沒有說一句話,我拿出合約書來,冷淡地丟在他面前,對他說:“你漲房租,我明天就去告你。”“你——你——你們西班牙人要欺負我們撒哈拉威人。”他居然比我還發怒。
“你不是好回教徒,就算你天天禱告,你的神也不會照顧你,現在你給我滾出去。”
“漲一點錢,被你污辱我的宗教——”他大叫。
“是你自己污辱你的宗教,你請出去。”
“我——我——你他媽的——”
我將我的城堡關上,吊橋收起來,不聽他在門外罵街。我放上一卷錄音帶,德弗乍克的《新世界交響曲》充滿了房間。
我,走到輪胎做的圓椅墊里,慢慢地坐下去,好似一個君王。
4.精彩書評
撒哈拉沙漠的天堂鳥
——讀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佚名
著名作家桂文亞曾這樣寫道:“欣賞一篇文章,不只為喜愛其中充滿生趣的情節,而是因為產生‘人世’的共鳴。”作家三毛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無疑具備了讓人產生“人世”的共鳴的魅力。
這部作品收錄了作家三毛的《沙漠中的飯店》《懸壺濟世》《娃娃新娘》《天梯》等十四篇作品,為我們生動地描述了她在漫漫黃沙的撒哈拉沙漠里極富色彩與浪漫的沙漠生活,以及她對生命意義、靈魂歸依的探索與思考,帶領讀者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心靈之旅。
閱讀這部作品,我們會體會到字里行間透露出的無法消釋的孤獨感,這也是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存有的與外部世界的疏離感。
作者在《極樂鳥》一文中寫道:“我羨慕你說你已生根在那塊陌生的土地上。我是永遠不會有根的。”又寫道:“一切的感覺就是那樣無助,好似哪兒都不是我該定下的地方……我已沒有自己的地方了。”從這些語句中,我們不難讀出作者那份難以言明的孤獨。
于別人言,這份孤獨源于個體與外部世界之間無法打破的隔膜。我們每一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都具有與他人不同的獨立的思想。然而外部世界又具有另一套普適的思想、輿論體系。于是,個體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不可調和與沖突,使之無法進行正常的交流,進而產生隔離感,也即孤獨感。而這,在當今這個舊有價值理念被摧毀,新的價值體系卻未建立的迷茫時代,愈加明顯了。物質文明不斷地向更高的層次發展,精神文明卻無法與其同步向前。外在的世界越來越喧囂,個人的內心世界不斷受到侵襲而愈顯空洞與蒼白,人們愈加感到焦躁不安,而這份無法言明的孤獨感也愈加強烈。《撒哈拉的故事》道出了人們心中的迷惑,表達了人們內心的痛苦,也因此與人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而于作者三毛而言,這份孤獨感或許更深入骨髓。
在別人眼中,這個“令人費解的、拔俗的、談吐超現實的”奇怪的女孩(文學院教授胡文清對三毛的印象),常常因為她特立獨行的思想、與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而成為眾人眼中的“怪女孩”,被“另眼相看”,成為眾矢之的,因此她的孤獨感愈加強烈。在閱讀《撒哈拉的故事》時,這種空虛的孤獨感常常縈繞心頭,也讓我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個體的思想與傳統的普適的思想之間的平衡問題。
同時,《撒哈拉的故事》折射出了點點智慧之光,它對人生意義的探索和生活價值的思考,帶有一定的哲學色彩。
作者對生命似乎有種超乎生死的淡然。生命在她看來,就是起點與終點的一個循環、一個輪回。在《撒哈拉的故事》中她寫道:“我們不斷期待再來一個春天,再來一個夏天,總以為盼望的幸運遲遲不至,其實我們不明白,我們渴求的只不過是回歸到第一個存在去,只不過是渴望自身的死亡和消融而已。”在她看來,生與死既是起點又是終點。正如她所說的:“人生是一場大夢。”
或許也正因為這樣,世俗的名利在她眼中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活著已花力氣,再要付出努力的代價去贏得成功的滋味我是不會的。我不要當那個連苦味都沒有的空杯。”所以,她辭去工作,離開家人與朋友,踏上前往撒哈拉沙漠的旅行,來到那片遼闊的沙漠,開始自己另一段的人生。
否定了外界對人生意義的定義,她在《撒哈拉的故事》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我來說,旅行的真正的快樂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過程。遇見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種種的困難,聽聽不同的語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樂。雖說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況世界不只是一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奇妙的現象累積起來的。我看,我聽,我的閱歷就豐富了。”于她,生命的意義在于行走,在于其過程。或許如她常常說的:“我喜歡流浪。”
三毛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一種命運抑或稱為不可知力量的神秘色彩。無論是《懸壺濟世》中沙漠居民對巫術的崇拜,還是《死果》中對咒術的神秘力量的描述,都營造了一種異國的神秘氛圍。
如《沙漠軍團》中所說的:“不記得哪一年,我無意翻到一本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那期書刊里,正好介紹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釋的,屬于前世回憶似的鄉愁,就莫名其妙,毫無保留地交給了那一片陌生的天地。”她將自己與撒哈拉沙漠之間的不可解的情結歸于一種前世回憶似的鄉愁,是命運的安排。而這種難以言明的心情,大概就是她所寫的“我只常常感到那種冥冥中無所依歸的心情,卻說不出到底是什么”。命運于她,是一種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可是,不同于他人將失敗、挫折、不得志歸結于命運的無情,三毛更多的是將每一次的嘗試,每一次的向前歸結于命運在冥冥中所做的決定,引導她走向她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因為對文字的特殊情感,她始終未放下手中的筆,將自己的所知所感都訴諸書;因為對撒哈拉沙漠的莫名的眷戀,她來到了那片異國的土地,與丈夫荷西相愛結婚。每一次的向前,是宿命,也是選擇。
“我是一個像空氣一樣自由的人,妨礙我心靈自由的時候,決不妥協。”
“……你要贏得你的人生,你就不能患得患失,是不是能夠贏,你盡可去賭,只要不把生命賭掉,可以一賭再賭。”
在我看來,《撒哈拉的故事》就是一本講述生命歷程的書——途中會感到孤獨,卻決不放棄對自由的追求和對生命的熱誠。一路旅行,撿拾灑落在沿途的生活光點,找尋自己的存在意義與生命本源。
這便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它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視角去看待生命,新的態度面對人生——健康,豁達,灑脫不羈。
我始終堅信:一本優秀的書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和歷史的沉淀。甚至,在經由歲月的錘煉后,它會更顯光彩。《撒哈拉的故事》1976年的出版橫掃了整個華文世界,并因此掀起了一股流浪文學的熱潮。而今,《撒哈拉的故事》再次出版,不但并未因時代的變更而被淘汰,反而愈加歷久彌新、芬芳香醇。生活在擁擠、喧囂的都市的人們,從《撒哈拉的故事》中感受到自由的快樂和生命的熱度,找到了共鳴,填補了空白,為其單調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動力。
5.關于作者
三毛,中國臺灣著名作家,英文名ECHO,1943年3月26日出生于重慶,浙江省定海縣人。本名為陳懋平,1946年改名陳平,筆名“三毛”,1964年進入文化大學哲學系,肄業后曾留學歐洲。婚后定居西屬撒哈拉沙漠加納利群島,并以當地的生活為背景,寫出一連串情感真摯的作品。1981年回到臺灣,曾在文化大學任教,1984年辭去教職,專職從事寫作和演講。1991年1月4日,三毛用絲襪上吊自殺身亡,終年48歲。她生前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廣為流傳,生平著作和譯作十分豐富,共有24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