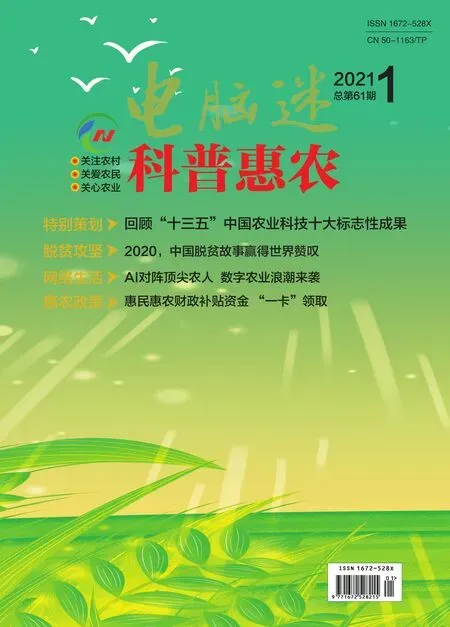鐵山沖的楊梅
本刊通訊員 遠山
時常遺憾自己沒有農村生活經驗,到現在也分不清很多植物。大約也就是這一遺憾,很喜歡在假期往鄉下跑。上個周末,幾個朋友相邀,去了一個叫鐵山沖的地方。這個地方估計哪一張地圖上也找不到,最大特色就是很少有人在那里居住。
下高速后,路就極不好走,汽車開得顛顛簸簸,但外面的景色卻宜人起來。當然,宜人的景色不外乎山清水綠,但對在城市生活慣了的人,見到這些,免不了有點振奮。
車子進入山路,變得七彎八拐,不知到了何處。問開車的朋友,答曰此處叫鐵山沖。
進入鐵山沖時已是下午4點多。這時應是人多的時候,但這里非常僻靜,幾乎見不到人,向眼睛圍過來的是層層綠色,遠山不高,種滿了樹。我正看著,車子陡然一個急彎,離開山路,上了個坡道。我很詫異,難不成這里是此行終點?
坡道上一溜小屋,里面走出一個山民。見到車來,臉上露出笑意,像是認識這車一樣。
他果然認識,開車的朋友姓曾,是本地人。下車后與山民說話。當地話我聽不懂,下車打量周圍。
那山民和曾姓朋友說完話后,曾姓朋友過來告訴我們,之所以到這里來,是這里有楊梅樹,料想我們很少見到,就先帶我們來看看。
那山民屋前便是一棵楊梅樹。
我平時偶吃楊梅,從未去想楊梅就是結在樹上。這棵樹不高,很低的地方就開始分杈,樹葉在空中占據很大的空間。我仰頭望去,在一層層樹葉間,果然垂下一顆顆紅色楊梅。我伸手摘下一顆,拿手里觀看。楊梅是什么樣子我當然知道,但這顆卻是我平生第一次從樹上摘下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左右看看,看有無水可來洗洗。那山民告訴我,從樹上摘下的楊梅,當即可吃,用不著洗。我不習慣吃水果不洗,但這時卻感覺一種天然就在楊梅身上,于是入口便食,這楊梅一咬,只覺得兩頰酸得厲害。曾姓朋友笑了,說吃楊梅,不能吃紅的,要吃紅得發黑的才甜。他把剛摘下的一顆深紅發黑的楊梅遞我,我再吃,果然唇齒生津,甜得很。
山民開始爬樹,一步步踩著樹杈上去。這對他是很經常的了,但爬樹于我卻大大不同。我爬樹的經歷得追溯到童年了。幼時喜歡養蠶,每到養蠶時節,我就去我們城市里河邊的桑樹林,爬樹摘葉。后來不養蠶了,也就沒再去過桑樹林,那桑樹林現在早已不在了,我也再沒爬過樹。
山民爬到樹上,曾姓朋友也開始爬樹。兩人各站一樹杈,將密葉中的楊梅一顆顆摘下,放入手中的塑料袋中。我在下面看了,心里不禁躍躍欲試。忽然感覺自己也一下子變小了,仿佛回到了童年一般。于是我也開始爬樹,但終究不敢爬得太高,總擔心樹杈會被踩斷,但那山民和曾姓朋友卻爬得很高,看他們體重,明顯要超過我,但我還是不敢往高處踩。
楊梅樹樹葉很密,隨便撥開哪里,都是一顆顆楊梅垂下。我有了經驗,就只揀深紅發黑的楊梅來摘,隨摘隨吃,乃至滿嘴都是涼涼的汁水。以前從未一口氣吃這么多楊梅,更不用說是親手從樹上摘下的如此新鮮的楊梅了。我也不由仔細打量手上的楊梅,忽然感覺這些平時熟悉的楊梅其實真是很美,就那么圓圓的一顆,卻長出渾身柔軟的刺來,似乎每一根刺都飽含著纖細甜味。這便是大自然的神奇了,它把很多東西長在自己身上,卻沒有一樣相同,因此每一樣都等著我們去認識,即使是很普通的東西,都有一種美等著我們去凝視。就像此刻,我感覺楊梅的美也許就在于你平時根本不覺得它美,但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和你相遇時,你卻能感覺到它的生機和自足。它也的確自足,曾姓朋友說,它自足到能擁有“天然的綠色保健食品”這一稱謂。
對“保健食品”,我向來不以為然,總覺得多了無數道人工,是否“保健”,已難說得很了。但楊梅樹倒真可以提高土壤肥力,調節微環境氣候,記得以前舟山、象山的馬尾松線蟲危害后,很多植物成片死亡,當地改用楊梅綠化荒山,成效顯著。那山民告訴我,楊梅樹易于栽培,經濟壽命長,生產成本明顯比其他水果低,他這一顆樹,一年能產幾百斤楊梅。我很是驚訝,因為這棵樹不大,但居然可結出如此多的果實,著實令人難以置信。
沒過多久,山民和曾姓朋友都摘了滿滿一袋楊梅下來。曾姓朋友看著我說,你是詩人,可否寫一首詩?我笑笑未答,腦中倒是想起宋代詩人平可正寫楊梅的詩來:“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
醫學典籍《本經逢原》里也說:“楊梅,能止渴除煩,燒灰則斷痢,鹽藏則止嘔喙消酒。但血熱火旺人不宜多食,恐動經絡之血而致衄也。其性雖熱,而能從治熱郁,解毒。”就從這點來說,葡萄和荔枝,還真就比不過楊梅。
回到車上,曾姓朋友說,晚上請我們喝自己釀造的楊梅酒。他說楊梅酒能通氣活血,清熱解暑,能治腹瀉,特別是我們坐了幾小時車,喝楊梅酒能消除疲勞。看來楊梅的功用還真是不少。
我回頭望去,眼前雖不是滿林楊梅,但畢竟楊梅滿樹,真不枉來這里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