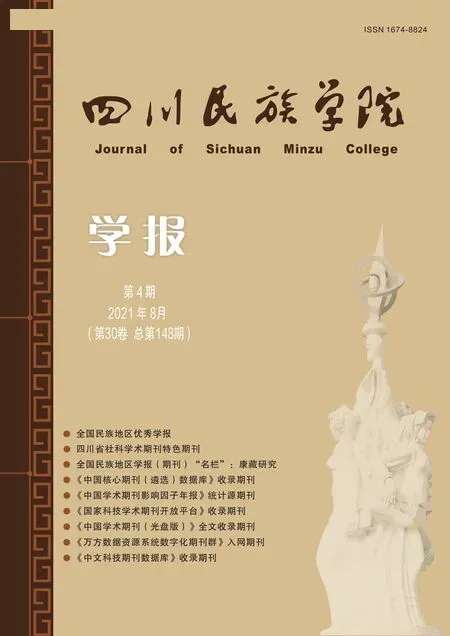18世紀清廷對川藏古道的使用與經營探微
公秋旦次
(西藏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
18世紀初,西藏地方的局勢搖擺不定,動蕩不安。第巴桑結嘉措(1633-1705)與蒙古和碩特后裔拉藏汗(?-1717)之間在藏爭權奪利,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巴被拉藏汗攻殺,西藏地方由蒙古和碩特拉藏汗控制。此時,準噶爾部的新首領策妄阿喇布坦(?-1727)對拉藏汗所控制的西藏野心勃勃。策妄阿喇布坦借衛拉特蒙古各部間互通婚姻之俗,通過策妄阿喇布坦其女與拉藏汗長子聯婚成親之事,蠱惑了拉藏汗。康熙五十五年(1716)準噶爾部策妄阿喇布坦從伊犁遣兵,由將軍策零敦多卜(?-1736)率領6000兵,經西藏阿里北部,挺進前藏,次年抵達拉薩北方當雄。準噶爾軍從當雄開始與拉藏汗軍隊交鋒,策零敦多卜率領的準噶爾軍隊勢力極強,很快戰勝了拉藏汗屬下的蒙藏軍隊,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底拉藏汗被準噶爾追軍所殺。西藏地方又被準噶爾部占據。準噶爾部在藏擾亂三年之久(1)1717年底至1720年9月。,期間清廷為“驅準保藏”,經青藏單一路線(2)即唐蕃古道路線,此為清軍第一次進藏路線。,派軍進藏,但此次清軍進藏未能征剿準噶爾部軍隊。西藏那曲一帶,清軍被準軍圍困多久后,最終全軍覆沒。[1]122-123為此,朝中議論紛紜,康熙皇帝(1654-1722)思來想去,最終決定從青藏和川藏兩條路線同時行進,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最終獲勝。18世紀初期至18世紀20年代間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最終促成了清廷既通過傳統的青藏路線進軍,也首次把川藏古道作為軍事要道使用。(3)史稱清軍第二次進藏。那么,關于清朝在川藏古道上開拓一條軍事要道的緣起、過程以及結果等方面已有前輩學者研究,如石碩和王麗娜的《清朝“驅準保藏”行動中對由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一文中從1717年準噶爾擾藏和清軍第一次進藏失敗開始,并就清廷開拓川藏驛道采取的措施、步驟以及沿著川藏古道進藏的過程做了比較全面而細致的分析,最后對清廷在建立川藏驛道上取得的成就和戰略意義作為了總結。[2]136-146另外,趙心愚的《清康熙雍正時期川藏道訊塘與糧臺的設置及其特點》一文以清代早期有關西藏的地方志《四川通志》以及乾隆初年成書的《西藏志》等為一手材料,對清代康雍時期川藏驛道的訊塘和糧臺設置的時間、若干特點與性質職能方面作出了專門的探討。[3]在前輩的研究基礎上,本文以18世紀初期蒙藏關系史作為歷史背景,對川藏古道成為軍事要道和官方驛道的歷史進程做了簡要梳理,從而力求認識其道路本身的戰略優勢,并對清廷通過川藏古道的積極使用和經營來實現控制康區和直接治理西藏的史實加以闡釋。
一、川藏古道成為軍事要道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通過蒙古親王羅卜藏丹津的疏報,第一次接到關于準噶爾部襲擾西藏的確切消息,[4]198次年2月底又接到拉藏汗信使的救援報告[4]203。不久之后,清廷決定從西北兩路進攻準噶爾部的根據地伊犁,這時又接到拉藏汗已經被準部殺死的消息,這時清廷終于把矛頭指向在藏擾亂的準噶爾部策零敦多卜率領的軍隊上。康熙皇帝“今即令色楞統率軍兵征剿西藏”[4]204,同時令西寧總督額倫特也率隊與色楞一同進藏。兩位將軍先后從西寧入藏,但兩者意見不同,進攻策略方面略存分歧。康熙五十七年七月(1718年8月)色楞和額倫特的軍隊抵達那曲一帶,兩位將軍不久會合。與準部激烈交戰,清軍因對藏北地區“不曉天時地利”[5],后勤被準軍襲擊,加之二將軍令不一,導致清軍遭到準噶爾部軍的圍困,進退兩難,軍糧緊缺,九月二十九日(11月21日)色楞將軍被俘虜,額倫特將軍戰死。[6]36
清廷為“驅準保藏”第一次派軍進藏時,被準噶爾部軍打敗。準噶爾部軍的挑戰,震驚朝廷。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1718年12月3日),皇帝封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禵(1688-1755)為撫遠大將軍(4)康熙皇十四子胤禛,雍正初年改為允禵。,決定讓允禵率軍入藏。十二月十日(1月31日)允禵從京城前往青海,在途中知曉,朝廷已決定除了青藏路線以外,另從四川至藏開辟進軍一線(5)即從川藏古道進藏。,并要求允禵軍中的護軍統領噶爾弼派往西南四川,與四川巡撫年羹堯一同辦理軍務[6]21。與此同時,大將軍允禵于五十八年三月(1719年4月)在西寧塔爾寺會見第六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要求協助南路進軍,遂同青海蒙古郡王察罕丹津分別派人去理塘、昌都、碩般多,攜帶轉世靈童的安民告示,宣傳清軍南北路入藏“收復藏地,以興黃教”的意義,[6]30-31從而得到了康區沿線民眾的順從和支持,為川軍進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西寧派往四川的噶爾弼授為定西將軍,率領兵丁進藏。[1]128
允禵在西寧辦理諸多善后事宜以及朝廷繼續觀察藏中事態的需要,朝廷決定當年(1719)不進藏,令允禵暫停西進。[4]225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下旬(1719年11月)至五十九年正月下旬(1720年3月),清廷為進藏之事,用了整整四個月的工夫,終于確定了進藏方案:清廷決定從南北路分別進藏,以北路作為主力軍,為獲得青海眾蒙古的聯合出兵,在塔爾寺的第六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將一同送往西藏,決議再撥兵增至一萬二千名[1]128;由護軍統領噶爾弼從打箭爐率川軍二千七百人入藏,經理塘、巴塘、芒康、察雅至昌都,從云南調兵進藏的三千名在昌都與川軍會合,共五千人從昌都前往拉薩。
北路的主力軍四月二十二日(5月28日)自西寧啟程,護送第六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同時,八月中旬(9月)到達那曲一帶,與策零敦多卜率領的準軍交鋒。至于南路,康熙五十八年(1719)噶爾弼將軍駐扎于打箭爐的同時,按照年羹堯的建議向打箭爐以東的理塘、巴塘等地逐漸擴張并設立驛站。[4]213這時從成都至打箭爐已經設立較為完善的驛站。噶爾弼率領的川軍抵達昌都,滇軍三千名與川軍會合,從昌都類烏齊分兩路進入拉薩;一是經類烏齊、結結樹、冰噶、三達奔卡(6)結結樹、冰噶即今那曲比如縣白嘎鄉,藏語地名為rgyas xod pad dkar;三達奔卡即今比如縣羊秀鄉的桑達寺,藏文寺名為bsam mda’bon dgon;從地域路線來看文中部分沿途地名被忽略或未記載,路線的順序應是類烏齊、丁青、江達(今索縣東南)、沙丁(今邊壩縣西北)、白嘎、三達奔卡、拉里。、拉里;二是類烏齊、落隆宗、碩般多、達隆宗(邊壩)、沙工拉、魯工拉、拉里,從拉里一同進入工布江達、墨竹工卡,[7]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1720年9月24日)抵達拉薩。[8]335沿川藏古道的軍隊早于北路主力軍,途中無阻,順利進入前藏。此次清廷把川藏古道首次作為朝廷的軍事要道,且順利入藏,為清廷帶來了巨大好處,在“驅準保藏”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清軍第二次進藏獲勝的歷史經驗與戰略意義來看,清廷為控制康區及治理西藏地方必將繼續重用川藏古道。
二、軍事要道和官方驛道的一體化
康熙六十年(1721)撫遠大將軍允禵“聞進藏二將軍(7)此處二將軍為應是從青海入藏的平逆將軍延信和從打箭爐入藏的定西將軍噶爾弼。,大約十一月初頭一齊回來,由巴爾喀木(8)巴爾喀木為藏文bar khams意為康區。路向四川來”。[9]1128允禵令“由打箭爐至藏所駐之站,斷不可撤,流備駐藏大臣等奏報交由彼路行遞。”原有的青藏路線“冬冷,驛馬難以生存……其間地極遠,格爾側郭洛特等唐古忒人等妄行奪取馬匹,致驛站中斷。”[9]1128《撫遠大將軍允禵奏搞》中還提到了:“我與將軍噶爾弼商議,將我來路撤驛(9)這時允禵在青甘一帶。,將軍噶爾弼來路駐驛,由藏至打箭爐,此路居人不斷,而燒柴豐富。唐古忒人又幫送遞,并無耽誤……將軍去路暖(10)這里的將軍為噶爾弼。,而燒柴豐厚,理應準此設驛。”[9]1129-1130從上引材料的字里行間來看,至少可以透露如下信息,其一,從南、北路進藏的清軍保藏后,次年從藏至打箭爐道路返回;其二,大將軍允禵令南路返川的將軍,無須撤回驛站,南路沿途驛站備用;其三,北路自然條件艱巨,人為隱患巨多,建議撤回驛站;其四,因川藏古道沿途采購糧食、放飼牲口較為便捷等緣故,南路作為日后的官方驛道。[10]71-78
雍正五年(1727),西藏諸噶倫之間發生內亂,清廷先派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領瑪拉、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前往西藏辦理事務,他們先后從打箭爐、理塘、巴塘至昌都,再從昌都、落隆、邊壩、拉里、江達進入拉薩。[1]158此時清廷派往西藏的官員軍從南路進藏,顯而易見,南路基本已成為朝廷的官方驛道。就在這一年,清廷為平定西藏的內亂,派軍進藏,與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入藏方針相似,使用北路的同時,再一次重用南路,[8]414-416使南路又一次成為朝廷的軍事要道。這期間,清廷在南路的昌都等重要沿線樞紐上派駐軍隊[1]179。南路上清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文書傳遞、人員接待、后勤供給等方面已經有了較好的保障。其后,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份議奏中顯示:川藏古道上設立的驛站、塘汛、糧臺等沿線設備,1746年前后清廷仍在完善和優化當中。[4]250乾隆十五年(1750)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在拉薩與駐藏大臣發生沖突,郡王隨從在拉薩進行騷亂,且阻斷漢藏官道。[11]43清廷準備從四川派兵八千人,[8]527-528后因藏地已平靜,大軍進藏計劃取消,由四川總督策楞為首的大員從南路進入拉薩。[8]533到18世紀末,廓爾喀侵入西藏,清軍先后兩次進藏征剿廓爾喀。(11)廓爾喀第一次侵藏于1788年,第二次侵藏于1791年。1788年清廷派川軍通過南路進藏,1791年清軍南北兩路入藏。總的來看,清廷自1720年從川藏古道上開辟軍事要道以來,逐漸建成官方驛道,并建立健全驛道的運行機制。在清末成書的《西藏圖考》中對川藏驛道的優勢條件做出了如下肯定:“川、陜、滇入藏之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戲重阻,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為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云。”[10]78黃沛翹所撰《西藏圖考》中的這一論斷,一方面是清末人對18世紀初清廷開辟川藏驛道的歷史和效能上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黃沛翹雖生活在清末同(治)光(緒)年間,但長期居住四川,并悉心于川藏邊地的鉆研,故上引斷論便可理解為他對進藏路線的研究成果。
三、川藏古道的路線及其驛站
從前所述,清軍于1720年從川藏古道進藏的過程當中,在沿途建立零散的驛站、糧臺、訊塘等,這是清廷首次把川藏古道作為軍事要道,亦是清廷在川藏古道上奠定驛道基礎的表現。18世紀20年代以來清廷治理西藏地方的過程當中,川藏古道上的驛站、糧臺等逐步完善和優化,并把川藏古道作為朝廷勢力進一步滲透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無論大規模軍隊的進出,還是央地官員的往來或物資的運輸,均在川藏古道上進行流動。這是川藏古道成為清廷與西藏地方之間的官方驛道的歷史表現。那么清廷把川藏古道先后作為軍事要道和官方驛道,在川藏古道上建立了制度性的驛道系統,即路線和驛站,這一內容在清代漢文文獻中有明確記載。本文在川藏驛道的路線和驛站上主要參考18世紀末成書的《衛藏通志》,18世紀末正好亦是川藏古道的驛道網絡發展到比較系統且具有制度性特點的成熟時期,因而《衛藏通志》所記載的川藏驛道路線和驛站應是18世紀的較為權威而可信的史料。根據乾隆六十年(1795)成書的《衛藏通志》記載,川藏驛道的干線為:成都至打箭爐、理塘、巴塘、芒康、察雅、昌都、落隆、碩般督、邊壩、郎吉宗(金嶺)、嘉黎、工布江達、墨竹工卡、拉薩。[12]227-240顯而易見,從康定(打箭爐)到昌都的驛道路線與現今的318國道一致的,昌都到拉薩的古驛道路線與現今的349國道基本一致(12)G349國道線路不經過加貢與嘉黎之間的魯工拉,從金嶺進入尼屋鄉再到嘉黎,到墨竹工卡時主線往山南乃東。,所謂干線,道路上人口流動、物資運輸最為繁榮,沿線上村落和寺院較為密集,起點和終點之間的所費時間較少、空間距離較近的道路。另外,川藏古道上也存在不少的支線,如康定至昌都可以經道孚、甘孜、德格、江達進入昌都:昌都至拉薩也可以經類烏齊、丁青、巴青、索縣、那曲、當雄進入拉薩等。支線多為民間商人、朝圣者以及游牧遷徙所開辟的羊腸小道,在此不贅述。
《衛藏通志》所記載的川藏驛道的驛站:打箭爐(康定)-折多-提茹-阿娘壩-瓦切-東俄落-高日寺-臥龍石-八角樓-中渡(雅江)-剪子灣-西俄落-咱馬拉洞-火竹卡-火燒坡-里塘-頭塘-乾海子-喇嘛丫-二郎灣-三壩-松林口-大朔塘-彭察木-小巴沖-巴塘-牛古-竹巴籠-公拉-莽里-南墩-古樹-普拉-江卡(芒康)-山根-黎樹-阿拉塘-石板溝-阿足塘-歌二塘-洛加宗-俄倫多-乍丫(察雅)-雨撒-昂地-噶喀-王卡-三道硚-巴貢-窟籠山-包墩-猛布-察木多(昌都)-俄洛橋-浪蕩溝-拉貢-恩達-牛糞溝-瓦合寨-麻利-嘉裕橋-鼻奔山根-洛隆宗(落隆)-曲齒-碩般多-中義溝-巴里郎-索馬郎-拉子-邊壩-丹達-察羅松多-郎吉宗(金嶺)-大窩-阿蘭多-破寨子-甲貢(加貢)-大板橋-多洞-擦竹卡-拉哩(嘉黎)-阿咱-山灣-常多-寧多-過拉松多-江達(工布江達)-順達-鹿馬嶺-堆達-烏蘇江-仁進里-墨竹工卡-拉木-德慶-蔡里-拉薩。[12]227-240自雍正五年(1727)起康區分為川、藏兩部分,芒康寧靜山以東隸屬川省,山以西為西藏地方轄區。隨后驛道運行與管理方面,川內“康區驛站歸四川總督具體負責,西藏驛站由駐藏大臣直接轄理”。[13]
四、結語
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道路作為一個基礎設施,在生活中是必不可缺的條件;從一個政權的視角來講,道路不僅僅是一個人流物流的基礎設施,更是擴大勢力、權力滲透的重要渠道。那么我們從清朝角度出發,對川藏古道的優勢條件以及清朝對川藏古道的使用和經營進行探討的時候,道路對一個政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更加明顯。川藏古道作為開辟的經商之路和朝圣之路的混合體。雖是古代時期的羊腸小道,但它的歷史已有上千年。[14]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從地理位置的意義上講,川、藏兩地都處于中國的西南區域,無論在歷史時期或著眼于現實意義,川、藏兩地均有重要的固邊、穩邊的戰略地位。川藏古道主要呈東西走向,連接著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貫穿橫斷山脈在內的川、藏兩地的大部分地區。如從成都平原啟程,經康區可以到達西藏腹地拉薩,甚至更遠的山南、日喀則和阿里等地,途中必然要經過多年被蒙古和碩特部勢力所左右的清廷尚未控制的康區。因此,從維護邊疆和鞏固地方的遠景目標來講,毋庸置疑,爭取川藏古道的經營權是極為關鍵的一個因素。18世紀初以來,由于西藏地方的種種局勢,導致了清廷不得不沿著川藏古道開拓一條軍事要道。清廷對川藏古道的探索、琢磨以及正式經營的過程當中,充分認識了川藏古道所具備的優勢遠遠勝于北路青藏線,“使清朝進藏道路由過去以西寧一路為主開始轉向以南路為主”。[2]145從1720至1791年期間,首先,清廷在“驅準保藏”的同時開辟出川藏古道的軍事要道,并為往后官方驛道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川藏古道上因軍事需要而建立的零星的驛站、塘汛、糧倉在長期內逐步完善和優化,建立了系統和制度化的驛站制度,為清朝和西藏地方的關系聯絡上創建了較為全新的并且有保障的道路網絡;再次,通過川藏古道上建立的驛道,清廷與西藏地方之間,無論大規模軍隊的進出,還是官員的往返或大量物資的運輸,發生了一系列的互動關系,在客觀的結果上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各民族間進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最后,清廷因積極利用川藏古道的戰略優勢,不僅僅是驅逐在藏準噶爾部勢力和廓爾喀的入侵等,并且對多年被蒙古勢力所困擾的康區逐漸贏得控制,實現了對西藏的直接治理,“將分散的領土連接成為一個國家的網絡,便利了集中化政治治理的興起”[15],從某種意義上講,贏得川藏古道的經營權,對于推進、擴展清朝在內亞和中亞的影響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6]
綜上所述,清廷因積極利用川藏古道的優勢,從而川藏古道上的流動成為“既是物資的流動,更是權力的流動”。[17]從18世紀西藏地方歷史處境來將,驛道應該是流通性和連通性極強的通道,那么對于清朝來說,川藏古道上的驛道,不僅僅是文書傳遞、人員接待、物資運輸的物質存在的通道,更是權力滲透和勢力輸送的隱形渠道。從政治意義上的中心與邊緣的角度來思考,清廷在川藏古道上不斷建立和完善驛站制度,可以認為是清中央政府主動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關系上的調整和對西藏地方秩序的重構,更是經營地方、維護邊疆穩定和國家統一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