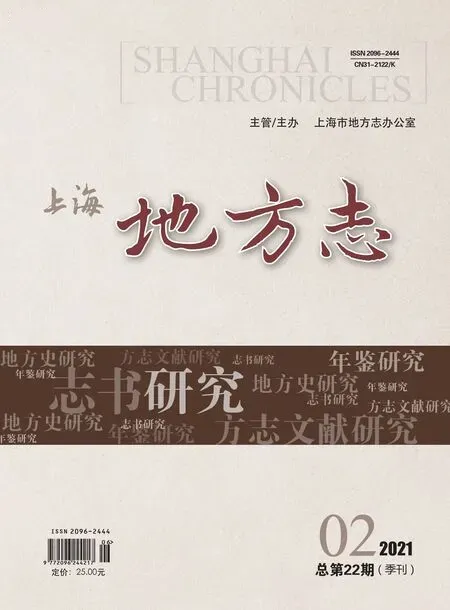地方志述體的發展: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
齊迎春
近年來,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新的書寫文體,或者說文化現象,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以這兩種文體書寫的作品大量涌現,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文學及新聞學領域,對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已經從實踐上升到了理論研究的高度。也正是在對這兩種新文體的不斷探索之中,它們與地方志在學科內涵上一致性逐漸顯露出來,甚至有了諸如“方志小說”等的命名,非虛構寫作目前雖然尚未直接和地方志聯結,但從寫作對象和方式等方面與地方志的一致性也日益凸顯。
值得方志界注意的是,與社會各界對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高度關注相比,方志界對這兩種新文體的反應卻相當冷淡,這一現象不但反映了地方志在學科交叉與理論拓展研究上的薄弱和局限,也反映出地方志事業在應用與開發方面仍然“任重而道遠”。
本文試從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產生及發展,地方志對方志文學、非虛構寫作的影響,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是地方志述體發展的必然結果三個方面闡述方志文學、非虛構寫作和地方志的關聯,以期更多地引起地方志專家及工作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從而更多地開展關于地方志述體發展趨勢以及地方志開發利用領域的研究。
一、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產生及發展
(一)方志文學
方志文學(方志小說)的出現,大致是從陜西作家賈平凹的“商州三錄”(《商州初錄》《商州又錄》《商州再錄》)和長篇小說《商州》系列開始。例如《商州初錄》開篇其實就相當于一篇志書里的概況,內容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物產礦藏、風俗習慣等,全書的書寫順序也非隨意設置,而是以與丹江的距離位置的順序鋪陳開來,類似于志書中“橫排豎寫”的編纂方法,可以說,“商州系列”其實就是一部帶有文學色彩的關于商州地方的地方志書,也有人稱之為商州地方的“風情志”。因此,有人開始以“新方志小說”或“新方志文學”為此類作品命名,此后,“方志小說”不論從數量上還是形式上也愈加豐富起來,有的是直接利用當地的志書進行書寫,例如貴州作家歐陽黔森的《看萬山紅遍》,以《萬山志》《銅仁志》作參照寫作,萬山地方的建置沿革及山川地理、輿圖、城池、關梁、人文、經濟、風物、傳說等,在作品里時見征引①杜國景:《為新時代方志文學喝彩》,《文藝報》2018年10月24日。。還有直接套用了志書的名稱以及框架結構的,如閻連科的《炸裂志》,除了小說的標題直接叫作“志”,全書的謀篇布局也參照了志體,如書中所設章節包括輿地沿革、人物篇、政權、傳統習俗、綜合經濟、自然生態等。2017年8月,在中國南部5個不同地方的村落,還開展了一項“方志小說聯合駐村寫作計劃”,邀請近30位寫作者和嘉賓參與在地寫作,從方志與小說兩種不同的方向去探索對地方經驗的表達和書寫。
目前,對方志文學的基本定義是“對地方性知識整體性、結構性、歷史性變遷的文學性、時代性、連續性、史志性表達。”當然,這里的“地方”不僅是指行政區劃,還包括特定的行業或領域在內,類似于地方志的區域志和行業志。
(二)非虛構寫作
非虛構寫作的概念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與虛構相對,非虛構寫作是一種邊界寬泛的文體概念,這種文體以‘忠于事實,還原真實’為準則”②張濤甫:《非虛構寫作:不可缺席的記錄者》,《青年記者》2017年12月上。。2017英國學者芭芭拉·勞恩斯伯里總結了非虛構寫作的特征:第一是記錄性,第二是詳盡研究,第三是場景,第四是細致寫作③劉蒙之,張煥敏著:《非虛構何以可能:中國優秀非虛構作家訪談錄Ⅰ》序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由此可見,非虛構寫作的核心其實就是對社會微觀現象的客觀記錄,而地方志的核心也正是翔實的客觀記錄。
作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近年來非虛構寫作風頭強勁,從雜志業、圖書業、新媒體到影視業對非虛構寫作都寵愛有加,傳統文學雜志如《人民文學》,新聞雜志如《南方人物周刊》,新媒體平臺如“騰訊谷雨”“網易人間”“彭湃湃克”“在人間”“單讀”等,歷史學、社會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知識傳播均借鑒了非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在各領域逐漸成為一種新型的敘事模式。“(非虛構)如同突然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泉水,我們意識到的時候才發現濕透了很多地方”④劉蒙之:《非虛構寫作不是什么?》《長江文藝》2019年04月。,這個“濕透的地方”自然也包括地方志領域。
非虛構寫作范圍廣闊,上通天文、下達地理,記述內容包括科學、哲學、新聞、歷史、人物、紀實、專訪,個人專記等林林總總、包羅萬象,但無論記述什么內容,都有一個共同交集——基于事實、述而不論。
二、地方志對方志文學、非虛構寫作的影響
雖然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有如此之多且并非偶然的一致性,但是從學理研究的角度看,方志小說與非虛構寫作仍然存在著諸多待解的問題,比如它的理論譜系、書寫范圍、學科屬性和社會功能等等,迄今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目前,對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研究與探索尚主要囿于文學和新聞學領域。其中有學者從社會功能的角度考察認為,非虛構寫作需要向更深層次的問題和更高的象征性意義挖掘,非虛構寫作可以超越具體的社會熱點和事件,以道德倫理教化眾生,以世情百態熏染人心;也有些學者更注重對非虛構寫作的知識譜系的勘察,他們從“舶來品”這一概念入手,細致辨析了非虛構寫作的歷史脈絡和發展方向問題,認為,非虛構作為一個詞語或許會過時,但中國當代轉型時期豐富的實踐,是非虛構寫作的永動機,盡管可能會以另外一個名稱或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筆者認為,這些看法其實正暗合了地方志的幾個基本特征,因此,本文擬試從地方志學科的視域下對二者做一個初步的探索。
從已經發表的方志小說和非虛構作品,以及目前對二者的研究成果來看,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與地方志在本質屬性上的一致趨勢:
(一)以“地方”和“微觀”為書寫對象
志書、方志小說都是以某個特定地方為書寫對象,如一縣、一鎮、一鄉、一村,甚至是一條街、一家店,非虛構作品更是細微到某個群體、某一個人……從近年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實踐來看,此類作品重視宏大敘事下忽略的一些邊緣題材。有的是關注一地,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有的關注某一地域的某個行業,如蕭相風的《南方工業生活》,這部作品在寫作方法上甚至類似于年鑒的條目體編纂方法;有的關注某一個群體,如張彤禾的《打工女孩》。
“史宏志微”,地方志與傳統史相比,注重微觀、聚焦民生的自身特性,事實上正是方志小說和非虛構作品萌芽和成長的土壤。“貼近鄉土、貼近人本”才會打動讀者,發揮作品的感染力,從而真正發揮出“教化”“育人”的效能。傳統史“從上到下”的視角,遮蔽了大量微觀的鮮活的事實,隨著“全球化”發展,已經有更多的人意識到搶救地方傳統、探尋邊緣群體的重要性。志書、方志小說、非虛構作品“從下至上”視角,最大的優勢就是將對“面”的觀察細化為“點”,將大量微觀事物帶入了讀者的視野。
(二)以“述而不論,揭示規律”為書寫準則
方志小說是一種文學表達形式,其本質是小說,是小說就有虛構的成分。但與傳統小說的不同在于,方志小說將自己置于觀察者的角度,作者不動聲色地進行寫作,敘述的過程中盡量不做主觀評判,力求忠于現實還原真相。其實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這種旁觀者的寫作方式并不少見,例如筆記類小說。《紅樓夢》之所以對歷代讀者保有如此大的魅力,也是因為作者沒有直接表達觀點,事實真相也只能由讀者自己憑借事物的表象自己去挖掘。非虛構寫作更是追求做一個記錄者,記錄和呈現一切現實元素。作者不只是一個歷史的參與者,更是記錄者。這些特點與地方志“述而不論、寓觀點于事實的記述之中”的編纂原則實則一脈相承,因為三者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客觀呈現。
此外,與傳統的文學作品和新聞作品不同,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十分注重結構設計,熱衷于對敘述內容進行分類,目的在于將表面似乎不相關的事物,通過結構設置與文字技巧,把它們內在的邏輯與因果規律揭示出來;非虛構寫作基于現實,但并非一定是時下熱點,它注重的是文章所揭示的現象或問題在一個階段里呈現出的趨勢和規律,美國非虛構作家何偉主張用非虛構喚醒人類經驗;志書既寫其然,又寫其所以然,既寫出客觀現實性,又揭示客觀規律性,為讀者正確認識一地的歷史和現狀提供科學的依據,起到鑒古知今的作用①朱永平:《例談志書述而不論與揭示規律的關系處理》,《廣西地方志》2011年第4期。。顯然,用事實發聲,探索規律總結經驗,是地方志、方志文學、非虛構寫作共同遵循的一個編纂準則。
(三)以“真實和客觀”為書寫特征
真實是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的首要特點和基本標準。美國非虛構作家何偉說:“非虛構寫作讓人著迷的地方,正是因為它不能編故事。看起來這比虛構寫作缺少更多的創作自由和創造性,但它逼著作者不得不賣力地發掘事實,搜集信息,非虛構寫作的創造性正蘊含在此間。”講真實故事正是方志文學、非虛構寫作一經問世便得以迅速傳播的核心因素。
近年來中國文壇創作出一批優秀的方志小說和非虛構作品。《人民文學》雜志2017年第12期推出《新時代紀事》欄目,歐陽黔森的《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看萬山紅遍》、鄭風淑的《金達萊映紅山崗》、范繼紅的《溢綠園》等作品陸續在欄目刊登,這些作品“實情和史事、藍圖相融”,“專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寫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意蘊和時代特征”①杜國景:《歐陽黔森創作的歷史理性與價值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GZWT01)。。非虛構作品方面,梁鴻的《出梁莊記》、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喬葉的《拆樓記》、鄭小瓊的《女工記》、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齊邦媛的《巨流河》,還有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等,都是建立在真實之上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成功印證了“真實”的強大感染力。
方志界常講,地方志就是要講好中國故事,地方志講的故事必須是以“真實、客觀”為前提條件,而“真實、客觀”亦是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誕生的前提條件,也是二者存在的最大價值。
(四)以眾手成書為書寫方式
“方志小說聯合駐村寫作計劃”邀請近30位寫作者和嘉賓參與在地寫作,且主辦方希望讓更多人參與進來。這一現象說明方志小說正在由一種個體寫作的模式向群體寫作發展,每個人寫一個部分,最后再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作品。
非虛構寫作活動也注重大眾參與性,非虛構寫作突破傳統文學寫作主要由作家主導的模式,主張讓普通人成為寫作主體。由鳳凰網推出的非虛構寫作平臺“有故事的人”,對非虛構寫作的理念是“每個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寫出故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業余的大眾參與到非虛構寫作中,記錄自己身邊的人事。
這與地方志“眾手成志”的寫作模式一致,它的出現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更廣泛地占有資料,一是多視角呈現事實。方志小說和非虛構寫作的生命力就在于對地方或某一群體的書寫并不是單線的描述,而是運用大量的資料或者說細節進行佐證,因此亦決定了這樣一種事實:越是占有大量翔實材料的作品,敘事角度越是多元化,其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就越是強大。
三、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是地方志述體發展的必然結果
以上論及的關于地方志與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的共同特征,有人認為是出自對地方志的借鑒,這種借鑒既包括書寫內容上的,也包括書寫形式上的。但筆者認為,這兩種“新文體”出現與迅速傳播并非偶然,與地方志的關系也并非僅僅是“借鑒”,事實上,二者是地方志“述體”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地方志述體的發展沿革
地方志從單純的“地志、地記”發展至“圖經時代”,開始有少量的記述文體出現并不斷演進,在記述內容和文辭方面也日漸豐富,特別是《山海經》,內容包羅萬象,囊括了地理、民俗、神話、醫學、科學等各學科資料,除了重要文獻價值外,還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此對后世影響也非常大。清代章學誠在編纂《永清縣志》等志書時,開始設置例議、序列、總論、考序等,例如《永清縣志·與地圖序例》②《章氏遺書·永清縣志六書例議》。。這些序例、總論、考序及各類目小序等等,極大地推動了地方志述體的發展,為現在新方志記述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新方志形成了完整的述體系統,在新方志中,述體大致分為總述、綜述、概述、無題述幾種類別,述體的類型主要包括鳥瞰式、濃縮式、橫展式、縱貫式、軸心式、簡介式、提要式、策論式等。隨著地方志編纂創新,還出現了“專記”“特記”“調查報告”等新文體。地方志述體的不斷發展,使各類地方志文獻在閱讀和利用兩方面變得更加直觀、更加便利,也因此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對地方志的關注。
(二)由地方志述體發展而來的新文體
方志文學是一些具有“鄉土情懷”的作者,因傳統小說書寫存在地域背景模糊、情節完全虛構的局限性,不足以寄托和表達“鄉愁”,便將目光轉向地方志。他們從地方志文獻中擷取對某個地方、某個領域的真實資料,再輔以詩意的書寫,使得此類作品比志書更生動、更有可讀性,比傳統文學更真實、更具感染力。
非虛構寫作亦是如此。喻國明認為:“非虛構呈現現實的手段,如果做得好的話,其實從很多角度看比虛構的手段更能產生震撼力,使得情景具有更巨大的力量,這是非虛構的力量。”
這兩種新文體在我國的興起,反映了讀者對傳統文學或傳統新聞學反映社會生活的銳度、廣度與深度不滿意,渴望一種新寫作方式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而地方志恰好為這些新的書寫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源源不斷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講,隨著地方志述體和方志數字化的不斷發展,地方志的未來發展必將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除了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之外,還會有其他的書寫形式出現,但只要其符合對某一特定地域或領域的客觀書寫,就基本上可以認定為地方志述體的某種“變體”,因為萬變不離其宗,這個不變的“宗”就是對某個地域或某個個案的客觀呈現。
結 語
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中指辦主任冀祥德在2019年全國省級地方志工作機構主要負責人培訓班講話中指出:“地方志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社會科學成果群.”值得深思的是,這一成果群所蘊藏的“礦藏”包羅萬象,不僅是關于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文化、人文等方面靜態的記述,在世代綿延不斷的記載之中,這些資料和數據還按照他們自身的屬性與發展,自發地產生聯結、融合,生發出不可預計的變體和變量。
地方志成果群并不是一座“死火山”,或許它表面曾長期呈現出某種靜態狀態,以至于方志界仍有不少人認為地方志文獻的開發和利用率很低,但事實上,地方志文獻并非處于通常所認為的低應用狀態,相反,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領域,對地方志的利用一直呈現出有增無減的趨勢,只是方志界對此反應較為遲滯,甚至很多地方志產品出現時,辨認不出其來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長期的學術不自信令地方志界低估了地方志的價值;二是學科建設薄弱,理論研究長期滯后于修志實踐,限制了方志界對自身學科的認知。
方志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持續走熱,提示了在方志領域即將展開的可能是一場關于地方志的“新記錄運動”,方志界亦要提高自身的學術敏銳性,開闊學術視野,從地方志編纂到應用的各個環節探索規律、發現規律,加快地方志學科建設步伐,樹立方志自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主動擔當其必然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