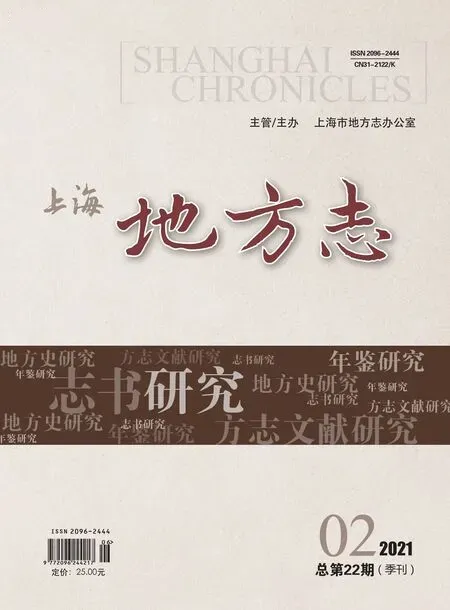近代上海市民社會與滬劇藝術的關系初探
石夢潔
一、滬劇的起源概述
(一)從“花鼓”到“本攤”
中國的許多民間戲曲起源于農村地區,滬劇也不例外。據《上海滬劇志》所載,滬劇原是在吳淞江和黃浦江兩岸鄉村傳唱的山歌俚曲,又稱為“東鄉調”①汪培、陳劍云、藍流主編:《上海滬劇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概述”,第1頁。。起初是一種連說帶唱的表演形式。到了清代同治、光緒年間,“逐漸向作為戲劇表現形式的‘對子戲’和‘同場戲’②所謂“對子戲”,由男女二人對唱對演。而“同場戲”又分為“小同場戲”和“大同場戲”。“小同場戲”演員人數在三人及三人以下,情節相對簡單;而“大同場戲”表演人數在通常在三人以上,劇本情節相對復雜,變化較大。見中國戲劇家協會主編:《中華戲曲·滬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過渡,當時群眾又把它稱為‘花鼓戲’”③《上海滬劇志》,“概述”,第1頁。。
眾所周知,花鼓戲起源于安徽鳳陽地區。有研究者認為,清代中葉,因淮河水災,鳳陽人從安徽流離至江蘇,故而將花鼓戲帶入吳地④柯如:《再論花鼓戲之起源》,《申報》1933年6月15日,第21613期,第15版。。
嘉慶年間上海南匯人楊光輔所撰的《淞南樂府》一書,有“村優花鼓婦淫媒”的詞句。這首樂府后面并有附注:“男敲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穢之詞,賓白亦用土語,村愚悉能通曉,曰‘花鼓戲’。演必以夜,鄰村男女鍵戶往觀。”⑤楊光輔著,許敏標點:《淞南樂府》,《滬城歲事衢歌·上海縣竹枝詞·淞南樂府》,《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4頁。若將此視為滬劇前身,則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
由于植根農村,起初花鼓戲多描寫鄉村男女的愛情故事,其中有一些低俗露骨的“淫穢之詞”。早在嘉慶年間,花鼓戲就遭到了明令禁止⑥嘉慶十一年(1806年),官府曾頒布《禁花鼓告示》,見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上海卷》,中國ISBN中心出版社1996年,第10頁。,但見效甚微。到了19世紀中晚期,由于花鼓戲的演出范圍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拓展,地方士紳也加入了打擊花鼓戲的行列。藝人們被迫將表演場地轉入租界。然而,在官府的窮追猛打下,在租界的演出也受到阻礙。1872年10月15日的《申報》上所刊《請禁花鼓戲說》:
“若花鼓戲則以真女真男當場賣弄凡淫艷之態,人所不能為……窮鄉僻壤偶爾開臺一闕,甫終片帆已掛。蓋恐當道聞風驅禁,猶存顧忌之心,而鄉間婦女尚有因之改節者密約幽期,尚有因之成就者誘人犯法,已屬不堪。今則倚仗洋商恃居租界,目無法紀,莫敢誰何。”①《請禁花鼓戲說》,《申報》1872年10月15日,第144號第1版。
演員們只能或邊走邊唱(即“跑筒子”),或在街頭臨時圈地賣藝(即“敲白地”)②《上海滬劇志》,“概述”,第1頁。,以此躲避追查。為了長久地維持生計,他們將花鼓戲改名換姓作“本地灘簧”③灘簧,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們對產生并成長于該地的由說唱嬗變為戲曲的表演藝術的一種習慣性的稱謂。見朱恒夫:《灘簧考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頁。,簡稱“本攤”或“申灘”。由于當時的“蘇州灘簧”在上海市民階層中廣受歡迎,于是本攤也借此東風,在形式上由立唱改為了蘇灘的坐唱。
(二)從“本攤”到“申曲”
20世紀初,報紙上屢有關于本攤在茶肆演出、客座滿盈的報道。如1904年的《申報》中就有言“馬家廠旁南園小茶肆主,招人歌唱灘簧,觀者如云,異常熱鬧”④《上海保甲巡防局紀事》,《申報》1904年10月1日,第11300號第9版。,可見這時本攤已開始為城市底層市民所接納。該時期代表人物許阿方和胡蘭卿,被視作滬劇界的“祖師爺”⑤其實,滬劇的“祖師爺”還有如“水果景唐”“麻皮雪春”“紅鼻頭掌生”“花鼓戲阿六”等一些只留下藝名的老先生。但因為沒有真名,無檔案可查,在1934年“申曲歌劇研究會”制“先輩圖”時,因此未能將他們列入其中。見胡曉軍、蘇毅謹等著:《戲出上海——海派戲劇的前世今生》第六章,文匯出版社2007年,第225頁。。
辛亥革命后,施蘭亭、邵文濱、胡錫昌、陳阿東等一批本攤藝人主動響應政府文化改良的號召,對本攤中的“淫詞穢語”進行了調整。1914年4月,《申報》上登出準予改良灘簧開唱的信息,本灘就此獲得了官方認可:
南市第一區境德興樓茶館擬設改良灘簧,遵章認繳同捐,補助地方公費。會經呈請上海工巡捐局,給諭在案。茲經朱局長函,由第一警區查明,該茶樓附設之灘簧確系改良小說,并無淫詞穢語,自當照準。故于昨日批示,給發執照矣。⑥《改良灘簧準予開唱》,《申報》,1914年4月12日,第14694號第10版。
而后,“天外天”“新世界”“大世界”等游藝場的出現,無疑又給本攤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⑦1917年,“丁少蘭等以東鄉調、本土灘簧之名,在上海天外天游樂場演出,這是本灘首次獻藝于游樂場”。見《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第126頁。1914年,施蘭亭等人組織了滬劇史上第一個專業藝人團體——“振新集”⑧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8冊第三十八卷,《文化藝術(上)》,第二章“戲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5217頁;屠詩聘主編:《上海春秋》下篇,第二十七章第六節《本地灘簧—申曲》,香港:中國圖書館編譯館1968年,第59頁。;同時,用“申曲”名稱替代了“灘簧”。這一名稱一直沿用到1941年上海滬劇社成立。⑨“1941年上海滬劇社成立,首次將申曲改名為滬劇。”見《上海滬劇志》,“概述”,第2頁。關于這一更名,20世紀30年代時任江蘇省吳縣縣長的吳企云寫過一篇《申曲研究》:
叫申曲,便與昆曲相并肩,似乎是雅了吧,于是申曲這名稱竟奪去了花鼓戲等的本名了。申曲這名稱,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八日上海市申曲歌劇研究會正式成立,在上海市黨部注冊,可說已是正式的了。我們對于“申曲”兩字,也很贊成,因為他能夠表出地方性的緣故,至于雅不雅,倒在其次。⑩吳企云:《申曲研究》,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正集》,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565頁。
至此,源于農村的滬劇開始正式面對都市群眾。
二、20世紀20-40年代滬劇在市民社會中的表現與接受
(一)市民社會與滬劇表演形式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的概念源于西方。關于這一概念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李天綱教授在其著作《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中就大量運用了“市民社會”及“市民意識”等相關詞匯。或許因為這是一個過于龐大的話題,書中并未就此給出具體定義,只是指出韋伯曾對此有所論述,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市民社會”一詞是在18世紀產生,且“歷來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在研究歐洲13世紀的城市時都用了‘市民’的概念”①李天綱:《近代上海文化與“市民意識”》,《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頁。。言下之意,所指的“城市”,是以西方城市為模型的現代城市,而非中國宋明時期的城市。②李天綱教授認為,中國歷史上那些高度發達的城市,比如六大古都,其經濟地位都依附于政治地位,“歐洲城市后來又自己的法庭、軍隊和警察,領主不得入內,就是國王也非請莫入。中國的城市就不同,都邑之內歷來還是皇家官府的天下”。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有自我權利意識的僅僅是上層的官僚、士大夫,而工商人士卻無法用社會制度來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生計。即便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盡管出現了一大批“小市民”,但他們的作為也僅僅體現在精致的物質生活上,而非對于地方事務的貢獻和參與。見《人文上海》,第27—28頁。但由于特殊的歷史機緣,上海較早地與西方文化碰撞、雜糅,因而在市民社會的成型過程中,上海與中國其他城市相比得以擁有近水樓臺的優勢。
申曲剛剛進入城市時,主要觀眾集中于茶樓酒肆。在這樣的瓦肆勾欄間受到歡迎,可見當時上海民眾普遍文化水平有限,審美情趣充滿了濃厚的世俗氣息。然而,底層民眾從來就不具有意見導向,話語權總是集中在有一定社會地位、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群中,如政府官員、大學教授、文人、記者等等。他們認為申曲并不能登大雅之堂,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申曲的發展。而另一方面,與當時上海最受追捧的京劇和昆曲相比,申曲無論是從自身的文化底蘊還是演員的表演功底來看,也的確難以望其項背。為了在困局中找到生存空間,申曲的改革迫在眉睫。
上海人看戲對舞臺效果十分重視。“(演員)長相要漂亮,服裝要鮮艷,燈光要明亮”③蔡豐明:《上海都市民俗》,第八章“聲色之娛·上海都市文藝娛樂民俗”,第一節“風靡上海的戲劇熱”,學林出版社2001,第277頁。,是講“腔調”的上海人對一出戲最基本的外在要求。為了適應城市群眾的欣賞習慣,申曲恢復了花鼓戲的站立演唱形式;而在布景、服裝、道具等硬件上也不斷完善,比如根據劇本內容繪制幕布、添加軟景等④《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第125頁。。
盡管申曲對京劇、昆曲、蘇州灘簧以及評彈都有所借鑒,但為了更好地彌補自身的“先天不足”,申曲也向“文明戲”⑤所謂“文明戲”是相對于舊戲而言的,當時更多稱為“新劇”,如歐陽予倩在《談文明戲》一文中寫道:“初期話劇所有的劇團都只說演的是‘新劇’,沒有誰說‘文明戲’的。新戲就是新興的戲,有別于舊戲而言,文明兩個字是進步或者先進的意思。文明新戲正當的解釋是進步的新的戲劇。”見歐陽予倩:《談文明戲》,葛聰敏編選:《歐陽予倩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414頁。而周劍云在《新劇評議》一文中認為,文明戲和舊戲的區別在于內容上的文藝美術:“新劇者,一般人士所呼為文明戲者也,此文明二字何等華麗,何等光榮……新劇何以曰文明戲?有惡于舊戲之陳腐鄙陋,期以文藝美術區別之也。”見周劍云:《新劇評議》,《繁華雜志》1915年第6期。文明戲的形式很多,過去有人認為只是早期話劇的形式,其實不僅如此,黃遠生先生認為劇本內容、表現形式上的有所革新者皆為“新劇”:“今日普通所謂新劇者略分為三種:(一)以舊事中之有新思想者,編為劇本……(二)以新事編造,亦帶唱白,但以普通之說白為主,又復分幕……(三)完全說白不用歌唱……亦如外國之戲劇者……”見黃遠生:《遠生遺著(下)》,《新茶花一瞥》,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76—379頁。汲取經驗。1918年,與文明戲首次融合的申曲《離婚怨》取得了成功。該戲由文明戲演員范志良與申曲“子云社”的劉子云合作改編,取材于發生在上海的真實事件,主要講述了一個愛慕虛榮的女子,因不滿于丈夫貧窮失業而與其離婚,之后被“拆白黨”所騙,繼而走向墮落;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離婚后的丈夫因勤勞致富而娶得淑女,重建了美滿幸福的家庭①文牧、余樹人:《從花鼓戲到本地灘簧——滬劇早期歷史概述》,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2集,上海藝術研究所1986年,第8頁。。《離婚怨》由丁少蘭和孫是娥擔任主演,上演后取得了熱烈反響。1921年,該劇在“花花世界”游藝場的首演更是轟動一時。
《離婚怨》開創了滬劇時裝戲的先河,也決定了后來申曲以時裝戲為重的發展路線。可見,當時這類具有現代風格的表演形式更受上海市民的喜愛。30年代以后,西裝和旗袍成為上海都市男女的主流服裝②關于上海西裝業,在《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中提到,早在1896年,上海就有了第一家“和昌西服店”。而關于旗袍的起源時間一直未有定論。據周錫保《中國古代服裝史》,在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婦女照片上,數十人中還只有一人穿旗袍,要到20年代中后期才逐漸流行起來,30年代以后才成為普遍的婦女服飾。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編纂委員會:《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09頁;周錫保:《中國古代服裝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534頁。。表演申曲時裝戲的男女演員,也多如此穿著。在這樣的風潮下,“西裝旗袍戲”變成了滬劇的一大標志。
在申曲發展的過程中,上海市民的日常活動空間、欣賞戲劇的習慣、關心的社會事件、穿戴的衣著服飾等等,都從不同的側面促進了它表演形式的改變。兩者之間彼此影響、相互照見。
(二)1938年以前的市民社會與劇本題材
與表現形式的改革一樣,滬劇劇目的革新也無外乎以生存為本,迎合都市人群的喜好,從而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多元的摩登都市文化下,申曲在劇目內容上也必須打破傳統農村劇目封閉、保守、低俗的風格,這就對新劇本的開發提出了要求。
這樣的要求使滬劇史上第一批“編劇”——“說戲先生”應運而生。這和“幕表制”的引入也密不可分。所謂幕表制,就是將戲中人物和情節以類似提綱的形式單列出來,讓藝人們在演出前的幾小時過目,上臺之后依此發揮。宋掌輕、徐醉梅、王夢良、范青鳳等人可謂“說戲先生”中的翹楚,他們在20年代后期就從文明戲轉入了申曲界③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下卷第十六篇,“戲劇”,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748頁。。盡管他們的“劇本”流于口頭形式,但一出戲的成功與否,和說戲先生表達能力及自身文化程度都有很大關系。宋掌輕曾口述:
“演出之前,先安排好分幕分場,寫出幕表。這項工作不能一個人做,一定要把擔任角色的主要演員湊在一起來商量,哪場是幕外,哪場是幕里。如果全本是十一場的話,就要按五場幕外,六場幕里分好。再規定好每一場戲的主要情節。確定哪些角色在這場戲里出場,哪些演員先出場,都做了規定。每場戲不能像‘拉洋片’那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拉過去就算數,而是要按照戲劇藝術的規律:做好構思與安排。規定了每場的情節以后,戲就初具輪廓了,然后就分派角包。演員少,角色多的,就要把戲不重的角色合并起來(這也要與幾個主要演員商量),然后分幕分場寫出來再廣泛吸收大家意見。這樣,一張幕表就基本上算寫成了。”④宋掌輕口述,范華群整理:《漫話幕表戲》,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2集,上海藝術研究1986年,第21頁。
可見,為了讓演員更好地演出,說戲先生們不但要幫他們理解情節,還要幫他們描摹、分析角色的心理狀態;只有高水平的說戲先生,才能最大程度上激發演員的表演天賦。
在說戲先生們的編排下,1921—1937年間,申曲引入了大量其他戲種的經典劇目。如彈詞戲的《珍珠塔》《孟麗君》,京劇的《火燒紅蓮寺》《十三妹》,文明戲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光緒與珍妃》等⑤上海滬劇院藝術研究室整理:《1916—1938年演出資料輯錄》,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2集,第130頁。。這是因為一方面這些戲目廣受歡迎,經久不衰,為當時市民所津津樂道,申曲自然也希望從中分一杯羹;而另一方面這些戲目大都是連臺戲,一連上演多日,能更長久地吸引觀眾。
(三)1938年以后的市民社會與劇本題材
1937—1938年可視作滬劇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戰爭的爆發嚴重影響了上海灘的娛樂行業,此前紅火的電影一度停滯。包括申曲在內的戲劇藝術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缺,適時彌補了這一時期城市市民的精神文明需求。
如上文所述,由于自身缺陷,申曲在傳統戲目上的表演并不占優勢,他們主動將目光轉向了電影、話劇以及中外文學作品。這些劇目的內容大多需要以時裝戲的形式呈現,為時裝戲成為滬劇主流奠定了基礎。
申曲對電影的改編相對較早。早在1924年,宋掌輕就將電影《孤兒救祖記》編排成了幕表戲①《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7頁。蔡豐明:《上海都市民俗》,第277頁。,是為滬劇史上的第一例。1941年,“滬劇”正式定名之后,真正“滬劇”意義上的“開山之作”是改編自美國電影的《魂斷藍橋》②《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68頁。。對話劇的改編則有1938年的《雷雨》③《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66頁。、1942年的《原野》④《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68頁。等;對文學作品的改編有1930年的《啼笑因緣》⑤《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65頁。、1939年的《駱駝祥子》⑥《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67頁。。1944年,還以莎士比亞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為底本,改編成了以中國社會為背景的《鐵漢嬌娃》⑦《上海滬劇志》,第二章《劇目》第二節“清古裝戲”,第64頁。。在原創劇本上,滬劇則借鑒《離婚怨》的成功經驗,主要取材于社會時事新聞,創作了《黃慧如與陸根榮》⑧《上海滬劇志》,第二章《劇目》第三節“時裝戲”,第65頁。《阮玲玉自殺》⑨《上海滬劇志》,第二章《劇目》第三節“時裝戲”,第66頁。《閻瑞生》⑩《上海滬劇志》,第二章《劇目》第三節“時裝戲”,第67—68頁。等。
從這些經典的申曲戲目中,可知上海市民所崇尚的藝術風格大多反映現實、貼近生活。而像《離婚怨》《啼笑因緣》之類表現家庭倫理、男女愛情的內容,尤其受到都市婦女群體的廣泛歡迎?《上海滬劇志》,《大事記》,第7頁。蔡豐明:《上海都市民俗》,第277頁。。
三、小 結
從源于鄉村的花鼓戲到深入都市的滬劇變遷中,可以看到地方戲曲和近代上海市民生活之間的相互影響。滬劇努力融入現代市民社會,通過在名稱、形式、內容上的不斷改變,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在海派文化的主流中占領一席之地;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上海社會的各類事件,小到家長里短、中到社會新聞、大到抗戰救國均在滬劇中有所折射,依此創作出《離婚怨》《阮玲玉自殺》《魂斷藍橋》等劇目。
除本文的上述研究之外,近代上海城市社會和滬劇之間關系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問題。比如滬劇對京劇、彈詞、話劇等其他曲藝的借鑒傳承有哪些表現,滬劇對周邊城市的社會生活是否有所影響,20世紀的報紙、雜志、廣播等傳媒業對滬劇的發展有沒有推動作用等等,都值得繼續探討研究。希望本文能開啟一個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新的觀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