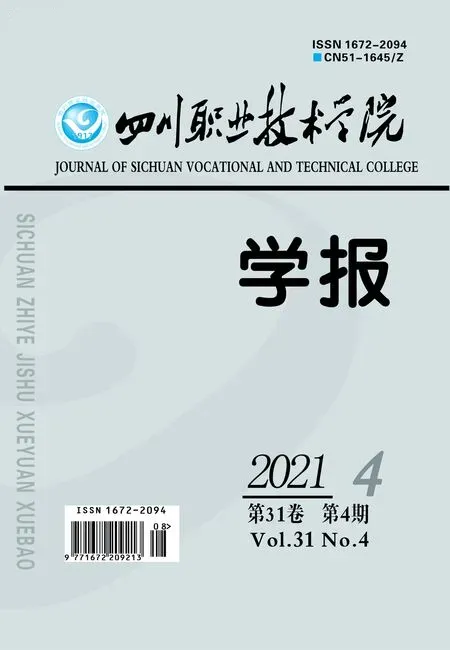家庭策略視角下“陪讀村”的形成及其實踐邏輯
——基于w 縣H 村的實地調查研究
袁錦銘
(安徽大學 社會與政治學院,合肥 230601)
陪讀即指陪同子女讀書,陪讀于古代是指大戶人家或官宦子弟為求得功名而找來年齡相仿的書童陪同子女讀書,而當代陪讀是為了提高子女學習成績及方便照顧子女生活,部分或全部家庭成員主動跟隨子女搬到學校所在的城市短期或長期居住的一種行為[1]。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家長的教育觀念逐漸改變,對子女教育的投資不斷增加,再加上城鄉教育發展明顯不均衡[2],鄉鎮和農村的教學質量已經不能滿足家長的需求,很多家長選擇把子女送到城鎮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時,為了照顧子女的生活和學習,家長選擇陪同子女學習,這不僅對親子關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也使得家庭以及陪讀成員各方面發生了重大改變。為了給孩子提供科學合理的家庭教育,幫助父母做出有關陪讀的理性選擇,有必要對陪讀原因及其影響進行深入探究。
一些研究表明,陪讀的對象已經從原來的中學生擴大到了小學生和大學生,其中中學生所占比例最大[3],陪讀的主體涵蓋祖父母、父親和母親,主要是母親[4]。有研究者從心理因素、教育因素和社會因素三個方面分析了陪讀的原因。對于陪讀類型的劃分,有學者將陪讀類型分為全職陪讀與兼職陪讀,其中兼職陪讀的家長指的是在陪讀的同時選擇在陪讀地靈活就業,即“半工伴讀”[5]。陪讀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家庭、學生、學校和社會,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6]。關于解決陪讀問題的政策,陳鋒等人認為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縮小城鄉教育差距[7]。張吉發倡導家長調整心態,消除攀比心理,走出教育誤區[8]。總結表明,目前對陪讀的研究主要涉及陪讀的概念、性質、類型、原因、影響和對策。但陪讀既屬于社會現象也屬于家庭行為,現有研究中從家庭層面分析陪讀原因的研究不多,對于陪讀群體的真正的生活世界關注甚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W 縣某高中陪讀家長為例,以家庭為研究框架分析“陪讀村”的形成,并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對陪讀群體的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探究,試圖尋找“陪讀村”經久存在的內在邏輯及其社會意義。
一、分析視角與研究資料來源
(一)分析視角:家庭策略
家庭是對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都能產生直接影響的社會單位,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領域轉變為半公共領域,和社會各系統相互作用。費孝通先生于20 世紀30 年代便在其著作《鄉土中國》中就提出過中國的“家”可以理解為“extended family”,即擴展的家庭[9],家庭的意義在于夫妻之間,更在于親子和代際之間[10]。從家庭的角度出發,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對家庭及其成員產生的影響以及家庭及其成員為應對社會變遷做出的調整策略。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的概念來源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研究家庭面臨新的外部環境時的決策過程,更好地理解家庭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11]。本文所分析的家庭策略是指家庭及其成員在面對子女學業問題時的決策過程。家庭策略主要是針對家庭問題提出來的,以家庭為研究框架,分析家庭內部決策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強調家庭成員的主動性、能動性,及其應對多元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的調整與適應,并對家庭的運行和發展做出合理的安排。在家庭受到外力沖擊時,家庭策略可以通過整合外部資源、充分發揮家庭成員力量,實現家庭發展的社會化和可持續性[12]。外力沖擊包含突發性自然災害(如旱澇災害)、經濟蕭條(如失業率增加)、家庭成員生命健康受到威脅(如車禍)以及政府政策的調整(比如教育政策)等。家庭策略的分析視角將宏觀的社會變遷過程與微觀的家庭成員行為及方式聯系起來,將對家庭的觀察和分析放在一個動態的背景中,從社會—文化情景的角度,動態地觀察家庭和家庭成員行為變化的細微,家庭策略因而成為研究家庭的能動性和變化的特殊性的分析工具。今天在面對教育問題的時候,家庭成員為適應變化而主動做出調整,該過程實際上是把家庭與社會變遷聯系起來,為我們重新理解當代中國和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基于上述觀點,本文從家庭作為一個生活共同體的社會事實出發,嘗試將陪讀成員置于家庭有機體中,基于家庭分工的策略視角,分析家庭的決策邏輯以及家庭成員的個體行動邏輯,進而呈現陪讀村的形成機制。首先,筆者從家庭的陪讀類型選擇方面,分析陪讀家庭的需求——陪讀家庭需要經濟來源并建立新的社會支持網絡。其次,筆者從原住家庭的成員分工方面,分析原住家庭的需求——原住家庭希望利用地理優勢,加快家庭發展速度。最后,通過陪讀村現象的啟發,討論陪讀村的形成邏輯并探討如何激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在給予子女陪伴的同時促進鄉村企業發展。
(二)研究地點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研究地點位于安徽省安慶市W 縣。W 縣總面積 1347.98 平方千米 ,轄 8 個鎮、2 個鄉 ,位于安徽省西南邊緣,皖贛交界處,長江下游北岸,一面負山,三面臨水,素有“水鄉澤國”之稱。W 縣下轄 8 個 鎮 ,2 個 鄉 ,共計 118 個行政 村 和 17個社區。當前W 縣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工業為輔,居民收入逐年來穩步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隨著認知結構不斷改善,人們對于教育愈發重視,多數家長在孩子高中畢業之前一直處于陪讀狀態。
現W 縣共有六所高中,兩所省重點高中、兩所市重點高中,兩所私人高中。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吸引著一大批農村的適齡兒童前來就讀,出于對子女健康的考慮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家長往往會陪同子女一同進入W 縣,在學校旁租房居住,方便對孩子的日常接送與監管,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陪讀居住群落。其中絕大部分家庭選擇的是單人陪讀的形式,即家庭經過商討,決定某一家庭成員獨自前來照顧適學子女,其他家庭成員外出務工、經商或在家務農,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
由于當地陪讀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租房業十分興盛。H 村地處學校附近,村內原住戶多將自家房屋分割成面積為20 至30 平米的小屋進行出租,年租金根據面積及居住條件,從5000 至12000 元不等。部分教師在校外居住,將校內教師用房出租給家長,年租金根據面積及居住條件,從5000 至20000 元不等。因陪讀規模大,且家長選擇住房時會選擇在離學校距離較近的住房,這也直接導致住房供不應求,所以即使居住條件簡陋且租金并不便宜,陪讀者仍選擇支付這份房租去租住距離學校較近的房屋。在調查中發現,陪讀者以女性為主,包括母親、(外)祖母等,其中陪讀母親在陪讀者中占比約為64%,且陪讀者多為兼職陪讀,兼職陪讀者在陪讀者中占比76%。
調查發現,H 村有服裝加工企業二十多家,這些服裝加工廠就是看中了陪讀者有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工廠老板大多為H 村村內居民,也有W縣各鎮人員,這些服裝加工企業規模較小,機器規模 15 至 20 臺,員工數量 15 至 20 名。由于員工技術水平有限,所以這些工廠僅負責服裝的生產和包裝,不負責需要專業技術的裁剪工作。各工廠均采用相同的管理制度,即計件工資制、彈性工作時間制度、“寒暑假”制和“不招新手”制。
筆者于2021 年1 月赴W 縣進行了為期20 天的實地調查。調查采用半結構訪談,根據事先擬定好的訪談提綱,在陪讀者集中居住的地區進行入戶調查。此次調查共訪談陪讀者27 人,其中男性2 人,女性25 人;房東5 人,服裝加工企業老板5人。對收集的訪談資料的編碼格式采用“調查地點(拼音首字母縮寫)+被訪者姓氏(首字母)+被訪者性別(M/F)+訪問日期+當日訪問序號”,如“HLQ-Z-F-202111601”表示在 2021 年 1 月 16 日在HLQ 訪談的第一個對象,姓Z,女性。
二、家庭策略視角下陪讀群體的選擇邏輯
從家庭策略角度來看,面臨陪讀選擇的家庭往往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問題:(1)陪讀成員的選擇問題,即選擇父母還是(外)祖父母的問題;(2)全職陪讀還是兼職陪讀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反映出家庭的兩大職能:(1)子代教育職能;(2)家庭經濟職能[4]。對處于成長期的家庭而言,不但要為家庭發展提供經濟基礎,還要為家庭可持續發展提供人力資本投資和保障。所不同的是,家庭的經濟職能需要在市場活動中實現,而子代的教育職能需要在家庭活動中實現。那么在家庭中誰應當將主要精力留在市場活動中,為家庭提供主要經濟來源,誰又應當將主要精力用于子代的陪讀中,這其中蘊藏著十分豐富的家庭策略。家庭策略表現出家庭決策的過程與結果,在家庭決策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誰?決策過程中各家庭成員分別是如何對家庭策略的最終結果產生影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家庭策略的最終結果產生影響?對于這類問題的思考可以將個人、家庭和社會變遷三者緊密結合在一起,進而理解三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家庭不是被動地受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是根據自己原有的特點對社會變遷做出反應,這種反應是家庭各成員之間的合力作用的結果,各成員在家庭中的地位影響著合力的方向抑或說使家庭策略的取向[13]。
(一)家庭的代際分工: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實地調查發現,在生活照料方面,父母與(外)祖父母在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上存在較大差異。年輕的父母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相較于年長的(外)祖父母更偏向于現代性。對于親代陪讀而言,父母對于孩子成績提高的期望值更大,而隔代陪讀更注重的是減輕家庭負擔。無論是選擇親代陪讀還是選擇隔代陪讀都是各家庭為使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決策。
案例1:曹某,女,65 歲,文盲。配偶因病去世,目前家里有5 口人,分別是兒子、兒媳、孫女、孫子。孫女目前大四,準備直接就業。兒子和兒媳均為初中文化水平,一直在江蘇工作,每月工資約為5000 至6000 元之間,除去日常開銷,年底大概能帶回5 至6 萬元,全家主要靠這筆資金來源維持生活。曹某目前身體狀況良好,但腿腳不利索,不可久站,平時會去服裝加工廠剪衣服線頭,工資大概1800 至2000。“我現在身體還行,能給孩子們幫點忙就幫點,他們現在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一家都得靠他們養,只能我來陪陪孫子。現在孫子處于高中關鍵期,學習上我也幫不了他什么,就希望在生活上能讓他吃飽了穿暖了。孫女馬上也出來工作了,孫子也快高考了,家里最難的日子馬上就可以熬過去了。”(HLQ-C-F-202111601)
在這種家庭里,祖輩有自理能力且能從事一些簡單的手工勞動,父輩在外務工,每年的收入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并能夠存儲部分資金以增強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在這種隔代陪讀的情況下,可以使家庭經濟狀態維持正常,不至于因陪讀開支大而使家庭經濟困難,且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家庭成員的勞動力價值。但隔代陪讀對于子女成績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陪讀只是為了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
案例2:李某,女,35 歲,初中學歷。目前家里6 口人,分別是公公、婆婆、丈夫、女兒、兒子。丈夫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8000 至10000 之間,除去日常開銷以及給家里的生活費之外,年底大約能帶回3 萬左右。李某公公71 歲,患阿爾茲海默癥,需要人照料,婆婆留在家照顧公公,李某丈夫的姐姐、姐夫在家開餐館,每周也會去照顧公公婆婆。李某在女兒讀高中之前一直與丈夫在外務工,每月工資5000 至6000 之間,直到女兒高一選擇回家陪讀。李某女兒高一,兒子小學二年級,為了能同時照顧兩個孩子,所以李某家將小兒子也轉學到了W 縣。李某大部分時間都圍繞著兩個孩子。女兒不需要李某接送,小兒子則需要李某接送。由于時間被分割的太過碎片化,所以李某平時會做一些手工竹編籃打發時間,一個竹編籃 20 至 30 元,一個月有 500 元左右的收入。“我現在沒辦法出去上班,兩個孩子都在讀書,家里老人身體也不好,幸好婆婆身體還好,可以照顧公公,不然我也沒辦法來陪讀了。我現在只希望在孩子的關鍵期給她提供一個好的環境,做父母的沒能在學業上給她太多指導,平時只能多和她溝通,適時督促她,只想盡我所能幫助她。”(HLQL-F-202111701)
在這種家庭里,祖輩因患疾病失去勞動能力需要有人照料,父親在外工作可以給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母親照料兩個孩子。盡管在陪讀期間,由于年輕母親暫停工作,會導致家庭收入大打折扣,但對于年輕父母而言,他們的教育觀念已經發生改變,他們更關心子女的心理狀態、學習成績以及親子關系,所以在家庭經濟能夠正常運轉的情況下,他們愿意在孩子的關鍵時期陪伴孩子。這表現出家庭在經濟理性和促進家庭成員發展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勞動力調整。
(二)家庭的夫妻分工:父親或者母親
陪讀意味著部分成員的主要精力將用于在家庭活動,導致家庭總收入的降低。對于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占據優勢的男性而言,退出以往的經濟生產活動要付出比女性更大的代價,家庭的收入來源得不到保障。基于家庭經濟理性的角度,一般家庭會選擇將在經濟活動中占據優勢的男性留在市場活動中,而將相對弱勢的女性留在家庭活動中,如上述案例2。對于在子女教育方面,女性較男性而言更為耐心,且大多數女性在生活照料方面比男性更有經驗。所以一般情況下,家庭會選擇母親陪讀,父親在外務工或經商。
案例 3:陳某,女,38 歲,大專學歷。家里 3 口人,分別是丈夫,兒子。丈夫在浙江經商,每年20萬左右。陳某屬于全職陪讀類型,平時孩子上學的時候陳某會去棋牌室打發時間,晚上會去跳廣場舞,結識不少朋友。“孩子他爸掙錢比我多,廠子也離不開他,而且孩子現在青春期,脾氣大,他爸脾氣也比較沖,兩個人一言不合就吵架。他爸也不懂照顧人,生活方面我照顧的更為妥貼。”(HLQ-C-F-202111702)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父親身體不好,也會出現父親陪讀或是夫妻共同陪讀的現象。家庭的一切決策都是在家庭成員能夠生活和發展得更好的基礎上考慮,所以在決策時會盡量照顧到每位家庭成員的狀況。
案例 4:肖某,男,41 歲,小學學歷。家里 4 口人,分別是妻子和兩個女兒。妻子在W 縣某服裝店當銷售,大女兒在W 縣銀行上班。肖某患有糖尿病,平時在附近做電工。“我的身體不太好,一不注意身體就不行,孩子他媽擔心我一個人在外面照顧不好自己,現在和我一起租住在這里陪讀。我現在白天在這附近做小工,家務活都是我包,孩子他媽在縣里上班,晚上到這邊來住,家里小孩懂事,現在高三了,我在這也呆了兩年了,學習上基本不用我們操心,我們主要還是想盡力做自己能做的,在生活、情感上照顧一下孩子,正常發揮的話應該可以考個好學校”(HLQ-X-M-202111801)
(三)陪讀方式的選擇:全職陪讀或者兼職陪讀
實地調查發現,陪讀者大部分人都選擇兼職陪讀,即半工伴讀。對于半工伴讀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原先活躍在市場中活動的勞動力轉到家庭中,增加了家庭開支的同時也減少了家庭收入,兼職陪讀可以適當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陪讀的居住條件沒有家好,而且離開了熟悉的社會支持網絡,陪讀者會感覺到孤獨與不適應,兼職陪讀過程中可以幫助陪讀者迅速建立起新的社會支持網絡,緩解陪讀者的心理壓力。
案例五:陳某,女,36 歲,初中學歷。家里9口人,分別是丈夫,公公、婆婆、兩個兒子、哥哥、嫂子和兩個侄子。丈夫在外經商,小兒子小學3年級,公公、婆婆在家經營超市,順便照顧小兒子。陳某在服裝加工廠上班,每月3000 左右。“我現在一個人在這里陪讀,周圍的人都出去做點兼職,就煮飯的時候回來坐會兒,那時候大家也忙也說不上幾句話。不出去做點事情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沒人說話很難熬的,我也就出去干點活,不僅可以管住我和孩子的日常開支,我自己也可以多認識些人,我們在一個廠里的人沒事還會聚聚餐跳跳舞,這樣陪讀的日子才不會太壓抑。”(HLQ-C-M-202111901)
綜上所述,無論是親代陪讀還是隔代陪讀,是父親陪讀還是母親陪讀,是兼職陪讀還是全職陪讀,陪讀都是家庭基于自身情況面對社會變遷所做出的主動性調整。對于陪讀中的農村家庭而言主要考慮經濟和子女教育兩個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環境的影響,農民家庭的發展目標不再僅僅為了基礎的生活保障,而是更加追求家庭的人才資源積累,各家庭也根據家庭發展目標的不同做出相應的陪讀策略,其目的都是為了家庭綜合利益最大化。
三、基于陪讀群體選擇的陪讀村村民的實踐邏輯
對于H 村原住民而言,將家庭住房隔成一間間20 至30 平米的小房間出租出去成為一筆不菲的家庭收入,且作為租客的陪讀家長,生活簡單,所以日常房屋管理比較方便。部分原住民也發現了陪讀家長除了洗衣做飯還有大量勞動力剩余,于是他們開始尋找新的商機,想要在村內發展適合陪讀家長打工的小型企業。他們發現,H村內大部分陪讀者曾去浙江等地做過服裝加工,對于服裝加工較熟悉,而且小型服裝加工企業一般采取計件工資制,具備彈性工作時間,十分適合在陪讀者聚集地發展。在具備地理優勢的前提下,為了使家庭能夠發展的更快,H 村原住民的代際分工以及工廠的選擇方面蘊含著豐富的家庭策略。
(一)家庭的代際分工
實地調查發現,H 村內管理房屋收租各項事宜的均為祖輩,他們的子女常年在外打工或在縣城繁華路段買了房子,所以會選擇將老年人接去身邊,將家里不住的房子出租出去。一方面,老年人適合收租。老年人身體各方面退化,不適宜較高強度的工作,收租相對較輕松。另一方面,出租家庭閑置用房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學校旁的房子供不應求,房租較高,所以有的家庭會搬回以前的老家或者是孩子們買的新房中居住,將學區房出租出去,增加家庭的收入;再一方面,祖輩通常會選擇去照顧孫子(女),以減輕子女壓力。有的家庭年輕夫妻上班,家中幼兒需要照料,所以年長者會去兒子或女兒家中照顧幼兒,自然就會選擇將老房租出去。
案例 6:何某,女,57 歲,小學文憑。家里 4 口人,分別是兒子,兒媳和孫子。兒子、兒媳是教師,二人在縣中心購房居住。孫子兩歲,何某住在兒子家,平時負責照顧孫子及收租。“我現在住在我兒子家里,在現在這個小區買了新房子之后,孩子們就讓我和他們一起過來住,把原來的房子出租出去。他們平時上班,家里有兩個小孩兒,我在這里能幫他們照料著,離老家也不遠,坐二十分鐘公交就到了,收租這些事情也簡單,有時候孩子們也會幫我去看看。”(HLQ-H-F-202112101)
(二)工廠的選擇
通過對服裝加工廠老板們的訪談中了解到,他們均為W 縣人,之前就在外地的服裝加工廠打工。一方面了解到陪讀群體日益擴大且存在大量的勞動力剩余,陪讀者需要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他們清楚服裝加工廠計件工資制和彈性的工作時間制度非常適合陪讀者,所以選擇在學校旁邊開辦服裝加工廠。
案例 7:何某,男,43 歲,小學文憑。家里 5 口人,分別是父親、母親、妻子、女兒。何某是H 村人,父母現在家務農,何某與妻子共同經營兩個服裝加工廠,女兒就讀大學。“我以前和我老婆在浙江做服裝加工,那邊很多都是咱們這邊的人,但是收入和大家的做工速度掛鉤,做得好的一年能拿十幾萬,慢的一年只能拿幾萬。我也是前幾年回老家陪孩子讀書,才發現這里很多陪讀者都想要找點事情做,而且我們這邊人很多都做過服裝加工,我就牽個線,做外面工廠的企業代理,從外面進原材料回來給大家做,這邊做得快的家長一年也可以掙個5 至6 萬,陪讀的額外收入挺好的,而且我們工廠的氣氛很好,大家平時出去聚聚餐,大家都多了些朋友。”(HLQ-D-M-202112501)
綜上所述,H 村村民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實現家庭勞動力與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加快了家庭的發展速度。首先,在家庭分工方面,安排勞動力弱者負責房屋出租事宜,勞動力較強者外出務工或經商,最大化實現家庭勞動力價值。其次,在家庭資源安排方面,將租金較高的學區房租住出去,祖孫三代一起生活,實現家庭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四、陪讀村形成的動力機制
陪讀村形成的動力機制的建構具有高度自覺、自為性,是陪讀家長與學校周邊住戶在科學的認識當前教育機制特點的基礎上,尊重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體能動性,建立健全陪讀村建設的動力機制,滿足陪讀相關群體需求的行為。通過對陪讀家庭與H 村原住家庭的家庭決策分析可以得出:陪讀村的形成及其運轉,是在教育機制運行背景下,相關家庭根據現實情況不斷調整,所最終形成的生活區域。
(一)外在動因:教育資源失衡
教育資源失衡始終是陪讀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自《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實施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各方面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教育資源不平衡仍是一項亟待解決的嚴峻問題。面對教育資源失衡的現狀,農村地區家長不滿足于當地落后的教育設施與師資力量,因此,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加優質的教育,他們寧愿花費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大的金錢,選擇在城市學校旁租房陪讀,這也就促成了城市學校旁一個又一個陪讀者聚集地的形成。
(二)內在動因:家庭觀念改變
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后,對于信息技術知識的需求量增大,社會的發展需要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勞動者來推動,沒有知識、文化和技術的民工較難有所作為。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過程中也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因此選擇加大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是家庭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最重要的途徑,對子女的教育既屬于家庭消費,也屬于家庭投資[14]。
有學者認為,當家庭處于陪讀階段時,陪讀者須放棄以往所從事的市場活動,導致其無法充分發揮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新的勞動力的配置會弱化家庭的經濟發展屬性,陪讀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積累會增加教育投資與家庭發展的風險性[15]。但不可否認的經驗事實是,隨著陪讀規模的擴大,因陪讀所形成的生活圈不斷進行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陪讀家庭的經濟需求與陪讀者個人的情感需求。
陪讀者在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合力作用下,選擇在陪讀村內生活,陪讀村原住民針對陪讀現象順勢而為,在出租房子的同時建立小型服裝加工企業以滿足租客需求。在需求與供應中,一個新的生活圈有條不紊地運行著。從農村到城中村,面對空間轉變帶來的種種挑戰,陪讀者與原住民共同努力,積極調動自身能動性,實現了空間再造,在城市空間建構了新的社會空間——“陪讀村”。“陪讀村”的建構為陪讀者提供了情感、經濟支持,降低了陪讀的成本,減輕了家庭的壓力。
五、結論與討論
研究發現,陪讀者的選擇會依據家庭情況的不同而分為親代陪讀與隔代陪讀,父親陪讀與母親陪讀,全職陪讀與兼職陪讀這幾種類型。實際上,陪讀類型的多樣化就是家庭在面臨變化時家庭策略的產物。首先農民家庭通過對家庭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即身體狀況良好的老年人陪孩子,年輕人外出務工,最大程度上調動勞動力,這樣既可以給孩子一個較好的生活環境,也實現了在陪讀條件下的家庭利益積累最大化。其次,通過判斷家庭成員在市場活動以及家庭活動中的優劣水平,來決定父親陪讀或是母親陪讀,即選擇在市場活動中占據優勢的男性在外務工,在家庭照料中占據優勢的女性在家陪讀,這樣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位家庭成員的勞動力價值。最后,由于陪讀生活對家庭和個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改變,在陪讀過程中,陪讀者根據對家庭經濟狀況的判斷以及自身重構社會支持網絡的需求而選擇兼職陪讀或全職陪讀,即家庭經濟一般或困難的陪讀者會選擇兼職陪讀,而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陪讀者會選擇全職陪讀。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家庭決策與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及家庭成員在各領域的能力大小相聯系,蘊含著豐富的家庭策略。
我們知道,農村家庭陪讀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資源在城鄉間及農村內部的不均衡,但是,要想改變這種不均衡,必定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過程。陪讀從來不是一個家庭的最優選擇,而是一個家庭在面對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和高考制度背景下所做出的次優選擇,因為陪讀常伴隨著陪讀家庭支出的增大。陪讀群體中,占據比例最大的兼職陪讀者兼具陪讀者與農民工的雙重身份,該選擇是在家庭活動和市場活動之間所做出的理性選擇,是小型企業與農民家庭發展目標合力作用下的結果。HLQ 作為W 縣其中一個陪讀村雖然不大,但卻已經形成了適宜陪讀者生存的社會空間,這背后的生成邏輯值得我們思考。如果在短期我們無法實現教育資源均衡,是否可以通過在當地引進合適的小型企業以此緩解陪讀對家庭所造成的沖擊?一方面可以實現當地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滿足陪讀者的需求,還有待進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