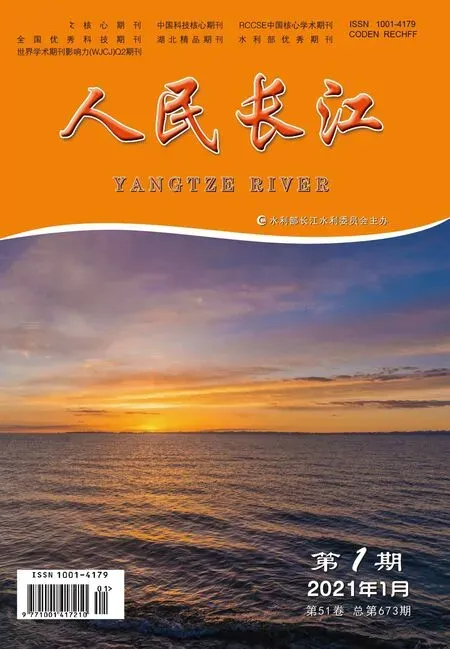不同大氣強迫數據集對流域地表溫度模擬的影響
孟 含,金 繼 明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地表溫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LST)是表征全球變暖的關鍵物理因子[1]。LST通過蒸散發過程影響地表能量收支和水分收支[2],其主要控制感熱通量的大小,從而改變空氣溫度。LST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土壤含水量和土壤蒸發量,進而影響區域植被生長和農業生產。地表溫度升高會加劇地表蒸散,致使全球多數地區干旱狀況明顯加劇[3]。因此,LST時空分布的準確評估是進一步研究地表蒸散發的重要依據,對加深陸氣相互作用過程的理解、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和流域水資源變化以及預防旱災和科學灌溉至關重要。
目前,可以通過站點觀測、遙感技術和模式模擬獲取LST數據。雖然傳統的站點觀測方法可以獲得高精度的LST值,但因站點數量及位置等的局限性,這些觀測值只能表征局部的LST變化特征。通過衛星遙感技術獲得的LST數據不僅具有較高的分辨率,且能充分描述其空間分布及變化特征,但是遙感數據時長較短,不能體現歷史LST的變化特征。而陸面模式能夠模擬出廣泛、長期、連續的高分辨率LST時空分布數據,既能模擬歷史LST的變化,亦能對未來LST變化進行預測。
通用陸面模式模擬結果的準確性與大氣強迫數據集的質量緊密相關,強迫數據集自身的誤差會傳遞至模擬結果。目前已有學者針對不同大氣強迫數據集對陸面模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Wang等[4]在通用陸面模式(Community Land Model version 4.5,CLM4.5)中輸入不同強迫數據集后模擬了蒸散發量、土壤濕度、雪深、徑流等物理量,結果表明使用多個強迫數據集的模擬結果的總體平均值通常優于單個模擬結果;降水、氣溫和向下的短波輻射等的差異導致了模擬結果的差異。Yin等[5]分析了4種大氣強迫數據集對中國土壤濕度模擬的影響,結果表明不同數據帶來的差異較大。沈潤平等[6]將國家氣象信息中心發布的陸面數據同化系統CLDAS(CMA Land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中的兩個版本作為大氣強迫數據,驅動CLM4.5模擬了青藏高原10 cm土壤溫度,結果表明高質量的大氣強迫數據能顯著降低模擬的誤差。孟現勇等[7]利用CLDAS大氣強迫數據集驅動CLM3.5模擬了中國新疆地區土壤溫度,表明 CLDAS 數據驅動CLM3.5模式能夠得到較為精確的中國新疆地區多年平均土壤溫度時空分布特征以及變化規律。朱智等[8]對5種再分析地表溫度資料(ERA-Interim,ERA-Interim/Land,JRA-55,NCEP/NCAR,NCEP/DOE)在中國區域的適用性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JRA-55數據在空間分布上最接近觀測數據。5種再分析資料在東部地區的適用性較好,但在青藏高原地區和西北西部地區的適用性較差,且5種再分析資料都存在低估現象。Guo等[9]利用CLM4.5和多個大氣強迫數據集模擬了近地表土壤凍融循環的變化,發現CRU-NCEP(Climate Research Unit-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數據集驅動模式得到的結果較接近實測數據,表明該數據集可優先作為未來大氣強迫預測的基礎數據集。綜上所述,陸面模式模擬的精確性與大氣強迫數據的數據精準度聯系緊密。然而,目前針對不同強迫數據集對通用陸面模式模擬LST的影響的研究亟待加強。
本研究選取了CLM默認強迫數據集CRU-NCEP以及目前應用較廣泛的CMFD(China Meteorological Forcing Dataset)[10-12]、GSWP(Global Soil Wetness Project)[13-15]3種大氣強迫數據集驅動通用陸面模式CLM5.0,模擬了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2003~2010年的LST,對夏季、冬季LST的多驅動輸出模擬結果進行了對比分析。
1 研究區概況
黃河全長約5 464 km,發源于青藏高原東部,穿過黃土高原進入華北平原,最后匯入渤海[16]。黃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點在鄭州附近的桃花峪[17]。本文的研究區為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如圖1所示,經緯度范圍是95°54′E~113°35′ E,32°12′N~41°50′ N,西起青藏高原東部,東至華北平原西部,南至秦嶺北麓,北至陰山[18],面積約為72.31萬km2。研究區內氣溫空間差異性較大,上、中游的年平均氣溫分別為1~8 ℃及8~14 ℃[19]。黃河流域上中游大部分位于溫帶干旱、半干旱地區的生態脆弱帶,其對氣候變化異常敏感,尤其是在多年凍土分布廣泛的黃河源區,地表溫度的變化一方面會影響冰雪凍土的消融,另一方面會影響區域內不同下墊面的蒸散發,進而影響黃河上中游乃至全流域水資源量的變化[20]。

圖1 黃河流域上中游Fig.1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Basin
2 研究數據
2.1 大氣強迫數據
CLM5.0模式所需的大氣輸入變量包括降水量(mm/s)、2 m氣溫(K)、2 m比濕(kg/kg)、風速(m/s)、向下短波輻射(W/m2)、向下長波輻射(W/m2)以及近地表氣壓(Pa)。本研究利用CMFD、GSWP、CRU-NCEP三種大氣強迫數據集驅動CLM5.0進行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LST的模擬。
CMFD數據集(http://westdc.westgis.ac.cn/data/7a35329c-c53f-4267-aa07-e0037d913a21)來自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Institute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該數據集是在現有的多個數據資料的基礎上,與中國氣象局觀測的氣象數據相結合得到的再分析數據集。其時間分辨率為3 h,空間分辨率為0.1°。
GSWP數據集(http://hydro.iis.u-tokyo.ac.jp/GSWP3/)是全球土壤濕度項目(Global Soil Wetness Project,GSWP)運用國際衛星地面氣候計劃(International Satellite Land Surface Climatology Project,ISLSCP)提供的資料,產生的一套多模式集合的數據集[21]。GSWP數據共有3期,本研究采用的是第3期,其時間跨度為1901~2010年,時間分辨率為3 h,空間分辨率為0.5°。
CRU-NCEP數據集(http://dods.extra.cea.fr/data/p529viov/cruncep/)是由兩個現有數據集合成的,這兩個數據集分別是由氣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研發的0.5°的月數據和由國家環境預測中心和國家大氣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a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EP-NCAR)開發的2.5°再分析產品。本研究使用了第四版CRU-NCEP數據,時間分辨率為6 h,空間分辨率為0.5°。
2.2 觀測數據
由于在GB/T 35221-2017《地面氣象觀測規范》中規定:LST傳感器放在裸地上,要求該地段地表疏松、平整且無草[22]。站點觀測數據為該地段的裸地地溫。而本文的研究對象LST根據地表覆蓋類型的不同,可能為裸地表面溫度、植被冠層溫度、雪表層溫度,這與MODIS(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通過衛星熱紅外測量獲得的LST相對應[23]。因此,通過衛星熱紅外測量得到的MODIS產品適用于對大面積LST模擬結果的評估[24]。本研究選取的LST數據產品MOD11C3和MYD11C3第五版,是分別由Terra和Aqua衛星提供的包含每個像素LST和發射率值的全球數據產品(MOD11B1和MYD11B1)通過重采樣和計算后得到的月平均數據。產品投影為等角投影,空間分辨率為 0.05°。本研究將兩套數據求平均,選取2002年12月至2010年12月LST數據作為觀測數據進行對比。
3 研究方法
3.1 CLM模式介紹
CLM來自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National Center of Atmospheric Research),是目前國際上較為完善的陸面模式之一[25]。本研究使用的CLM5.0模式是CLM的最新版本。
CLM5.0用嵌套的次網格結構來描述空間異質性,每個網格有3個層次,第1層為陸地單元分類,有冰川、湖泊、城市、植被和作物(打開作物模式選項時);第2層是柱單元,分別由25層土(其中20層為土層,其余的為基巖層)和10層雪(視雪的深度而定)表示;第3層是植被單元上的植被功能類型或裸地。模式按照植被的生物、物理以及化學性質將植被分為16種植被功能類型。CLM5.0的地表參數空間分布和季節氣候學來源于MODIS衛星地面數據產品[26]。
3.2 LST的計算
本文選取了2003~2010年的LST進行模擬,3組模擬實驗分別記為CLM-CMFD,CLM-GSWP,CLM-CRUNCEP。本研究在模擬時已通過spin-up獲得基本穩定的初始場。
在CLM模式中,地表包括植被表面的冠層、裸露地面的土壤表層和裸露雪地表面的雪層表層。由于模式并沒有直接輸出LST,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向上長波輻射、向下長波輻射以及地表發射率來計算得到LST的模擬值[27]:
(1)
式中:RLW↑和RLW↓分別為向上和向下的地表長波輻射,W/m2;σ為Stefan-Boltzmann常數,值為5.67×10-8W/(m2·K4);εg為地表發射率,取值范圍為0.95~1.00。
3.3 模擬結果的評價指標
本研究采用以下評估方法來衡量不同大氣強迫數據驅動下LST的模擬值與觀測值之間的差別[28]。
(1) 偏差。
(2)
(2) 均方根誤差。
(3)
(3) 相關系數。
(4)

4 結果分析
4.1 時間尺度對比
3種大氣強迫數據驅動下CLM5.0對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2003~2010年間冬、夏季節LST的模擬值及觀測值如圖2和圖3所示。在冬季,CLM-GSWP方案的模擬值最接近觀測值,且出現高估,而另兩種方案的模擬值出現低估。在夏季,3種方案模擬值均出現高估,其中CLM-CMFD的模擬值最接近觀測值,CLM-GSWP和CLM-CRUNCEP兩種方案模擬值之間較接近。

圖2 冬季月平均LST的觀測值和模擬值的時間序列Fig.2 Time series of observed and simulated monthly mean LST in winter

圖3 夏季月平均LST的觀測值和模擬值的時間序列Fig.3 Time series of observed and simulated monthly mean LST in summer
2003~2010年冬、夏季區域平均LST模擬值與觀測值的偏差,均方根誤差和相關系數的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3組實驗的LST模擬值與觀測值間的R值均不小于0.93,這說明3種大氣強迫數據驅動下CLM5.0對研究區冬、夏季LST變化趨勢的模擬效果均較好。而通過對比Bias和RMSE發現,3種方案對夏季LST模擬效果均高于其對冬季LST的模擬效果。冬季的3種實驗方案中,兩組方案(CLM-CMFD和CLM-CRUNCEP)的Bias出現負值,夏季的Bias均為正值。綜合Bias,RMSE和R來說,區域平均LST模擬值中,CLM-GSWP方案的模擬效果最好,夏季CLM-CMFD方案的模擬效果最好。

表1 LST觀測值和模擬值的Bias,RMSE值與R值
4.2 空間尺度對比
CMFD、GSWP和CRU-NCEP三種強迫數據驅動下,CLM5.0對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冬、夏季2003~2010年多年平均LST觀測和模擬的空間分布如圖4和圖5所示。由圖4~5可知:3種實驗方案均能較好模擬出與觀測值較接近的LST空間分布,都抓住了研究區西部LST較低,關中平原LST較高的空間分布特征,都能體現LST隨緯度、季節、地形、和土地利用類型變化而變化的特點。
冬季LST受緯度和地形影響較大,模擬和觀測值都出現了在西部區域自東向西降低,在中部和東部區域成帶狀自南向北降低的分布特征。研究區西部地處青藏高原,海拔較高,出現了最低LST,低于-15 ℃。在研究區的北部和東北部以及中南部有部分狹長區域LST也較低,因為研究區北部為陰山山脈,東北部為呂梁山,中南部狹長區域為六盤山,地形因素對黃河流域上中游的LST影響較大。

圖4 冬季LST的觀測值和不同方案模擬值的空間分布(單位:℃)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ST in winter based on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s of different schemes

圖5 夏季LST的觀測值和不同方案模擬值的空間分布(單位:℃)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ST in summer based on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s of different schemes
夏季LST的空間分布依舊出現西部和中、東部差異較大的現象,西部夏季LST雖高于0 ℃,但仍然較低,約為4 ℃~10 ℃,中部和東部大部分區域均高于20 ℃。在關中平原的北部有兩處區域明顯低于周圍LST,是由于該區域土地利用類型為森林,植被覆蓋率高,植被蒸散發大,導致潛熱通量較大而感熱通量較小,進而使得LST較低。
冬季LST模擬值與觀測值的偏差、均方根誤差以及相關系數空間分布如圖6所示,CLM-GSWP方案的LST模擬值在大部分地區比觀測值偏高,而CLM-CMFD和CLM-CRUNCEP的模擬值在大部分地區比觀測值偏低,且CLM-CMFD方案的模擬值在關中平原的小部分區域出現了異常高溫,這是由于CMFD強迫數據集中向下長波輻射和向下短波輻射比其他兩個大氣強迫數據集高。對比RMSE可以發現,CLM-CMFD方案的冬季LST模擬結果較差,而CLM-GSWP的模擬結果總體上較好。3 種方案模擬值與觀測值的相關系數在西部較低,在中部、東部較高。
夏季3種方案模擬值與觀測值的偏差、均方根誤差以及相關系數如圖7所示,CLM-CMFD方案的LST模擬值與觀測值的Bias較小,CLM-GSWP和CLM-CRUNCEP的模擬值相近,由RMSE和R的空間分布可知,夏季LST模擬結果中,CLM-CMFD的模擬值明顯優于CLM-GSWP和CLM-CRUNCEP的模擬值。局部區域模擬值與觀測值相關性不夠顯著,可能是由于強迫數據集在這些區域上的向下短波輻射數據與觀測數據存在一定誤差,更確切的原因還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做更深入的探索。
5 討 論
LST的模擬是陸面模式中較為關鍵的部分,其時空分布的準確評估至關重要。而利用通用陸面模式模擬LST的準確性與大氣強迫數據集的精準度聯系密切。雖然目前已有研究直接對多種LST再分析資料進行了適用性評估[8],也有研究對比了不同陸面模式對LST的模擬能力[29-30],另外一些研究主要針對蒸散發量、土壤濕度、雪深、徑流等物理量探究了不同大氣強迫數據集對模型模擬結果的影響[4-5],但尚未有研究探索不同大氣強迫數據集對CLM5.0模擬LST的影響。本研究利用3種大氣強迫數據集(CMFD,GSWP,CRU-NCEP)驅動CLM5.0模式模擬了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2003~2010年冬夏季的LST,并對其進行了對比分析。由于本文選用的觀測數據為MODIS數據,其在日尺度以下不同時刻的空間缺測情況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在月、季節和年尺度上進行了LST的模擬與分析,未來有必要進一步開展更精細的時間尺度上的模擬。

圖6 3種方案中冬季LST模擬值與觀測值的偏差、均方根誤差以及相關系數Fig.6 Bias,RMSE and R between simulations in three schemes and observations of LST in winter

圖7 3種方案中夏季LST模擬值與觀測值的偏差、均方根誤差以及相關系數Fig.7 Bias,RMSE and R between simulations in three schemes and observations of LST in summer
6 結 論
(1) 陸面模式CLM5.0對LST的模擬結果受大氣強迫數據的質量影響較大。雖然3種方案均能較好地模擬出LST的時空分布,但不同強迫數據集驅動下的結果仍然有明顯差異。
(2) 在冬季LST的模擬中,GSWP數據集驅動下CLM5.0的模擬結果最好,偏差為0.87 ℃,均方根誤差為1.24 ℃,相關系數為0.95;而在夏季,CMFD數據集驅動下CLM5.0對LST的模擬結果最好,偏差為0.54 ℃,均方根誤差為0.63 ℃,相關系數為0.95。
(3) 在基于陸面模式對未來LST進行模擬時,可以選用CMFD數據集和GSWP數據集分別驅動模式。其中,可選取CMFD數據集驅動的夏季LST結果和GSWP數據集驅動得到的冬季LST結果作為最終的模擬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