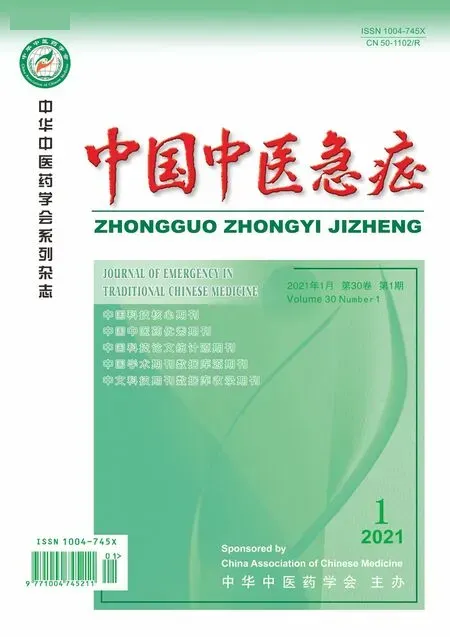“肺炎1號”聯合西醫常規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回顧性研究*
王林群 胡剛明 巴元明 賀朝雄 李偉男 張 馨
(1.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1;2.湖北省漢川市人民醫院,湖北 孝感 432300;3.湖北省中醫院,湖北 武漢 430061;4.湖北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湖北 武漢 430061;5.湖北省中醫藥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61)
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發伊始,在國醫大師梅國強教授的指導下,巴元明教授團隊擬定的“肺炎1號”是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推薦的4個官方組方之一[1],并獲得省藥監局備案批號(鄂藥制備字Z20200003)。筆者進行了“肺炎1號”聯合西醫常規治療新冠肺炎的回顧性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診斷標準參照文獻[2-5]執行。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年齡18周歲以上;具有COVID-19影像學特征的住院患者。排除標準:治療期間不能保證服藥依從性者,難以通過口服給藥者;合并嚴重原發性呼吸系統疾病,或患有需與COVID-19相鑒別的其他病原微生物型肺炎者;孕產婦,尿妊娠試驗陽性者;合并有惡性腫瘤、精神疾病等其他系統惡性疾病者;合并有其他嚴重疾病如尿毒癥、嚴重心力衰竭者;COVID-19危重型者。
1.2 臨床資料 臨床分型參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2],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采用病例回顧性分析方法,按治療方法的不同,將湖北省中醫院收治的47例患者病歷資料作為治療組,漢川市人民醫院早期收治的40例患者病歷資料作為對照組。治療組男性19例,女性28例;年齡20~64歲,平均(44.68±11.42)歲;病程 2~15 d,平均(5.89±4.76)d;基礎疾病為心血管系統疾病11例,內分泌系統疾病4例;普通型44例,重型3例。對照組男性19例,女性21例;年齡20~64歲,平均(49.70±13.13)歲;病程1~21 d,平均(6.47±5.24)d;基礎疾病為心血管系統疾病8例,內分泌系統疾病2例;普通型37例,重型3例。兩組性別、年齡、病程、基礎疾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治療方案參照文獻[2-5]的方案:臥床休息,支持治療,有效氧療措施,抗病毒治療,抗菌藥物治療,糖皮質激素、腸道微生態制劑等。治療組加用“肺炎1號”:柴胡20 g,黃芩10 g,法半夏10 g,黨參15 g,全瓜蔞10 g,檳榔10 g,草果15 g,厚樸15 g,知母10 g,芍藥10 g,生甘草10 g,陳皮10 g,虎杖10 g。水煎服,每天3次,每次200 mL。
1.4 觀察項目 1)統計患者退熱時間、新型冠狀病毒核酸轉陰時間、出院癥狀、治療轉歸等。如果記錄中缺失數據,通過與主治醫師溝通獲取數據。2)記錄出入院癥狀并積分。根據發熱、咳嗽、乏力、呼吸困難的程度分別記分。發熱:無發熱計0分;診前24 h最高腋溫37.3~37.9℃計1分;診前24 h最高腋溫38~39℃計2分;診前24 h最高腋溫>39℃計3分。乏力:無乏力計0分;輕微乏力計1分;乏力明顯,少氣懶言計2分;全身無力,不能起床計3分。咳嗽:無咳嗽計0分;偶爾咳嗽計1分;間斷咳嗽,不影響休息和睡眠計2分;咳嗽頻繁,對休息和睡眠有影響計3分。呼吸困難:無呼吸困難計0分;安靜時無呼吸困難,活動時出現計1分;安靜時有輕度呼吸困難,活動時加重,但不影響睡眠和進食,無明顯缺氧計2分;明顯吸入性呼吸困難,喉鳴音重,三凹征明顯,缺氧和煩躁不安,不能入睡計3分。根據惡寒、咯痰、咽痛或咽癢、鼻塞流涕、腹痛、腹瀉、惡心嘔吐、納差、頭身痛、肌肉酸痛、胸悶、氣短、頭暈頭痛癥狀的有計1分,無計0分。
1.5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治療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退熱時間、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的比較見表1。兩組退熱時間無顯著差異(P>0.05),兩組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差異顯著(P<0.05)。
表1 兩組退熱時間、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比較(d,±s)

表1 兩組退熱時間、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比較(d,±s)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組 別 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n 時間 退熱時間治療組對照組8.68±4.18△12.14±4.08 47 40治療前治療后3.61±1.92 3.68±0.87
2.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 見表2。兩組治療后癥狀積分均明顯降低(P<0.05),且治療組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
治療后1.33±1.93*△2.31±1.16*組別治療組對照組n 47 40治療前6.12±4.54 7.22±2.40
2.3 兩組病情轉歸的比較 治療組死亡0例,對照組死亡1例,兩組由普通型轉重型各1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 論
COVID-19 屬于中醫學“溫疫”“疫”病范疇[6]。COVID-19的病邪性質為夾濕的疫癘毒邪。清·朱蘭臺《疫證治例》云“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失時……中其毒者,率由口鼻入,稽留氣道,蘊蓄軀殼,病發為疫,證類傷寒”,明確說明了疫病的癥狀和“傷寒”類似。明·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到疫毒侵襲,從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未發之時,未有感覺;交并營衛而發,離原而表里分傳。解于太陽為順;若傳于內,毒邪內陷則為逆,或陷于陽明(目痛、鼻干)、或陷于少陽(口苦、惡心欲嘔、寒熱)。清·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云“吸受穢邪,募原先病”“穢濕邪吸受,由募原分布三焦”,指出溫疫毒邪由口鼻而入,內伏膜原,繼而彌漫三焦,上犯心肺,中阻胃腸,下困肝腎的病機演變規律。疫氣裹挾寒濕侵襲體表,表氣郁閉,則見低熱或不發熱,微惡寒,肢體酸痛等表證;疫氣從口鼻而入,侵入上焦肺衛,肺宣發肅降失常則出現咳嗽、胸悶、呼吸困難等上焦郁閉的臨床表現。疫邪從皮毛而入循六經由表及里進行傳變;亦可從口鼻經氣道,循三焦傳變。隨著疾病的發展,或熱化,或寒化,或燥化。清·王士雄在《溫熱經緯·仲景疫病》指出濕熱疫毒彌漫三焦表現為“陽中于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酸,所為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上焦怫郁,藏氣相熏,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沖,脾氣不轉,胃中為濁”“嚏而出之,聲嗢咽塞”“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不論寒化、熱化,均具有明顯的濕毒裹挾之癥,病位在肺,累及脾胃。
《疫證治例》認為疫毒郁于少陽,樞機不利,治宜和解少陽、透邪解毒。《溫熱論》中指出“溫疫病初入膜原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陷而入為險惡之病;舌色絳而上有黏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之”,清·雷少逸《時病論》亦說“所謂穢濁,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澀之藥,益使穢濁之邪,膠固氣分,而無解病之期”。通過宣肺降濁,芳香化濕之法,截斷其內陷之路,使濕濁之邪從胃腸而解。“肺炎1號”是在國醫大師梅國強教授指導下,巴元明教授團隊在COVID-19的診療實踐過程中逐漸確定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4個官方推薦組方之一,由柴胡陷胸湯、達原飲化裁。全方具有和解少陽、化濕解毒之功效。本次COVID-19屬于疫癘毒邪夾濕作祟,因此治療應重視祛濕化濁、辟穢解毒,用氣清性潔、芳香辛烈之品以化濁避穢、宣通氣血,慎用清熱解毒。若過度使用寒涼藥物,導致濕邪加重,出現“冰伏”現象,不利于疾病康復[7]。因此,“肺炎 1 號”去掉了“小陷胸湯”之黃連。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初期可用解表藥:麻黃、陳皮、厚樸、藿香等;中期可用清熱藥:石膏、知母、大黃等;重癥期可用人參、山茱萸;后期可用補虛藥和半夏、陳皮等。以上用藥特色在“肺炎1號”的處方中均有體現[8]。本研究中,兩組退熱時間無顯著性差異,可能由于突發疫情,在疫情之初,部分患者不能及時入院治療,在院外已經治療,或使用激素、免疫支持治療有關。在新冠病毒核酸轉陰時間方面,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說明中西醫結合治療能縮短新冠病毒核酸轉陰的時間。治療組兩組患者癥狀積分治療后均明顯降低,與治療前比較有顯著性差異,且治療組治療后與對照組治療后有顯著差異,說明“肺炎1號”能明顯改善COVID-19患者發熱、咳嗽、乏力等癥狀。
在抗病毒的同時,中醫藥干預的優勢還在于可調節人體免疫功能,激發機體自身防御抗病能力,達到祛邪與扶正相結合。臨床應“謹守病機、隨證治之”,運用和解少陽、開達膜原、辟穢化濁、活血化瘀和健脾益氣等方法,及時“截斷扭轉”病勢,使輕型患者趨向痊愈,普通型患者控制其病情向重型、危重型轉化,利于疫情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