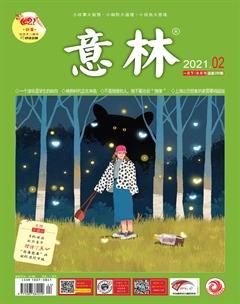融在豆腐里的年味
桂孝樹

邁進臘月的門檻,就聞到了年的味道,這個時候的鄉村都被年味包圍著。外出打工的人們背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回到家鄉,一路上的鄉民們手上提著,肩上挑著,車上搭著大大小小的年貨。
看著為年貨而忙碌的鄉親,品味著家家戶戶飄出的濃濃豆腐香,仿佛家鄉那一塊塊柔軟的豆腐在我手上冒著絲絲熱氣,蒸騰飄逸出滋心潤肺的香甜,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時候的年味。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農歷臘月二十五打過年豆腐。家鄉的賽陽豆腐歷史悠久,外觀與普通豆腐無異,但口感頗有不同。使用廬山的泉水,柴火灶燒漿,正宗的純手工制作,口感特別鮮美,非常好吃。
每到這個時候就是我姊妹五人非常高興的日子,像豆腐之類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享用,特別是打過年豆腐,場景比較莊重,在農家人看來“豆腐”,就意味著“渡福”呵,寄托了一家人對新一年的祝福與期待!所以一定要打好。
打豆腐其實是一件挺辛苦的活兒,頭天晚上媽媽就用簸箕把黃豆簸干凈,用篩子把雜質篩出來,并用磨子磨破褪去黃豆殼,我最喜歡干的活是破黃豆,比起磨豆腐來那是很輕松的活,媽媽將磨好的黃豆用水浸泡直到把黃豆泡軟了,等到開始磨豆腐時,一勺子、一勺子的被浸泡過的黃豆從磨孔中送進去,奶白色的豆漿也就源源不斷地從磨子的四周流出,一桶黃豆要磨上大半天。
我們姊妹幾個人分工負責,弟弟太小不懂事在一邊看著我們做,三妹年紀小點就負責用勺子下磨,母親、我和大妹、二妹兩人一組輪流推磨,當豆腐磨好時母親開始忙碌著,從灶屋頂上系著一條繩子懸著的木質十字架,對著下面大鍋,四角系一塊帳子布,然后把磨好的豆漿倒進帳子布里,濾出的豆汁流進下面的大鍋里。鍋下的灶里塞進大柴塊,燒起大火,到豆漿翻滾時停火,豆漿煮好后倒進一口半人高的大木桶里,母親便用搟面杖在小木桶內調好石膏水(即鹵水),邊往缸里慢慢地、細絲般地倒,邊攪動豆漿,名曰:點漿,也就是點豆腐。食用石膏經燒、磨,碾成粉末,用涼水化開即成鹵水。
石膏汁少了豆腐太嫩;多了、粗了,豆腐太老,不好吃。待豆漿變成豆花時,然后用水缸蓋子蓋好。不出半個小時,就生出一大桶豆腐腦。豆腐腦又白又嫩,觀若凝脂,舀似凍乳,撫之如綢似錦,觸之即破,含之即化,品之味甘,食之潤喉。放點白糖慢慢地喝,那個香味啊,沁人心脾,這個時候母親總是給我們五人每人盛上一大碗,心急的我還沒有來得及品味,嫩嫩滑滑的豆腐腦從喉嚨滑下肚,含都含不住,直到現在我依然忘不了豆腐花味道。
最后是包豆腐,將冷卻好的豆漿小心地舀進早已鋪好放在桌子上的過濾包袱里,母親舀完后包起來,蓋上木板,用大石頭壓上,擠掉水分,這叫“壓豆腐”,壓上一個夜晚,第二天早上,一包白嫩的過年豆腐就打好。媽媽將包袱打開,把壓好的豆腐劃成小方塊,撿起來放到盒子里,等待過年做菜。
豆渣放在鍋里炒熟后,等完全冷卻后,捏成圓球,放在有草的籮筐里,上面蓋上草,用爛棉襖保溫。過幾天后,豆渣表面長出了毛,說明酶渣已經酶好了,拿出來切成半圓形狀,曬干,豆渣加臘肉,粉條做湯,味道鮮美。
這時候全家人都是一臉的幸福,年真的來了,我們好像看到了新一年最美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