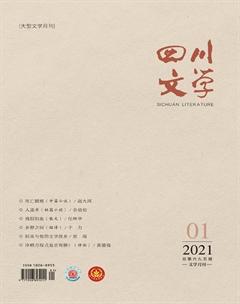阿來與他的文學故鄉(xiāng)
梁海
2020年7月,中央電視臺播放了系列紀錄片《文學的故鄉(xiāng)》,繪制了賈平凹、阿來、遲子建、畢飛宇、劉震云、莫言六位作家的文學地理軌跡,講述他們如何把現實的故鄉(xiāng)轉化為文學的故鄉(xiāng),從而探尋文學發(fā)生的起點,抵達精神世界的原鄉(xiāng)。其實,每一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都會與他的故鄉(xiāng)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童年記憶、民間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甚至融化到他潛意識深處的家族記憶,都會呈現在他們的文學故鄉(xiāng)里。文學與故鄉(xiāng)的關系,的確是一個永遠也討論不完的話題。
就阿來而言,故鄉(xiāng)是一種特別的存在。他說:“對于故鄉(xiāng),我曾經很不愛,現在有點愛。我不想美化,也不想丑化它。我所有的書寫,都想還故鄉(xiāng)一個本來的面目。其實故鄉(xiāng)也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投影。寫故鄉(xiāng)也是寫自己。”我認為,阿來這種對故鄉(xiāng)的情愫始終貫穿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可以說,他幾乎所有的虛構與非虛構文學作品都在書寫故鄉(xiāng),無論愛與不愛,故鄉(xiāng)構建了阿來文學世界的全部。
一
阿來出生在嘉絨藏區(qū)阿壩州馬爾康市一個只有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村莊的藏語名字叫卡爾谷,漢語名字叫馬塘。在《大地的階梯》中,阿來這樣講述自己的故鄉(xiāng):
我只是知道,馬爾康這個地名由來已久。
在那些年代里,馬爾康寬廣的河灘曾是狐貍的天堂。
馬爾康得到這個名字,完全是因為,在此寬廣的河灘上,有一座叫作馬爾康的寺廟。寺廟本身在那時荒蕪的河灘上,相對來說,確實也算是一個燈火明亮的所在。
光明與黑暗,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一座佛寺起這樣一個與光明相關的名字,肯定還有其意欲在蒙昧的時代里開啟民智這樣一種象征的意義。佛教典籍的名字中,就不斷有與燈火相關的字眼出現。
通常意義上,“馬爾康”這個藏語組合詞的字面翻譯是“燈火旺盛的地方”。在這里,阿來的闡釋,除了文化學意義上的正名之外,我認為,更多的在于表達出對故鄉(xiāng)復雜而矛盾的情感。光明與黑暗,啟蒙與蒙昧交織在一起,這是阿來對故鄉(xiāng)存在樣態(tài)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他對故鄉(xiāng)的空間記憶,往往也夾雜著一種民族身份認同感的焦慮。阿來的母親是藏族人,父親是一個把生意做到藏區(qū)的回族商人的兒子。有時談到族別,阿來會幽默地說,自己是個“遠緣雜交品種”。“回藏混血”讓天性敏感的阿來深受影響,以至于在他很多早期作品中,都有一個叫作“阿來”的懦弱孩子的影子。像《舊年的血跡》《孽緣》等都是阿來早年生活和思想的真實寫照:身處貧困卻又想獲得尊嚴。在文本中,“父親”和“舅舅”不只一次鄭重提出“阿來”是讀書的料,而讀書是擺脫貧困、走向外部世界的唯一路徑。可以說,族裔的歧視深深困擾著童年的阿來,他在《遙遠的溫泉》中寫到:“藏蠻子是外部世界的異族人對我們普遍的稱呼。這是一種令我們氣惱卻又無可奈何的稱呼。”我想,正是因為這些生存環(huán)境的壓力,早年的阿來并不喜愛自己的故鄉(xiāng)。“少年時代,我們一起上山采挖藥材,賣到供銷社,掙下一個學期的學費。那時,我們總是有著小小的快樂。因為那時覺得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不一樣的未來不是鄉(xiāng)村會突然變好,而是我們有可能永遠脫離鄉(xiāng)村。”
于是,“離鄉(xiāng)”成為阿來早期作品常見的主題。短篇小說《環(huán)山的雪光》發(fā)表于1987年。藏族女孩金花對新事物充滿了好奇,卻又難以擺脫生存環(huán)境的桎梏,開始靠“回憶”打發(fā)時光,最終忍受不住一連串打擊走上極端,用刮油彩的小刀刺殺了圖畫老師。那是一個曾經打開她生活視域,卻又擾亂了她心境的人。金花的故事,就是她“怎樣小心翼翼地側身穿過現實,與夢交接的故事”。可以看出,阿來在滿懷對外部世界渴望的同時,又用一種不確定的理想,來反觀現實,金花正是這種復雜、懷疑情緒的表現。這種情感實際上也是阿來童年情感的真實再現。2002年,阿來寫了一篇小散文《詞典的故事》,用平實的語言回憶自己童年時期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一本幾角錢的《成語詞典》對于幼小的阿來是那樣可望而不可及。在小學畢業(yè)的那一年,阿來跟隨全班同學去一個“遙遠的小鎮(zhèn)”拍畢業(yè)照。在小鎮(zhèn)的新華書店見到了那本令他魂牽夢繞的詞典。但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需要學校出具的證明信才能購買。于是,沒有證明的阿來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絕望。“這本書就在我面前,但是與我之間卻隔著透明但又堅硬而冰涼的玻璃,比夢里所見還要遙不可及。”最后,阿來奔涌的淚水感動了售貨員,“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像閱讀一本小說一樣閱讀這本詞典。從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書。從此,我對于任何一本好書都懷著好奇與珍重之感。”
童年時期走出家鄉(xiāng)的愿景,寄托在阿來多部小說中都出現的地質隊員身上。他們大多沒有名字,只有身份:地質隊員。在“機村系列”短篇小說《水電站》中,“地質隊的這些家伙比工作隊還要神氣”,“他們出現了,看見機村這么大一個村莊,但就像沒有看見一樣。他們趕著馱著各種稀奇東西的騾子隊直接就從村子中央穿過去了,對這么大個村莊視而不見。完全是一種見過大世面的樣子。”然而,這些“傲慢”的地質隊員卻是科學的啟蒙者。他們送給機村“一座畫在紙上的水電站”。三年后,當這座水電站真正建起來的時候,“整個機村就在黃昏時發(fā)出了光亮。”在《云中記》中,地質勘探隊登上了出現地質裂縫的云中村,宣布云中村即將隨著地質滑坡消亡的科學信息。顯然,地質隊員是科學與啟蒙的符號表征。在阿來的少年時期,正是地質隊員第一次讓阿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曾說:“因為我自己出生在一個很小的村子里面,當然有著對外部世界的向往,但是外部世界僅僅是一個象征、一個符號。我們接觸外部世界最早的,就是這些勘探地下有沒有礦藏的地質隊員。……他們讓我看到自己與他們的不同,他們就是外部世界。”當時,他對外面世界的全部了解,都來自這些地質隊員,他天真地認為,只有地質隊員走得很遠、很神氣。所以,在高考填報志愿時,他在志愿表上鄭重地填上兩所地質學院,但命運只讓他上了本地的一所師范學校——馬爾康師范學校。想必,今天的阿來一定會發(fā)自內心地感激命運之神,讓他陰差陽錯地選擇了自己熱愛的事業(yè)——文學。
但是,走出故鄉(xiāng)之后又會怎樣呢?這是阿來在自己走出故鄉(xiāng)之后,經常思考的問題,也成為《塵埃落定》之后,他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空山》中的色嫫可以看作“金花系列”的延續(xù)。色嫫是機村的妙音天女,她的歌聲美妙無比,宛如天籟。她愛上了惹覺·華爾丹。她要離開村子,進文工團當歌唱家,讓她的聲音通過收音機驕傲地傳播到更遠的地方,而解放軍班長惹覺·華爾丹有條件幫助她。但是,色嫫唱出的是塞壬的歌聲,讓惹覺·華爾丹心亂神迷,他并不理解色嫫,為了與色嫫盡快結婚他復員回到村里,做了獵人達戈(傻瓜)。一個傻瓜怎么可能擁有色嫫呢?“色嫫這個詞,本身就包含著妖精和仙女兩個意思。”色嫫還是離開了達戈,離開了村莊,奔向她向往的光鮮舞臺。顯然,對于色嫫的背叛與離鄉(xiāng),阿來沒有給予情感認同,她的離鄉(xiāng)與達戈的回鄉(xiāng)構成了一對文化意蘊上的象征。回鄉(xiāng)的達戈最終以最為悲壯的方式為“獵人”正名。他是機村最后一個獵人,他的死帶走了埋藏在機村泥土中最深層的氣息。文本最后縈繞著挽歌式的基調,那是對行將落寞的機村文明的哀悼。
顯然,在阿來真正走出家鄉(xiāng)之后,距離讓他對家鄉(xiāng)有了重新認識,以至于那本在他童年時代魂牽夢縈的詞典,“化身”為《大百科全書》,走進了中篇小說《三只蟲草》。此時已經是21世紀,小說的主人公桑吉是一名小學生,他的家在海拔3300米的青藏高原上的一個小村莊。桑吉用三只蟲草打開了人生的視界,看到了向往已久的百科全書。“百科全書里有著他生活的這個世界所沒有的一切東西”,相比之下,桑吉的小村莊邊緣渺小得如此可憐,以至于桑吉“再回望他生活的小村莊,心里便生出一點點的凄涼。”從《詞典的故事》到《三只蟲草》,半個世紀過去了,山村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貧窮,人們可以用蟲草、柏木、松茸等山珍換取物質財富,但所有這些都是消費主義時代打造的幻象,以掠奪自然為代價,最終將在惡性循環(huán)中走向更加深度的貧窮。小小的桑吉看到了這一點,他“回到村里新修的定居點,看著那些一模一樣的房屋整齊排列在荒野中間,桑吉心里禁不住生出一種凄涼之感。他心下有點明白,這些房子是對百科全書里的某種方式的一種模仿。因為住在這些房子里的人并沒有另外的世界中住著差不多同樣房子里的人那種相同的生活。”文本的最后,凝結著桑吉愛心的三只蟲草,在被算計和欺騙中開始了它們通往外部世界的旅行,這似乎暗示了桑吉的命運。或許外部世界充滿了算計和欺騙,但是,走出去,是這個小村莊自我救贖的必由之路。
我們看到,阿來對家鄉(xiāng)的書寫,從“很不愛”到“有點愛”,是阿來情感立場和文化立場的雙重蛻變,這不僅是因為阿來走出了故鄉(xiāng),產生了距離的美感;更多的在于理性的反思,古老家鄉(xiāng)的傳統(tǒng)正在不斷發(fā)生著變化,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是那些傳統(tǒng)中殘存的詩意和美好,同樣也將隨風飄散。正因為如此,阿來愛他的故鄉(xiāng),緣于不舍,更緣于堅守。
二
愛默生說:“沒有哪個作家能夠在書中拋棄傳統(tǒng)與地域的影響。”(愛默生《不朽的聲音》,張世飛等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無論對故鄉(xiāng)愛或者不愛,故鄉(xiāng)的水土、故鄉(xiāng)的草木、故鄉(xiāng)的氣息都會滲透到作家的基因深處,在作家的筆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流淌出來。我認為,阿來是有著自覺意識去書寫自己家鄉(xiāng)的作家,不去美化,也無須丑化,他要展現的是一個真實的嘉絨藏區(qū)。
那么,阿來在文學中是怎樣呈現故鄉(xiāng)的呢?阿來說,“我與腳下的這片土地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怎樣找到這種關系?我就一座山一座山地去爬吧。”行走在自己故鄉(xiāng)的大地上,以文學的在場去記錄去書寫,成為阿來處理故鄉(xiāng)與文學之間關系的一種獨特方式。《大地的階梯》就是這樣一部“以雙腳和內心丈量故鄉(xiāng)大地”的長篇地理文化散文。這次寫作緣于一次文化地理考察,阿來從藏文化中心的拉薩開始,沿著大地的階梯逐級而下,大渡河、嘉木莫爾多、贊拉、馬爾康、金川……阿來在群山的各個角落進進出出,以真切的自我體驗穿越時空,試圖為我們展現一個真實的嘉絨藏區(qū)。阿來說:“長期以來,大家都忽略了青藏高原地理與藏文化多樣性的存在,忽略了在藏區(qū)東北部就像大地階梯一樣的一個過渡地帶的存在。我想呈現的就是這被忽略的存在。她就是我的家鄉(xiāng),我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故鄉(xiāng)。”我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大地的階梯》就是阿來寫作的文學地理圖譜,他將嘉絨藏區(qū)的山川草木、城鎮(zhèn)古寺、土司官寨,聚焦到我們面前,將潛藏在山巒褶皺中的文化密碼和集體記憶,挖掘出來,將它們深埋在他一個又一個虛構的小說文本中,正如學者丹珍草所指出的,“這讓我們接近一個事實:阿來的作品幾乎都是以青藏高原和川西北藏區(qū)的地理空間為背景,而任何一個地域都不只僅僅意味著一個地理位置、物理空間,而是地理空間與時間、文化的多維存在,是一種心理,一種更為多樣化和獨特生活方式的象征,是滲透了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這樣一個復雜立體的有意義的‘地圖。對于‘異文化研究者而言,‘地方性知識幾乎是不可企及的知識領域,而且這一領域也最容易引起文化阻隔和文化誤談。本土學者的近距離研究并非不是客觀的,‘近距離研究的相對客觀性是建立在對本土知識背景的深刻理解基礎上的。”丹珍草在此提到的“地方性知識”,是美國闡釋人類學家格爾茲提出的概念,以此區(qū)別于全球性知識或普遍性知識。對于相對邊緣的地域,地方性知識對外界的傳播和接納都不是那么容易,因為文化深深植入人的情感中,只有真正體驗、擁有這種情感才能真正把握文化,傳播文化。從這個意義上看,阿來是有意識地通過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讓我們去深入了解嘉絨藏區(qū)“地方性知識”的獨特性。
《塵埃落定》這部創(chuàng)作于1994年的長篇小說,盡管帶有一定的魔幻色彩,但是,阿來說,這部小說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是真實的,虛構的故事滲透著可以視作“地方性知識”的土司文化。實際上,在閱讀《塵埃落定》之前,很多人會將藏地文化視為一個整體,忽略其中的差異。而《塵埃落定》的努力恰恰是讓我們看到嘉絨藏區(qū)的文化獨特性。《塵埃落定》的故事發(fā)生在川西藏區(qū),這是一個“兩頭不靠”的地域,一方面離中原的政治權利中心有很大距離,另一方面又遠離拉薩這個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中心,成了一個藏漢兩種文化輻射范圍內的邊緣地帶。文本中寫道:“有諺語說,漢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陽下面,達賴喇嘛在下午的太陽下面。我們是在中午的太陽下面和靠東一點的地方。這個位置是有決定意義的。它決定了我們和東邊的漢族皇帝發(fā)生更多的聯系,而不是和我們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地理因素決定了我們的政治關系。”其實,不僅是政治關系,在宗教方面,嘉絨也保留了更多藏區(qū)原始宗教——苯教的印記。“苯教雖然有自己系統(tǒng)的教義和儀式,但它很大程度上還帶有巫文化的色彩,它不像佛教哲學化地追尋宇宙的普遍性,它審視的是有限的宇宙——‘物理宇宙”。《塵埃落定》中的門巴喇嘛就是一位掌握高超巫術的巫師。他不僅能夠驅鬼治病,而且能夠占卜兇吉。文本中描寫的那場荒誕的“罌粟花戰(zhàn)爭”實際上就是一場巫術大戰(zhàn),門巴喇嘛阻擋了汪波土司作法降下的試圖毀壞罌粟花的冰雹。除了神秘的巫術,遠古神話、部族傳說、文化原型等“地方性知識”構建了《塵埃落定》的厚重底色,讓我們發(fā)現了一個曾經陌生的文化地理空間。
與《塵埃落定》一樣,《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也貫穿著地方性知識。這部作品是阿來歷時五年,翻閱百萬字史料創(chuàng)作的長篇非虛構文學。“瞻對地處康巴。康巴人向來強悍,而瞻對人在康巴人中更以強悍著稱。當地人以此自豪:瞻對就是一塊鐵疙瘩!”對于這塊對大多數人而言“生僻”的土地,阿來選擇了自清代至民國的兩百年,著眼于清政府七次對瞻對用兵的始末,以及民國年間川藏雙方對此地的歸屬權爭奪,講述了一段獨特而神秘的藏地傳奇,以“據史以書”的方式進行文學上的再創(chuàng)造。為此,阿來在真實性上做足了功課,力求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他參閱了正史、稗史、地方志、游記、有記錄的口頭傳說等等,不一而足,在凸顯歷史敘述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的同時,也從多維度、多視角思考同一歷史事件,讓歷史的紋理顯得更加豐富和復雜。阿來面對的是歷史,對話的卻是現實,最終傳達出對川屬藏族文化的現代反思。難怪李敬澤說,“有了《瞻對》,阿來就不僅僅是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而將是一個民族意義上的大作家。”
的確,阿來的每一次創(chuàng)作,都非常自覺地書寫家鄉(xiāng),并將嘉絨藏區(qū)的民間文化融入他的故事里。《格薩爾王》的創(chuàng)作緣于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發(fā)起的“重述神話”系列圖書項目。史詩《格薩爾王傳》被稱為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詩,至今依然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傳唱。作為口傳文化的代表之作,口口相傳是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唯一傳播方式。千百年來,《格薩爾王傳》在其傳播的過程當中,融入了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其基本的故事和文化精神是定型的。因此,阿來的“重述”不是改寫,他是將過去的英雄召喚到現在,努力去挖掘藏民族的民間信仰和民族意識,呈現藏民族的民情風俗、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對于很多人,西藏是一個形容詞,因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當成一個真實的存在。我寫《塵埃落定》、寫《格薩爾王》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西藏,要讓大家對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達拉宮,還要能讀懂西藏人的眼神。”另一方面,阿來在《格薩爾王》中還專門設置了說唱藝人晉美的一條敘事線索,讓晉美來講述這一史詩。這就使得文本在保留史詩原汁原味的同時,又賦予了它現代性的內涵。每一個時代的說唱藝人都會將自己的理解融入說唱當中,說唱藝人每一次的講述都是對《格薩爾王傳》的一次再創(chuàng)作。但是,在現代文明和現代媒體的沖擊下,晉美這樣的說唱藝人也面臨著極度尷尬的生存處境。畢竟,影視、網絡、自媒體等有著強烈誘惑,已經很少有人對說唱藝術感興趣了。為了吸引聽眾,晉美做了各種努力和嘗試,甚至不惜學唱流行歌曲。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晉美的失語實際上意味著口傳藝術和史詩文化在當下的悲劇命運,史詩文化只有在說唱藝人神色俱佳的表演中才能真正煥發(fā)生命的活力,一旦停止演述,人們便會失去對它的記憶,它的生命力也便由此衰竭。顯然,阿來在《格薩爾王》中提出了一個令人憂慮的民族文化保護問題。
三
當然,阿來對歷史關注的落腳點是對現實的關照。其實,我們把阿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連綴起來,便不難看出,阿來始終都在書寫故鄉(xiāng)的前世今生。從“家馬與野馬剛剛分開”的遠古英雄時代,到清末民初的瞻對,再到20世紀上半葉的麥其土司家族,20世紀下半葉的機村,消費主義時代下的“山珍三部”,阿來將不同時間點的故鄉(xiāng)連接在一起,建構起了自己的文學世界。隨著時間光影的流動,阿來越來越關注的是,在現代性沖擊下故鄉(xiāng)發(fā)生的變化。
《塵埃落定》的故事背景選在20世紀初,這是一個現代性進程已然無法阻擋的歷史階段。此時的麥其土司家族已經十分衰落,連懲處一個叛逃頭人的能力都沒有。麥其土司只能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從一個鑲銀嵌珠的箱子里取出清朝皇帝頒發(fā)的五品官印和一張地圖,到‘中華民國四川軍政府告狀去了。”麥其土司請來了軍政府黃特派員,組建了一支現代軍隊,輕而易舉地打垮了敵人。然而,通過這扇向外部世界敞開的大門,還流入了英國的鍍金電話、美國的收音機、德國的照相機、令書記官贊嘆不已的鋼筆;還有美麗而充滿誘惑的罌粟。“這些我們土地上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是那么熱烈,點燃了人們骨子里的瘋狂。”顯然,來自外界文明的力量是無法拯救麥其土司家族的。在現代性面前,麥其土司失去了屬于他的時代。于是,在種滿罌粟的大地上,傻子二少爺前瞻到了未來:
有土司以前,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長。有土司之后,它們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土司之后起來的又是什么呢,我沒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傾倒騰起了大片塵埃,塵埃落定后,什么都沒有了。是的,什么都沒有了。塵土上連個鳥獸的足跡我都沒有看到。大地上蒙著一層塵埃像是蒙上了一層質地蓬松的絲綢。
時代的更迭,文明的更迭總是那樣毫不留情。土司文明在現代性的沖擊下是如此不堪一擊,終歸化作一縷塵埃,隨風而去。實際上,現代性的沖擊還不僅僅是呈現摧毀性的暴力,還有腐蝕性的滲透。這種滲透最直接也是最明顯地表現在語言上。《馬車》是“機村系列”中的一部短篇。文本開篇寫道:“此前機村有馬,也有馬上英雄的傳奇,但沒有車,沒有馬車。其實,哪里只是機村,方圓幾百里,上下兩千年,這個廣大的地區(qū)都沒有這個東西。”可是,有一天,農業(yè)合作社社長格桑旺堆帶回一堆馬車零件,拿回一張馬車組裝的圖紙。當格桑旺堆向好奇的村民說出“馬車”這個詞的時候,“大家還是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奇怪的是,只要有了一個名字,即使這個東西還沒有成形,還沒有以名字指稱的那個事物本來的樣子呈現在人們面前,大家立即就相信了。”當然,還不只是“馬車”這樣的物質形態(tài)名詞,諸如“積極分子”“人民公社”“生產隊”“工作組”“共青團員”“干部”等等,這些機村人聞所未聞的抽象概念,也頻繁轟炸著他們幾近飽和的大腦。語言學家沃爾夫指出,語言是作為一個體系與文化中的思想體系相聯系的。“一旦我們進入語法體系,進入語言建構方略,我們就可能在相應的文化思維方式、文化心理、文化哲學上找到結構上的一致關系。反過來,文化上的思維方式、哲學、心理,也能幫助我們從整體上、方向上把握民族語言的結構特征,深刻理解民族語言紛繁外表之下的文化固定性。”正是語言與文化這種內在的同構性,讓機村人在大量新名詞的撞擊下不知所措。《空山》第五部《輕雷》中的一段對話很形象地闡釋了機村人的困境:
拉加澤里從不多話的母親有些激動,終于不能自制,開口道:“兒子,你不能跟那些降雨人說話,雷要打死這樣的人。”
“媽媽,雷不會打死他們。他們懂得科學。他們用避雷針把雷電的憤怒引入土里。”
老太婆不但激動,還有些憤怒:“避雷針也是太聰明的東西嗎?人太聰明神會發(fā)怒的。”在機村,有些頑固的老人,把一些新發(fā)明歸類于“太聰明”的東西。電話太聰明,發(fā)電機太聰明,收音機和錄音機太聰明。降雨的火箭當然也太聰明了。
“太聰明”引發(fā)的不是企盼與渴望,而是恐懼。因為這些外來的新詞匯、新思想,已經讓機村的民族話語在不知不覺中悄然退場。現代性以深入人心的方式來瓦解機村的原生態(tài)文化。可以說,在阿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現代性始終作為一面鏡像,映照著阿來對故鄉(xiāng)的書寫。伴隨著消費主義時代的到來,現代性的侵入方式由“輸入”變?yōu)榱恕拜敵觥薄Ox草、松茸、岷江柏這樣稀有的山珍,成為外部世界關注嘉絨藏區(qū)的一條物質通道,正如阿來所說:“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如果邊疆地區(qū)不具有旅游價值,基本上已被遺忘。如果這些地帶還被人記掛,一定是有一些特別的物產,比如蟲草,比如松茸。”“山珍三部”的三個主人公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藏地淳樸的“原生態(tài)人格”,蘊含著一種理想主義的詩意,而他們最終無奈的命運,也是現代性造就的必然結局。《蘑菇圈》中的阿媽斯炯美麗、善良而剛毅。面對生命中的欺騙和偽善,她從不抱怨,也從未想到去報復那些給予她傷害的人。她想要捍衛(wèi)的僅僅是屬于她的一小塊蘑菇圈,這是支撐她生命原動力的一塊詩意的棲居地。所以,最終當蘑菇圈被現代科技出賣之后,支撐斯炯的精神支柱轟然坍塌了,她只能離開自己的故鄉(xiāng),因為“蘑菇圈沒有了”。《三只蟲草》中的小學生桑吉有著與斯炯一樣的純凈和善良。當一年一度的蟲草季到來的時候,在換購蟲草的商人眼里,蟲草只是物化的人民幣而已。然而,蟲草對于桑吉而言,“的確有點糾結。是該把這株蟲草看成一個美麗的生命,還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幣?”盡管這根蟲草在桑吉的計劃中意味著奶奶的骨痛貼膏、姐姐的李寧牌T恤、表哥的無指手套,還有送給老師的剃須泡和洗發(fā)水,但是,桑吉依然非常糾結。因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早已將自然的律動融入自己的血脈,尊重自然中的每一個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即使是親情和金錢都無法徹底將其暈染干凈。桑吉的命運如同蟲草,最終也會走出山村,可是,在外面那個充滿欺騙和算計的世界,淳樸的桑吉又會怎樣呢?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在《河上柏影》中的王澤周身上可以看到桑吉的未來。大學畢業(yè)的王澤周,依然透著一股淳樸的氣息,厭惡虛假與做作,執(zhí)著于自己的堅守,不受惑于虛名,無視社會上的一切規(guī)則和潛規(guī)則。在與柏樹傳說形成鮮明反差的各種社會亂象中,王澤周建構了一種獨特的人格“奇觀”。
其實,在“山珍三部”中,阿來都設立了兩種具有象征意味的對立人設:《蘑菇圈》中的母親斯炯和兒子膽巴;《三只蟲草》中的桑吉和他的父親;《河上柏影》中的王澤周和他的父親,代表著對傳統(tǒng)的固守與掙脫。其中,斯炯是守望的失敗者,王澤周是守望的回歸者,桑吉則是一個不失傳統(tǒng)卻也不被傳統(tǒng)禁錮者。顯然,對于桑吉,阿來給予了更多的希望。畢竟,面對外部世界的撲面而來,全然故步自封已有的生活狀態(tài)是不可能的,對傳統(tǒng)的固守最重要的是固守那個精神實質。這一點,在《云中記》中呈現得更為明確。《云中記》中的祭師阿巴是苯教非遺傳人。在汶川地震過去四年之后,他所在的云中村被地質學家判了“死刑”,預言不久之后整個村莊將隨地質滑坡徹底在地球上消失。所有的村民遷往移民村,而阿巴卻決定一個人留在云中村,守護那些逝去的亡靈。于是,整個文本就在倒計時中,從阿巴回到云中村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村莊消失的“那一天”,書寫了一個祭師的堅守,書寫了責任、信仰、犧牲和崇高。在我看來,這種堅守在一定意義上帶有蘇格拉底之死的意味,阿巴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捍衛(wèi)他的信仰。盡管阿巴并不是一個天生的靈媒,他超度的“技術”還是在地震后現學的。但是,他卻堅信他做的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他要把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亡靈,引導到云中村的一棵棵樹上。這樣,即便云中村消失了,這些亡靈也會隨大地樹木一起,寄魂于雪峰的祖先阿吾塔毗。阿巴的獻身讓死亡這樣殘酷的事實變得如此美麗,一切都將獲得永恒,就像阿巴所說的:“原來消失的山并沒有消失,只是變成了另外的樣子。”阿來說,汶川地震三四年后的一天,他看到一張攝影師朋友拍攝的照片:在一個廢棄的村莊,一位巫師孤身一人為死去的鄉(xiāng)親們做法事。這張照片對阿來的震動極大,盡管當時他沒有立即動筆,但這個揮之不去的巫師形象終于在10年后,定格到這部長篇小說中。在這個人物身上,呈現了阿來所看到的群山環(huán)繞的故鄉(xiāng),還有她的精神內核。
阿來曾說,故鄉(xiāng)是一個永遠搞不清的東西,清楚了就不是故鄉(xiāng)了,所以資源當然無限。阿來還說,“小說就是一個探索可能性的過程,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你在實際的生活當中,你也只能做一個選擇,只有在小說里,我們可以活成各種各樣的自己。我并不認為必須回到我老家,我出生的那個村子,它才是我的故鄉(xiāng),當我們日漸擴大的時候,我會把故鄉(xiāng)放大,我現在可以說,整個川西北高原,我都把它看成是我的故鄉(xiāng)。”在阿來的文學世界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故鄉(xiāng),也看到了一個作為文學家的阿來。
責任編輯 崔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