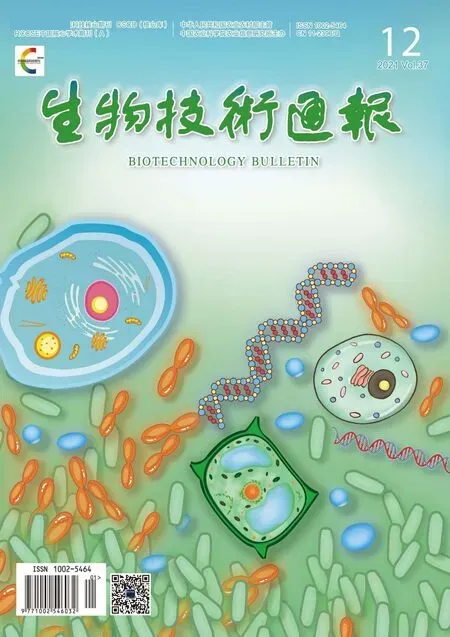奶牛乳腺炎治療及抗炎分子機制的研究進展
王晉鵬 羅仍卓么 王興平 楊箭 賈立 馬云 魏大為
(1. 寧夏大學農學院,銀川 750021;2. 寧夏回族自治區反芻動物分子細胞育種重點實驗室,銀川 750021)
奶牛乳腺炎是乳腺組織受到病原微生物感染和理化因素刺激等發生的炎癥反應,可導致奶牛泌乳量減少、奶品質下降、生長發育減緩、繁殖力降低、產奶年限縮短和死淘率上升,造成牧場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制約奶產業的發展[1]。據統計,全世界奶牛乳腺炎的發病率高達50%,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350億美元[2];在我國,奶牛乳腺炎的發病率高于國外,且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30億元[3]。因此,奶牛乳腺炎是一個亟需解決的難題。為了能夠及時有效地預防和治療奶牛乳腺炎,研究人員不斷優化檢測方法和治療策略(圖1),并積極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目前,雖然在奶牛乳腺炎的致病原因和治療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對奶牛乳腺炎治療的分子作用機制還不是十分清楚。其治療的分子作用機制對于精準的藥物研發至關重要。本文綜述了奶牛乳腺炎的致病原因、治療及抗炎的分子機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以期為相關領域的研發人員提供有效的參考資料和新的視野。

圖1 奶牛乳腺炎防治策略Fig.1 Control strategy of dairy cow mastitis
1 奶牛乳腺炎的致病原因
奶牛乳腺炎是遺傳、環境、管理和營養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4]。有報道顯示,奶牛在飼養管理相同的條件下,乳腺炎的發生既與個體差異有關,也與自身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在環境因素中,最常見的致病原因就是病原微生物感染[1]和血液循環障礙[5]。
1.1 病原微生物感染
引起奶牛乳腺炎的病原微生物一般分為接觸傳染性病原菌(又叫牛依賴性病原菌)和環境性病原菌(又叫條件病原菌),前者主要有無乳鏈球菌(S.agalactiae)、金黃色葡萄球菌(S. aureus)和停乳鏈球菌(S.dysgalactiae)等,后者主要是革蘭陰性菌,如大腸桿菌(E. coli)、沙雷氏菌(Serratia)和克雷伯菌(Klebsiella)等[6-7]。
大多數乳腺內感染是由于病原微生物克服乳頭管的解剖物理屏障所致[7]。乳頭管是防止病原微生物入侵第一道防線,也是外界病原微生物進入乳房的唯一途徑[8]。當病原微生物入侵乳頭括約肌和乳頭管時,引起乳腺內感染,由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組成的第二道防線產生獲得性免疫反應[4]。病原微生物一旦突破防線,進入乳區,在乳頭池和乳腺池中定植,然后入侵到泌乳組織引起感染,從而產生炎癥,導致乳汁體細胞數(somatic cell count,SCC)顯著增加,若感染嚴重,會導致泌乳量減少,甚至停乳[4,7]。
1.2 血液循環障礙
乳腺內乳汁的形成依賴于血液循環。在泌乳期,尤其是高產奶牛對乳房要進行定期護理,若因操作不當造成乳房血液循環障礙,會引起乳房局部淤血,造成組織缺氧、乳腺腺泡上皮細胞排列紊亂和炎性細胞浸潤,使得乳腺組織對外界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下降,進而環境性病原微生物入侵而產生炎癥反應[5,9]。隨之受損乳腺的血管擴張,血乳屏障通透性增加,血液中產生大量炎性介質,滲出物很快在乳腺管內凝固,造成泌乳障礙[9]。
此外,當乳房受到理化因素刺激時,角蛋白和粘膜內皮的乳頭竇受損,使得病原微生物易于入侵、定植和感染[4]。在形成感染區后,病原微生物快速增殖并擴散到其他部位[1],超出動物機體自身免疫的防御能力,從而造成機體損傷并引發乳腺炎[4]。
2 奶牛乳腺炎治療及抗炎分子機制的研究
目前,抗生素作為治療奶牛乳腺炎的首選藥物和最佳途徑,取得了很好的療效。但是,長期廣泛地使用抗生素,會導致一系列副作用,如抗生素殘留、耐藥性增加和奶品質下降等,給人類健康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1]。為了緩解這一現狀,研究人員一直在努力尋找合適的方案用于奶牛乳腺炎的預防和治療。至今為止,學者們開展了多種物質(生物活性物質、礦物元素、維生素和生物制劑等)對奶牛乳腺炎分子治療技術的相關基礎研究,并取得了較好的結果。
2.1 生物活性物質對奶牛乳腺炎的抗炎機制
E. coli和S. aureus是引起奶牛乳腺炎的主要的的病原微生物,可通過在乳腺組織中的快速繁殖和持續粘附,繼而導致臨床型和亞臨床型奶牛乳腺炎的發生[7]。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和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LTA)分別是E. coli和S.aureus細胞壁上的病原體相關模式分子,也是導致奶牛乳腺炎加劇的重要因素[10]。值得一提的是,中草藥富含酚類、酸類、生物堿和黃酮類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是純天然的“綠色”藥物,具有抗炎、抗菌和抗癌等生物活性。近年來,學者們以E. coli(或LPS)和S. aureus(或LTA)誘導的牛乳腺上皮 細 胞(bovine mammary epithetlial cells,bMECs)炎癥模型為研究材料,陸續發現多種生物活性物質能抑制炎癥性bMECs中的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白 細 胞 介 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細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和白細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等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阻斷κB抑制劑α(κB inhibitor α,IκBα)的降解和p65磷酸化(P-p65)來減弱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信號通路的活性;或抑制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p38和c-Jun并阻斷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1/2(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1/2,ERK1/2)磷酸化水平,使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通路的活性減弱;最終減輕bMECs的炎癥反應和細胞損傷(表1)。此外,還發現少數生物活性物質能消除炎癥性bMECs的自由基,抑制活性氧(ROS)的產生,維持細胞內氧化還原平衡,進而保護機體免受炎癥損傷(表1),為奶牛乳腺炎治療的藥物研發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綜上所述,上述生物活性物質具有較強的靶向抗炎作用,有望成為治療乳腺炎的潛在藥物,并解決藥物殘留和抗藥性的問題。

表1 生物活性物質對奶牛乳腺炎的抗炎機制Table 1 Anti-inflammatory mechanism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on cow mastitis
2.2 礦物元素對奶牛乳腺炎的治療機制
礦物元素可參與酶活性中心調節等多種生物學過程,在動物生理過程和體內代謝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國內外學者在嘗試用礦物元素治療奶牛乳腺炎方面展開了積極的研究,并取得一定進展。
研究表明,作為飼源性微量元素——硒(selenium,Se)在機體內可發揮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調節等生理功能[27-28]。Wang等[28]研究發現,Se能抑制 Toll樣受體 2(toll like receptors 2,TLR2)、NF-κB和MAPK信號通路的激活,從而顯著下調炎性細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的表達,進而緩解S. aureus誘導的炎癥過程。此外,在小鼠乳腺炎中,發現Se缺乏會導致S. aureus性乳腺炎中TNF-α、IL-1β、IL-6和TLR2的表達量以及IκB、NF-κB、JNK 和p38的磷酸化水平均顯著增加[27,29],這一結果進一步證明Se對S. aureus性乳腺炎具有輔助抗炎治療的作用。
此外,金屬納米粒子主要包括銀納米粒子(AgNPs)、銅納米粒子(CuNPs)和合成的銀-銅納米粒子(AgCuNPs),是近期炎癥和癌癥治療領域研究的熱點[30]。研究表明,AgNPs具有潛在修復組織、抗菌、抗糖尿病和抗氧化的醫療保健效益,并有利于炎癥和癌癥的治療[30]。Kalińska 等[31]發現市售的AgNPs、CuNPs和AgCuNPs對人和bMECs無毒性作用,但能降低病原微生物的生存能力,然而分子機制尚不清楚。這些數據表明,金屬納米顆粒可以用于未來乳腺炎的預防和治療,有望成為治療奶牛乳腺炎的潛在藥物。
2.3 維生素對奶牛乳腺炎的抗炎機制
維生素是以輔酶的形式參與體內代謝,對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生長發育和健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32],其中維生素A、維生素B3、維生素B9、維生素D和維生素E等對奶牛乳腺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研究表明,維生素A能夠維持上皮細胞的完整性和細胞器膜結構正常的通透性,可形成物理屏障抵御病原微生物的入侵,提高機體免疫力,降低隱性乳腺炎的發病率[33]。煙酸(維生素B3)通常用于改善奶牛能量負平衡、治療脂質紊亂和心血管疾病,近年來也應用于奶牛乳腺炎的治療[32,34]。Wei等[32]研究表明,煙酸對S. aureus的生長和bMECs活力無影響,但對S. aureus的內化抑制率為13%-42%,并能下調抗菌肽TAP和BNBD5的mRNA表達、抑制NF-κB的p65亞基從細胞質向細胞核的轉移,使NF-κB信號通路得到了抑制,從而減輕炎癥損傷。此外,Guo等[34]研究發現,煙酸能激活G蛋白偶聯受體109A(GPR109A)和磷酸化AMP依賴 蛋 白 激 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促進核因子紅細胞2相關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cyte two related factors-2,NRF-2)核導入和自噬,并降低細胞內IL-6、IL-1β和TNF-α的表達,從而減輕LPS誘導的bMECs炎癥反應。
隨著奶牛良種化程度、產奶量和飼養管理水平不斷升高,學者們發現補飼葉酸對預防和治療奶牛隱性乳腺炎也有積極的作用[35]。劉雪琴等[36]發現,給患隱性乳腺炎的奶牛補飼包被葉酸后,乳汁SCC顯著下降,且在補飼組檢測到105個顯著上調和172個顯著下調的基因,主要富集在細胞因子生成調控、炎癥反應和免疫反應等免疫學調控相關的GO條目以及富集在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信號通路、NF-κB信號通路和細胞因子與細胞因子受體的相互作用等炎癥和免疫學重要信號通路上,說明葉酸可能通過上述通路而調節機體免疫力,進而對隱性乳腺炎有積極的預防作用。
研究表明,奶牛在干奶期給予維生素E-硒可增強乳區的免疫反應,降低產犢時的乳腺感染,當乳腺內部受到病原微生物入侵時,巨噬細胞活化,分泌出大量的多形核白細胞(polymorphonuclear,PMN),PMN進入乳腺,改變乳腺的內環境,發揮殺滅和吞噬細菌的功能[37]。因此,補充或注射維生素E-硒可增強乳腺免疫系統。此外,維生素D可抑制 S. aureus感染的 bMECs中IL-10、IL-1β和TNF-α的表達,從而減輕炎癥損傷,是乳腺炎良好的調節劑[38]。
綜上所述,目前維生素在奶牛乳腺炎的作用,更多是提高機體免疫力,緩解奶牛乳腺炎,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缺乏大規模對照試驗,使其不能推廣使用。因此,未來亟需更深入的研究補充維生素的種類、最佳劑量和投喂時間,及其對產奶性能的影響等補飼細節,方可在改善奶牛乳腺炎中推廣應用。
2.4 生物制劑對奶牛乳腺炎治療的機制
生物制劑主要是由動物細胞、微生物及其代謝物和動物血液等產品加工而成,不僅能預防和治療相關疾病,而且具有針對性強、治療效果明顯、多靶點殺菌、無毒和無殘留等優點[39]。迄今為止,學者們進行了抗菌肽[40]、溶菌酶[41]和乳酸菌[42]等生物制劑在奶牛乳腺炎中的治療及其機制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相應成果。
抗菌肽在動物體內可直接抑制或殺滅病毒、真菌、細菌和腫瘤細胞[40],是最近在抗炎機制上研究較多的生物制劑。研究表明,bMECs表達的多種抗菌肽,可通過直接作用于微生物感染,并作為炎癥反應的一個組成部分積極促進天然免疫的形成[43]。李連彬[40]通過對菌絲霉素源抗菌肽(NZ2114和MP1102)在bMECs中殺菌效果的研究,發現對S.aureus E48的殺菌效果較好,原因是能抑制炎性細胞因子IL-6和TNF-α的迅速升高,緩解由S. aureus引起的乳腺炎癥反應。此外,β-防御素是一類具有固有免疫的抗菌肽(主要包括DEFB1、BNBD4、BNBD5和BNBD10等成員)[44]。當奶牛乳腺受到病原微生物感染時,β-防御素的表達水平顯著上調[45],可啟動固有免疫,從而發揮殺滅細菌、抗炎和保護機體的功效。
溶菌酶是一種消炎、抗菌和抗病毒的堿性酶,既能水解致病菌中的粘多糖,也能與帶負電荷的病毒蛋白直接結合,使病毒失活[41]。于是,孫懷昌等[46]構建了人溶菌酶基因的重組質粒,并將其注射到患有奶牛乳腺炎的病牛中,結果顯示,人溶菌酶基因的重組質粒對奶牛乳腺炎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且呈現出劑量和次數依賴性。究其原因有3點:(1)溶菌酶對細菌具有一定的溶解能力;(2)溶菌酶能夠增強PMN和巨噬細胞的消化、吞噬能力以及抗菌素等其他藥物消炎和修復組織的能力等;(3)該溶菌酶質粒是在pUC質粒基礎上構建的,該質粒中的CpG序列可激活以IL-6、IL-12和干擾素γ(interferon γ,IFN-γ)等產生為特征的非特異性免疫應答,提高機體抵抗力[46]。此外,Donovan等[47]從S. aureus基因組中分離并純化出S. aureus(NCTC 8325)噬菌體phi11溶菌酶,可降解宿主細胞壁的肽聚糖,溶解細菌,使感染噬菌體逃逸,而且該純化的溶菌酶可以溶解從乳腺炎感染中分離的6種代表性菌株(包括S. aureus),使其成為了候選蛋白抗菌劑。
乳酸菌通過與病原微生物競爭組織定植、調節毒力表達或刺激先天免疫系統,有助于維持自然微生物群的平衡,是治療炎癥的一種良好選擇[42]。Assis等[48]研究表明,L. lactis V7可抑制E. coli和S. aureus在bMECs的粘附能力和內化作用,也可使bMECs中趨化因子8(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8,CXCL8)的表達量輕微增加,從而增加bMECs炎癥反應。上述結果表明,L. lactis V7有望成為一種潛在的預防牛乳腺炎的益生菌。
綜上所述,生物制劑在奶牛乳腺炎的治療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已成為國內外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熱點。當前,國外科研工作者已取得璀然可觀成績,相反,國內則是剛剛起步,故加強生物制劑在奶牛乳腺炎甚至是其他炎癥方面的開發與利用是至關重要的,可為奶牛“健康養殖”的發展方向提供動力。
3 展望
奶牛乳腺炎病因復雜,提倡預防為主和治療為輔的防治原則。科學家們已挖掘出一些能抑制奶牛乳腺炎的生物活性物質、礦物元素、維生素和生物制劑,并初步探索它們的分子作用機制。但是,上述大多數研究僅停留在細胞水平上,而對奶牛個體水平的驗證實驗尚未開展。此外,受活性物質獲取難、成本高和奶牛乳腺炎致病機制復雜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基于生物活性物質類藥物的精準治療技術研發相對滯后,未真正在現代化牧場中應用。近年來,許多學者積極開展奶牛乳腺炎的分子調控機制研究,試圖挖掘調節炎癥的重要分子或信號通路,并在此基礎上研發成本低、殘留少和效價高的乳腺炎治療新產品,以期提高乳腺炎的治愈率,從而提高牧場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