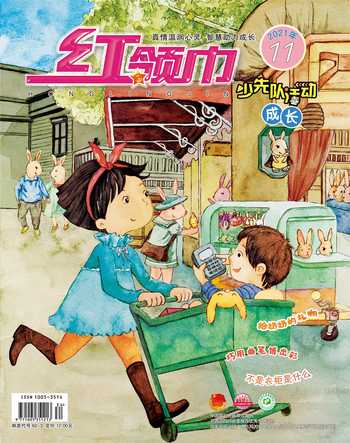扒扒看,他們不為人知的寫作怪癖(上)
夏半



身為創(chuàng)作老,難毛有著各式各樣難以想象的怪癖。從古至今,大作家們的怪癖足以讓人捧腹不已:有人一天只寫5個字,有人愛聞爛蘋果味兒,右人喜歡狂喝咖啡……感覺若不養(yǎng)成一個怪癖,都不好意思稱自己是作家了。一起來細(xì)數(shù)一下那些大作家們的寫作怪癖吧。
作息“怪咖”
“深夜讓人更有靈感”成了不少人熬夜的借口,福樓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就通常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寫作。除此之外,福樓拜寫作時還喜歡留白。他的學(xué)生曾問他:“您這樣寫,不是太浪費稿紙了嗎?”福樓拜回答:“我一直有這樣的習(xí)慣:一張稿紙只寫第1行,而其余9行是留著修改用的。”
但列夫·托爾斯泰(代表作《戰(zhàn)爭與和平》)卻恰恰相反。他只在早晨寫作,并偏執(zhí)地認(rèn)為人在早晨時才能保持一種清醒的批判精神,而在夜間時往往會寫出大量胡說八道的廢話。
與現(xiàn)代人的生活更類似的寫作模式是:利用業(yè)余時間來進行寫作,卡夫卡(代表作《變形記》)就是采用這一作息模式的代表作家。卡夫卡最初在保險公司上班,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根本無暇寫作。后來他轉(zhuǎn)職到勞工意外保險機構(gòu),2年內(nèi)晉升到主管,工作時間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2點半。他3點半結(jié)束用餐,回家睡到晚上7點半,起床后做點兒運動,與家人吃晚餐。一直到晚上11點,他的寫作工作才正式開始。這時,卡夫卡會根據(jù)自己的“力氣、意愿和運氣”,一直寫到凌晨1點甚至更晚。如此日復(fù)一日,直到自己的身體健康漸漸受損。
相對合理、健康的作息方式或許應(yīng)該和村上春樹(代表作《挪威的森林》)的一樣:“我進入寫小說的狀態(tài)時,會在凌晨4點起床,寫個5到6小時。午后,我會去跑步或游泳(或兩者都做)。之后,我會讀一點兒書,聽一些音樂,到晚上9點就上床睡覺。”
環(huán)境“怪咖”
光有寫作時間還不夠,作家們還得有理想(未必良好)的寫作環(huán)境。
喜劇大師莫里哀(代表作《無病呻吟》)在舞臺上滑稽多智,離開舞臺卻拙于言辭。他的袖筒里經(jīng)常藏著一個筆記本。他喜歡在公共場所偷聽別人談?wù)摰脑掝},并將它們記錄下來。無獨有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為了觀察市民們的生活,一有閑暇,就坐到咖啡店里,假裝拿著報紙看新聞,暗地里卻偷偷注意各種顧客的相貌、動作,傾聽他們的談話。
和這兩位相反,美國傳奇詩人艾米莉·狄金森(代表作《云暗》)更享受只有自己的生活。她從25歲開始,就過上了獨居生活。她寫詩30年,留在世間的詩歌有1800多首,生前卻只發(fā)表了7首。除了寫作,她的另一大愛好是做面包,她經(jīng)常把香噴噴的面包放在籃子里,通過繩索從窗戶吊下去給附近的小朋友們吃。
安徒生(代表作《安徒生童話》)也喜歡安靜,不過,他更喜歡安靜地在樹林里構(gòu)思童話。他有明銳得異乎尋常的視力,所以連掉落的一小塊樹皮或者一枚老松球,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透過放大鏡那樣纖毫畢見地看出那上邊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并輕而易舉地用這些細(xì)節(jié)構(gòu)成童話。
普魯斯特(代表作《追憶逝水年華》)和席勒(代表作《陰謀與愛情》)這兩位大作家有一個共同點——都要在絕對密閉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作。他們會用簾子把房間遮擋得嚴(yán)嚴(yán)實實,不讓一絲光透進來。普魯斯特甚至不允許仆人隨便開窗。而席勒還有一堆神秘的寫作“伴侶”,他的桌子里有一個抽屜,里面全都是腐爛的蘋果,據(jù)說他離不開這種“芳香”,沒有它,他就無法生活或?qū)懽鳌?/p>
杜魯門·卡波特(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聲稱自己是一個“完全的橫向作者”,必須躺在床上或者沙發(fā)上才能寫作。
(未完待續(xù))
- 紅領(lǐng)巾·成長的其它文章
- 為孩子扣上一粒紅色的扣子
- 大頭回信
- 秀秀臺
- 一模一樣等4則
- “財商”大闖關(guān)
- 暖暖的菠蘿抱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