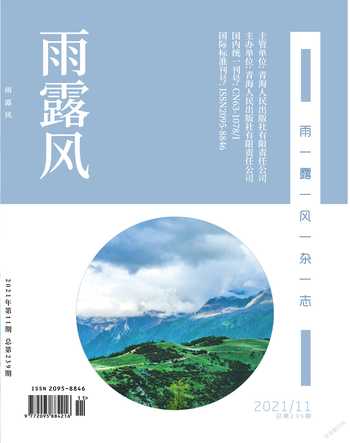論《姽婳詞》對晴雯、賈寶玉形象的塑造作用
文海闊
摘要:《紅樓夢》第七十八回中的《姽婳詞》看似游離于敘述主線以外,為可有可無的游戲文字,實則含蘊豐富,不可或缺,尤其是對晴雯、賈寶玉的形象塑造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姽婳詞》以林四娘性情的勇烈、重情、重義暗含晴雯形象,進而與《芙蓉女兒誄》回旋呼應,共同突出“晴雯之死”這一事件對寶玉影響頗深的作用;又通過聚焦寶玉與長輩之間的隔膜,呈現寶玉經歷“晴雯之死”后對現實、自我的清醒認知,刻畫了他性格上的轉變,深化了寶玉的形象。
關鍵詞:姽婳詞;人物形象;塑造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作者在描摹“晴雯屈死后,寶玉悲痛難忍,渴盼去祭奠晴雯而又不得”的情節之中,筆鋒一轉,插敘了一段“老學士閑征《姽婳詞》”,即賈政與眾幕友們談論林四娘和恒王的奇聞,并讓寶玉、賈環、賈蘭三人為此賦詩,寶玉則做了一篇七古,即《姽婳詞》。
關于《姽婳詞》,有些研究者從它本是一首命題詩、林四娘的形象比較蒼白、作者為逞才而作等方面,指出《姽婳詞》一段僅僅是作為《芙蓉女兒誄》的陪襯,為可有可無的游戲文字,是曹雪芹在結構和剪裁上的敗筆。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誠如周汝昌先生所言:“《紅樓夢》無閑文贅筆”[1]。
筆者認為《姽婳詞》是意蘊深遠的,是《紅樓夢》第七十八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故事情節的發展、結構上的完善皆有重要作用,文章主要探討《姽婳詞》對于晴雯、賈寶玉形象的塑造作用。且因《紅樓夢》第七十七回、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聯系緊密,多有回旋呼應之處,遂將其視為一個情節單元,來進行整體分析。
一、暗含晴雯形象
《姽婳詞》是賈政為在眾賓客面前展露寶玉才思,而給寶玉安排的命題詩,但從詩句中可以看出寶玉并非虛情假意地應付,他是有感于林四娘有情有義,無所畏懼,而油然而生的欽佩、贊賞之情。其筆下的林四娘形象也頗為鮮活生動:開頭的“眼前不見塵沙起,將軍倩影紅燈里。叱咤時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將女性列陣挽戈時的英武之氣與特有的嬌弱、柔婉結合起來,更加襯托出其俏麗與利落之風神,凸顯出女性性情中柔中帶剛的特質,自帶有一絲風致。及至后半段,寶玉又精心為其營造了鮮明的對比場景:“強吞虎豹勢如蜂”“紛紛將士只保身”“不期忠義明閨閣,憤起恒王得意人”“號令秦姬驅趙女,艷李秾桃臨戰場”,在戰爭惡劣,生死未卜的環境下,“真正有勇力”的將士卻明哲保身,而“叱咤時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鮫鮹”的嬌弱女性,反而迸發出一往無前的氣概,前往沙場臨陣殺敵,誓死回饋所愛之人的深情厚誼,其勇烈、重情、重義的特質遂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2-3]。
對比大觀園中的女性形象,不難發現晴雯性格中勇烈、重情、重義的特質也極為突出。
晴雯是大觀園眾多女兒中極具個性的一個人物,做事干脆爽利,言語中始終透露著鋒芒,每每遭受委屈,就定然以諷刺、冷笑進行回擊,即便是寶玉對其縱性使氣,也絲毫不放在眼里,這也便有了“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暢快情節。偌大賈府,恐怕也就只有晴雯這個丫鬟敢這般恣情大膽了。晴雯又極為聰敏,當王夫人聽信王善保家的讒言,傳喚晴雯并對其不留情面地指斥后,晴雯就意識到兇多吉少了,但值此危急時刻,她絲毫沒有畏懼,既沒有向寶玉求助,也沒有向襲人、麝月等人吐露苦衷,而是表現出了一種自尊自傲、獨立不屈的獨特風神,后來王善保家在搜檢她的箱子時,她便“挽著頭發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捉著底子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一個性情勇烈,敢愛敢恨、敢于反叛的女性形象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另外,晴雯也是情深義重之人,大病之中還是奮力掙扎著為寶玉補“雀金呢”氅衣,她“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發,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撐不住。若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著。”即便體力不支,也還是為了這份主仆情而勉力撐持著,的確令人為之動容。
可見,晴雯性情中的勇烈、重情、重義恰與林四娘的性格特征相呼應,因而可以說作者設計“老學士閑征《姽婳詞》”這一情節,表面上是在稱頌林四娘,實質上還是在緬懷晴雯。那么作者刻意蕩開一筆,游離于晴雯之死的敘述主線,而特意去塑造隱含著晴雯性情的林四娘形象,又有何獨特用意?
筆者認為,其一,作者借助寶玉所作的“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四句詩,將林四娘抬高至超越滿朝文武,足以挽救家國危亡的高度上,實際上是為了刻意抬高晴雯的價值,以告慰晴雯的亡靈,彌補晴雯屈死時的無辜與遺憾。畢竟,晴雯之死與寶玉有著直接的關系,寶玉當時并沒有向王夫人說情,未做出有力的實際行動來保護晴雯,因而他的內心是無比歉疚的,作《姽婳詞》高度頌贊晴雯,實際上也是在勸解自己。
其二,這是作者在結構上的有意安排。作者刻意將兩篇緬懷晴雯之辭——《姽婳詞》《芙蓉女兒誄》分別放置于這一情節單元的最前端與最末端,敘述線索的暗線與主線之中,藝術風格也成對比之勢:一含蓄一熱烈,一平實一絢爛,其目的便是讓二者共同營造出交相呼應、不可分割的情感氛圍,讓晴雯逝去帶給寶玉的傷痛縈繞在整個情節之中,揮之不去,進而突出寶玉對于晴雯之死感慨頗多,晴雯之死對他的影響至深的感情。
二、深化賈寶玉形象
(一)突顯賈寶玉與長輩之間的隔膜
《紅樓夢》進行到第七十八回,已是將整體故事推演至三分之二處,然而此時賈府的長輩們并非全然真切地了解賈寶玉的性情。正如:王夫人驅趕晴雯后向賈母回話,賈母和王夫人閑談道:“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也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確是難懂。我為此也擔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由此可見,連一向對寶玉呵護有加、無微不至的賈母、王夫人,也不能夠理解賈寶玉和丫頭們好的緣故,不能理解他對世間靈秀女子除去欲念的體貼、憐惜與尊重,更無法覺察到他性格中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情不情”[4]。
《姽婳詞》居于“賈母和王夫人不解寶玉性情”的情節之后,正是有特殊用意的:其一,寶玉借助外表雖柔弱,內心卻蘊蓄著無限勇氣和深情厚誼的林四娘形象,來突出晴雯等眾女兒們“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月不足喻其精”的特質,表達自己對女兒們真誠的贊賞,從而闡明自己被這種美好的特質所吸引,愛和女孩們交往,并且心甘情愿地沉浸于對女孩的憐恤、關懷之中,回應了賈母和王夫人的疑惑[5]。
其二,強調寶玉與長輩之間的隔膜。“情不情”本是寶玉最本真最美好的品性,卻始終得不到家中長輩的理解與認可,這是令寶玉深感失望與悲哀的,以至于寶玉在《芙蓉女兒誄》中一改平日的溫和角色,大發怒氣道:“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這里寶玉以諷喻的形式,越過禮教的藩籬,大膽指斥長輩們的無情,宣泄出心中積蓄已久的委屈與壓抑。與此同時,這種隔膜也恰恰表明寶玉是世俗評價體系中的異端,與社會期待大相徑庭。
(二)表明賈寶玉對現實及自我的清醒認知
由上文可知,《姽婳詞》《芙蓉女兒誄》一脈相承,都是寶玉為悼念晴雯所作,那么寶玉為何對此事耿耿于懷,以至于用如此多的筆墨反復吟詠呢?與晴雯感情深厚其實只是其中一個方面,細細分析下來,還有諸多深入的因素。
晴雯之死是寶玉洞察世事變更,認清自己命運的一個重要窗口。第七十七回,寶玉探望病重的晴雯,晴雯讓他倒半盞茶來喝,寶玉目之所及:“雖有個黑沙吊子,卻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了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手內,先就聞得油膻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汕過,方提起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太不成茶。”然而,晴雯卻將這樣的茶視為甘露一般。寶玉不禁感慨:“往常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的‘飽飫烹宰,饑饜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昔日怡紅院的富麗堂皇與生活的養尊處優,和此刻眼前房間的破敗骯臟以及晴雯躺在蘆席上無助可憐的狀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令寶玉震懾不已。他意識到:生活的一落千丈可能會發生在一夕之間,自己所擁有的榮華富貴實際上毫不穩固,而且自己也無力呵護世間的靈秀女孩。
正如寶玉面對晴雯被驅趕時的表現:“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此處深深揭露出寶玉內心的無可奈何——即便是賈府里萬眾矚目的“金鳳凰”,也沒有一點自主的行事權力。小到祭奠金釧,大到讀四書五經、走科舉之途、與達官顯貴交往、婚姻大事的選擇上,都有家人的層層限制與要求,難以按照寶玉自己的心意來抉擇。猛然意識到這種無能為力的境況,對于寶玉而言,必然是致命的一擊,這也為下文寶玉性格的轉變埋下了伏筆。
(三)呈現賈寶玉性格的轉變
正因為寶玉面對現實無可奈何,才會更為渴慕率性而行、不為流俗所拘的真性情,更加贊賞像林四娘、晴雯那般勇烈性情的人物,更渴盼從中汲取反叛力量。這便促成了寶玉在《姽婳詞》中將怒氣、憤懣的情緒噴薄而出:“王率天兵思剿滅,一戰再戰不成功。” “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這一段內容并沒有出現于賈政所敘述的奇聞之中,可見是出于寶玉自己的視角之下,所傳達出的情感態度。筆者認為,寶玉此處表達的,實質上是對封建倫理綱常、科舉制度教化下的一批批無用臣子的鄙薄,進而痛快淋漓地宣泄出自己對封建倫理、病態科舉、傳統教育觀以及世俗評價標準的深惡痛絕,宣示自己的人生態度。
經歷“晴雯之死”以及創作《姽婳詞》 《芙蓉女兒誄》,正是寶玉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他的性格發生了很大轉變:從只知沉浸于大觀園這個世外桃源,做著呵護世間靈秀女兒美夢的純真少年,到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與長輩的隔膜、與社會評價標準的悖離,再到認知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再到汲取晴雯勇烈的反叛力量,自然而然地就會走上一條反叛的道路。只不過這種反叛帶有情感審美與人生志趣全然被摧殘的巨大傷痛,以及身為賈家繼承人的身份限制,只能以沉默、隔絕、無力的吶喊的形式來實現——在心底暗暗強化出家的念頭。
生活的荒誕無奈,精神的孤寂絕望,讓寶玉將一切都看淡了,看空了,幻滅的哀意隨之涌上心頭,這在第七十九回就有所體現:黛玉聽見寶玉吟詠《芙蓉女兒誄》,建議將“紅綃帳里,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改為“茜紗窗下,公子多情”以求清新之意,寶玉大贊,并轉而將詩句改為“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干正經事罷。’”
此處黛玉的慌亂反應正說明了寶玉所言有著無限的意味:“無緣”“薄命”籠罩著濃濃的哀意,表明寶玉由晴雯之死轉瞬意識到大觀園也將群芳散去,以及自己與黛玉終無緣結合的悲哀,因而才會對著黛玉脫口而出了那句詩。黛玉如此聰明之人,一下子就意識到了寶玉話語中的無奈與悲涼,遂不得不用“快去干正經事罷”來打斷他出家的念頭,將其從空茫的世界中拉回現實。對比之前黛玉與寶玉的對話,黛玉又何曾對其說過這些“正經事”呢?
可以說,正是“晴雯之死”以及《姽婳詞》《芙蓉女兒誄》這一系列貫穿的情節,為讀者呈現了寶玉性格的轉變,突出時間、環境發展下人物性格的成長,使人物形象更富有真實感與生動性,更為深入立體。
綜上所述,《姽婳詞》意蘊深遠,其作用不容忽視。它應與《芙蓉女兒誄》結合起來,放在“晴雯之死”這一個情節單元之下進行整體地分析,這樣才不至于遺失關鍵信息,才能細致捕捉到林四娘之事暗含了晴雯形象以及寶玉經歷這一事件后性格的顯著變化,從而對人物形象有更深入的理解與把握。
參考文獻:
〔1〕梁競西.論《葬花吟》、《姽婳詞》和《芙蓉女兒誄》的意蘊和作用[J].紅樓夢學刊,2000(3): 108-121.
〔2〕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3〕成敏.《姽婳詞》在《紅樓夢》中的作用[J].紅樓夢學刊,2007(5): 265-277.
〔4〕曹雪芹.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5〕朱志遠.論《姽婳詞》的寫作意圖——古典文學“張弛”美學之一例[J].紅樓夢學刊,2011(3): 24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