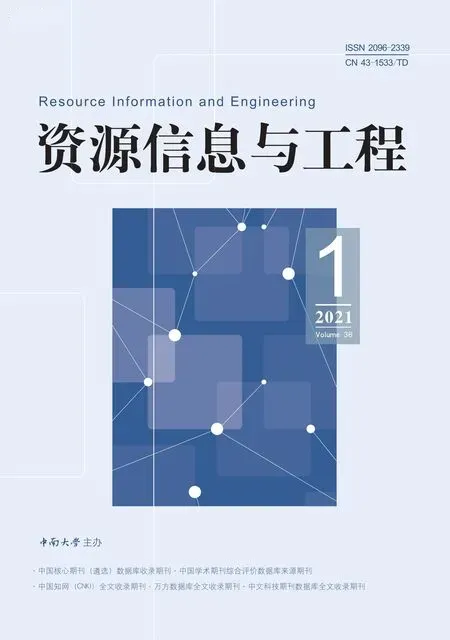凍融作用下碎石路基填土三軸壓縮試驗研究
田洪偉
(中鐵十九局集團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遼寧 沈陽 110136)
0 引言
我國東北地區四季分明,屬于典型的季節性凍土區。在季凍區修建公路面臨諸多困難,如凍土問題、凍脹問題等。
目前,我國學者對于凍融循環作用下土的力學特性研究成果頗豐。崔高航等[1]對松花江含沙黏土進行了循環三軸試驗,考慮了凍融循環、動應力幅值、頻率以及圍壓等因素,分析了不同影響因素對飽和粉砂土的動剪切模量和阻尼比影響。范昊明等[2]以東北地區幾種典型土為試驗材料,分析了凍融循環作用下各土樣的變化差異,總結了產生土樣變化差異的原因。師智勇等[3]采用電鏡掃描和分散性測試的方法對吉林乾安地區的土體進行了凍融循環后的試驗,分析了凍融循環作用后土體的微觀表現及分散性變化規律。任昆等[4]通過開展三軸固結不排水試驗,分析了煤渣改良路基土的凍脹性與強度特性,并基于灰色理論建立了考慮凍融循環作用下路基土的凍脹預測模型。
綜上研究結果可見,凍融循環對路基土的影響較為明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進一步對路基土受凍融后的力學特性進行研究,分析不同試驗條件下土樣的抗剪強度參數、彈性參數的分布規律,以期為季凍區路基施工提供可靠的試驗依據。
1 試驗介紹
1.1 試驗材料
本文材料取自遼寧某在建高速公路碎石路基上部素填土。按照《公路土工試驗規程》(JTGE40—2007)中的相關試驗規定對本文試驗用土進行粒徑篩分試驗,得到的顆粒級配曲線如圖1所示。

圖1 試驗用土顆粒級配曲線
為檢測本文土樣級配是否良好,需根據式(1)計算本文土樣的不均勻系數Cu和曲率系數Cc:

(1)
根據土樣級配曲線可知,d10=0.0045 mm,d30=0.021 mm,d60=0.058 mm,則由式(1)計算得到本文土樣的不均勻系數為Cu=12.9,曲率系數Cc=1.69,滿足Cu>5和Cc=1~3,因此本文試驗用土樣級配良好。
1.2 試驗方案及步驟
本文凍融試驗在恒溫恒濕環境下進行,采用保鮮膜對試樣進行密封包裹,以此來阻斷試樣內部水分與周圍環境的交換。一般情況下,季凍區和高寒地區所面臨的工程建設問題主要為土的凍結和融化問題,因此凍融循環是使土體強度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遼寧屬于明顯的季凍區,因此對遼寧地區路基土進行凍融循環作用后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工程實際意義。
為了對比分析不同試驗條件下土樣抗剪強度、彈性模量、黏聚力及內摩擦角等力學參數,本文同時考慮了凍融循環次數、含水率和圍壓3種試驗條件,其中凍融循環次數擬設置0、2、4、6、8、10次,含水率擬設置12%、14%、16%、18%和20%,圍壓擬設置50,100,150,200 kPa。具體試驗方案如表1所示。

表1 試驗方案
試驗步驟:首先根據土工試驗規程制備滿足試驗要求的三軸圓柱試驗,試樣尺寸為(Φ39.1 mm×80 mm),將制備好的試樣用保鮮膜密封包裹,做好記錄;然后將密封處理好的試樣放入凍融試驗箱進行凍融循環試驗,設置最低溫度為-20 ℃,凍結12 h,再將最高溫度為+20 ℃,融化12 h,至此為一個完整的凍融循環周期,將所有試樣按試驗方案進行凍融循環試驗;最后將凍融循環后的試樣進行UU(不固結不排水)三軸試驗。本文三軸試驗全部在從英國進口的全自動三軸試驗機GDS上進行(圖2)。在UU試驗中,對經過凍融循環處理后的試樣施加圍壓,并保持軸壓恒定,設置剪切速率為0.2 mm/min,試驗結束條件可根據軸向應變進行控制,通常認為軸向應變達到15%時認為土體試樣完全破壞。

圖2 GDS全自動三軸試驗機
2 應力-應變曲線分析
圖3為不同試驗條件下試樣的應力-應變曲線,限于篇幅,文中僅給出當含水率為12%、凍融循環0次和10次時的應力-應變曲線(圖3(a)、(b))和當圍壓50 kPa時,凍融循環0次和10次的應力-應變曲線(圖3(c)、(d))。由圖可知,在相同含水率和凍融循環次數下,隨著圍壓的逐漸增大,試樣的抗剪強度逐漸遞增。在土體的凍結過程中,受剪脹力的影響相對較小,裂隙發育緩慢,抗剪強度降低速率在減小。在應力-應變曲線初始階段,隨著圍壓的逐漸增大,曲線上升相對較快。在相同的凍融循環次數下,偏應力與圍壓之間近似呈線性遞增變化,原因是圍壓能夠明顯限制試樣的徑向變形,使土體的承載能力顯著提高,導致偏應力逐漸增大。當試樣處于相對較低圍壓作用下時,應力-應變曲線隨凍融循環次數表現由應變軟化向應變硬化的趨勢,即土體強度達到峰值后并未出現降低,而是逐漸趨于穩定。因此,凍融循環作用是導致土體抗剪強度降低的直接因素。從微觀角度可解釋為,土體在經歷凍融作用后,其內部骨架結構發生了變化,水在土體中的熱脹冷縮使原始骨架結構反復受到外力作用而逐漸劣化,導致承載能力逐漸降低。

圖3 不同凍融循環次數下試樣的應力-應變曲線
同一圍壓和凍融循環次數下,當試樣的含水率為12%時,試樣內部土顆粒之間的骨架結構基本沒有發生改變,隨著含水率的逐漸增大,土顆粒之間的摩擦力逐漸減弱,骨架結構的承載能力逐漸降低,致使試樣的宏觀抗剪強度逐漸降低,應力-應變曲線逐漸朝軟化趨勢發展(含水率為20%)。在圍壓相對較高條件下,應力-應變曲線表現為硬化型。隨著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同一含水率下的峰值強度之間降低,應力-應變曲線逐漸由軟化型向硬化型過渡,土體塑性破壞加重。
3 抗剪強度分析
圖4(a)為含水率12%時,不同圍壓下試樣的抗剪強度隨凍融循環次數的變化曲線,4(b)為圍壓50 kPa,不同含水率下試樣的抗剪強度隨凍融循環次數的變化曲線。本文應力-應變曲線中包含應變軟化型和應變硬化型,對應變軟化型,試樣的抗剪強度取峰值點處應力值;對應變硬化型,試樣的抗剪強度取軸向變形達到15%時對應的應力值。由圖4(a)可知,同一含水率下,隨著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試樣的抗剪強呈波動變化,但整體上呈逐漸遞減趨勢變化。由圖4(b)可知,同一圍壓下,試樣抗剪強度的變化趨勢與圖4(a)基本一致。這是由于土體內部的孔隙富含水分,當溫度降低時,水凍結成冰,體積增大;當溫度升高時,冰融化成水,體積縮小,但此時受膨脹作用后的顆粒估計不能夠完全恢復變形,導致土體孔隙逐漸增大,致使土體內部水分逐漸增多,如此循環往復,土體劣化程度加深,承載能力降低。

圖4 土體抗剪強度與凍融循環次數之間關系
4 彈性模量分析
彈性模量研究土體力學性質的重要參數,在凍融循環作用下,彈性模量同樣受劣化作用。通常情況下,彈性模量可根據三軸試樣的應力-應變曲線得到,本文將軸向應變為1.0%和1.2%時對應的偏應力增量與軸向應變增量的比值定義為彈性模量E,可由下式表示:

(2)
式中:σ1.2%、ε1.2%軸向應變為1.2%時對應的偏應力和軸向應變;σ1.0%、ε1.0%軸向應變為1.0%時對應的偏應力和軸向應變。
根據式(2)可計算不同試驗條件下試樣的彈性模量如圖5所示。其中,圖5(a)為含水率為12%時試樣的彈性模量隨凍融循環次數的變化規律,圖5(a)為圍壓50 kPa時試樣的彈性模量隨凍融循環次數的變化規律。可以看出,兩種情況下試驗的彈性模量均隨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而增大,受凍融循環影響最為明顯的為第二次,且劣化程度逐漸趨緩。表明初始凍融作用是影響土體彈性模量的關鍵,隨著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劣化程度逐漸減弱,最終趨于穩定。

圖5 土體彈性模量與凍融循環次數之間關系
5 抗剪強度參數分析
土體的抗剪強度參數包括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對于同一種材料來說,二者在同等試驗條件下是保持不變的。內摩擦角主要體現出土體顆粒之間的滑動摩擦和相互咬合作用,黏聚力則體現出顆粒之間的膠結作用。研究土體在不同凍融循環次數下的抗剪強度參數變化,可為更好地分析凍融循環對土體的劣化機理提供理論基礎。本文通過4種圍壓來計算試樣的抗剪強度參數,對于UU試驗,莫爾應力圓的半徑為(σ1-σ2)/2,圓心坐標為[(σ1-σ2)/2,0],繪制4種圍壓下莫爾圓的公切直線,則切線與y軸截距為黏聚力c,切線與水平線夾角為內摩擦角φ。則黏聚力c和內摩擦角φ可表示為:

(3)
式中:α為切線與水平線夾角,(°);d為切線與y軸的截距,mm。
圖6為不同含水率下,試樣的抗剪強度參數隨凍融循環次數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凍融循環次數的逐漸增加,試樣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均呈逐漸減小趨勢,且減幅逐漸減小。隨著含水率的逐漸增大,同一凍融循環次數下試樣的抗剪強度參數減幅逐漸減小,曲線逐漸密集,且在凍融循環次數為2次時最為明顯。Origin軟件對圖中曲線進行擬合發現,試樣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隨凍融循環的增加均滿足如下函數關系:

圖6 土體抗剪強度參數與凍融循環次數之間關系
6 結論
(1)在相同含水率和圍壓下,土樣的抗剪強度隨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逐漸降低;在相同凍融循環次數和圍壓條件下,土樣的抗剪強度隨含水率的增大而逐漸降低;在相同凍融循環次數和含水率條件下,土樣的抗剪強度隨圍壓的增大而逐漸遞增。
(2)在相同圍壓及含水率下,土樣的彈性模量隨凍融循環次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小,同時減幅也在逐漸縮小,即隨著凍融循環次數的無限增加,土樣的彈性模量最終會趨于穩定。土樣彈性參數劣化程度最嚴重的是在凍融循環初期。
(3)采用M-C強度準則(Mohr-Coulomb強度準則)計算土樣的抗剪強度參數發現,同一含水率下,試樣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均隨凍融循環次數逐漸減小;同一凍融循環次數下,試樣的抗剪強度參數表現出相同的變化規律,采用Origin軟件對黏聚力和內摩擦角的數據進行擬合發現,不同含水率下二者與凍融循環次數之間均呈負指數函數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