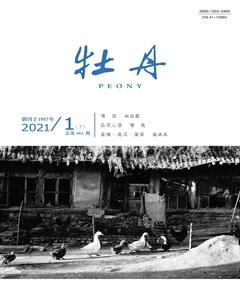柳 青
周萍如
曾經以為,詩就是那種穿過一年四季的東西。看春天花開燦爛,卻也有落花紛飛的幻妙;賞一棵千年常綠的松柏,卻也有冰封青翠歲月的奇觀。原來,一個人的孤寂、一首詩的感傷也可以深深地觸動著人們的心。翻開《旅者》時,短短的小詩像是有一個人在憂傷,兩三行言語像是在述說失落、迷茫、彷徨。柳葉青青,每一年的柳絮飄揚恰如詩人漂泊的生命,讓詩歌散發出憂傷的美麗。
孤獨不是一個人的心情,而是一個人的心境。因為當你感到孤獨的時候,這種孤獨就不是喜怒哀樂情緒下的悲和苦,而是你的心不再與外界聯絡,被圍困在虛渺的一個空間當中。然而,世界上沒有相同的兩片葉子,自然也找不出相同的兩個人。每一個人的理想追求不盡相同,更何況他們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孤獨很當然,也很必然。柳青很小的時候就萌發這種孤獨感。母親在她幼年的時候就去世了。一個幾歲的小孩,懵懵懂懂,常常因為好奇而恨不得把家里的東西都拆壞;每當大人要懲罰她的時候,她又喜歡哭著鼻子,用一雙呆萌的眼睛望著大人,企圖可以免去責罰。童年是一個人最快樂的時光,她時刻被愛保護著,無拘無束地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可是,病魔奪走了母親的生命,一夜之間,只剩下一張空病床。小女孩再也不能拉著躺在病床上的母親的手,聽媽媽講故事了。白日里,她望著那扇緊閉的大門,等待著善良的母親再次把它打開。一天、兩天、三天……無望的等待讓她害怕。母親的離開讓這個家庭殘缺,給她這個小女孩的心靈留下一塊傷疤。其中有一首詩《你走了》是這么寫的:
“心里空空的/像是/剛買回來的手提箱//你走了/煙熄了/點燃了/我的淚/失去了/平衡//找不到出口/夾在憂傷的縫隙里/窒息。”
你走了,心里空空的,就像剛買回來的手提箱。心里的方寸之地本來是充滿的。你走了之后,好像把“我”的思緒都掏空了。心里的慌亂、虛無好像因為一個人的不在而擴大,內心的空洞就像是新買的手提箱那樣空空如也。你走了之后,煙火燃盡,時間仿佛變成了焚燒而剩下的灰,一去不返。可是,那火焰并沒有消失,卻不知怎么轉移到了“我”的眼眶。可惜火焰再也沒有溫度,只能冷冷地貼著。情到深處的不舍讓眼圈的淚珠越來越沉重,終于失去了平衡,滾落下來。而“我”的心也失衡了,不愿接受現實,更寧愿去逃離,選擇不可逆轉的相反方向。時間漸漸褪去,人慢慢走遠,憂傷逐漸在空氣中飄散開來,將人吞沒,仿佛不能呼吸。詩中的“手提箱”“我”“你”“淚”“煙”等平平淡淡的事物寫出了心底的傷感。手提箱的空間比喻心里的失落,將抽象的情感賦予了形象上的空間化,說明了一個人的離去令“我”的心不知道失望了多少回,無望過多少回。落寞的心境如同比心臟大幾十倍的手提箱的空間那樣空虛。然而,煙是一種回憶,這是用一種借代的修辭,刻畫離去之人此前的形象,比喻“你”。煙火熄去的動態描寫瞬間讓人感受時間的流逝、事態的發展是一去不回的。煙將要熄滅的瞬間,只剩下那團小小的火焰,仿佛“我”的眼里即將看不到那最后一絲僅存的溫暖,留下的唯有冷卻了的淚水。最后的“出口”被具體化,形象化,說明心里的感情仍舊遲遲不得化解,仍舊找不到出路,便只能不斷地被自己的悲痛擠壓,直到窒息。
從這首詩的內容上面看,走了的那個人定然是“我”最愛的人,不然不會淚盡。天下的離散乃是常情,對于相隔兩地的人來說,時間久了,傷感也會漸漸淡化,因為大家都相信雖然天各一方,也總有團聚的時候。可是,“我”卻憂傷到窒息,那就是唯有天人永隔的處境了。我想這首詩所寫的離去定是柳青對她生命里最摯愛的人的一種表達。這里也定包含著那位曾經非常愛她的母親。曾經小女孩被抱在懷里,感受被愛的溫度,可是還沒讓她好好地去感受,突如其來地被放開了。父親是這家里的支柱,在外打拼支撐著這個家,可小女孩的心里依舊孤獨,因為她也需要媽媽。父親的愛就像是一棵大樹,遮風擋雨;而母親的愛則像是一個港灣,撫慰心靈。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需要父親提供的柴米油鹽,也需要母親睡前的呢喃。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作者構造“我”和“你”這一對關系,用你走后,襯托出“我”的獨自一人。從此,生活的空虛、孤獨給“我”蒙上了一層感傷的性格色彩。
柳青很小的時候就跟著家人到國外生活和學習。她選擇了理工科作為主攻專業。海外的文化差異讓長大后的她更加喜歡一種安靜的孤獨感。然而在我看來,理科的學習是一種理性的學習,因為它過于接近真實與絕對。現實的冰冷、規律的確定性一方面會讓人變得理智,賦予人客觀的智慧,但另一方面也會讓人感覺到人的無奈和渺小。現實永遠是殘酷的,這也讓憂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后來,她又選擇了她喜歡的專業,轉而去學習攝影藝術,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文科,由于造詣頗深,獲得了悉尼電影學院的獎項。這種藝術的學習讓柳青擁有了感性與理性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影響著她的創作,也成了她寫作《旅人》這部詩集的一個特點。正如詩集中所寫的《頂點的另一端》:
“不必擔心三角形的三條邊/是否可以圍住她的愛/她會回來的//不必學習古老的拉丁語/去解釋她暫時的離開/她會回來的//與其想象著她慢慢離去/不如借給自己一個月的時間/因為人在頂點的另一端時/永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三角形是數學的幾何概念,作者選取三角形作為意象,并從第三者的角度去勸說那位失落者。封閉的三角形就好比一個人際關系圈,不要企圖用關系去困擾別人,他若要離開,終究還是要離開的。也不要妄想用咒語去留住別人,那是困不住的。“我”想告訴你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有著兩面性,離去和歸來也是對立統一的兩面。正如三角形,不論你選擇哪一個角,都會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線。放心吧,她一定會回來的,因為你不管選擇哪一個方向,向左或往右,都會回到原點。這里三角形是封閉的三條線相連,一個三角形的角度和線條數都是固定的,這是規律。沒有一定夾角,沒有合理的邊長比,沒有固定的邊數,均不能構成一個三角形。所以,從這方面來講,它體現著客觀規律。作者卻能運用三角形的夾角所發射出來的兩條邊的透視法思維來比喻普遍事物所存在的矛盾性質——人的命運好像都是冥冥之中被注定一樣,逃不出一個封閉的圈。不管你選擇矛盾的哪一方,都會回到原點。所以,“與其挽留著她,不如讓她走吧”的勸說所折射出來的是一種對命運旅途的哲理思考。同時,這也巧妙地將起初那種規律的東西上升為一種處世的人生哲理。
然而,不管是這里所說的輪回觀念,還是上面所說的情到深處的嘆惋,都表現出一種憂傷的情懷。萬事都會有始有終,世上許許多多的事情不斷在重復上演。但是,世間有多少人真的能夠等到一切都回歸原點呢?傳說中的人參果樹,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可又有誰能夠像彭祖一樣長壽呢?恐怕生命的有限早已被萬事萬物的永恒超越了。都說西方的文學以悲劇為美,因其能直戳人心深處的脆弱,調動人的感受去思考。而在《旅人》這個詩集里,它總能抓住人小小的情感——離別、現實的無奈等,傳達出淡淡的憂傷之美。這與作者的經歷是有關的,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對細微事物的敏感,加上攝影藝術賦予,這都讓她在詩歌中表現出生命追求中的微妙感受。作者是孤獨的,她的一兩百首詩歌中,沒有過多人物對象,也很少描寫歡快的喧囂場面。
讀柳青的詩歌,仿佛像是在讀詩人的生活,了解她的心境。正如她在詩集的開頭所寫下的:“寫文字/只為了/有一天/可以被你偶然讀到/看著一行一行的句子/對照著自己/想起,曾經還有一個我。”我在這些詩歌中常常能夠看到一對戀人的影子,但他們的愛情不得長久;也常看到一個人在獨自等待、觀望,但最終都只剩下失落。他們都在努力地追求一種人性的完美,但又不得不去面對現實的缺憾。這一兩百首簡短的詩歌都是作者自己的真實體驗。長大后的詩人就是一個漂泊的游者,她一直生活在異國他鄉,受到種族差異的影響,而后又輾轉世界各個角落,去拍攝一些素材。攝影藝術者的視角都是獨特的,因為他們常常需要一個人獨自去思考。作為理工科出身,這些知識背景本身就奠定了她基本的人生價值觀念。在我看來,或許,她早就看到那些亙古不變的規律和定理——從生到死的不可逆轉性。所以,她的詩歌和其他藝術作品不僅流露出孤獨憂傷之情,更有對生死的感悟和人生哲理的思考。但最打動我的是,她寫的一切都不是虛構,而是一種真實的她,被命運捉弄的她。生活的一次一次不幸都好像砸中了她,她認真刻苦,努力去改變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得到一些寬慰。可是,母親走了還能回來嗎?那個曾經說愛她的人又去哪兒了呢?命運奪走了她最初的愛,奪走了她對困頓生活的最后一絲自慰。她努力去追尋一種完美,祈求這個世界的兩全。偏偏病魔選中了她,讓她無法去訴說,讓她抑郁,讓她最后的希望淹沒在她無盡苦痛的思考中。她說“最痛苦的/不是/找不到/通往門的那條路/而是/走到門前/被拒之門外”(《路》),那些壓在心底里的不平、哀怨、痛苦等,她無力去改變,只能選擇夢一般的方式,站在高處,飛向天空……最后的那首《抑郁癥》的絕筆成為她生命中最后的追問。堂妹柳笛在對她的悼念里寫道:“萌萌,天堂里沒有病魔、沒有煩惱,沒有塵世的喧囂與嘈雜,在那里你可以安心地構思,靜靜地寫作,再也沒有人去隨意打擾。”雖然美好年華的消散令人嘆惋,但我們依然尊重她的想法。也許,這個世界并不適合她,她要去另一個沒有太多牽絆的地方——更真、更善、更美的地方去解放自己。我想,于她而言,這不應該是一種悲痛,反而是一種成全。就像她的家人給梁潮老師寫的信中所寄托的那樣:“我們都希望她的詩、她的電影和攝影能夠讓她的精神生命繼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她的家人是很愛她的。雖然母親逝去的不幸,愛情的擦肩而過,病痛的折磨傷害過她,但正是生命中那些深深淺淺的感傷讓她的人生譜寫出了優美動人的詩歌,那一幅幅在獨自旅途中捕捉到的鏡頭展現了世界某個角落里獨具韻味的故事……而她的逝去不也是對她所有的文藝作品,乃至她的生命旅途意義的最哀艷、最凄美的焰火燃放嗎?我想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命路途中的旅行者,我們常常面臨失落、悲傷。當我們失望之時,總會記得身邊有一群人在忍受著一切痛苦,但仍努力地追尋夢想。這份精神不也恰如詩人在憂傷中仍執著以詩活在許多人的心中嗎?她的詩永遠是美麗的,她說過詩歌中有個曾經的她,我們都記住!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