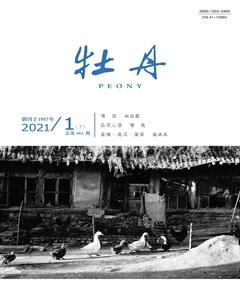法國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融合與實踐
以波德萊爾、蘭波、魏爾倫等人為代表,象征主義作為法國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流派,作為現代文學的開端,其象征主義思潮和對詩歌的改革創新已經越過法國的界限,影響了整個世界。象征主義認為,現實的世界是虛幻的、痛苦的,而內心的“另一個世界”是真的、美的,詩歌的任務就是通過象征、暗示來連通兩個世界,啟發讀者的思緒和聯想,并主張通過對詩歌語言的特殊排列,形成撲朔迷離的藝術效果。這些主張對于中國現代派詩歌的產生與發展都形成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中國現代派詩歌在接受象征主義詩歌理論及特點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探索,開拓一種適合于中國詩歌的象征主義模式。
一、中國現代詩作中早期出現的象征因素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象征主義在中國傳播,在當時曾掀起了一股熱潮,成為一種時尚并風靡一時。在其傳播初期,很多作家會有意無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象征主義的印記并以此為榮。例如,羅家倫曾經把沈尹默的《月夜》稱為“頗是代表‘象征主義”的作品。而周作人則直接在其作品《小河》中說該詩與“法國波德萊爾提倡起來的散文詩略略相像”。而冰心的《瘋人日記》,魯迅的《野草》《狂人日記》等作品在當時也被認為是渲染著濃重的象征主義色彩的。由于象征派主張對詞語進行特殊的排列組合,因此中國的現代派也進行了一些詩語試驗。例如,穆木天、王獨清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作品中運用了不同字體、奇特的排列順序以及許多的象聲詞,這就是初學。
但是,這一時期由于象征主義的傳播并不是非常的徹底和全面,早期的象征理論批評與實踐都還停留在比較淺表的層面上,要么只是單純地強調象征的表現手法及其應用,要么就是把象征所暗示的一些東西完全歸結為抽象的“哲理”,甚至把這種特殊的抽象與藝術思維的形象性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在中國詩人對象征藝術借鑒的早期存在著“抽象”與“形象”分離的問題。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派詩歌的創作也只能說是作品包含一些有價值的象征主義元素,還不能稱其為完全意義上的象征主義作品。
二、中國象征詩作的初步實踐
隨著法國象征主義詩學理論逐漸成熟及其在中國的理論傳播逐漸深入,中國象征詩學慢慢成熟起來并且結合漢語古典詩詞的傳統,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風格。
談到中國的象征詩,首先要提的代表人物就是“詩怪”李金發。李金發深受法國象征主義大師波德萊爾、魏爾倫等人的影響,將污血、殘陽、死尸、枯骨和荒野等灰色意向引入詩歌,先后出版了《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兇年》三部詩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詩人在旅歐期間所作。當李金發在巴黎忙于象征詩創作時,國內的新文學也正在把象征主義作為引進的思潮之一進行討論。李金發的象征詩對于早期引進的象征詩學理論是一個非常好的補充和說明。因此,從他開始,中國的象征詩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就迅速地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流派,這充分說明了漢語本身在象征詩的創作方面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在李金發之后,20世紀20年代,中國詩壇曾一度出現象征詩的繁榮景象。其代表人物有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石民、林英強、胡也頻、侯汝華、于賡虞和張家驥等。他們也都在象征詩的創作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開拓與創新。
一般認同是,中國的象征詩發展到戴望舒就基本上呈現出了一種成熟的局面。戴望舒是前期象征主義向中期現代派新詩過渡的中堅人物,他將象征主義詩學與中國傳統詩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向讀者展現了象征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學具有的潛在親和力。戴望舒不認同李金發為詩的怪異艱澀、神秘難懂,其詩作的旨意大多明朗,讀起來比較簡單通暢。比如其作品《寂寞》,題目“寂寞”二字即“文眼”,這首詩主題鮮明,下筆平易,行文流暢,整篇詩歌都環繞著“寂寞已如我一般高”的哀愁氛圍。再如,其象征詩的代表作《雨巷》蘊含了多層象征主義的元素,同時彌漫著“冷漠、凄清又惆悵”的中國傳統士人儒雅而落寞的情懷,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一種中西詩學的共融。這種融合讓中國讀者在讀戴望舒的詩歌時,既能勾畫出象征主義的意境,又不會感覺其像以往的象征詩那樣晦澀難懂。戴望舒初步確立了一種具有民族色彩的詩學范式,將象征詩學的“隱喻性”同漢語中“言近旨遠”的特征結合起來,將象征詩學所強調的“彼在世界”融入中國古典詩學的情境中,在現實之外又開拓出了一個意境幽遠的想象空間,在傳統詩學與現代詩學之間建起了一座橋梁。
從李金發到戴望舒,這一時期,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融合使得中國的象征詩確立起了一種“中西融合”的詩歌導向,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規定了中國現代詩學發展的基本取向。
三、中國象征詩的深化與拓展
隨著象征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后期的象征主義與意象論糅合在了一起。龐德的意象理論是法國后期象征主義直接推演的結果,其最終目的是要使意象成為“思想與情感在瞬間的復合體”。在后期象征主義的影響下,中國現代派詩歌由20世紀30年代的主“情”轉化為20世紀40年代的主“思”,追求思辨美和思考的深度,探討人生領悟,關注哲學命題。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廢名、卞之琳、何其芳和艾青等,每個代表人物的詩歌在實踐象征主義的同時也是各有各的特點。
廢名并不是以詩而是以詩化的小說聞名,其作品以禪宗佛學為根基,以禪機頓悟為表里的詩學形態。但廢名并不是通過他的作品來宣揚某種佛理。精研佛學給廢名所帶來的只是“知識”,而在這種知識的啟發下,廢名所感悟到的是一種在他看來切實而可靠的生存方式,這才是廢名真正有別于其他人的關鍵所在。
卞之琳的詩透著一種“思辨之美”,如“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其并不完全等同于哲理詩,而是用智能喚起了某種令人驚奇的效果。而何其芳的詩則是在淡淡的象征主義色彩中營造了一種中國古典婉約派詩詞的夢境般的氛圍。
艾青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第一個將象征主義的手法、浪漫主義的激情與現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詩人,其詩歌將其個體的生命體驗與時代精神綜合在一起。這種“綜合”已經揚棄了早期詩學探索中的那種表象化的融合。他為中國的象征詩開辟出了一條新路,使中國的象征詩學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拓展,為中國象征詩學的最終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的來說,法國象征主義的詩學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中國傳播,20世紀30年代被中國現代派結合中國詩學傳統,進行適合中國現代社會特點的借鑒和改造,從而成為中國現代詩學的理論產物。法國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融合實現了中西方詩潮的對流,中國現代派詩歌對法國的象征主義做出了大膽而有魄力的揚棄。中國現代派象征詩學的思想成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派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的朦朧詩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國新詩現代化的進程。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的詩學傳統的民族,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完全遵循西方詩學的導向來發展本民族的詩學。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一切既有的詩學資源都將是中國詩學發展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營養,只有懷著兼容并包的心態,汲取中外詩歌文化的精髓,并結合自身的實際進行再創造,才能進一步地推進中國詩歌的長足發展。
(安徽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孔曉理(1989-),女,安徽合肥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法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