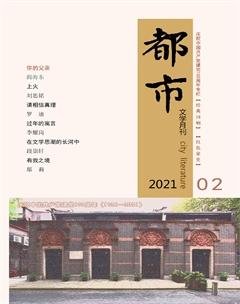母親與書
寫下“母親與書”這個題目,我的內心是復雜的,抑或是矛盾的。
總覺得,母親作為一名農家婦女,而且是一位養育了六個孩子的母親,如今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讓其與書聯系起來,實在是一件難以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的母親生在舊社會,長在苦難中,少小家境貧寒,出嫁后艱難度日,學堂一天未進,大字不識幾個,是個典型的農村婦女。
按理說,一般是有文化的人愛書,有知識的人藏書,會識字的人讀書,可我的母親,既沒文化,也不識字,卻偏偏愛書、藏書,甚至“讀書”,而且是年紀愈大,愈發愛書惜書。
生活中的母親,常為得到一本書而欣喜,也常常盯著一本書愣神。以至于凡來我們家的客人,誰要是帶來一本書或一本雜志,哪怕是一張報紙,如客人走時沒拿走,母親一定會收拾起來,好像這些比人家帶來的稀罕吃食都金貴;我們兄妹中,誰要是在家看一會兒書,母親一定會湊過來認真端詳,看上幾眼,仿佛自己也從中讀到或讀懂了什么。
母親用她樸素的感情和生活的經驗,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愛,不一定要懂;懂,不一定就是愛。
一
母親愛書。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情感流露。
母親什么時候喜歡上書的,我不得而知,但從我記事起,也就是我們兄妹六個大都在上學的時候,每當開學,我們一個個領回新書時,母親看著那一本本嶄新的課本,總會格外興奮,好像那些書本不是我們各自的,是她自己的。
于是乎,即便母親的農活和家務再忙,也要跑前跑后地張羅著給我們包書皮。母親把她積攢的平時村里隊上包裝化肥用的牛皮紙,一一分給我們。我們兄妹幾個,或炕頭或窗前,或堂屋或檐下,一個個接過母親分發的牛皮紙,手忙腳亂地開始包起了自己的書皮。
此時的母親,像是一個監考老師,來回地在我們跟前走動著,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瞅瞅那個,生怕誰把書本折壞了,或把紙皮浪費了。并不時地為這個遞剪刀,幫那個拿糨糊,誰最小,誰手笨,母親就親自動手來幫誰。每當此時,母親總會露出辛勞生活重壓下難得的笑容,她似乎從這窸窸窣窣的聲響中看到了她在生產隊耕種的田地里種下的土豆,在一場細雨后,紫色的小苗破土而出,緩緩長出地面時的情景。
這充滿生機的畫面,生動著一個家庭濃濃的親情,生發著一個母親切切的希望。
那時的農村,尤其是像我們這樣世代貧苦的農民家庭,既無家族傳承,也無念書之人,家里很少甚至根本就沒什么書籍。
在我的記憶中,家里最早的書是父親從生產大隊領回來的《毛選》四卷,那是母親的最愛。紅紅的封面,金色的主席頭像,甚是引人注目。母親說,里面寫的甚我不清楚,單看這外面就喜氣。
母親把這厚厚的四本書,擺放在了家里最為醒目,也最重要的位置——堂屋正面的柜頂上。她每天用雞毛撣子拂去書上的灰塵,并整整齊齊地和毛主席像放在一起,還時不時地叮囑小孩子們別亂動亂翻那寶書。
我們兄妹幾個上學用完的課本,也是母親的心愛之物。母親常說,讀過的書,耕過的地,收成都在后面哩,怎么能隨便丟棄呢。
我們兄妹中誰升級了,誰畢業了,母親都會在第一時間把那淘汰的課本,一本本收集起來,放在人們不常去的空房子里,保存起來。時間長了,還要去摸一摸,翻一翻,存放著的像是一家人的口糧一樣,用心著,在乎著,生怕受潮發霉,或是被老鼠給啃了。
母親愛書,看似無意,實則有心。七八十年代的農村,生產隊,大集體,人民公社作為一級組織,為了抓革命促生產,常有公社干部駐村下鄉。記得有一個叫老郭的下鄉干部,據說是個中專生,挺愛讀書,就是在村里下鄉,也經常是書隨人走,人書不離。因父親是村主任,又和老郭相處甚好,老郭就常在我們家,有事說事,遇飯吃飯。
一次,老郭把一本老舊泛黃的線裝書落在了我家的炕邊上。母親看著這農村很少見過的老書,雖識不得書名,但感覺一定是本好書。就用報紙包好放了起來,等著老郭有一天來拿。
時光把門口的老榆樹涂抹得綠了又黃,黃了又綠,也沒見老郭來拿他留在家里的書,就是平時到家里來,也從未提及。
那年冬季,高中畢業后在所在的人民公社工作了一陣后的我,就要應征入伍了。
在和親人告別,即將離開山村老家的那天中午,忽然間母親把堂屋里那個平時有幾分神秘的榆木柜柜蓋掀起,一邊解開用布包裹的舊報紙,一邊說,兒啊,你算是個念書之人,眼下你就要當兵走了,媽沒什么值錢的東西送你,今兒個就送你一本書吧,是老郭留下的,老郭喜歡的,一定沒錯。
這是一本像古書一樣書皮有些焦黃的舊書,隱隱約約中我辨認出了書的名字,是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此時的我不亞于得到一份或一件家傳珍寶,激動中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也許讀高中時政治課所涉及的一些哲學概念,在這本書里能得到系統的闡述,也許中學老師講的哲學就是認識世界的聰明學的提示,能在這本書里得到印證。還有什么東西比這本書更金貴呢?一直圍著我轉的父親也說,那天老郭到家里看你來了,說你在公社干得不錯,喜歡讀書,愛動腦子,就把這本他讀過的書留著送你了。
心暖責重。從此,我帶著這本有字之書一起從家鄉出征,它隨我出三晉,越陽關,翻天山,一直陪伴著我。三十多個春秋過去,這本閃爍著哲人智慧的書籍,仍然留存在我的書架上。
母親愛書也有發火生氣的時候。
大哥是個老高中生,在我們村子里算個識文斷字的文化人,喜歡讀閑書,抽旱煙。一閑下來,大哥就一邊抽著用紙卷的小蘭花旱煙,一邊有滋有味地盡情看一些雜七雜八的閑書。一次,正看得投入的時候,煙癮來了,大哥手頭有煙葉卻無卷煙的報紙。情急之下,大哥就順手從看的書背面撕了一綹下來。卷了煙葉正準備點著抽的時候,背后傳來了母親的喊聲:“虧你還是個讀書人!讀書人有扯書燒書的?”一句話說得大哥再也不好意思干這等粗魯的事了。
母親愛書,也愛聽翻書時那颯颯的聲音,那聲音勝似春天山坡孩兒吹起的柳笛,悅耳,入心;亦如夏天田間飄灑的細雨,動聽,酣暢。
因此,時不時,母親便翻翻書,聽翻書的聲音掠過耳畔,常常著迷得忘了手頭干的活兒。母親更愛聽子女們翻書的聲音,借著這聲音,母親似乎找到了一種生活的節奏,無論是燒火做飯,還是喂雞打狗,母親的腳步一定是輕盈的,歡快的。
二
母親藏書。藏書讓一個農村婦女,尤其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的內心豐富和充實起來。
母親藏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挑不揀,不分類別,也不論新舊。只要是書籍或書本,母親都會積攢起來,一本本,一摞摞,捋展鋪平,仔細存放起來。
在母親的眼里,只要是紙質的本本,都是書籍。我們兄妹幾個上學時的作業本,但凡拿回家里的,母親大都收拾起來,和那有限的書籍存放在一起。
七八十年代的農村,不像現在,上學所有的作業本,都是買的制式的。那時,我們所用的作業本,十之八九是用母親喂養的幾只母雞下的雞蛋,在村里代銷店換回的四分錢一張的連四紙,折疊成三十二開大小,用牛皮紙作本皮,拿線繩裝訂起來,只要一開學,每人都要訂厚厚的三四個作業本。
兄妹六人中,我的作業本訂得是最整齊、最漂亮的,也是我最愛惜的。所以,在母親收藏的書本中,我的作業本最多。從小學,到初中,直至高中畢業,母親都把我的作業本幾乎一本不落地收集起來,和我們上學用過的課本,一起存放在家里正房旁邊的小耳房中。
歲月總能把平常打磨得光亮起來,并且讓這平常凸顯而芬芳。在我奔赴遙遠的大西北當兵之后,母親把她收藏的書,特別是我念過的書和寫過的作業本,更加視若珍寶。
母親一有空就要到這間小房子里,面對我上學時曾經念過的書和寫過的作業本,或摸摸,或動動,或翻翻,或看看,那動作,仿佛是博物館的學者在揣摩他心愛的文物;那神情,又像是戰場上的將軍在審視他統領的士兵;那心境,其實就是一個母親在睹物思人,想念她的兒子。
就在我當兵離開家鄉四年,第一次回老家探親的時候,不經意中,在我家這間小房子里,發現了母親收藏存放的書籍和作業本。我隨便抽出幾本,有上中學時利用假期,用拔青草、撿廢品換來的錢,在縣城新華書店里買來的長篇小說《建設者》,自傳體小說《高玉寶》等書籍,以及我上學時寫過的作業本。
這些過往多年的一本本書籍,連同這寫滿密密麻麻字跡的白紙本本,像一枚石子落入故鄉村頭的小水壩里,一下子擊碎了我平靜的心湖,蕩漾起我兒時的點點記憶。
我宛若又背著沉甸甸的書包,行走在村莊和學校之間的十里山路上,好像又靜靜地坐在了那土窯泥凳的教室里。頓時覺得,母親似是個識字教書的先生,而我是她教出來的學生。
母親收藏書本并非都是順風順水,也有讓她不悅甚至傷心落淚的時候。
在我當兵走后的四五年里,我們家還居住在舊村一個叫南頭的地方。這年秋天,村民們正在忙著秋收,突然間,天空陰云密布,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態勢。頃刻間,暴雨便盆倒一樣傾瀉下來。
農諺說,秋雨露頭,農民犯愁。這雨一下,村民發愁秋收,母親發愁屋漏。
我家住的三間瓦房,頂上多是青瓦鋪好的,一般雨天是不會滲漏的。只是這旁邊搭建的耳房,房頂是用草泥抹出來的,平常小雨沒事,但遇有暴雨,特別是連著幾天的陰雨,小屋一定承受不住,非漏不可。
暴雨如注。母親急急忙忙,連爬帶跌地從田里跑回家,沒來得及進門喘口氣,就直沖那間存放雜物的小房子。看看屋頂,又看看墻邊的那一摞摞書本,確認沒有雨水滲漏的跡象,母親才忐忑地離開了這間寄予著一個農村婦女夢想的地方。
但是,雨還在下著,而且一連下了五天五夜,這讓母親懸著的心揪得更緊了,她時不時地側耳聽聽那間房子的動靜,從窗戶瞅瞅那間房子的情形,就怕屋頂漏了,把書本給毀壞了。
生活中,常常是事與愿違,你擔心什么,什么往往就會發生。就在連陰雨下到第五天天快亮的時候,母親忽然間聽到了院子里“轟隆、轟隆”的聲響,母親不無疑惑,擔憂地問熟睡中的父親,是不是旁邊的小房子有動靜?睡眼蒙眬的父親生怕急性子的母親天不亮就起來折騰,便隨口說,沒事的,聽聲音不像咱家院子。
天亮了,雨小了。母親第一個跑到院子,耳房的屋頂幾乎全塌了下來,屋內存放的雜物,尤其是母親收藏多年的書本,都和泥水攪和在了一起。此時母親手足無措地站在那里,悲痛欲絕。
女人的任性其實是與女人的倔強共生并存的。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雨水,也分不清是前晌還是后晌,母親把傷感化作了和命運抗爭的動力,從泥水中一本一冊地撿拾多年的珍藏,抖落沾在書本上的泥水,將那些看似完好的書本,很快轉移到了我們住的堂屋的柜頂上。
守著這些全力搶救回來的書本,母親如同守候一個失散多年后回到自己身邊的孩子,呵護有加,并試圖通過晾曬、撫摸、按壓、翻動,來恢復其本來面目。
明知有些努力是徒勞的,母親還是不厭其煩地做著這些努力。母親想以此來補救這次天災帶來的損失,并以此來釋放自己內心的不快,甚至是怨恨。
那些天,家里人經常能聽到母親像魯迅小說中的祥林嫂一樣,念念有詞,絮絮叨叨:唉!是我對不住孩子們啊!是我對不住念書的娃娃們啊!仿佛那天夜里小房子的屋頂塌下來,壓住的不是那些書本,而是我們兄妹中的哪個。
其實,比“漏雨事件”更為嚴重的,是幾年后的搬家。
20世紀80年代初,我的老家舊村搬遷新村的計劃開始實施,村里大多數家庭已經陸陸續續搬到了新村。我家兄妹六個中,當兵的當兵,上大學的上大學,父母親身邊缺少幫手,新房蓋得遲不說,單這搬家就拖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90年代初,我家作為留在舊村最后的幾家之一,不得已決定搬往新村。人們常說,要想忙,就請客;要想窮,就搬家。雖說一個家庭的貧富不是搬家而決定的,但舉家搬遷中的搬運倒騰,損壞東西甚至是丟失物件,總是難免的。
這天一大早,父親早早地把騾車備好,大哥也從村里借來了馬車,加上幫忙的鄰居銀虎哥、潤全和四全叔幾家的平車、板車,我家的院子,一下子像戰爭年代的戰場轉移,人聲鼎沸,雞鳴犬吠,只是這轉移的綽綽人影中,箱箱柜柜、壇壇罐罐,代替了號令硝煙和輜重糧草。
此時的母親,既費力又操心,忙里忙外,跑前跑后,一刻不停。母親,以一個女人的細心和主婦的操持,關心著大件受損,小件遺忘,忙亂中,始終沒有忘記她的至寶——那些歷經風雨、跟隨了她幾十年的書書本本。
母親是隨搬家的最后一輛馬車離開她生活了近半個世紀的舊村,以及那個充滿溫情和不舍的老屋的。
回到五里外的新村新家,已是下午時分。母親來不及休息,就一邊擺放收拾家什雜物,一邊清點著搬來的物件。
母親好像有一種預感,她積攢下來的書本,很可能隨這次搬遷發生變化。
果不其然,母親翻遍了滿院子的東西,找到的只是捆書本的一團繩子和散落的十來本舊書。于是,母親忙不迭地找幾個幫忙搬家的詢問,找卸車時圍觀的一群孩子盤查。奔走了一圈,只從幾個小孩子手中找到了其中的五六本書,她的尋找最終以失望告終。
轉而,母親又怪父親不操心,嫌大哥沒管事,最后,歸結為自己過于大意了。唉聲嘆氣中,母親終于找到了說服自己的理由:唉!書不就是讓人看的嘛,娃娃們拿去看了讀了,比我藏著掖著有用,找它做甚哩!
當然,母親并沒有因這次搬家造成的書本丟失,讓她的藏書夢喪失或破滅,只是變得更從容,更大氣了些。
無論是親戚朋友上門帶來翻看的書籍,還是我們兄妹們回家帶著閱讀的閑書和雜志,都是母親獲取或收集的藏品。只不過,現在母親不再把書籍真正地藏起來,而是放在堂屋的柜子上,或是土炕的窗臺旁,人們隨時可以翻看閱讀。
母親儼然像一個圖書管理員,靜靜地伴著流逝的歲月,守護著她的守護。
三
母親“讀書”。大字不識的母親,以其濃厚而奇特的“讀書”興趣,讓平淡無奇的農村生活有趣了起來,給這沉寂而遠古的山村續寫了幾多近乎荒誕的故事。
何謂讀書?讀書,就是看著書本,出聲或不出聲地讀。
母親以一個鄉村婦女的率真和一字不識的膽量,詮釋并堅持著她的讀書之法。
“端坐靜讀”法。在母親的心里,讀書其實就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把書當作圣賢看待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是隨著母親年齡的增長,自然而然地積淀之后形成的。
只要是母親正兒八經、認認真真“讀書”的時候,一定是家里沒有其他人或人特別少的時候,也一定是農閑時節或干完家務活的時候。
此時的母親,拿著家里唯一的那把木頭方凳,不是在堂屋里,就是在屋檐下,反正是找一處亮堂清靜的地方,手捧一本或厚或薄的書,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身體前傾,頭顱微低,目不轉睛地一頁一頁地翻看著書。并不時地翻翻停停,指指點點,母親真的像能認得那對她來說如若“天書”般的文字,進而明白書上寫的內容,以及其中的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當母親“讀書”讀到一定的時候,或者是“讀”到感興趣的一刻,便念念有詞起來,那聲音或高或低,若有若無,但,你一定不會聽清楚母親念叨的內容。
那情形真有點像小學生在學堂讀書學習的神情,只是,學堂里的學生是一群,這里的學生是一個;學堂里的學生是娃娃,這里的學生是老人。
母親這樣正襟危坐地“讀書”,是由最初的好奇,逐漸養成了一種自覺不自覺的習慣,沒事了,總想摸摸這本,翻翻那本。
即便是認不得字,讀不懂書,母親似乎也從這一頁一頁翻動的書聲中,得到了些許安慰,讓自己躁動的情緒平靜下來。所以,母親這種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有時會讓她情不自禁,甚止出神入化起來。
記得一年冬天,入伍在外多年的我,因思家心切,利用出差的機會順便回老家看看。在我急匆匆踏進院子,推開家門的時候,恰好目睹了母親“讀書”的情景。
此時的母親也許目光或心思還沉浸在書里,猛然間分不清是我從書中走出,還是本來就在書本里,一下子激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當我走近母親身邊,母親才恍然大悟,是遠在邊疆的兒子回來了。靜下來,才發現母親是在“讀”我寫她老人家的那本有文字,有照片的小冊子。
“看畫讀圖”法。熟悉母親的人都知道,母親喜歡“讀書”,其實,她更喜歡讀書里的繪畫和配的照片。
在母親的心里,“讀書”和“讀圖”是有區別的,母親一直認為,“讀書”是背上背了一袋玉米棒子回家的感覺,雖沉重但內心喜悅,總能看到收獲就在眼前。而“讀圖”其實就是看花花草草,像勞作了一天收工回家,輕松愉快,還滿眼的山山水水,人人馬馬。
母親讀書中的插圖繪畫,都會自然而然地和家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一田一地、一磚一石聯系起來。而且在聯系中對比,在對比中聯想,你一定會在書中靜止的圖畫中尋找到她眼中流動的風景,在一靜一動的感覺中,讀出滋味,甚至是韻味來。
母親在翻看有插圖繪畫的書籍的時候,常常是一邊看圖,一邊抬頭遠望,有時候還拿著書本站在自家屋檐的臺階上。向遠處的山看看,向對面的梁瞅瞅,母親一定是通過遠近觀望和虛實對比,找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那一部分。
母親愛讀書中的照片,尤其愛讀書中那些反映部隊生活的照片。
因為母親的六個子女中有四個,先后被她送進部隊這座“大熔爐”里進行冶煉鍛造,所以,母親偏愛翻看反映軍旅生活的書籍,尤其是書中每一張軍人的照片。
有學者稱,21世紀,由于科技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已進入“全民讀圖時代”。看來,年邁的母親還真的趕了一回時髦,成了這個時代不折不扣的“讀圖老人”。
母親是帶著感情“讀”書里的一張張照片的。二兒少小離家,在遙遠的大西北從軍戍邊,保家衛國。母親就根據人們的描述和自己的想象,對照書中照片相應的情景,試圖在茫茫戈壁和巍巍群山中,找到兒子站崗放哨、踏雪巡邏的身影。
三兒、四兒在省城消防部隊工作,母親就在這書中眾多的照片中,或在那高樓大廈下,或在那濃煙火海里,試圖看見兩個兒子平安無事地出現在眼前。
女兒軍校畢業分配到了部隊醫院,母親就在翻書“讀圖”中,不斷地尋找軍人或戰爭年代救死扶傷的照片,或是和平時期治病救人的場景,眼巴巴地看白衣天使里是否有自己的女兒?
女婿在蘭空駐疆某部服役,在母親的眼里,當空軍是最神奇的事情,在書中,只要有飛機的照片,無論是空中飛行的,還是地面停留的,母親都會眼睛瞪得大大的,想法子在藍天衛士中,辨認出哪個是自己的女婿。即便是看不清楚,或根本就無法找到,母親也會自言自語地說,這當空軍的女婿呀,忙得連個人影也找不到。
“積極參與”法。母親是個樂觀的人,她用笑看生活的心態,積極地面對生活中的一切。
就是“讀書”,母親也認為應該是“樂讀”,不應該是“苦讀”。有書同讀,好書分享,是母親對“樂讀”的最好解釋。
每當我們兄妹幾個探親休假回到老家的時候,總要帶些閑書抽空看看,只要我們中的哪個找一隅安靜之處看書的時候,母親便會悄悄地湊過來,和你一起“讀書”。此時,即使是手頭有活,母親也會邊忙邊走到你的跟前,或低頭瞅瞅,或彎腰看看,有時是靜靜地聽聽。
真不知道母親的那顆心有多大?但我想,那心房里一定能裝下整個世界,至少能容得下一方水土。
其實,母親在靜守子女們讀書的時候,最大的奢望是我們念出聲來,想聽聽那書里說的盡是些甚事,講的是些什么理兒。
再沒有什么比滿足一個人的愿望,更讓人開心的事了。我們便把一個人默讀變成了放聲的朗讀,而且語速也放慢了許多,語調輕松了許多,有時還盡可能地把文字變成方言土語,為的是讓母親能聽清楚書里的內容。
我相信,這時候的世界是最靜逸的,靜逸得只有這瑯瑯書聲,還有母親輕微的呼吸聲。
母親最期望和歡心的是“小字輩”們回到她身邊的那種歡聲笑語、嘰嘰喳喳的“讀書”氛圍。
母親的孫子外孫逢年過節,或是假期,都一個個候鳥般飛回了老家。這些孩子們,在短暫的節假日里,多是伴著假期作業和課外讀物度過的。這段時間,也是母親“讀書”最好的日子。
但凡孩子們寫作業的時候,母親一定會安靜而規矩地陪伴在跟前,眼花繚亂地看大家寫寫算算,一心等著孩子們把作業做完,像學堂里等待下課那一刻。
趁著孩子們作業寫完輕松愉快的時機,母親便把大家招呼過來,“娃娃們,念一會兒書吧,該換換腦子了!”母親把讀書和念書混為一談,她一向覺得讀書是城里人的洋話,念書才是鄉下人的土話,念和讀不就是個聽見和聽不見聲音的事嘛!
于是,孩子們便有的給奶奶讀一段童話,有的為姥姥講一個故事,七嘴八舌地滿足著一位老人家的“讀書”要求。這時的母親像吃了糖一樣,滿心的甜蜜,嘴微張著,眼半瞇著,并不時搖頭晃腦贊地嘆,拍手揮手稱道,以此表達自己“聽書”“讀書”的心情。
一時間,笑聲,鬧聲,讀書聲,穿過屋頂,越過小院,如清晨的薄霧,在山村里彌漫開來……
光陰荏苒,人生如夢。不是一晃就老了,而是一晃就過去了。
轉眼之間,母親已走過八十七個春秋,但母親說她沒老,老的只是那些過往的事兒。
她的從容如村頭的那棵老榆樹,自然地葉黃葉綠;她的淡定若門前的那塊鎮午石,沉穩地靜觀靜守。
母親依然如故地每天行走在這個和她一起風雨兼程的小村莊,每天一如既往地忙碌在這座給她快樂和溫馨的小院里。只是母親和書的故事,隨著日月,被時光的風雨浸染得斑駁陸離,一頁一頁地翻卷著。
“低徊愧人子,不敢嘆風塵。”母親,回憶這段往事,寫下這些故事,兒絕無嘲諷之意,只有敬仰之心。
其實,敬愛的母親,您就是一本無字之書,值得我們做子女的一生閱讀,一世珍藏。
責任編輯 管曉瑞
作者簡介:
呂鳳君,男,1960年生,山西五寨人,1978年入伍,長期從事新聞宣傳、理論研究和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大校軍銜,2016年退休。業余愛好文學、攝影,有300多篇(幅)作品被軍內外媒體采用。現居烏魯木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