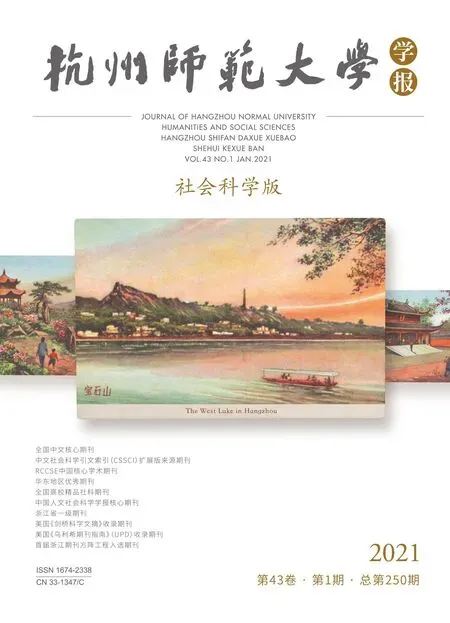體制藝術及其審美過渡
——從連環畫看傷痕思潮
李徽昭
(江蘇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1)
視覺文化研究認為,看的方式決定經驗獲得的方式、內容與效果,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視覺方式及所見之物關聯、影響著時代審美。從當下電子傳媒發達、圖像閱讀盛行,回望1949年后連環畫等印刷圖像的興旺,再細究1985年后連環畫藝術的沒落,可見視覺機制轉換中的時代意義與審美差異。70年代末,由劉心武《班主任》、盧新華《傷痕》、鄭義《楓》等小說起步,傷痕思潮逐漸延伸至高小華《為什么》、程叢林《1968年×月×日雪》、王亥《春》、何多苓《春風已經蘇醒》等傷痕主題油畫,形成全國性的傷痕文藝思潮,80年代新文藝大潮由此肇始。而在傷痕小說與傷痕油畫之間,連環畫以《傷痕》《班主任》《楓》等傷痕小說為腳本,借由圖像、文字的綜合媒介功能,進行繪畫再創作,形成風靡一時的傷痕連環畫文藝潮流。傷痕連環畫將水彩、水墨、版畫等美術類型納入圖像建構,以此與文學敘事相呼應,成為文學、美術融匯的復合型第三文本。在國家藝術制度推動下,傷痕連環畫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歡迎,出版發行數億冊,以視覺圖像形式擴大了傷痕思潮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形成大眾化觀看、通俗化認知的準支配性連環畫視覺機制。傷痕連環畫既與1949年后的“紅光亮”視覺審美拉開了距離,又潛在地溝通了新潮美術的視覺方式。其中《連環畫報》及其主推的《傷痕》《楓》等作品,以架上繪畫的精耕細作強化了色彩與構圖的沖擊效果,突破了舊的連環畫視覺審美意識,為視覺機制的先鋒轉換提供了新的可能。1985年尋根、先鋒等張揚個性、帶有現代主義特質的文學興起時,連環畫也轉向衰落。由此可說,連環畫作為“毛澤東同志文藝大眾化方針最出色的成就之一”[1](P.3),與傷痕小說密切合作,共同將20世紀50年代開啟的革命現實主義推向了最后的高潮。從美術視角來看,《連環畫報》期刊及其主推的連環畫《楓》《傷痕》等作品的構圖、用色已具有視覺審美的現代主義因素。傷痕連環畫這種緊密配合革命現實主義內容的高純度色彩、多元現代構圖的視覺新因素,通過大眾化普及方式潛在地轉換著舊的視覺機制,構造了80年代早期中國人的現代主義視覺審美經驗。因此,《連環畫報》期刊及其主推的傷痕連環畫發揮了視覺審美的中間過渡作用,為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潮美術的興起打開了視覺審美感受的新通道。
一、作為體制藝術的連環畫
連環畫藝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文化遺產。盡管“典型形式的連環畫主要形成于清末民初時期”[2](P.37),但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由于含有言情、武俠、神怪等低俗內容,連環畫曾“遭到社會的指責,致使其社會聲譽日漸下跌”[2](P.43)。魯迅等也竭力從木刻藝術和歷史發展的視角為之辯護,然而受精英文化影響,鮮有大成效,導致民國時期連環畫并未得到充分發展,只是在現代出版業及底層民眾需求的主導下,連環畫的印刷、出版、職業作者逐漸成形。連環畫發展的轉機在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區,中國共產黨及解放區政權捕捉到連環畫圖像簡單形象、易為民眾觀看認知的特質,開始以版畫、木刻畫等視覺方式介入連環畫創作,通過面向底層大眾的軍民題材宣傳革命政策,彰顯了政治動員功能。貼近民間百姓的視覺圖像使解放區連環畫主題內容“更易理解、更敏捷、更有效率”[3](P.5),在視覺意義上普及了這種屬于底層民眾的觀看方式,為新中國連環畫藝術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1949年后,通過解放區連環畫藝術的發展,新興的人民政權認識到底層民眾的欣賞能力適應于連環畫,連環畫、年畫、宣傳畫等圖像藝術與底層民眾的審美認知間存在著視覺方式的內在一致性,于是,主管部門在契合底層工農群眾視覺圖像偏好(版畫、木刻、線描等美術圖像)的前提下,對連環畫藝術進行了體制化改造,使之適應革命和政治需要。1949年底,毛澤東指示周揚要加強連環畫工作,隨后成立了專門出版連環畫的大眾圖畫出版社。[4]1950年,專門的發行機構連環圖畫出版業聯合書店成立;同年,上海開辦連環畫研究班,到1952年一共辦了三屆。1951年,國家文化部工作報告指出,“發展新連環圖畫與新年畫,改革舊連環圖畫與舊年畫,這是美術工作方面的重點”[5](P.105)。隨后,上海等城市開始回收舊連環畫(當年底75%左右的上海舊連環畫被處理)[2](P.76)。同年5月,《連環畫報》創刊。其他美術出版社也大量出版連環畫,據稱上海新美術出版社平均每周出版連環畫書籍10余種。1960年,中國美協專門召開連環畫工作者座談會。1963年,國家文化部設立連環畫創作獎,并進行第一次評獎;《人民日報》等報刊也不斷刊載連環畫。由上述系列行動可見,自1949年起,國家文化政策不斷主導、推動著連環畫的發展,連環畫也緊密地配合社會政治運動,逐漸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文字、圖像雙重閱讀觀看媒介。同時,受意識形態限制和印刷條件影響,連環畫也逐漸形成版畫與線描居多、黑白色彩為主、情節沖突為要的大眾視覺審美機制,這一視覺機制成為民間百姓習焉不察的審美行為。連環畫由此也具有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體制藝術的特征。作為體制藝術的連環畫視覺風格多直觀明朗(便于老少觀看),強調畫面的情節沖突性,主題內容上主要配合國家社會、政治需要展開,視覺審美性小于政治社會性,形成了革命現實主義的視覺風格。
1949年起,國家以政治方式規劃并引導連環畫等藝術的發展,竭力從最高領導指示、文件命令、獨立發行、題材規范、媒介建構、評獎鼓勵、作者培養、教育體系等方面打造連環畫藝術,看中的無疑是連環畫通俗易懂、文圖結合、深入群眾的特點。回溯20世紀中國視覺文化藝術發展史,在影視成為普及化的大眾傳媒之前,鮮有一門藝術受到國家體制如此大張旗鼓的推動,因此連環畫顯然是國家政權著力建構的藝術類型,其對于國家社會、政治的建構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50年代《連環畫報》幾乎每一期都有與社會政治同步的主題內容,如“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特刊”等,不斷彰顯其社會政治性。作為國家文化體制層面的一種特殊藝術,連環畫通過建構適應于革命意識形態的獨特視覺機制,形成配合社會主義中國文化的一種結構性、大眾化觀看形式,成為與中國民眾政治生活息息相關的視覺方式。“在每一個社會和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套與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相適應的支配性的觀看方式。”[6](P.14)從觀看的主體與客體兩方面來說,連環畫及其受眾間形成了認同,并主導了新中國社會文化的支配性觀看方式,官方主導的連環畫藝術由此建構了新中國民眾獨有的大眾化視覺方式。連環畫的這種貼合社會主義中國社會文化的觀看方式,以時代政治主題和大眾化視覺成為國家體制藝術,其藝術自律與他律形成同一關系,政治性便是他律性,連環畫大眾化審美的視覺機制由此建立。
其后,在“文革”一元化模式主導下,“連環畫在內容上基本以政治宣傳為目的,藝術手法和樣式模式化”[7](P.93),圖案注重情節、主題,視覺方式簡單化、通俗化,更是將他律性的連環畫藝術運作到了極點。盡管如此,在經典美術幾近絕跡的“文革”語境中,連環畫以政治化的體制藝術方式大力推動了美術的普及與發展。1949年后,由于國家竭力倡導并推動連環畫發展,使得這一藝術從民國時期廉價的圖像商品提升為人民的藝術,一大批有成就的畫家進入這一領域,如顧炳鑫、劉繼卣、賀友直等名家。他們不僅以多樣化的繪畫藝術探索、提升了連環畫藝術品位,也通過《雞毛信》《鐵道游擊隊》《山鄉巨變》等經典作品傳遞著國家政治思想主題。隨著前賢名家諸多名作的廣泛流傳,加之國家體制藝術的強勢引導,1949年后,連環畫行業闊步發展,“為其他的藝術尤其是國畫、油畫培養了人才”[2](P.133),70年代末的眾多美術人才都因參與連環畫創作而塑造了形式審美感覺。例如,80年代“傷痕”油畫重要作者幾乎都曾參與過連環畫創作,陳逸飛、陳丹青、劉宇廉、陳宜明、何多苓、程叢林等在傷痕思潮中突破較大的畫家,“當年都曾得到過《連環畫報》的扶持和幫助,都曾因其創作連環畫的‘牛刀初試’而引起畫壇的重視”[2](P.134)。 “文革”中,羅中立便“擅長用毛筆畫連環畫”,因此“在縣城小有名氣”[8](P.84)。陳丹青插隊時,“在田里種地之余開始畫連環畫。居然出版了三四本連環畫冊”[8](P.109)。可見,作為密切配合政治的體制藝術,“文革”連環畫以大眾化方式,成為其后傷痕美術畫家最好的藝術操練方式,為傷痕思潮啟動與發展儲備了美術人才,同時也昭示著,傷痕思潮與連環畫藝術之間存在著隱秘的革命現實主義審美關聯,傷痕連環畫因此具有了契合國家政治號召的藝術內驅力。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藝術的連環畫,其視覺機制受制于革命現實主義。1949年后30年中的連環畫作品,主要以傳統線描方式繪就,圖案簡潔、平實、直觀,色調主要以黑白為主,畫面強調情節性、沖突性,人物造型臉譜化特征鮮明。這種視覺圖像正是連環畫具有政治性、通俗性、大眾化等藝術特質的重要原因,切合革命現實主義的視覺機制恰恰滿足了民眾的觀看期待。這一時期連環畫圖案主要配合文字,相對居于次要地位,構圖、用色等藝術語言與同時期“紅光亮”革命美術相類似,鮮有較大變化。盡管顧炳鑫、劉繼卣、賀友直等連環畫名家對藝術形式做了相當大的探索,但由于受眾、連環畫自身特點與時代等多重原因,其繪畫語言探索明顯弱于吳冠中等人的油畫、水彩畫創作。直到70年代末,在國家的主導推動下,《班主任》《傷痕》《楓》等小說陸續發表,匯成傷痕思潮,連環畫也應時配合并進行諸多探索,突破了陳舊的連環畫審美視覺機制,才抵達了藝術高峰。
《班主任》《傷痕》《楓》等小說開啟了傷痕文學思潮,作為國家主推的體制藝術形式,連環畫及時呼應、配合傷痕文學,迎來了藝術發展新高潮。據統計,1980年,全國出版連環畫1000余種、4億多冊,部分連環畫首印數即高達百萬冊[9](P.241);1982年,出版連環畫達2100余種、8.6億冊,創下了新中國成立后連環畫出版最高年記錄。[10]如此龐大的連環畫發行量,隱隱地傳達著藝術委托人——國家體制的政治意識,在不同層面上策應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傷痕思潮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蘇。與此相應,被不同繪畫類型(版畫、油畫、國畫、木刻及其相應的色彩、構圖)介入的連環畫也打開了被“紅光亮”色彩固化已久的視覺機制與審美束縛。其中專業期刊《連環畫報》以突破時代規約的視覺審美方式,不斷推出新的連環畫藝術作品,尤其是陳宜明、劉宇廉、李斌合作的連環畫作品《傷痕》《楓》,影響廣泛,在視覺認知與審美感受方面突破了傳統連環畫的視覺機制與審美模式,以渲染色彩、高純度色塊、精巧構圖、拼貼圖案等,傳達了“文革”之傷以及其于個體、家庭之痛,與“85新潮美術”及其后部分作品的審美形式、視覺感受等內在呼應,表現出一種過渡性的視覺審美特質。
二、傷痕連環畫的視覺新風
《班主任》《傷痕》等小說發表后,揭露“文革”創傷、反思“文革”的傷痕敘事主題小說紛紛涌現,形成了傷痕文學潮流。傷痕文學潮流有其弊端,那就是傷痕小說多與“文革”文學有著相似的革命現實主義故事架構,形成固化的“傷痕”模式。正因如此,傷痕小說的審美功能便無形間受到與“文革”敘事相通的革命現實主義限制,受眾審美習慣容易回返到強化情節、人物扁平等舊的敘事與審美結構桎梏中。直到陳宜明、劉宇廉、李斌合作的連環畫《傷痕》《楓》發表,將傷痕的宏大敘事引向現代視覺審美的新軌道,使傷痕文學內蘊的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等,以視覺傳播的方式得到更深更遠的擴散,并通過色彩、構圖、形象塑造等視覺形式的探索,重構了80年代大眾的新視覺審美經驗。

圖1 連環畫《傷痕》封面 依次為江蘇1978年版、上海1979年版、廣東1979年版

圖2 連環畫《傷痕》內頁 廣東1979年版、上海1979年版
連環畫《傷痕》是以盧新華小說《傷痕》為底本進行的繪畫再創作,共有6個版本,其中5個版本是相對獨立的小人書單行本,分別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蘇華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5月齊雁與樂健版、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楊利祿與陶雪華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與傷痕小說革命現實主義敘事架構一致,《傷痕》小人書單行本圖像與文字中規中矩,多使用傳統中國畫工整、寫實特質的線描手法。白描線條營造著直觀質樸的畫面感,沿襲了連環畫典型的視覺審美風格。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人美版以黑白塊面風格繪制圖案,有著電影的畫面感,視覺效果大于文字內容,對讀者視覺經驗構成了一定沖擊。5個小人書單行本多緊扣小說進行創作,著意營造平和簡淡的日常生活氛圍,如對曉華坐火車的情節描繪,諸多版本均刻畫乘客閑談聊天的日常生活狀態,與《傷痕》小說中強調情節沖突的革命現實主義敘事形成反差,也凸顯了連環畫視覺傳達的直覺體驗功能,超越了小說原作簡單的情節沖突。
小人書版本外,有較大視覺異質性的是陳宜明、劉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的《傷痕》連環畫。該作刊于《連環畫報》1979年第3期,以水墨繪制。黑白效果中呈現出油畫質感,視覺穿透力更強,黑白色塊突出的畫面質感帶來凝重的視覺體驗,與主人公曉華的精神“創傷”形成潛在的對應關系。有的畫面構圖甚至溢出現實主義邊界,如夸張的人物形象、突出的空白效果等,顯示出強烈的抒情性,帶有架上繪畫創造性的藝術手法營造出新的視覺效果,遠遠超越了小說《傷痕》的敘事審美效應。如第20幅描繪曉華過春節的情形,作者把“人物壓到了下部的炕沿,造成了大塊的空白……這樣處理,利用空間和黑白關系,都幫助它造成一種壓人的空寂”[11](P.50)。這種俯視構圖強化了視覺壓抑感,與“文革”美術習慣仰視(《毛主席去安源》《我是海燕》等“文革”美術經典作品均以仰視構圖取勝)的人物構圖形成反差,卻給予觀者由視覺觀看達成對主人公孤寂的同感體驗,進而帶來體察、同情的情感認同。第21幅二人海邊散步,畫面只有兩個人,簡潔空明,抒情性畢現,完全擺脫了“文革”繪畫情節沖突的舊視覺,反而與90年代初新生代畫家劉曉東等寫實性繪畫形成視覺審美的相通性。總體而言,陳宜明等三人版《傷痕》連環畫圖片幅幅精致,每幅都可作為獨立的美術作品來咀嚼觀看(所以該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2007年起李斌又單獨以油畫方式創作該套連環畫,并重新發表于2018年第4期《連環畫報》),其藝術性、視覺效果、社會影響已遠大于小說《傷痕》,顯示出傷痕主題通過連環畫視覺傳達所具有的視覺審美開拓意義,以及連環畫轉為架上繪畫的藝術與歷史價值。

圖3 連環畫《傷痕》第20、21幅,陳宜明、劉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版
6個連環畫《傷痕》版本的創作腳本均是盧新華同名小說,但繪畫手法及傳播方式存在一定差異。陳宜明等合作的連環畫將故事轉為第一人稱敘事,并在《連環畫報》刊載,不可以獨立傳播。5個小人書版開本較小,依照原作為第三人稱敘事,可獨立傳播,社會傳播范圍更廣。由于當時小人書是“家喻戶曉、老少咸宜的讀物” [12],5個版本的小人書《傷痕》大大超出了小說《傷痕》原文本的影響,使《傷痕》的人道主義思想得到相當大的擴散。尤為重要的是,陳宜明等人的連環畫以帶有現代主義技巧的繪畫手法開闊了當時國人的視覺認知空間,突破了舊的視覺認知機制,打開了視覺審美感受新通道,這種視覺新經驗給閱讀個體帶來的沖擊有著身體視覺器官認知的特殊意義,是小說閱讀所無法抵達的。
實際上,在中西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文字與圖像之間一直存在著互補性、沖突性或差異性等多重復雜的審美關系。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必須借助文字來傳達審美意識、文化思想,其受眾需具備一定的語言文化修養,從而獲得理解小說語言的文化意識與審美思想結構的能力。與之相對照,連環畫等圖像的視覺觀看則可以不需要其他媒介傳導,而達成對文本的直觀認知與理解,圖像認知與交流因此更為簡便直接,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力主推廣連環畫的重要原因。正是源于連環畫綜合了圖像與文字的雙重特質,在《傷痕》眾多小人書版本連環畫之外,陳宜明、劉宇廉、李斌合作的連環畫《傷痕》便顯示出超越了小說《傷痕》以及其他小人書《傷痕》的審美意義。隨后三人合作的連環畫《楓》(刊于《連環畫報》1979年第8期)更有著超越文字、張揚視覺審美性的突出意義。
《楓》是鄭義的一部影響并不太大的小說,和《傷痕》同發表于上海《文匯報》(1979年2月)(1)其實傷痕思潮起點應是小說《傷痕》發表,連環畫《傷痕》《楓》逐步擴散,從下到上,才匯成人道主義為核心的傷痕思想潮流。。《楓》的故事架構較為簡單,有傷痕小說類似的模式化特征,小說發表后并未引起太大反響,文學研究也甚少關注。與之相反,美術研究卻對陳宜明、劉宇廉、李斌合作的連環畫《楓》給予較多關注,是眾多美術史教材繞不過去的美術文本。這種文學與美術間的反差不僅顯示出連環畫藝術在轉折年代的特殊作用,也表明傷痕思潮與連環畫的審美關聯,更是因為連環畫《楓》在色彩效果、形象處理、構圖角度等方面打破了舊的視覺審美思維,為先鋒文學、新潮美術等奠定了視覺審美基礎。

圖4 陳宜明等 連環畫《楓》 1979年
連環畫《楓》使用水粉畫法,畫面塊狀色彩代替了連環畫常見的黑色線條,并對各畫面單獨創作繪制,視覺沖擊力更強。《楓》以純度相當高的絢爛紅色展現武斗血腥空間,沖鋒槍、鋼盔、藤帽、女性等畫面直觀凝重,重要細節有視覺沖擊力與真實感。在影視尚未普及的情況下,《楓》的高純度色塊富于畫面感染力,觀眾的視覺感官瞬間被吸引并受到審美沖擊。《楓》的形式突破也相當大,其以“章法構圖的大膽開闔和色彩色調的大塊冷暖對比而代表了當時美術創作的最新探索。特別是整套連環以朱紅色為主調,既有利于‘盧丹楓’主角人物的形象塑造, 也對《楓》全篇小說意境的營造和主題寓意的深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2](P.4)。該連環畫還直接借用林彪、江青照片繪制于畫面中,頗具現代主義拼貼意味(“85新潮美術”與先鋒小說慣常使用手法),也使得“真實性或紀實性已成為一種手法,新聞照片的搬用改變了戲劇性構圖的方式,有一種強烈的現場感與歷史感”[13](P.57)。從當代美術史來看,《楓》可說是完成了形式審美與視覺機制的先鋒突破,在更廣泛層面上為80年代美術創造提供了視覺審美示范。
連環畫《楓》的視覺沖擊力主要來自畫面直觀呈現的人物悲劇,凸顯的正是傷痕思潮竭力張揚的人道主義關懷。畫面描繪的是盧丹楓、李紅鋼二人的愛情所寄寓的人性之美,卻無情地被扭曲的“文革”政治所破壞。李紅鋼放棄戰斗立場,本是人的反省精神的勝利,卻在反對派上臺后被處死,這種悲劇通過畫面視覺傳導到觀看者的感官心理層面,繞過了小說語言文字的審美轉化傳導,以直觀性的視覺認知形成銳利的思想沖撞與審美對照。正源于此,傷痕連環畫以視覺敘事包蘊并擴展了文學文化批判意識,使連環畫《楓》較之小說文本有著更深刻的藝術魅力。
《楓》的藝術突破還離不開連環畫傳播的影響。“刊發《傷痕》和《楓》的《連環畫報》,在當時的訂數有110多萬份”[14](P.36),如此巨大的發行量,使連環畫《楓》甫一發表即引起廣泛反響。由于對武斗畫面的渲染,該期《連環畫報》曾短期被禁,畫報社向主管部門力爭、申訴后,禁令才取消,這一事件更是擴大了該作的影響。主流期刊《美術》雜志在1979年第8期曾刊載多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對連環畫《楓》進行討論,顯示出該作突出的形式審美價值與視覺突破意義。今天來看,連環畫《楓》不僅以色彩渲染打開了視覺感受新空間,而且其“文革”的視覺空間描繪也啟發了現代主義美術創作。如連環畫《楓》對紅色革命標語的視覺描繪與“85新潮美術”吳山專“紅色幽默”、王廣義“大批判”等系列鋪天蓋地的紅色、亂糟糟的文字、“文革”畫面的復現等元素相同,這不能不說《楓》等傷痕連環畫對新潮美術有著內在的現代主義視覺啟蒙。不同的是,連環畫《楓》呈現的是與“文革”敘事模式相通的革命現實主義主題。
應該注意的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風靡大江南北的黑白色調小人書之外,主推了連環畫《傷痕》《楓》的《連環畫報》,有著更為多元的視覺審美新探索。作為國家主辦、主導的連環畫專業雜志,《連環畫報》在呼應時代、發揮連環畫圖文并茂、老少咸宜的宣傳教育功能的同時,也逐漸走出中西經典故事、小人書黑白色彩、單一圖像審美的單調性,開始不斷彰顯連環畫文學性與美術性兼顧的特質。雜志通過類似《傷痕》《楓》等新興連環畫美術家獨具視覺與形式審美特質的藝術探索,通過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俯視或留白構圖、高純度色彩等新的視覺表現手法,不斷呼應著現代生活律動,以此推動大時代轉換中的審美性與思想性并行、主導與突破同進。正是借助《連環畫報》這個期刊媒介平臺,以《楓》為代表的傷痕美術才能給人以視覺審美沖擊,受到社會上下的廣泛關注,《連環畫報》也由此與單行本小人書連環畫拉開了距離,以更具個性的視覺審美探索成為80年代視覺機制轉換中重要的媒介平臺。
三、審美過渡與連環畫沒落
借助《連環畫報》這個傳播媒介,《傷痕》《楓》連環畫以新的視覺審美形式省思了“文革”,傳達了傷痕文學的人道主義思想,這種帶有現代主義特質的視覺圖像和形式審美超越了傷痕小說所內蘊的批判精神,而有著更寬廣的視覺審美突破性。實際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對連環畫的關注與反應遠勝傷痕小說,這究竟是美術形式審美的特殊魅力,還是傷痕小說人道主義主題的沖擊,抑或是連環畫融匯美術圖像與文學主題形成的藝術合力呢?綜合來看,三種因素都存在。尤為重要的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帶來的觀看主體的審美期待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這一時期觀看者對于“文革”時期支配性、單一的“紅光亮”為核心的視覺審美已經產生疲倦,這為《連環畫報》及其推出的《傷痕》《楓》等連環畫提供了受眾,使視覺機制由單一性的“紅光亮”轉向多元化、個性化的現代視覺審美。盡管“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所接受的視覺體制往往是不同的……視覺體制不僅設定了其理想的觀看主體,并且還在詢喚主體,讓人們來自覺地認同這個主體” [6](P.14-15),面對大時代的召喚,以《連環畫報》為核心的新的視覺體制實現了對新的觀看主體的詢喚,并通過刊載連環畫《楓》的當期雜志被禁又重新發行的事件,實現了視覺機制轉換上的潛在勝利。
應該注意的是,《傷痕》連環畫這種視覺機制的悄悄轉換還暗含著視覺意識形態的重新建構。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作為國家體制主導的藝術形式,在社會文化變革的特定歷史階段,連環畫進行了藝術材料(水彩畫、水墨畫等)與形式(張揚的色彩、夸張的構圖等)的多重突破,取得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這兩種異質視覺形式雜糅并用的審美效果,這種視覺審美與傷痕文學人道主義思想形成了特殊的時代張力,在連環畫大眾化傳播的引導下,有效地發揮了視覺藝術的審美過渡功能。當然,也應注意到,連環畫《傷痕》《楓》乃至其后《張志新》的視覺形式審美的突破只是傷痕美術思潮中的典型文本,它們與高小華油畫《為什么》、邵增虎油畫《農機專家之死》、程叢林油畫《1968年x月x日雪》等傷痕美術作品一起構成了呼應時代的視覺審美現代新形式。與之相伴的是賀友直《山鄉巨變》、趙宏本《三打白骨精》、王叔暉《西廂記》等其他革命或古代題材小人書作品依舊在80年代產生著廣泛影響,并已成為較為經典的美術作品,但較之于《連環畫報》推出的《傷痕》《楓》等連環畫所帶有的現代審美特質(高純度色彩、留白與拼貼等藝術手法的運用)的視覺形式,明顯后者更有沖擊力、突破性,影響也更為深遠。
作為美術類型之一的連環畫,主要借助視覺圖像傳遞信息。如前所述,文字理性知覺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圖像畫面的視覺觀看具有身體器官接受反應的直接有效性,視覺圖像內容可以直接作用于觀看者。1949年后,在國家鼓勵引導下,連環畫、年畫、宣傳畫等大眾美術正彰顯了視覺畫面的通俗性、直觀性,策應與推動了國家政策的落實,但也因此固化了大眾化審美的視覺機制。就連環畫而言,1949年后較長時間里,黑白色彩、傳統線描、工筆等是其主要的技術手段,也是印刷條件制約下連環畫視覺形式所能發揮的最大影響(同時也限制了大眾的視覺審美意識)。1978年傷痕思潮開啟,作為體制藝術的連環畫及時、大量地出版發行,如《李自成》《山鄉巨變》《雞毛信》《鐵道游擊隊》等,盡管也都是名家繪制,并在視覺形式上有著精致的呈現,但大多未能走出連環畫體制藝術傳統的視覺審美與技術模式,直到陳宜明等人合作的連環畫《傷痕》《楓》的出現。
連環畫《傷痕》的紙本水墨、《楓》的紙本水粉色彩,對照相寫實主義與拼貼等形式的借用,對日常生活的直觀視覺呈現,這些新的形式語言與畫面不僅突破了連環畫大眾化觀看的舊視覺機制,也具有潛在的形式審美過渡意義。其審美過渡首先在于創作者將連環畫這一大眾化體制藝術進行了帶有個體自由創造傾向的新突破,彰顯了藝術家的主體性。陳宜明等人盡管也緊扣傷痕小說文本、突出人道主義主題,但繪制過程中,傾注了對時代變革、思想文化、畫面構圖與視覺效果的個人理解,藝術家的創造精神、自由度遠大于傳統連環畫創作者(這也是他們當時能獲連環畫大獎、持續受到廣泛關注的原因),更接近于“85新潮美術家”的自由創造精神。《傷痕》《楓》的審美過渡性還在于,大膽借用拼貼等現代主義藝術手法,通過高純度色彩、大膽留白構圖等不同于傳統連環畫的視覺審美突破,形成了新視覺模式的廣泛傳播,刺激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各階層受眾的視覺感官,拓展了受眾的審美期待。陳宜明等人的連環畫將新視覺形式與舊故事模式恰當結合,成功實現視覺審美的現代過渡,為“85現代主義”為核心的先鋒思潮培養了受眾人群。今天來看,這種視覺審美過渡之所以落在連環畫藝術身上,主要在于,連環畫的視覺形式語言不是唯一的,水粉畫、素描畫、版畫、傳統線描等多畫種都可以介入,只要傳達故事腳本主題即可,這使得連環畫形式創造自由度相對更大,藝術表現空間與形式探索渠道也更寬闊。因此,《傷痕》《楓》等連環畫,不僅將文學作品以圖像形式再創造,提供了傷痕主題的視覺化途徑,而且將傷痕人道主義思想以圖文互動新方式進行了廣泛傳播,助推了傷痕思潮的視覺化演進與深化。同時,連環畫在視覺藝術創造中,得以借助體制藝術的大眾化傳播,以審美過渡的方式,為先鋒現代文藝發展奠定了視覺審美基礎。
正是這種視覺審美過渡,使傷痕連環畫等美術作品傳播效果及影響遠遠大于小說文本。《楓》最典型,作品發表一個月內,《連環畫報》編輯部接到130多封來信,其背后涉及的思想轉折、精神關懷等問題顯而易見。這“顯示了美術作品形象教育特有的影響和力量,——這組畫無疑達到了小說無論如何達不到的藝術效果,感染力之強,已經見于各界的反應”,可見,“美術作品一旦發揮了它形象的作用,哪怕只是從小說那里改編成連環畫,也能產生非常強烈的尤其是獨特的藝術力量”[15],連環畫審美過渡帶來的視覺審美突破及其影響是應該重估的。
然而,作為國家主導的體制藝術,連環畫隨著傷痕思潮一起抵達最高峰,推動了時代思想與社會文化轉折,卻在1985年遭遇發展瓶頸,銷售量急劇下滑,出版品種、發行數量大幅減少,幾乎陷于停滯。[2](P.148)有研究者將之歸于創作粗糙、發行矛盾、電視與通俗書刊及日本漫畫沖擊等內外多種原因。上述解讀不無道理,然而回到連環畫藝術內部來看,或可發現,作為體制藝術,連環畫存在著自身的藝術生命問題。首先是80年代文藝重要扭結點在于,文學、藝術力求掙脫政治體制的牽制與束縛(所以“純文學”呼聲始終回蕩在80年代文化場域中),試圖回到文學、藝術的自律軌道上。80年代這種“純文學”“純藝術”誘惑對于連環畫而言面臨雙重難題。其一,從藝術自律性角度而言,連環畫是一種依附型藝術,其創作受文學腳本制約,在其匯集視覺畫面與語言文字兩種認知體系優點,以圖畫呈現彌補文字抽象思維不足的同時,也弱化了面向藝術自律(單一畫種、強調形式語言等)的自我藝術主體性,也就是說作為美術類型之一的連環畫藝術自律性是弱于油畫、國畫的(盡管它可以借用油畫、國畫的藝術形式),這導致在純文藝不斷發展的趨向上,連環畫落伍了。其二,作為1949年后國家主導的體制化藝術,連環畫主題內容不得不順應或緊貼時代政治潮流(主題內容從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都是《連環畫報》所主推主導的,但如《楓》等作品也有旁逸斜出),這也與力求脫離政治影響的藝術自律性潮流逆向而行。
應注意的還有,連環畫推動傷痕思潮發展并借此抵達自身藝術高峰的原因,主要在于其配合傷痕小說,恰切地運用了現實主義藝術手法,也就是說,作為體制藝術的連環畫與革命現實主義具有同一性。而傷痕思潮后興起的尋根、先鋒小說是屬于藝術自律的現代主義行列,這就挑戰了內在呼應現實主義的連環畫的藝術發展動力,成為連環畫發展的自身難題。連環畫這種體制藝術能否以現實主義視覺圖像來表達一個現代主義敘事,或者說連環畫能否實現自身的現代主義轉向,是一大難題。作為連環畫發展高峰的《傷痕》《楓》高純度色彩、拼貼形式等現代主義繪畫因素的突破,也正是連環畫應對其后文藝發展現代趨向的一種藝術自律性掙扎,但其形式也受到諸多局限,僅能在部分作品與畫面上有所借鑒,顯然難度極大(可以想象,以連環畫圖像方式來呈現孫甘露、馬原、格非等先鋒魔幻敘事非常困難)。80年代文藝思潮迅捷變幻,面對突然到來的現代主義形式挑戰,配合主題、現實主義審美表達的連環畫藝術,已漸漸喪失了應對能力,只能漸漸走向沒落。
當然,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藝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觀看方式與視覺審美習慣。連環畫、年畫、油畫、國畫等眾多藝術形式,各自有其適應時代的獨特生命力。作為體制藝術的連環畫,是一種被建構的、適應社會政治需要的大眾化觀看方式,在觀看者的思想觀念、視覺審美與認知能力不斷轉換的大時代背景下,或許其生命高潮也只能與傷痕思潮同步。從19世紀末《點石齋畫報》風行,以中國傳統繪畫布局與西方透視畫法融匯出新的視覺審美,塑造了一種新的觀看方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連環畫、年畫、宣傳畫等張揚紅色的大眾化視覺機制的形成,都是觀看方式與視覺審美習慣的內在轉變。在時代轉換的大趨勢中,《連環畫報》及其推出的《楓》《傷痕》等連環畫以特有的現代視覺方式與小人書連環畫拉開了距離,潛在地推動了一種新的視覺審美形式與觀看方式的形成。然而,在“85現代主義藝術”風起云涌時,連環畫暗自沒落,其后電子圖像媒介崛起,連環畫也轉換了自己的生命方式,在報紙雜志角落,悄悄呼應著漫畫藝術。直至90年代社會加速轉型,現代主義、消費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多元混合的視覺形式及觀看方式呈現,乃至當下電子媒介觀看獨步天下,我們仍不能忘記,《傷痕》《楓》連環畫作品,以畫面與故事交叉融匯的人道主義關懷,創造性的視覺審美形式,沖擊了被禁錮已久的大眾視覺感官與精神意識,通過高純度色彩、新穎構圖、大眾化傳播等,使傷痕思潮超越了自身一直被視為“文革”模式的單一趨向,實現了向現代先鋒藝術的審美過渡,這是重新審視傷痕思潮時應特別注意的。
- 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其它文章
- 何來勝《李白憶東山(其一)》
- 黃印凱《聽風》
- 崔水良《龍井方向》
- 顧致農《高山流水》
- 徐境懌《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 林浩浩《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