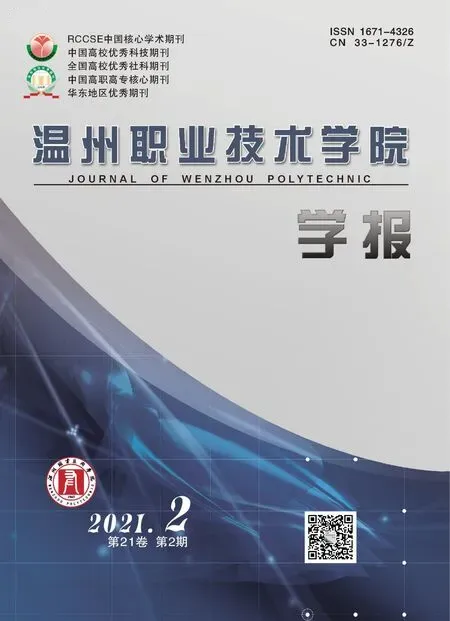“南懷瑾現象”綜論
陶祝婉,沈 潛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自20世紀90年代起,南懷瑾的著作在大陸大量出版,一時成為最暢銷的系列文化讀物之一。如今,南懷瑾的著作幾乎都有大陸版,其人也受到“許多人的高度的崇敬”[1]。這一著作熱銷、作者被熱捧的現象堪稱“南懷瑾熱”。同時,在這波熱潮中,學界也就南懷瑾的著述及為學問題展開了爭鳴,熱捧和爭議并存,形成了“南懷瑾現象”。本文從這一現象的成因、圍繞南懷瑾著述的爭議、對南懷瑾其人的評價及定位三個方面,結合學界主要意見做簡要述評。
一、“南懷瑾現象”的成因
“南懷瑾現象”形成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這一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并非偶然,它既有深刻的社會時代背景,又基于南懷瑾為學及其著作的自身特點。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基于不同視角的解釋,主要有四類觀點。
1.適應道德人心療救的需要
楊志剛認為,因為商品經濟的繁榮、物質生活的繁盛、法制建設的滯后、道德領域的失范和無序,人們試圖通過挖掘傳統倫理道德資源以重建道德體系,因而形成“國學熱”。“南先生談文化,往往談的就是人格修養,道德教育”,這是他的作品得到贊許的原因[2]。徐洪興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五四”先輩們摧毀了舊道德、舊文化,但新道德、新文化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這使得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進退失據,致有“文革”,又有之后的功利至上、道德淪喪。南懷瑾的著作重在講人格的培養,其目的在于啟發我們“在進退失據的現實環境中”,如何避免“在紛紜混亂中忙得團團而轉,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適從”[3]。汪涌豪則強調自19世紀西方物質文明對中國社會、文化形成沖擊以來,人們面對物質膨脹和道德淪喪,失去了有效應對,南懷瑾先生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精研儒釋道三家,發見民族精神和理想人格,為在現實環境中進退失據的人們及紛亂之世中的頹敗人性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療救[4]。由此可見,“南懷瑾熱”與“國學熱”同步,其成因與后來的“于丹熱”有諸多類似之處。
2.成功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
徐洪興認為,南懷瑾的著作讓人趨之若鶩,原因在于南懷瑾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進行了必要的現代化、世俗化、大眾化的調整、轉換,適應了人們渴望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5]。張紅霞認為,一般學者對經典的研究往往注重于考據、訓詁和疏釋,而南懷瑾對經典所包含的思想精髓有著深切的體認,進行了極其睿智的發揮和闡釋,講述經史合參、旁征博引,語言表達通俗流暢、生動詼諧,使得讀者在輕松、浪漫的氛圍中潛移默化地接受傳統文化的熏習,開啟人生智慧,因此對之好評如潮[6]。邢東風也認為,南懷瑾的著作深入淺出、觸類旁通、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文筆流暢,沒有干澀古板的學究氣,并不時閃現智慧的火花和獨到的見地,因此能夠吸引廣大的讀者[7]。陳士強、郭建慶認為,南懷瑾的著作之所以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并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是因其能從古代的人和事中擷取經驗教訓,作為今日的參考和借鑒[8]。姜義華也認為,南懷瑾著作之所以暢銷,重要的一條就是南懷瑾先生為學術大眾化和大眾學術化盡心竭力,他以博大精深的學術功底和在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面的高深造詣,對人們所關切的現實問題所作的貼近人心與人情的解說,使讀者不僅將其視為嚴師,而且視為知己[9]。也就是說,南懷瑾的思想精髓和表達方式符合大眾口味,契合了傳統思想文化普及化、大眾化的時代需求。
3.一種面對新的文化情境和文化大眾的釋義
顧曉鳴認為,在現代文化格局中,人們閱讀時更看重聯系自身生活和工作需要,不將作者本意作為閱讀追求的主要目標,且與文本相比,人們更看重作者的闡釋方式和寫作行為。如南懷瑾按照“自己的領悟和講授對象的需要”對經文進行主動的“別裁”和“他說”,就頗為符合現代文化機理。南懷瑾的機鋒和智慧、“身體力行”的修持以及“社會性事業”的成功,也符合“(后)現代思潮對以西方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及其推演方式的懷疑和顛覆”以及“世界范圍對人的軀體體驗與文化關系的興趣和研究”的大環境[10]。由此看來,南懷瑾的傳統文化敘事不僅體現了道、禪的體驗式、悟道式特點,也正呼應了后現代以來闡釋學的新思潮。
4.諸多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曹曉虎認為,南懷瑾廣泛閱讀傳統文化元典,有自己的學術創見。他“用現代學理性方法傳播傳統文化”,修養扎實,境界高深。南懷瑾攜在臺灣等地奔波教化三十多年的經驗和影響力進入大陸,適逢大陸民眾熱切渴求國學之時,其著述語言生動通俗平實,使用現代商業傳播手段。總之,“南懷瑾現象”是古代文化和現代文化交融的產物、思想研究和修行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海峽兩岸文化市場交流的成果[11]。
5.南懷瑾本人長期苦心經營的結果
姚彬彬認為,南懷瑾及其門人的作品經常寫到南懷瑾與早已有定評的近現代儒釋道諸領域的著名學人以及各界名流的“令人難以置信”甚至“駭人聽聞”的傳奇交往經歷,有意識地利用了常人潛意識層面的偶像崇拜的心理,神化自己的形象;而南懷瑾鼓吹所謂的“實證”或“修正”,其實是給予儒釋道等傳統文化典籍以神秘主義角度的詮釋,從而吸引了許多具有獵奇心理的讀者。因此,“南懷瑾現象”的形成,或可導源于文化啟蒙的不夠成熟,中國社會多年來重視科學技術而忽視科學精神的誤區,亟待彌補[12]。
二、關于南懷瑾著述的學術爭議
大陸讀者主要是通過南懷瑾的著作了解其對傳統文化經典的解讀,因而圍繞其著述的學術爭論也必然成為“南懷瑾現象”中的熱點。這些爭議大致分為肯定和否定兩派。
1.肯定其解讀視角的價值和文化普及之功
學界普遍認為,從學術視角考察,南懷瑾的著作確實存在“硬傷”,但從傳統文化普及的效果上看,他的著作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
郭冰認為,南先生在學術研究上也不可避免有先入為主之念,陷入主觀臆斷,致時有為合題意而生硬解釋之嫌,他的主觀隨意性決定了《論語別裁》不可能是一部學術性很強的《論語》研究著作,他并不重視考據訓詁,而多雜取百家且切合他生活經歷的“一家之言”,所以書中很多地方有明顯錯誤。但“南先生解讀《論語》時時體現著他自己的思想特色,旁征博引,深入淺出,將《論語》講得妙趣橫生,這是他的《論語別裁》大受推崇的原因。雖然他的講解并不一定是《論語》本義,但至少他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角度,為傳統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貢獻”[13]。他既指出了《論語別裁》存在明顯錯誤,不是學術性很強的研究著作,又分析了它受歡迎的原因,肯定了它的價值,這是中肯而客觀的評價。
曹曉虎認為:“不可否認,南懷瑾也有一些言論的學術性不強,甚至有些說法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不能過于苛責。畢竟,南懷瑾普及傳統文化的受眾不是學術界,而是普通大眾,傳道、授業、解惑都只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南懷瑾思想涉及面太寬,涵蓋易學、儒學、佛學、道學,兼及醫卜天文、拳術劍道、詩詞曲賦,不可能在每一個領域都達到專家級的水平。即使是學術大家在專業領域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學術錯誤。”[11]10他認為南懷瑾著作面對的是普通大眾,語言表述上不宜過于學術化;南懷瑾思想涉及面太廣,不可能全部精通,偶然的錯誤在所難免。既分析了這些“硬傷”產生的原因,又指出了它合理的一面。
宋紅寶也認為南懷瑾的《論語別裁》“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學術史上的價值還是可圈可點的”[14]。劉建軍認為南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典籍的新詮釋,為人們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文化空間與人生天地[15]。劉燕菇認為南著在眾多詮釋經典的作品中別具一格,既講究實用性,又兼具哲理性,是傳統文化經典詮釋作品中既通俗又不失水準的優秀作品,“他以傳統文化經典蘊含的哲理思想照察人心,從文化的角度剖析當今社會,其詮釋傳統文化的方式方法及內容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16]。徐祝林、徐徐兩位學者也認為,南懷瑾博古通今,盡管學術界褒貶不一,但他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使深奧的古籍通俗化、使專門的學術大眾化方面,確實做出了成功的探索[17]。
總之,對南懷瑾的著述,學界的聲音還是肯定者占據優勢。
2.指出南懷瑾著作中的“硬傷”
學者們指出南懷瑾著作的“硬傷”,主要在于解讀方法和知識的錯謬兩個方面。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著名學者張中行先生就撰文指出南懷瑾著作的問題。張先生認為,南懷瑾的《論語別裁》意見卻還是五四前后極少數人圣道天經地義、反對打倒孔家店那一路,講《論語》不能不牽涉到古事,專說小范圍的典籍,南懷瑾的看法,都是《古史辨》以前,流行的信而好古那一路。借用桐城派的術語,是只要義理、辭章而不要考據[18]。張榮華也認為,南懷瑾提出,秦漢后道家一直“隱伏于幕后”,充扮“幕后之學”和“歷史文化的導演”,《論語》二十篇的編排都是首尾呼應等結論,論據的分量不足,有些地方以老解孔,有些地方近乎“戲說”,只能“姑妄聽之”,他最終是站在佛教的基本立場上研習、詠味或闡論儒道兩家學說、義理[19]。李健勝認為,《論語別裁》中,南懷瑾釋讀的前提是使孔子語錄合理化,他以上下文相連貫的釋讀辦法,試圖消解孔子語錄中存在的驚論或不合理的成分,這樣的闡釋目的與現代學術意義上的闡釋目標顯然不相吻合,有一定的隨意性,且他有時是曲意引征古史的;他對孔子語錄進行了道家化、佛學化的闡釋,詮釋方法存在著不合理、不嚴謹的缺陷與不足;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對東西文化之間差異性的看法也過于偏頗[20]。邵盈午列舉了《歷史的經驗》和《論語別裁》中多個“確實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和“令人遺憾的‘硬傷’”,認為南懷瑾先生的古文今譯,沒有“以古人之心為心”,“錯逞私智望文生義以至‘六經注我’之處,頗不乏見”[21]。
如果上述批評只是不同方法論之間的選擇和爭議,那么下面這些關涉的就是知識性問題。如張中行先生指出《論語別裁》存在的錯誤:一是歷史知識錯誤,如把小戴《禮記》說成是孔子所編。二是對《論語》原文的有些解釋“不管語文規律,自己高興怎么講就怎么講”。如講《學而》篇“無友不如己者”時,將“無”解釋為“沒有”;講《學而》篇“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竟解“在”為“在面前”,“沒”解“在背后”,“志”為“言行一致”;講《八侑》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把通“無”的“亡”讀為“亡國”的“亡”[18]83-85。朱瑞新也指出,《論語別裁》在講解《雍也》篇時竟把吳起也當作荀子的學生[22]。
3.否定其著作的價值
由于南懷瑾著作的這些“硬傷”,有的學者對其持全盤否定態度。張中行先生說:“至于我,算作杞人憂天也罷,頑固守舊也罷,總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聽見下一代,由于讀了這‘妙趣橫生’的著作,竟至發出‘不如諸夏之亡(wáng)也’的書聲。”[18]86牛澤群認為,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迂闊、陳腐、謬誤、悖理,一應具在”“毫無明辨、透見、新獲不必多怪,但新添的唬人的玄說、夸誕,以及隱約的神秘,則嘔人”“更像是以《論語》強為引子的蹩腳的海聊神侃大雜燴”。它的暢銷,除“包裝炒作的成功外,足見中國大眾文化的落后、辨別力的低下,以及青年的易被欺惑”[23]。他不但全盤否定南懷瑾《論語別裁》的價值,且把它的暢銷歸因于包裝炒作及受眾文化層次問題。對此,北京大學李零教授表示贊同[24]。
方舟子列舉了南懷瑾《論語別裁》《南懷謹談歷史與人生》《歷史的經驗》等著作中存在的一些“中國歷史常識錯誤”后,評論道:“對這位喜歡信口開河的‘國學大師’的大部頭著作,我也就沒有閱讀的興趣。《論語別裁》據說是當代講解《論語》的名著,但我只讀了這一章,就知道這位‘國學大師’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什么意思也沒搞明白。”[25]深圳大學文學院徐晉如認為,“南懷瑾的書,錯謬荒悖滿篇,真稱得上是‘滿紙荒唐言’”“毫無價值”,根本不值得一讀;南懷瑾本人,“文言閱讀能力連現在的初中生水平都不如”“尊南懷瑾為南師的必系文盲”[26]。
當然,這種全盤否定南懷瑾著作價值的觀點,在學術界并不占主流。
三、對南懷瑾其人的評價定位
觀其書,想其人。在對“南懷瑾現象”的成因分析及著述爭論中,自然會涉及對南懷瑾其人的評價和歷史定位問題。而這同樣不乏不同意見。
對南懷瑾其人,無論學界還是民間對他毀譽皆有。史飛翔對之總結得較全:“他集教授、居士、護法,宗教家、哲學家、雜家于一身,被人贊之為‘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有人稱他是佛學大師、禪宗大師、密宗大師、易學大師、國學大師;有人稱他是當代道家、現代隱士、‘通天教主’;也有人稱他是‘高明術士’‘江湖騙子’。”[27]
不過,總的說來,學界持高度贊揚、崇敬或全盤否定兩極觀點的學者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學者所持的觀點都較為中正。學界通常稱其為“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15]65,“當代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28],“國際知名的文化學者”[29],或直接稱“南懷瑾先生”。
對他的學識,學術界基本還是肯定的,如前文所舉,姜義華認為南懷瑾先生有“博大精深的學術功底和對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面的高深造詣”;曹曉虎認為南懷瑾“廣泛閱讀傳統文化元典,有自己的學術創見”“修養扎實,境界高深”;徐祝林、徐徐兩位學者認為“南老的學問博古通今”,等等。
學界肯定南懷瑾在傳播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普遍認為他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做學術研究的學者。正如復旦大學王雷泉教授說:“南懷瑾先生的學問規模和抱負,很難用通常的學術尺度來格量。”[30]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這樣評價南懷瑾:“他似乎從來也不是一個學院中專門研究一個學科的學者,而是一個穿行于政商兩界,深入到華人社會的多方面的重要的角色,也是媒體和公眾所需要的焦點人物。……他最重要的貢獻卻是始終以儒釋道三家的闡釋者的形象賦予了中國傳統的價值一種現世的生活意義。”[1]文化譚、薛仁明兩位學者認為:“南懷瑾讀書極多極廣,卻絕非一般所說的學者。他沒有學問的包袱,也不受學問所累。”[31]既肯定南懷瑾的學識、貢獻,又看到了他的不同之處,理性而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