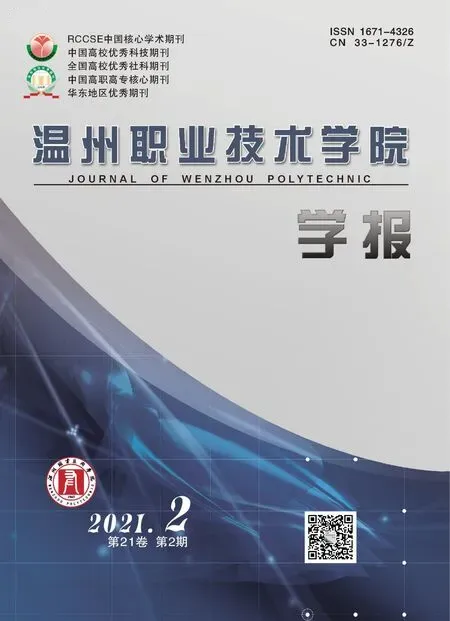時間·時·時節:朱利安的時間觀
姜 楠
(南京師范大學,南京 210023)
朱利安是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哲學家,其治學思路是經由中國反思歐洲思想產生的弊病。對于西方哲學中“時間”概念,他有獨到的見解,相關論述主要體現在《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一著中。西方對“時間”的思考非常豐富,但無論是從物理時間概念去思考,還是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將時與間對立,都是把時間劃為可以切分的序列,而這便造成了一種斷裂的罅隙。然而,朱利安發現,在中國思想里,時間并非均質,也沒有辦法去切割,中國古代并沒有“時間”一詞,中國人強調的是“時”與“時節”。中國人通過對“時”的思考去強調事物的過程與變化;“時節”可以使人們順勢而動、因時而變,從而準確地了解節令的變化。因此,朱利安認為汲取中國“時節”所流露的智慧同樣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將以朱利安的時間研究為核心范疇,探討中國古人對“時節”的思考以及“時節”的益處,從而進一步分析“時節”中蘊含的智慧與價值意義。
一、可切分的序列:西方對時間的思考
早在古希臘時期,自然哲學便有本源的時間意識。在柏拉圖之前,有關宇宙起源的一些學說就已經出現。柏拉圖之后,哲學便與時間這一概念綁在了一起,人們就如此安居在“時間”這一概念之中。無論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奧古斯汀,還是現代哲學家康德、柏格森、胡塞爾等,都對時間進行了豐富且多樣的討論。發展至今,西方的時間觀念也一直以明確性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視野之中。
朱利安在《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中把西方的時間觀劃分為物理的時間觀與形而上學的時間觀。顧名思義,物理的時間觀指的是物體運動所占有的時間,它思考的是“運動當中的物體”,這是根據物體進行位移的地點來思考以及測量物體運動的時間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時間,如動植物的生長所占有的時間[1]3。這種生長周期、生長運動也具體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顯而易見。在這個過程中,時間與運動之間相互測量、相互規定,物體也只能在時間當中運動。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物理的時間觀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時間的切割性。
柏拉圖認為,時間屬于永恒的摹本,理念是個永恒的“一”,但它的摹本又是永恒的運動著的事物,因此時間就是永恒的運動。這種說法認為,宇宙在創設之初,最缺少的就是這種永恒。亞里士多德認為,時間是運動的數,他的時間觀也落回到形而上學的追問方式當中去。亞里士多德把時間進行了空間化,在《物理學》中,他就認為一切物體都是在空間之中的,離開了空間,其他事物將不復存在。奧古斯汀也曾說道:“時間不論如何悠久,也不過是流光的相續,不能同時伸展延留。永恒沒有過去,整個只有現在。”[2]因此,他所強調的“時間”,也是不能夠伸展和延留的,它不是一個過程的延續,而只是表示了“現在”。這種說法,將時間的“永恒”直接限定于“現在”的框架之中,忽視了“過去”和“將來”。但眾所周知,時間不可能沒有過去和將來,如果空有一個“現在”,那么便會造成一種割裂的現象。因此,形而上學的時間觀具有一種“斷裂”的特點。
無論是物理的時間觀還是形而上學的時間觀,在西方的時間觀念里,它們都強調了時間中“間”的概念。“時間”被理解為一種可以切分的序列,人不能夠回到過去,亦不能夠預知未來,所以“過去”和“未來”這兩個部分由于自身的不確定性而無法成為時間的一個部分,它們并沒有“時間”的屬性,有這種屬性的只能是可把握的“現在”。所以說,在西方的時間觀里,確定性是“時間”的基本特征,西方人遵時、守時觀念的形成,也正是受到這種流傳至今且根深蒂固的時間觀的影響。當然這種時間觀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是一個可以切分的均質,它們每一塊都是確定的,是明了的,更是有始有終的。人們可以清楚明白地認識到每一部分的時間,明確每一個階段需要去做的事情;此外,由于西方的時間觀不強調過去與未來,所以這種觀念讓人更加珍惜當下存在的生活,并更好地去把握當下。但是,西方哲學對于時間的思考方式也存在巨大的弊端:由于把時間當成序列進行了切分,西方對于“間距”這個概念也進行了刻意的強調,這種思考方式便制造了裂縫、制造了“間”。由于這種斷裂的特性,它就自然而然地忽視了事物發展的動態變化和過程,并且呈現出一種快速僵化的傾向[1]5。西方的時間,在世界當中制造了裂縫,而人們恰恰又生存于這個裂縫之中。相反,古代中國都是用“時”字來表示現在所說的“時間”這個概念的。中國古人并沒有從物理時間的概念去思考“運動中的物體”,亦沒有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將時間與永恒進行對立。
二、跳出“時間”的皺褶:中國對“時”的思考
在朱利安看來,思想是容易產生皺褶的,“時間”這一概念,在西方的思維模式之中被塑造成形,已然變成一種墨守成規的思維習慣。他認為不能沉溺于這種思維習慣之中,必須跳出“時間”的皺褶,看向外部[1]7。中國,正是西方人需要看向的外部世界。如前所述,古代中國用“時”表述時間概念。那么,中國為什么要制造這種無“間”之“時”[3]呢?
朱利安發現,西方思想對于時間起點與終點的思考很全面,思考“創世記”、思考“世界末日”,并且采取公元紀年的方式來記錄時間[1]21。中國人對于西方“從何開始”這種歷史開端的說法沒有興趣。中國古漢語中沒有“是”這個動詞,“是”字的意思指“這”。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中國古人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模式,而是一種流變的觀念,所以沒有“間”這樣的裂縫存在,也沒有去思考與設想對立于時間的“非時間”[1]22。因此,中國古人跳出“時間”的皺褶,轉而對“時”進行了思考。
這樣一種對時間的思考方式在中國其實是貫穿始終的,中國古人在對“時”進行定義時,往往都不會給出明確的概念,如古詩當中的“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月上與黃昏,都是非常模糊的時間概念。縱使亦有詩云“奄奄黃昏后,寂寂人定初”,這里的“黃昏”是作為時辰名出現,而非前者與“月上”這一模糊時間相對應的詞語“黃昏”。但是,這種看似“精確”的時間概念,不確定性依舊是顯而易見的:“黃昏”和“人定”分別對應現在的19—21時、21—23時。如果從原詩《孔雀東南飛》的上下文進行分析,便會發現這是女主角劉蘭芝殉情的時間。但是從19時到23時,足足有4個小時間隔,這顯然又是不符合邏輯的。雖然這種描寫手法有古體詩行文時講究藝術表現的因素,但也同樣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于時間的思考仍然是模糊的,它沒有對時間進行清楚明晰的界定,沒有明確的時間意識。
此外,由于沒有“間”所制造的裂縫,中國人也不強調起點和終點。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對于這句話,通常可理解為孔子在為生命的短暫而感傷。但前文已經指出,中國古人不強調起點與終點,因此孔子這里講到的河水是流動的,是不斷變化的。可人們只看到水從始流向終,卻忽視了它的流動性與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逝者如斯”或許并非一種悲觀的思想,而是面對奔流不息的大河產生對人生的思考,對水頑強生命力的樂觀態度。在中國的思想里,“終點”就是“起點”。中文里有“周而復始”“終而復始”等成語,中國人認為生命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狀態,而是一種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的過程,這并非“時間”這一詞語所能夠限制的。因此,中國古人在思考時間時,注重的是事物的過程與變化,強調“終始”而非“始終”。“終”的本身也就是“始”。所以,中國人耐心厘清的并非“時間”,而是“過程”。
中國人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更加關注的是事物發展的“過程”。《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論是陰盛陽衰還是陽盛陰衰,都是陰陽往復的過程。它們不是一個個呆板的對立面,而是事物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關系。《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四十二章》)萬事萬物都可以在陰陽二氣的互相激蕩之中,最終形成新的和諧體。《周易》云:“生生之謂易。”萬物是生生不息的,變化也是前進不已的。因此,在中國人看來,并不存在著時間之外的永恒的東西,因為現在所擁有的,就是生生不息的變化過程。這說明,中國古人注重過程的“流變”,他們認為世界的運行是無窮無盡的,且這種運行模式必須被置于一個整體之中,它們是緊密相連的,是無“間”的。此外,中國人既講“陰-陽”,也講“春-秋”。人們通過“春”與“秋”來道出時間在一年中的運行。
既然中國對“時”的思考是模糊的、是過程的,那么它必然不會像西方的時間觀一般去創造裂縫的罅隙。既然不是斷裂的,而是變化的過程的,那么它強調的就是“久”。這便容易讓人們誤會中國的“時”只注重過程,而不強調時刻與節點。事實也并非如此,因為朱利安在這里也講到了“適逢”的概念,即“良機”。朱利安說道,當“時”轉變為“機會”,它便開始體現為一種個別而明顯的特殊狀態,足以讓為求制勝的謀略家攫取掌控[1]136。所以說中國人也在通過“時”來思考機遇,比如《道德經》中提到“居,善地”和“動,善時”(《道德經·八章》)。“善時”的“時”所指并非時間,而是“時機”。老子這里意在說明需要“等待”且不容錯過時間。再如“圣之時者”的孔子,他之所以會被尊為圣人,也正是因為他懂得順應“時”,順應良機。因此,中國人思考的是位置和機會,而不是空間或時間本身。
中國古人跳出了西方“時間”的皺褶,轉而對“時”進行思考,無“間”之“時”強調了過程與連續,但它又沒有否認“節點”與“時機”的存在,而是提出了順應良機的重要性。那么這種思考方式有什么好處呢?由此,必須提到另外一個概念——“時節”①朱利安認為,時節這一觀念在發展過程中始終主導著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想,無論是在祭祀、禮儀上,還是在政治上,皆如此。參見朱利安《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
三、“時節”存在何以可能:凡舉大事必順其時
“時節”是中國特有的概念,語出《管子·君臣下》:“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朱利安認為,在中國雖然沒有“間”的存在,但人們會去思考位置和機會,這說明中國古人也是注重節點,并伺機而動的。
“時節”在法語中是saison,而這個單詞本身也有季節、四時之意。中國的“時節”特點是透過氣候顯示出來的,且每個時節都有不同的活動,這個詞本身便含有情況和機會的意思。既然中國的時間思想中蘊含“機會”之意,那么“時節”的出現便顯得順理成章。首先,“時節”在農業生產活動當中最為常見。《禮記·月令》云:“凡舉大事,毋逆天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這句話就完整地概括了古代中國“時節”的含義:先民根據每個時節不同的特點進行多樣的勞動,亦根據農業出現的具體問題在恰當時機采取行動,他們順勢而動、因時而變。舉大事,必順其時,中國古人通過“時節”與萬物和諧相處。
中國古人以“凡舉大事,必順其時”來說明“時節”在中國得以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時節”的存在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呢?中國有關時節的闡述在《禮記》當中出現最多。如:“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禮記譯解·月令第六》)[4]209又如:“水潦降,進獻不用魚鱉。”(《禮記譯解·曲禮上》)[4]24這些,足以見得時節的觀念始終主導著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想,它無論是在祭祀禮儀還是政治上皆如此,“時節”所揭示的意義便是“合乎時宜”。《禮記》嚴格地規定了每個時節、每個月份應該去做的事情,作為規范的四時鼓舞著人們各種各樣的行為,使人們在四時中適應著天地之間的變化。如“孟夏之月,日在畢”“其日丙丁”“其蟲羽”“其數七”,等等。可見,“四時”構成了每一個“時”應該做的“細目”,而禮的制定者便在此基礎上規定出一系列符合時節的模式。朱利安認為,四時是不斷更迭的過程,是一個時節透過另一個時節進行更新的過程,“四時”所代表的并非僅僅是生活環境的點綴,而是組織著生命律動的場景。中國人也并沒有因為不斷交替的“時節”而把“時”所蘊含的過程性局限在周而復始的刻板印象里[1]61。莊子認為,“真人”既是“凄然似秋”,又是“煖然似春”的,他的喜樂與四時相通,他的情緒貫穿在各個時節當中(《莊子·大宗師》)。因此,“時節”之所以出現在中國,且讓中國古人如此重視,正因為它不僅具備了“時”的過程性和連續性,還強調了時間的機會性,從而揭示出世界生生不息的綿延進程。中國古人通過“時節”從農業生產中汲取智慧,遵循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的規律特點。這便是中國“時節”的特殊意義所在。
那么,注重“時節”在中國古代有什么好處呢?首先,由于每個時節皆召喚、對應著不同的活動,所以遵循時節有助于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古人“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才能不“違”農時、無“失”其時、勿“奪”其時。《呂氏春秋·審時》云:“凡農之道,厚之為寶。伐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災。”這里強調,農作的原則必以篤守天時最為重要,每一個人都應該在合適的時節伐木、捕魚、狩獵以及屠宰,如若違背天時,便必然遭到上天的懲罰。人只有通過遵照“時節”的變化才能與自然合拍,只有懂得正確地利用和保護資源,方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同樣也是自然和社會的雙向互動[5]。其次,遵循時令有助于統治者的統治。如果政治活動按照節令的變化而推行,對于統治者來說,便可為所推行的政令找到客觀依據:好的政令便是遵循時令,因為這是自然界所賦予的,并非是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所強求的,如果出現朝令夕改,那么“時節”就會遭到破壞,社會秩序將會變得紊亂。君王必須充分尊重不同時期的農業活動,尤其要注意不能夠在收割時期征召百姓。因為只有遵循時令的規律,才能使人民真心誠意地服從于統治者的統治。最后,遵循時節同樣有助于奠定一個國家的道德觀。這一點是建立在第二點基礎之上的,如果統治者通過遵循時令的方式使人民對其統治心服口服,人民安居樂業、和睦相處,就會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積極向上的道德觀念。
由此觀之,古代中國之所以強調“時節”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利用了自身所蘊含的“機會”特點與過程性,使得中國古人凡舉大事必順其時。如今,由于已經習慣于對自然的駕馭,人們在“所有的時節”進行任一活動。科技的進步雖然能夠確保人們在面對自然環境時擁有更多的自主性與選擇性,但這也同樣會導致對時節秩序的無動于衷。朱利安重新提到“時節”,正是為了讓人們重新認識古代中國的獨特時間觀,重新回到使人成為自由且具使命感之主體的事物上游。
總體而言,朱利安對西方的時間觀進行了反思,并主張跳出“時間”的皺褶,重新思考中國的“時”與“時節”。他認為,中國的時間思想突破了“間”的局限,更加注重過程與“久”,而“時節”則更體現出中國古人對機遇的把握。它們脫離了“時間”的框架,更加貼近實際,也更加貼近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