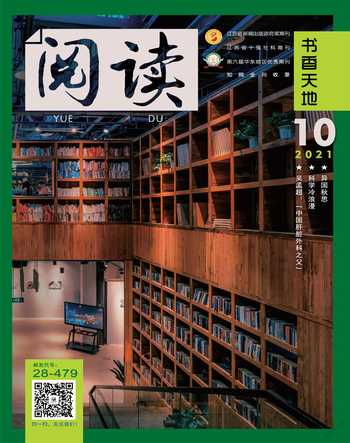王安憶:寫作是我的宿命
茱茱


很難說王安憶是不是上海女人的臉相,寬額高鼻長手長腳,聽人講話常常伸長脖子,卻把情緒藏得很深。不笑的時候簡直肅穆,大概是常年以筆作犁在格子田里勞作的關系。
王安憶長年保持著旺盛的產量,也不斷變換著寫作題材和寫作方式,德國漢學家顧彬說,王安憶寫作是神經質的,根本不能停筆,自1979年以后,沒有人能像她那樣寫出這么多值得嚴肅對待的作品。這種對待寫作的方式,仿佛是她與自己,和讀者達成的一個契約。之前去香港書展,她先講了一個關于讀者的故事。
監獄里的讀者
有一年冬天,她在布魯塞爾一個小書店里作講演,來的聽眾不多,其中有一個中年的中國男人,早早來到,讓她在一本《長恨歌》上簽名。講演完畢的提問環節,男人站起來講了一個故事,他先給大家看那本《長恨歌》上的公章,印的是“布魯塞爾非法移民拘禁所”,他是當年的非法移民,拘禁期間,監獄里放了兩本中文書供人消遣,一本金庸的,一本王安憶《長恨歌》,在大家爭著看金庸的時候,他無意地打開了《長恨歌》。曾經是上海人的他,頓時感到“我家臨街的一扇窗打開了”,他在監獄里把這本書翻了兩遍,后來想盡辦法把書帶了出來,而后還帶著這本書進了法國的監獄。最后他說:今天是我51歲的生日,我帶著這本書來到這里見到作者,當度過我的生日。
她講述的語調是平淡的、迅速的,講完故事就很快把情緒拉回來,她說自己和讀者的關系是微妙的,讀者喜歡的,也許是自己不喜歡的一部分。“所以我跟讀者更多的是尷尬,讀者還是隱性的存在比較好。”
作者與讀者,彼此不相見的緣分是奇妙的。當年讀《啟蒙時代》讀到數米的情節,在筆記本里恭敬地抄下來:“在那逼仄彎曲的街巷里,還有一對老年夫婦,你知道他們每天的功課是什么?數米。上午數出的米中午下鍋,下午數出的米晚上下鍋。這就是他們的內心生活。不是為生計勞苦,也不是純精神活動,是在兩者之間,附著于實物而衍生于內心。他們看上去是有些悶的,不大有風趣,其實是有著潛在的深刻的幽默。”新作《眾聲喧嘩》里面又安排了歐伯伯數紐扣的橋段,帶點禪味,像兩段獨幕劇,聚光燈定格在上海后街弄堂里、細水長流過日子的小市民背上,那是王安憶小說里的城市靈光。
戀戀俗世
昌平盛世里的俗世生活或許叫人倦乏,待經歷了動蕩苦難,或者犯錯惹禍,日常生活就現出療愈的功用,“它是那種煨藥的細火,漸漸地藥香滿屋,沁人肺腑,瘡痍漸平,元氣恢復”。她把感官全部打開,反復寫市井生活,不厭其煩。有人說,讀王安憶的小說最痛苦和最享受的都在于細節,她下筆有如繡花,針腳綿密繁復,她寫縫被子的線,“一針一針抽出來,理順,洗凈,曬干,再縫上。今年過了有明年,明年過了還有后年,一點不是得過且過。”日常生活是足以和虛無對峙的,“人生不能看遠,看遠了都虛無,要有一些近的東西來把你的眼睛擋一擋,就是市井。”所以老百姓是不大會虛無的,要掙錢、養家、追逐情愛,這些足以把虛無感填滿。
在她看來,張愛玲和魯迅都虛無,只是在這條路上,張愛玲和魯迅邁出了不同的步伐。張愛玲的虛無簡單而徹底,她相信人生是沉淪的、走下坡路的,所以她從虛無的入口抽身,轉而堅守現世安穩。而魯迅執意往虛無里走,“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
虛無本身沒有欲望,也能讓人從欲望中抽離出來,所以王安憶說,虛無本身就是升華。可以注意到的是,這種升華很多時候是由她筆下的女性來承擔的,尖刻也好,厚道也好,大多是堅韌的,幸或不幸,都能扛下自己的選擇。這種女性書寫也寄托了她的審美。“在我的認識當中,男性留給審美的余地不太大,我總覺得他們是主流社會的中心,他們在生活舞臺上已經被社會生活塑造過,不像女性帶有一定的原始性,所以從美學上來說我是比較傾向于女性。她們更加接近自然本色,這是我的審美,也有點人生觀吧。”
她寫《我愛比爾》,那個叫阿三的姑娘,怎樣因為執著于自己的西方幻想,由師范大學的美術學生,一步步成為專做外國人生意的“暗娼”。讀的時候竟有些捏一把汗。王安憶寫小說慣用敘事體,作為操控人物命運的作者,她的主體意識很強烈,人物對話不多,而以畫外音般的敘述推動情節的前進,作者的立場和評判很是一目了然,也因如此,拿捏火候變得很重要。王安憶覺得這種寫作方式能更方便明確地表達作者觀念,“其實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還是比較喜歡寫對話,你看《小鮑莊》里還是有很多對話,到后來慢慢我就比較迷戀敘述。敘述有一種客觀性,它可以讓我和我要寫的故事拉開距離,然后客觀地再寫,可能寫出來的面貌會很豐富。對話其實要作很多鋪墊,小說畢竟不是戲劇,小說有個方便之處就是它可以敘述,小說的長處是敘述。”
她寫的是人,也寫的是塑造人的城市。每個作家都有一個施展想象力的舞臺,這個舞臺通常是與其休戚相關的山鄉或城廓。沈從文有他的湘西邊城,莫言有他的高密,上海似乎是王安憶別無選擇的書寫場域,她輕易不流露自己對上海的愛恨,哪怕是有講述上海盛衰的煌煌長篇《長恨歌》與《天香》,繁華落盡唏噓無盡,她還是要說這個城市其實是粗糲的、不浪漫的。
遠去的理想國
1983年,她和母親茹志鵑來到愛荷華參加聶華苓的國際作家寫作計劃,臺灣作家陳映真去機場接她們母女,那段經歷,成為她人生的轉折點。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常帶著些被時代虧欠的怨憤。那一年同去愛荷華的有很多來自“問題國家”,菲律賓、波蘭、印度尼西亞。陳映真對她說,“你看看你周圍,他們問題都很嚴重,不要以為就中國問題嚴重”。這是很重要的轉折,視野打開,也從耿耿于懷中走出來。而陳映真,這個來自中國臺灣的具有左翼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無疑成了她極其重要的前輩。王安憶時常強調前面要有人:“我的焦慮是很想尋找前輩,因為前輩意味著傳統。”
陳映真對王安憶和那一輩人的影響也許是深遠和復雜的,羅崗說,“陳映真和魯迅的契合點,更重要的在于,他們到晚年,都接受了社會主義”。時代變遷,以大家都看到的方式無可阻擋地前行,世界變得一樣,她想要緊跟的前輩,未及趕上他,“他已經被時代甩在身后,成了落伍者”。陳映真對很多人和事失望,未竟的事業,未完成的理想國,讓身后的王安憶也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們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也是同一年,聶華苓的丈夫保羅·安格爾生病,從紐約請來一個大師,順便給這些中國作家看相,看到王安憶母女,“他說得很微妙,我很難表達清楚,他說你們倆都是艱辛,但你媽媽是苦的艱辛,你是樂的艱辛”。我欲要將這讖言同她的寫作生涯拉上關系,她又很迅速地打斷:“我跟你說,宗教的事情、哲學的事情都不能說得那么死,你們這個年齡不能這么快下判斷。”
我無以得知她的失落或希冀,只知道寫作是她的使命,大概也是宿命。我也寧愿縮回讀者的距離,繼續等待下一個虛構的理想國。
(摘編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無物之陣》一書)
378550118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