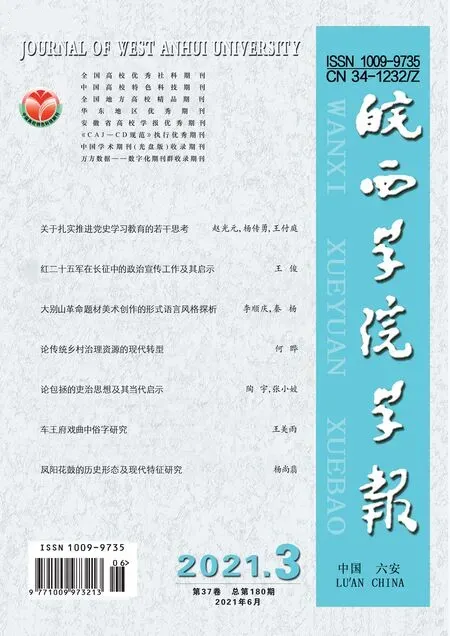《湘江評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桂運奇
(皖西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一、《湘江評論》創刊的歷史背景
《湘江評論》創刊于1919年7月14日。其時,就國際形勢而言,正值一戰結束不久,歐洲衰弱分裂,為社會主義革命在沙俄的興起創造了條件,不久蘇維埃俄國誕生,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激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斗爭熱潮。
就國內環境來說,腐朽的清王朝雖被推翻,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并未完成,志士仁人仍在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1919年5月,因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并迅速席卷了全國。消息傳至湖南立即引起反響,在毛澤東的積極推動下,湖南學生聯合會于6月3日宣告成立,并于當日決定發動湖南學生總罷課,以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1](P33)。此時,毛澤東等人認為迫切需要出版一份有高度思想性的刊物來鞏固群眾的革命熱情,推動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湘江評論》隨后問世,毛澤東擔任主編。
五四時期雜志和報紙的區分并不特別明顯,因此《湘江評論》究竟屬于雜志還是報紙,學界至今仍是見仁見智。《湘江評論》每期都刊發“本報啟事”,毛澤東也自稱該刊為“本報”。但刊物本身在編排形式上分(卷)號出版且主要欄目及出版周期固定,表現出雜志的某些屬性和特征。《湘江評論》深受《每周評論》的影響,內容上長于政論,以評論為主,設置有“述評”“雜評”“放言”等主要欄目。
二、《湘江評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湘江評論》傳播馬克思主義首先表現在,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及其意義。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毛澤東認為蘇俄“勞農兩界合立的委辦政府”,“協議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他稱俄國的十月革命為“怒濤西邁,轉而東行”,不僅使英美法資本主義世界“演了多少的大罷工”而且促使朝鮮印度也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最后,這股影響力讓東方的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并“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使“洞庭閩水,更起高潮”,以至于“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2]。在《這個使得》一文中,新民學會會員熊瑾玎以幽默的筆調將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比喻為“一個做工的圣人”。熊氏以講故事的口吻來謳歌十月革命,認為俄國的統治階級“硬把勞心的當作君子,把勞力的當作小人”,此舉觸怒了布爾什維克這個“做工的圣人”,“他決定親自出馬,來和這些學者先生們講講道理”[3],十月革命于是爆發。
其次,《湘江評論》還對反動軍閥政府污蔑、貶稱馬克思主義及其信仰者的言徑予以駁斥。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引起了反動軍閥政府的恐慌。反動勢力害怕并反對馬列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過分激烈,因而稱其為“過激主義”以示責貶,同時將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們貶稱為“過激黨”[4](P551)。其時,北洋軍閥政府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自俄國傳播中土”,實際被“構亂之徒”憑借利用,稱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任意煽惑勞工,主張共產,反抗政府,邪說橫行,其禍甚于洪水猛獸。”污蔑馬列主義為“越軌言論,屬于內亂罪范圍”,聲稱“過激黨人之言行,危害國家,甚于盜匪之行為”[5](P623)。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等部門發布告示,表示要對宣傳馬列主義的人們“懸賞查拿,以彌隱患”,對營業印刷馬列主義書籍的鋪戶則“立予查封,并以同黨論”[5](P625)。湖南地方軍閥亦乘機污蔑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進分子為“到處煽惑,淆亂人心,實含有過激主義”,嚴令警察廳“偵騎四布”,“一體拿辦”[6]。
面對這種情形,毛澤東發表雜評《研究過激黨》一文,認為既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能自蘇俄迅速傳播至東亞、南亞各地,必有其“利害”之處,我們對它的態度應該是“研究研究”,弄清楚它“到底是個什么東西”而不應“閉著眼睛,只管瞎說”,只會說“抵制”“拒絕”等等的“空話”,盲目視其為“洪水猛獸”[7]。在《盲目的中國人》一文中,署名“慎廠”的作者開篇即言明不能簡單將“違背舊思想舊習慣的言論或行事” 動輒斥為“過激黨”。因為俄國的“布耳色維克”從字義講,意為多數黨;從其信仰的主義講,是要建立一個“以工民辦理國家事務”的“工民共和國”,它其實是一個“有政府,也有憲法”的國家。至于“過激黨”這一貶稱源于日本軍閥貴族恐懼、抵制馬克思主義者而給予其的一種貶義譯名。“慎廠”提醒國內習慣于“襲用日本的名詞”,視“過激黨”三字“為口頭禪、為一種罪名”的一類人,不應偏信盲從而是要用心思考“布耳色維克”是否真的算是“過激黨”[8]。在《哪一個是過激?》一文中,新民學會會員陳子博斥責軍閥政府揚言“湖南了不得了,過激黨來了”,不過是一種“捕風捉影的話”。他直斥“倡言過激黨來了的人”實際上并不知道“過激黨的主義若何?什么叫做過激黨?過激黨的人物怎樣?”相反,他認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是一群“舍命救國的志士”,是“拿出良心來從強權者索還自由的志士”[9]。
第三,《湘江評論》積極宣傳唯物史觀以傳播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分析方法及其根本旨趣就在于一切從實際出發,高度重視對現實世界、社會關系及人本身的研究。因此,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及其著作皆強調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對歷史發展有著重要作用。他們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而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10](P531)。1918年8月毛澤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后,逐步在思想上確立了唯物史觀,而《湘江評論》因毛澤東擔任主編,亦因之成為五四時期積極宣傳唯物史觀思想的重要刊物之一。
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指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人類應如何生活”是“一個絕大的問題”,各國的民眾正是“為著生活痛苦問題”才“起了許多活動”[11]。實際上,《湘江評論》編輯群體在實際斗爭中已逐漸認識到,只有從“吃飯”等最廣大民眾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入手,才能夠將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喚醒,使他們成為實現反帝反封建任務的根本力量。
看似瑣碎而又平常的吃飯問題其實是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正是通過它,《湘江評論》尋找到了作為進步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廣大底層民眾溝通與交流的共同話題。正是對于國民生計的高度關注,《湘江評論》幫助進步知識分子消除了與底層民眾之間心理猜疑、階層和文化隔閡。一方面促使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最平常不過的“吃飯”等瑣碎的日常生活恰恰是他們“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所在;同時也讓廣大民眾逐步意識到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必須變孤立的、單個的人為一群人的大聯合,以實現自身的根本利益。對“吃飯”問題的重視可以說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打開了重要突破口。
《湘江評論》宣傳唯物史觀的另一表現是,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認為民眾聯合是世上最強大的力量,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提出了“民眾大聯合”的主張。人民群眾是社會主體的根本組成,是否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可謂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非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標志。舊社會史觀忽視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和地位,而唯物史觀則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2](P932)。
《湘江評論》所提出的“民眾大聯合”思想和主張,是以青年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不滿于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等強權思想長期統治中國而給予的某種強力回應和反擊,是一種符合當時實際社會需求的先進理論和思想。雖然《湘江評論》編輯群體當時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文本中“民眾”“聯合”“小聯合”以及“大聯合”的主張和思想表現出了《湘江評論》編輯群體對唯物史觀思想的信仰和宣傳。
三、《湘江評論》的影響與不足
《湘江評論》創刊之前湖南各地的進步知識分子就曾創辦過《新湖南》《女界鐘》等多種刊物,但影響力均有限。而《湘江評論》在問世之后,其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倡導和主張民眾大聯合思想、揭露與鞭撻腐朽封建制度,凡此種種使其在當時湖南甚至全國都產生了較大影響。
《湘江評論》雖是創辦于長沙的一份地方性刊物,但發行地區卻超出湖南省,暢銷于湖北、廣東、北京、上海等地。1919年8月,胡適在看到《民眾的大聯合》這篇“大文章”后為作者的“議論痛快”“眼光遠大”所折服,贊譽本文為“現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胡適指出,《湘江評論》在文風上長于議論,可以說是《每周評論》的“一個好兄弟”[13]。李大釗盛贊《湘江評論》為全國見解最深、最有分量的刊物之一。他看到《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后在《新生活》上發表《大聯合》一文予以回應。在文中,他熱情期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都能為民治社會打下基礎[14](P428)。
北京的《又新日報》全文轉載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上海的《時事新報》也部分摘錄登載了該文。《新青年》《晨報副刊》《新潮》等刊物也都推薦和介紹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晨報》稱贊《湘江評論》內容完備、魄力充足,是一份優秀的新刊物。上海《湖南》月刊認為湖南讀者若想了解“世界趨勢”和“湘中曙光”則“不可不閱”《湘江評論》,贊譽該報為“吾湘前所未有之佳報”[15](P117)。可以說,《湘江評論》在當時就已被公認為是比較出色的進步刊物之一,尤其是它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對十月革命勝利的歌頌、對反馬克思主義勢力的抨擊,使它與當時國內諸多同類性質刊物比較起來,其在政治性、思想性等方面都顯得更勝一籌[16](P31)。
《湘江評論》對當時的進步青年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毛澤東后來回憶說,自己所主辦的《湘江評論》對于當時的華南學生運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17](P129)。蕭勁光回憶說,自己和任弼時在長沙求學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自己和任弼時由于受到《湘江評論》所傳播的革命思潮影響才開始了革命覺悟[18]。向警予也因為受到《湘江評論》的影響,才開始逐漸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積極投身革命事業[19]。
需要指出的是,1919年前后,《湘江評論》編輯群體基本都還是革命閱歷淺顯、理論知識水平有限的青年學子,他們在思想上尚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系統且深刻的認識。《湘江評論》雖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卻并不認同。從《〈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可看出,刊物當時認為“有血革命”“炸彈革命”會“張起大擾亂”,對改造社會實際“沒效果”,更傾向于“無血革命”“呼聲革命”和“忠告運動”[11]。可見《湘江評論》此時在主旨上更認同用改良主義手段改造社會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還缺乏深刻認識。
而同一時期發行的《每周評論》刊登有陳獨秀譯自《共產黨宣言》并添加按語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陳氏直指蘇俄道路是未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20]。李大釗亦在《每周評論》發文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并指出中國革命必須放在世界革命的范圍之內[21]。上述情況表明,相較于《湘江評論》,《每周評論》此時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則更顯先進性和深刻性。盡管如此,《湘江評論》在五四前后得以創立正是適應了當時革命形勢在長沙乃至國內發展的需要;《湘江評論》有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毛澤東、向警予等眾多進步青年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