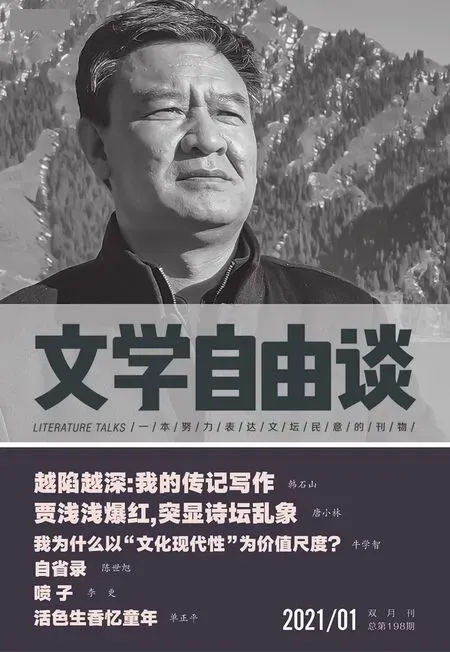普希金的“混不吝”與葉芝的“通靈術”
□狄 青
“文如其人”這句話能否成立我是一直比較懷疑的,雖然它看上去并非全無道理。比如我們讀李白、杜甫的作品,的確能多多少少讀出來他們二人各自的個性與樣貌,字里行間亦的確有許多細節與他們的仕途遭際、生活境遇相關。反例其實也不少。周作人與胡蘭成的文字都很過硬,但從他們的文字中,我們對他們的政治傾向與人生選擇很難有一個準確判斷。莫言當年也寫了不少打油詩,雖然其難以卒讀的程度遠比不上郭沫若先生在某個年代里的所謂詩歌,但也無疑令人大跌眼鏡了。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后,這些打油詩被人翻找出來,讓人實在想不出會是莫言寫的,完全談不上文如其人。倒是莫言自己曾經說過,“好的作家應該寫出與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作品來”,只是不知道這是否就包括了打油詩。
事實上,古往今來的很多文人,在現實的世界里迷戀極端的生命體驗,在文學的世界里卻往往保持著中庸之道。也許是因為藝術世界是文人理想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和諧完美的,可以盡情謳歌愛情、謳歌時代、謳歌大自然,而現實中的世界緊張殘酷,并且哪有那么多的花花草草花前月下,倒不如干脆來個“混不吝”。
我小時候對外國詩人中的兩位印象特別深刻,一位是普希金,一位是葉芝。此二人,一個被公認為帶有革命性且激情澎湃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一個則是集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和神秘主義于一身的現代詩人。共同點在于,二人據說皆是謳歌愛情的圣手:前者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我曾經愛過你》,后者的《當你老了》《在七片樹林里》,都曾被各種大眾媒體反復刊載推介過。即使在當下,一些大專院校的外國文學史課程中,普希金與葉芝還都屬于那種看上去代表著文學正脈乃至于正義、正氣、正統的詩人。他們的名言也被收入各種“文學雞湯”類書籍,但是,那些看上去無比“端正”的話和極富“哲理”的語言,到底是不是他們說的呢?我無從考證。我們實際上忽略了一種細水長流般有意無意的“引導”,而這種引導對我們認識一個作家抑或詩人是多么重要啊!
普希金最喜歡的事情據說有三樣,第一是愛情,愛情是人類感情的極端表現;第二是決斗,決斗是面臨死亡的極端體驗;第三是賭博,賭博是糅合了冒險、偶然性和過山車式大起大落的刺激體驗。這三樣無疑都是人生中最富有刺激性的感受。普希金在生活中其實就是個“混不吝”的主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小子。他與我們當下文壇上某個流行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個說法是說,文人在生活上要做個規矩人,在創作上要做個壞小子;而普希金則在生活上是個壞小子,在創作上卻充滿了“正能量”。普希金是莫斯科警察局嚴控的“重點人”,排在莫斯科全市著名賭徒的第三十六號,同時也是排第1號的詩人。
有一句玩笑話是這樣說的:想讓家里老人吃某一樣東西,最有用的方法不是告訴他們哪樣東西吃了有營養,而是告訴他們哪樣東西不吃馬上就要過期了。普希金即是這樣的“老人”。你如果告訴他某個活動上有哪些著名作家和著名詩人參加,他往往面無表情;但如果和他說這個活動會有很多美女名媛出席,去晚了可能就看不到了,他立馬就眉飛色舞,并一定會排除萬難,提前到場,還會將自己打扮得煥然一新。
普希金上的是貴族學校,那屆一共畢業了二十九個學生,他的綜合排名是第26位。他的擊劍、俄羅斯文學史和法國文學史都排在第一,但其他科目卻乏善可陳,好幾門都掛了科。普希金自恃劍術出眾,一言不合便要與人家決斗。他有過多少次決斗經歷呢?他的一個情人說是“三十次”,另一個情人則說,他總是在前一次決斗的傷口愈合之后,便馬上去尋找下一個決斗對象,而且他總不是死的那個。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普希金在劇院看戲,因為不喜歡看,就在座位上不停地大聲抱怨。鄰座的德尼塞維奇少校提醒他不要影響他人,普希金斜著眼看了看他,繼續吵嚷,毫不顧忌別人的指責。幕間休息時,少校找到他,告訴他剛才的行為非常失禮。普希金傲慢地向對方發出了決斗的挑戰。第二天一大早,普希金真的帶人去找少校決斗了,結果,德尼塞維奇少校在朋友的勸說下,不得不向普希金道歉。
我發現,很多質疑《普希金秘密日記》真偽的人,都是我們國內研究普希金多年的學者。我能理解他們的苦衷和焦慮。當一生焚膏繼晷致力于將普希金塑造成一位愛情、道德楷模之后,他們怎能眼睜睜看著這一大廈轟然坍塌呢?我并不認為普希金的日記一定沒有摻假的成分,但聯系他那些并沒有被完全公開的一生作為,我們不難看出,普希金一定想過自己將如何才能變得不朽,但絕不是以道德的名義。
從少年時代起,普希金就非常喜歡當時被俄羅斯主流文壇所唾棄的色情文人巴爾科夫的作品,并在其影響下創作了《加百列頌》和《巴爾科夫的幽靈》等色情作品。他在詩中曾這樣寫道:“少女那幽秘的私處,宛如上帝的容顏。”這樣的詩句,在他那一時期的作品中比比皆是。由于言語上過于無忌,這些作品長期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由蘇聯著名文學評論家嘉科洛夫斯基認真校勘之后,它們才被允許進行少量研究性“內部出版”(有點像咱們的《金瓶梅》),但出版社不允許女子打字、校對,并且,至今仍未獲準編入權威版的《普希金全集》。為尊者諱肯定是原因之一,但顯然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被人們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制造出來的革命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如何與這些不堪的文字共處?
沒錯,普希金的身上兼容并蓄了難以計數、甚至截然對立的異質成分。如果說,一個人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復雜矛盾的程度,還在于截然對立的元素在他身上和諧共存的程度,那么,我認為,普希金絕對可以作為這方面的典型個例。
長久以來,我們總是逃脫不了一個怪圈:倘若想“樹”一個人,就要千方百計地否定這個人的缺點甚至壞處的存在,而否定的前提就是要遮蔽更多的事實和資料。當年,俄羅斯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文中,僅僅因為寫了“普希金邁著色情的小腿跑上詩壇”這樣帶有調侃意味的句子,竟然連索爾仁尼琴都站出來攻擊他對普希金太“不尊重”了。
我發現,作家和詩人往小了說可能微不足道,但朝大了講,卻能成為一個時代人們心目中神祗一般的存在,甚至是道德律的組成部分——普希金便是這樣。一百多年前,俄羅斯批評家羅扎諾夫就認為,普希金是“迄今為止出現的所有詩歌形式創作的天才”:“他能自如地運用八行詩和抑揚格,他的心靈是融合了全世界音響的共振器。他從完整的世界中擷取聲響,并將新的音樂涌現出來,從而使世界更為豐富。在普希金之后,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普希金活著的時候,對他的溢美之詞便車載斗量,這也令他無比自信。他曾預言:“不,我不會完全的死去,我的靈魂在我的詩歌中,將會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而且絕不腐朽……我的聲名將會傳遍整個俄羅斯大地,現存的一切民族都會訴說我的名字,無論是高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芬蘭人,還是現今野蠻的通古斯人,和草原的朋友卡爾梅克人。”不過,普希金可能沒有想到,他的名字不僅在他所提到的這些地方,在他的地理知識尚未涉及的那些地方同樣是如雷貫耳。
據說,普希金的妻子娜塔麗亞·尼古拉耶夫娜·岡察洛娃是俄羅斯不世出的絕色美女,不僅人民喜歡,沙皇也喜歡。有一種說法,沙皇日夜嫉妒著普希金,因而,挑唆丹特士去找普希金決斗。事情當然不是這樣。決斗不僅是普希金提出來的,岡察洛娃與丹特士有曖昧關系,起因也在于普希金。
普希金在決斗前夕,對自己一生的風流韻事曾經做過總結,開列了一份與自己有染的女人名單,竟然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岡察洛娃排在第一百三十七位。也就是說,在與岡察洛娃結婚之前,普希金就已經同一百三十六位女性有過關系,而婚后又與近二十個女人有染。普希金做的很多事情并沒有瞞著岡察洛娃,這令她十分不滿。她可是一位絕色美人啊!順便說一句,岡察洛娃高出普希金十厘米。出于這個原因,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不得不被迫在各種社交活動中與妻子保持距離,以免產生強烈對比。普希金本人究竟有多高呢?根據與他同時代的藝術家切爾涅佐夫于1832年的精確測量,普希金的身高是166.7厘米。
國內的很多人,尤其是普希金的研究者們,總喜歡說普希金是謳歌愛情的能手、圣手,但普希金實際上從來沒有謳歌過忠貞不渝的愛情,即使有過,他一定也是紅著臉寫的。他或許在寫下那些閃亮的愛情詩句的第一秒相信了自己的話,但接下來的一秒他又將剛剛寫下的詩句背叛了。普希金的朋友們,包括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維亞賽姆斯基等,當年都對他不顧輿論、違背道德的放縱行為表達了不滿,他們在通信中譴責他的輕浮和放任。
有一次,維亞賽姆斯基對普希金說:“詩人的使命應該是用自己的詩歌喚起人們對美德的熱愛和對丑行的憎恨。”普希金回答說:“完全不是這樣,詩歌高于道德,或者說它們是兩碼事。”換句話說,在普希金眼里,詩歌只是詩歌,道德只是道德,二者并沒有必然關聯;詩人寫了什么是一回事,他做了什么是另一回事,不要與他寫了什么相提并論。
一直以來,我們的心靈普遍都習慣了接受某種完整性,并不接受將一切事物分門別類;它追求絕對。尤其是在對文人的評價上,往往奉行的是“要么是一切,要么是零”。
法國作家安德烈·特洛亞認為,普希金從步入生活起,就已經感到應該蔑視一切危險。他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為自己準備了一種辛辣、矛盾而又緊張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只有生活在極端歡樂和危險之中,他才能夠感覺到幸福。
并不是隨便一個文人就可以比照普希金的人生軌跡和對待生活的方式方法的。普希金生于貴族之家,從小就學習過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還通曉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希臘語和不常使用的斯拉夫語。多語種的學習,讓他能夠通過原文閱讀各國的文學作品。十一歲以前,他就閱讀了父親書房的所有書籍,包括文學、哲學和各種色情讀物。之后,在皇村學校圖書館,他更是大量閱讀以古希臘羅馬文學為開端的世界文學。普希金還喜歡繪畫,他為情人沃隆佐娃畫過三十多幅速寫像;這段感情因沃隆佐娃老公的介入而中斷,但她對他一直保持著美好的回憶。她在彌留之際銷毀了一捆她珍藏多年的普希金寄給她的書信與情詩,那些被銷毀的文字據說十分“驚世駭俗”。
比起在生活中可以“混不吝”的普希金來,據說不太喜歡普希金詩歌的葉芝則顯得較為內斂,卻無疑更加“神秘”。直到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葉芝的許多詩作,有相當一部分可能被我們“誤讀”或過度解讀了。葉芝的女兒就曾經說,他的父親厭惡一切,也包括他寫的很多詩作。有一次,他們父女二人一起乘坐公交車出行,葉芝一路都在喃喃自語。下車的時候,葉芝問女兒:“你確定你不是面對一個漁夫嗎?”女兒知道,他的父親又開始被“通靈術”糾纏了。
我承認我很難理解葉芝的某些思想、行為。我發現,當把葉芝的那些詩作通俗化地“為我所用”時,我們或許并不清楚,我們所認定的那些東西與葉芝本人所想要表達的事情,很可能是南轅北轍的。
香港歌星莫文蔚在春晚上演唱的那首根據葉芝同名詩作譜寫的歌曲《當你老了》,讓原本已經很紅的這首詩更為家喻戶曉。雋永深沉的詩句,配上優雅傷感的旋律,膾炙人口,感人肺腑,受到無數人的追捧,也讓更多人記住了這位愛爾蘭大詩人的名字。
我們出版了葉芝的多少著作,《當你老了》有多少個不同的翻譯版本,它曾出現在多少雜志的扉頁上,這些我都說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在我來看,葉芝這一生主要做的其實就是兩件事,而這兩件事從我認為的那個角度去看,很可能又是同一件事。
許多人對葉芝與茅德·岡的愛情感覺不可思議,卻忽略了葉芝之所以屢敗屢戰地向他的這位女神求婚,很可能并非緣于我們慣常理解的那種愛情,或者說,他熱愛這個女人已經到了難以自拔的地步。這段愛情大概緣于某種“神啟”,因為熟悉葉芝的人曾說,他小時候住在一處古堡里,家里的老保姆經常給他講各種神靈故事,包括告訴他將來會娶到什么樣的妻子——那與茅德·岡的年齡、出身、相貌十分相似。
與他的愛爾蘭老鄉、才子王爾德一樣,葉芝也是一個美男子(據說喬伊斯年輕時長得也不賴,我很想研究一下愛爾蘭作家們的顏值),因而他同樣是全愛爾蘭懷春女郎們的夢中情人。他又何嘗不是全世界愛好他詩歌的女人們的夢中情人呢?有人說,葉芝就像西斯廷教堂穹頂上米開朗基羅留下的證明——半醒的亞當撩撥著全世界的女郎。因為相貌英俊,葉芝一直是藝術家們癡迷的對象,據說他是愛爾蘭被收入鏡頭和畫布中最多的詩人。影像和畫布上,他白皙的脖頸瘦弱纖長,金絲邊眼鏡后面是一雙深邃的眼睛,透著幾分與快樂相當的憂郁,那是一種極富遠見的憂郁,仿佛與生俱來的純粹。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帥氣并且比較富裕的著名詩人,卻一直未能實現他愛情上的夢想,不得已,1917年他五十二歲時,才“被迫”結婚。
葉芝最后一次向茅德·岡求婚時已經五十二歲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經三次求婚被拒。當又一次毫無懸念地被拒絕后,葉芝轉向對茅德·岡的女兒伊莎貝拉求婚,不出所料,他又被拒絕了。這一次,葉芝終于停止了這種無望的想法,只是不知道他的內心是否因無法達成“神靈的啟示”而不安。
他在五十二歲這一年的結尾,為躲避他自認為的占星術的詛咒,四處尋找適合的結婚對象,最終在年末潦草地與一位愛慕他多年的女子結了婚。說潦草也不確切。葉芝對朋友說,占星術顯示的結果,他不能晚于1917年結婚。他向喬吉·海德·李斯求婚,不僅是因為他“被迫”,還因為這個女人是許多地下神秘組織公認的“靈媒”,對中世紀占星術頗有研究。換句話說,她可以將葉芝更便捷地引向他另外一個靈魂——十六世紀的冒險家利奧·阿非利加奴斯。據葉芝自己說,他曾于1914年6月在英格蘭的漢普斯特德見到了他的靈魂伴侶利奧,從此二人便成為密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與一個幾百年前的魂靈的友誼從此開啟。按葉芝的說法,利奧經常給他提出各種建議,他的妻子則引導著他們二人進行著對話。葉芝不斷說,利奧·阿非利加奴斯賦予了他無窮的力量。
結婚以后,葉芝夫婦開始共同嘗試風靡一時的“無意識寫作”。這種無意識的寫作在他的名詩《麗達與天鵝》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之前,我們國內一些研究詩歌的人,總是將葉芝終其一生迷戀的“通靈術”,用“葉芝的部分創作受到神秘主義影響”一筆帶過。而實則呢,葉芝的創作與生活已經不是“受到影響”,而是早已對星相、月相、自然神靈和預言之間的關系深信不疑。葉芝更把這些神秘的預言運用于他的愛情、詩歌創作乃至民族獨立革命運動上。他對許多人說,在1888年的一次降神會上,自己有過魔鬼附體的切身體驗,而那一次魔鬼附體令他明白,自己是受到某種神秘力量操控的,一切都要按“占星術”的結果去實行。
1885年,葉芝和他的好友共同創立了歐洲著名的新神秘主義組織“都柏林秘術研究會”。這一組織后來影響了數代生活在科學時代,卻迷戀神秘現象的西方人。這個組織在1885年6月16日在都柏林召開了第一次集會,葉芝被選為領袖。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學會館在通靈法師婆羅門·摩西尼·莎特里的組織下正式開放,葉芝于次年第一次參加降神會。之后,他沉迷于對煉金術和通神論的研究,并親自實踐煉金術的操作。1890年,他又秘密加入“金色黎明秘術修道會”,并于1900年成為該會的領袖——盡管此時他還是愛爾蘭議會的議員。
作為擁有著英國血統的愛爾蘭人,葉芝對宗主國英國的感情是比較復雜的,這與199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作家謝默斯·希尼,以及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圣盧西亞大詩人德瑞克·沃爾考特十分相似。他恨英國人造成了他不能用愛爾蘭的民族語言——蓋爾語寫作的事實,同時又使他得到直接學習莎士比亞等文學大師以及更多神秘主義大師著作的便利。有一度,葉芝與他的妻子一起,曾試圖用通靈術,來實現與歷史上創作過神秘主義“名著”的大師們見面的愿望。
關于葉芝走路的時候喜歡手舞足蹈這一事實,得到了當年很多都柏林人的證實,包括對他頗有好感的愛爾蘭女詩人凱瑟琳·泰南。凱瑟琳·泰南了解葉芝,緣于他們都熱衷于通靈術。但她并非葉芝最好的朋友。葉芝最好的朋友只有一個,那就是死于十六世紀的利奧·阿非利加奴斯。
葉芝有多么喜歡墨索里尼呢?許多人都知道,葉芝經常把墨索里尼的照片放在貼身衣袋里。他主動請纓,為愛爾蘭的納粹組織——藍衫黨寫了三首進行曲,因為這一組織效仿的是墨索里尼所推崇的棕衫黨。實際上,葉芝對墨索里尼的崇拜也影響到他的學生——美國大詩人埃茲拉·龐德。從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葉芝和龐德都在亞士頓森林的一個鄉間別墅中度過。這段時間里,龐德擔任葉芝的助手。龐德公開宣稱,到愛爾蘭就是來拜見葉芝的。龐德多少繼承了葉芝的神秘主義和對法西斯的崇拜,而詹姆斯·喬伊斯和T. S. 艾略特更多的是喜歡葉芝文字里的靈性;好在是這樣。
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種高度藝術的形式表現了整個民族的精神、永遠富有靈感的詩”,葉芝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為這次獲獎,葉芝竟然寫了一首贊頌斯德哥爾摩的詩作。當有人指出他這樣寫涉嫌對諾貝爾獎評委“諂媚”的時候,他說這是通靈術叫他這樣做的。
W. H. 奧登曾尖銳地批評晚年的葉芝是“一個被關于巫術和印度的胡言亂語侵占了大腦的可嘆的成年人的展覽品”。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葉芝寫出了他一生中很多不朽的作品。其實,倘若想理解葉芝晚年詩作背后想要表達的主題,就必須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靈視》一書。這本書基本上屬于神秘主義思維體系的框架。葉芝最滿意的作品并非那些詩作,而恰恰是這本哲學思維和個人冥想雜糅的著作。在書中,他不斷推舉柏拉圖、布列塔諾以及幾位現代哲學家的觀點,來證實自己的占星學、神秘主義及歷史理論的靠譜。
晚年的葉芝變得越來越古怪,他甚至公開了自己陽痿的事實。因為陽痿,葉芝到奧地利維也納做了當時有名的“施泰納赫手術”,這一手術就是將猴子的腺體注入到人體內。那應該是在1935年前后,也就是葉芝七十歲的時候。具體療效不好說,但他很快便有了一個新情婦——年輕的女詩人馬格特·拉多克。后來,葉芝受命編選牛津皇家詩選,收錄的拉多克的詩歌竟然比埃茲拉·龐德與W. H.奧登加在一起還要多。
葉芝死于1939年1月28日。那之前他寫了一首詩,末尾處這樣寫道:“冷眼一瞥/生與死/騎士/且前行”。這幾句話,最終成了他的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