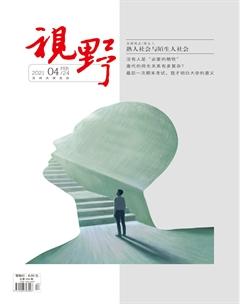博士生們都在讀什么書
嚴飛
博士生們都在讀什么書?我一直都在好奇這個問題。因為我發現,至少在我接觸的博士生里面,無論是理科博士,抑或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會主動讀書者,似乎鳳毛麟角。
依常理而言,學問做到博士階段,這一路走來,書自然讀得不少,對于挑燈夜讀的讀書之苦,也肯定都有著切膚之痛。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課程要求而布置的讀本、因論文寫作而參考的書目,仔細想想,又有多少雜書、閑書、枕邊之書、無關痛癢之書、不務正業之書、信手翻閱之書,是我們這些博士生因興趣而發,主動去閱讀的呢?
前幾日和一位牛津畢業的博士生聊天,當談及他所攻讀的管理學領域時,他可以就某一篇論文所闡述的觀點侃侃而談,但當話題轉移到某一社會議題時,他炯炯的眼神就會黯淡下來,不自覺地縮在角落里,難以繼續對談。
在專業學科領域,我相信我的這位朋友定會做出卓越的貢獻,但我總感到有小小的遺憾,遺憾他在人文底蘊和人文見識上的缺乏,而這根源所在,就是在年少正好讀雜書的黃金時期,將閱讀的時間都交給了專業的學科讀物。其結果是,專業知識突飛猛進,學養氣質卻無法跟上,那種對于文化的敏感、對于社會的關懷,以及對于憂患的反思,都會于潛移默化間有所欠缺。
所謂術業有專攻,系統而專業的學科訓練自然是必須的,但過于專注于某一學科的專業強化,特別是對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會科學領域,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而言,過分強調對技術和職業化的訓練而忽略對人文內涵的拓展,其結果,就是李澤厚在20世紀90年代就曾提出的,“學問家出現,思想家退出”的學術走向。
讀書本該是一種心靈的活動、思想的激蕩,然而在大多數博士生的長期“讀書”生涯中,讀書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之事。本該“乘興而來、盡興而返”的自得,反而演變成一種機械式的攝取。等博士們畢業后成為學院里的教授,學問是有的,但知識結構狹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沒有聯想,只有技術而沒有文化,只有實證而沒有批判,缺乏社會理想和人文關懷,對本專業以外更為重要的社會結構、政治倫理、文化形態等問題也就缺乏應有的信念和投入。“專家沒有了靈魂”(韋伯語),那就會成為“一根筋”和“工具人”。
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米爾斯就十分厭惡那些只具有“技術專家氣質”的社會科學家。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米爾斯曾毫不客氣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養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對人類理性尊重的價值指引了他們生活”的人,屬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術專家”。
在米爾斯看來,人文精神和價值信仰是激發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確立社會科學對于我們時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含義”的關鍵。而現今,“科層制的氣質滲透文化、道德和學術生活領域”,這種實用主義橫行、功利主義作怪的狀況是社會科學的重大災難,技術專家式的學者因其實用性取向,不僅遠離了社會學的想象力,也遠離了社會學的思想力與行動力。
米爾斯的批判并不僅僅局限于社會學,當我還在香港的大學里工作的時候,就曾深感米爾斯筆下所謂的“科層制的氣質”對于思想、理念無孔不入的侵襲和束縛。
我所在的學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進了幾位。指標壓力之下,博士、教授們都成為論文生產線上的機器,一項課題可以就其中幾個變量的異同顛來倒去地翻炒出好幾篇論文。更有甚者,這條論文生產線也講究專業化的分工,在某一社會科學系,有位副教授最為擅長統計運算,被奉為鎮系之寶,因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論文牽涉復雜的統計分析,就好像裝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須交給他來做。他每年也因此能發表十幾篇學術論文,但迄今鮮有一篇具有影響力和創新性。這種學術思想上的僵化,正因囿于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而忽視了人文底蘊這一本為內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人文修養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強調知識自主性的分量,是因為我更加看重學者的公共責任。
在我看來,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者,他并不應該局限于自己的專業學科。他也應該是一個行動者,應該關心社會,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時將自己的思想力投入社會議題,去參與、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會運行的不合理之處,從而帶動起大眾,或者說大多數人的認知和思考。
在這一過程中,一個具有良好人文底蘊的學者,必然會秉承自己的價值標準,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時,社會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爾斯語)。
——摘自中信出版集團《學問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