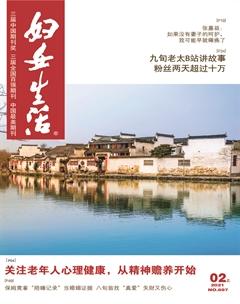不能不愛,那就用最佳方式去愛吧
王月冰
流著相同血液的人,值得用最寬厚的方式來相處——
父親去世之后,我對母親和弟弟的不滿到了難以抑制的地步。
母親和弟弟一向感情很好,只是對我和父親一直比較冷淡。父親母親感情不和,母親非常辛苦,弟弟心疼母親,對父親很有意見。
父親幾次生病,都是我送他去醫院,住院期間也一直由我照顧。弟弟剛開始也來,但來了也不說話,后來父親就不讓他來了。
父親去世后,我總想起他在世時的孤獨,覺得母親和弟弟對此都有責任。
母親大約是看出了我的不滿,擔心我恨弟弟,便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還一個勁兒地替弟弟說好話。我嘴上沒說什么,但心里對她和弟弟的埋怨與不滿絲毫未減。因此,我很少給母親打電話,與弟弟更是極少聯系。我想,既然母親不需要我,她有弟弟已經足夠,那我就離她遠遠的吧。
可沒過多久,我還是和母親大吵了一架。
有一天,母親主動給我打電話,說她從鄉下來城里幫弟弟帶孩子,想來我家看看——我和弟弟的住處離得并不遠。
我接母親來到我家。吃飯時,母親不停地站起來,說臀部脹痛,不能久坐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問:“我弟沒帶你去醫院嗎?”母親擠出笑臉,似乎是想討好我,說弟弟夫妻倆都太忙,才生了二胎、買了車庫,生活壓力大,她不想麻煩他們。
我頓時愣住,也徹底明白母親來找我的目的——她不是想我了,而是想要我帶她去醫院!她總是這樣,平時只想著幫弟弟,碰到問題才會想到我。我實在生氣,給弟弟打電話,質問他為什么不帶母親去看病。弟弟說他要帶她去,但母親不信任他,說我帶她去她才放心。我幾乎吼起來:“她只有在需要看病的時候才會信任我,平時可都是把信任給了你!”
母親只好蔫蔫地要回我弟弟那兒去,我因為生氣沒有挽留她。看著她微微弓著背、腳步沉重地消失在樓梯拐角,我心里又恨又痛。
兩天后,弟弟打來電話,一再拜托我帶母親去醫院。我終究還是忍不住去找了母親,氣沖沖拖著她去醫院。到了醫院,我急匆匆跑在前面,遠遠地把她甩在后面。母親像個討糖吃的孩子,費力地跟著我。
我好想甩掉她呀,可我的心真是痛——這一幕如此熟悉。
小時候,母親在鎮上一個包子店打工,我總是央求她帶我去,可店老板不喜歡母親做事時帶個孩子在身邊,于是母親總悄悄去上班,不讓我跟著。
一個寒冬的清晨,母親去上班,我遠遠地跟著她。母親快步走著,大聲喊著要我回去,可我倔強地跟著。突然,一頭大水牛從側邊朝我瘋狂奔來。母親喊我趕緊躲開,我哪里知道躲,只顧著追她。母親朝我飛奔過來,又擔心驚了水牛,只好快速從水田里蹚過,一下子抱住我,直到水牛遠去。由于鞋子在水田里灌滿了水,母親凍得瑟瑟發抖,一邊背起我往鎮上趕,一邊呢喃:“真想把你扔在這兒,可我就是舍不得呀!”
如今,我也舍不得扔下你呀,我偏心的母親!你也曾那么愛我,你與父親多年不和、身心皆苦,卻始終沒有離婚,舍不得的因素里也有我這個女兒吧?!
母親的病需要住院,我為她辦好住院手續,弟弟來了。看到弟弟,母親兩眼放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識趣地離開病房獨自難過。
我再回到病房時,看到床頭放著一堆價格昂貴的進口水果,很顯然,這些都是弟弟帶來的。看到我,母親臉上泛著滿足的微笑:“你弟弟就是會買東西,這些一盒四五塊錢,可好吃了,你嘗嘗。”我驚訝地看著弟弟,他朝我笑了笑,示意我出去說話。
在病房外,弟弟塞給我一張銀行卡:“我知道咱媽怕麻煩我,不讓我帶她來看病,但錢不能讓你出。我給她買的那些水果,都是重新貼過價格標簽的,你不要說出來。媽老了,內心固執,很多事拒絕改變,就讓她以她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生活吧。”說完這些,弟弟看看我,看看地面,又抬頭看我,繼續說:“我知道咱媽確實疼我多一些,我曾極力勸她多關心你,但咱媽總說她一樣愛你,只是你本來就強,不太需要她的愛。可我知道,哪有女兒不需要母親的愛呢?我理解你的委屈,但我控制不了咱媽。如果我硬要她怎樣來愛你,她會不自在,就像如果她知道那些水果本來的價格,她定然不能享用得這樣輕松和愜意一樣。所以,姐,我請求你原諒咱媽的固執,也原諒我選擇了尊重她的固執。”聽了弟弟的話,我一時不知說什么好,只覺得鼻子酸酸的。
我回到病房時,母親已經睡熟,臉上掛著微笑。我知道,是弟弟給了她這樣輕松的微笑。母親始終以她幾十年前的方式在愛弟弟,弟弟也以這種方式來孝順她,讓她覺得自由而舒適。
仔細想想,母親又何嘗不是以她幾十年前的方式在愛我?即使在病房里,即使身受病痛,她也依舊抓住一切機會告訴別人她的女兒多么能干,從小到大從不要她操心。
我想,母親也是深愛我的吧,雖然或許不如愛弟弟那么深,可我已不想再計較。流著相同血液的人,值得用最寬厚的方式來相處。有人說,人與人之間最好的相處方式是讓對方覺得舒服,最佳的孝順方式又何嘗不是如此?弟弟明白這一點,我又為什么不能呢?
【編輯: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