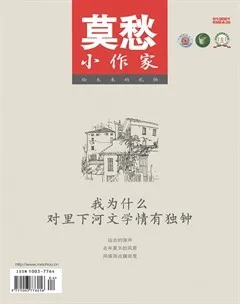一山明月望長(zhǎng)安
安史之亂百年后,衰落許久的大唐西北邊塞再次燃起了戰(zhàn)火。受制于吐蕃的沙州諸城終于得到了機(jī)會(huì),在遭遇連年災(zāi)荒之時(shí),邊塞兵民急切歸唐,用十余年的時(shí)間收復(fù)了河西走廊的諸多城池。大唐的邊疆又得到了五十年的安穩(wěn)日子。
唐大中二年十月,西北邊塞已經(jīng)是寒風(fēng)刺骨,漫天飛雪,連年的災(zāi)荒讓冬天愈加難熬。沙州的大漠覆滿(mǎn)了白雪,鳴沙山東麓尚未鑿好的佛像也被模糊了神情。開(kāi)鑿山體的叮咚之聲在疾風(fēng)里變得恍惚不可聞,月牙泉結(jié)了冰,映著岸邊的篝火和遙遠(yuǎn)的明月。每到這樣的時(shí)節(jié),大漠的人們總是更容易想起千里之外的長(zhǎng)安,百年的歲月逝去,當(dāng)初從長(zhǎng)安來(lái)到沙州的人們?cè)缫褵o(wú)法再給孩子們講述都城的繁華盛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故事,只能成為入夢(mèng)時(shí)的美景。
星夜里,營(yíng)帳內(nèi)燈火如豆,沙盤(pán)上擺放了幾面小旗,正中掛著的地圖上圈出了沙州城的位置。張議潮此時(shí)難掩激動(dòng)之心,趁著夜色急忙點(diǎn)兵,一路疾行,率軍攻打吐蕃。一百年來(lái),河西似乎終于等到了回歸大唐的機(jī)會(huì)。災(zāi)荒讓吐蕃無(wú)暇顧及其他,劫掠沙州的計(jì)劃也因難以聚齊兵馬而給了張議潮先發(fā)制人的機(jī)會(huì)。“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zhēng)先”。張議潮的軍隊(duì)突襲得勝,沙州的城門(mén)上揚(yáng)起了“唐”字大旗。這一次勝利讓河西的百姓看到了歸唐的希望,紛紛隨軍而戰(zhàn),并一舉奪回了瓜州。
可是奪回沙州的消息卻難以傳回長(zhǎng)安。自沙州戰(zhàn)火起,河西的路就更加難走了,張議潮派出報(bào)信的十隊(duì)人馬,在河西的沙漠草原上與諸多番邦周旋。長(zhǎng)安似乎從未如此遙遠(yuǎn),十隊(duì)人馬在一路的圍追堵截下只剩一隊(duì),到長(zhǎng)安的路足足走了兩年之久。大中四年,僧人悟真大師終于到了長(zhǎng)安,收復(fù)沙州的消息傳到了宣宗皇帝殿前。此時(shí),遠(yuǎn)在河西的張議潮又率兵收復(fù)了幾座城池。大中五年八月,除了涼州,河西走廊的其他州縣都回歸了大唐,張議潮也帶著十一州的地圖入長(zhǎng)安告捷。河西的人們聽(tīng)到的不再只是故事里的長(zhǎng)安,縱是路途遙遠(yuǎn),也結(jié)束了百余年的分離。
敦煌藏經(jīng)洞中的《張議潮變文》只將故事寫(xiě)到了收復(fù)伊州的時(shí)候。前后的內(nèi)容都在一千多年的時(shí)間中丟失了,又或許當(dāng)初在匆忙間寫(xiě)下張議潮的故事時(shí),還沒(méi)有來(lái)得及將前因后果來(lái)龍去脈都詳細(xì)寫(xiě)盡。變文只從劫掠沙州寫(xiě)到收歸伊州,還有幾首詩(shī)夾雜其中,但依舊可見(jiàn)河西戰(zhàn)爭(zhēng)的艱難。在變文記載的故事之外,是張議潮十余年的奮戰(zhàn),是收復(fù)涼州,又依唐律至長(zhǎng)安為質(zhì),再到后來(lái)其侄張淮深駐守河西。敦煌莫高窟的經(jīng)卷和壁畫(huà)只記載了短短一瞬,在一百多年的時(shí)間里,顯得單薄,卻也生動(dòng)。
只是關(guān)于張議潮的故事實(shí)在是太少了。不知為什么,我總覺(jué)得他像極了李白。同樣是自邊塞而來(lái),李白的俠氣和張議潮的果決似乎相通。他們都懷著對(duì)大唐的赤誠(chéng),一人寫(xiě)盡繁華風(fēng)流,一人率軍守土歸鄉(xiāng)。
張議潮的人生也十分傳奇。身處世代為沙州州將的家族,安史之亂后,沙州陷落,這樣的世家也不能免于遭受吐蕃侵?jǐn)_的命運(yùn)。就像那些漂泊在外的敦煌經(jīng)卷一樣,張議潮起義前也是在異邦生活,直到他將大唐的旗幟豎立在沙州城上,流散的日子才漸漸結(jié)束。
后來(lái)再看敦煌的紀(jì)錄片,有一種說(shuō)不上來(lái)的感覺(jué)。余秋雨在《道士塔》中,痛斥將敦煌文物賣(mài)給外國(guó)人的王道士。大概是出于文人的憤怒,當(dāng)看到千年的文獻(xiàn)壁畫(huà)被盜走販賣(mài),他只能將怒火發(fā)在目光短淺修為不足的王道士身上。在那樣一個(gè)難以維生的年代里,守著荒漠中的石壁,王道士或許只想好好活著。千年時(shí)光里,敦煌終究只有一個(gè)張議潮。流落異邦的苦痛只有曾經(jīng)的張議潮能感同身受,王道士的情懷,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
猶記得第一節(jié)敦煌文學(xué)的課上,我們以紀(jì)錄片作為開(kāi)端,視頻結(jié)束,大家都很沉默。了解過(guò)藏經(jīng)洞從發(fā)掘到文獻(xiàn)遺失的過(guò)往,再去讀一篇篇俗賦、曲子詞、變文,就多了幾分顛沛流離的味道。字句中有很多情感輾轉(zhuǎn)起伏,尤其是《張議潮變文》中所記載的沙州、伊州兩次戰(zhàn)爭(zhēng)的歷史,“白刃交鋒,橫尸遍野,殘燼星散,霧卷南奔”,這遠(yuǎn)比單純的故事要驚心動(dòng)魄太多。
“敦煌上將漢諸侯,棄卻西戎朝鳳樓。”沒(méi)有被細(xì)細(xì)講解的故事被寫(xiě)進(jìn)了詩(shī)中。張議潮帶領(lǐng)一方歸義軍鎮(zhèn)守大唐邊疆安寧,又親身入朝為質(zhì)。他必定是深得沙州百姓之心,所以在莫高窟的壁畫(huà)上也能有一方筆墨,讓后世之人得以窺見(jiàn)當(dāng)年出行儀仗的壯觀。只是無(wú)法追尋,在莫高窟還未建成的時(shí)候,張議潮歸義軍的故事究竟在河西流傳了多久,以致敦煌藏經(jīng)洞中能留存著一段記憶,壁畫(huà)上也描繪著統(tǒng)軍出行的盛況。
如何評(píng)價(jià)張議潮?在眾多風(fēng)流人物譜寫(xiě)大唐的時(shí)代里,關(guān)于張議潮的講述總是不夠真切。他耗費(fèi)十余年時(shí)間收復(fù)故土,又在歸唐后與西域的百姓相處融洽,大唐邊庭五十年的安穩(wěn)得益于他竭盡心力的付出。只是歸義軍離長(zhǎng)安還是太遠(yuǎn)了,朝廷仍然不放心邊疆有這樣一支強(qiáng)大的軍隊(duì)。于是拆分各部、設(shè)節(jié)度使,歸義軍的作用就在沙州和瓜州兩地?zé)o法施展。很快,歸義軍也衰落了。“河西淪落百余年,路阻蕭關(guān)雁信稀。賴(lài)得將軍開(kāi)舊路,一振雄名天下知。”這是夸贊張議潮的詩(shī)句,當(dāng)世之人以詩(shī)頌他,唐宣宗也贊嘆說(shuō)“關(guān)西出將,豈虛也哉”。他“繕甲兵,耕且戰(zhàn)”“列烏云之陣,四面急攻,蕃賊糜狂,星分南北”“西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余里,戶(hù)口百萬(wàn)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舊”……只是這一個(gè)個(gè)故事不像其他英雄人物的經(jīng)歷那樣被人熟知,但在許許多多的英雄俠客中,他同樣是大唐的氣象和風(fēng)流。
“百年左衽,復(fù)為冠裳;十郡遺黎,悉出湯火”,這是張議潮和歸義軍十余年的時(shí)間換來(lái)的結(jié)果。于是他終于將河西恢復(fù)唐制,改賦稅、編戶(hù)籍,他把一個(gè)完完整整的河西還給了大唐。
落日孤煙,長(zhǎng)風(fēng)橫越,胡笳聲從遙遠(yuǎn)的黃沙深處傳來(lái),羌笛聲也在烽煙中響起。一山明月望長(zhǎng)安,再遠(yuǎn)的距離,再久的年歲,也終究在三危山的鐵蹄駝鈴中漸漸消散。
雷文昕:蘭州交通大學(xué)文學(xué)與國(guó)際漢學(xué)院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zhuān)業(yè)學(xué)生,出版散文集《人語(yǔ)驛邊橋》。
編輯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