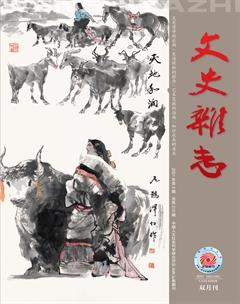成渝經濟區兩次歷史巨變的互補效應
張學君



成渝經濟區在兩次歷史巨變中,都顯示出極為強烈的互補效應,對整個巴蜀地區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帶動作用。
在唐宋時期,當成都以穩定的地域經濟優勢,與揚州并列為全國兩大都會時,渝州(今重慶)以水陸交通便利,支撐著長江上游新興市鎮的經濟交流。迨入19世紀下半葉,《煙臺條約續增專款》簽訂后,重慶對外開放,成為西南地區交通、商貿、金融樞紐時,成都緊隨其后,成為重慶經濟騰飛的堅強后盾,同舟共濟,直至八年全民族抗戰,贏得最后勝利。
一、唐宋時期,成渝經濟因沿江經濟帶形成互補效應
唐宋時期,在歷史上形成的若干巴蜀對外通道中,以川陜干道為陸路通道,與以長江上游航道構成的水上交通網羅互相配合,形成通往西北和東南各地的兩大交通運輸干線。這兩條交通動脈的交匯點,西在成都,東在渝州,遂成四川盆地商貿交通之東西樞紐。
(一)北路的陸路貿易
川陜干道稱為“北路”,是當時成都與長安、汴梁(今開封)等中原城市進行政治和經濟聯系的主要通道,也是成都與中原和西北地區進行客旅往來和通商貿易的重要交通線。入唐以后,隴右及河西諸州的商旅“莫不取給于蜀”[1]。關中商人則“販鹽于巴渠之境”[2]。據學者考證:香藥、仙茅生西域,從武城(今甘肅武山縣),取道成州(今甘肅成縣)或階州(今甘肅武都縣)運來成都。珍珠、蛤蚧從西域入玉門、陽關,南至大積石山,順岷江河谷進入成都。[3]蜀商亦販運大量川貨北上貿易,“蜀民為商者,行及太原,北上五臺山。”[4]吐蕃贊普因得到川東所產昌明茶而夸耀于唐使。[5]五代地方政權割據一方,成都與中原交通陷于困難。由于行旅稀少,虎患抬頭,“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6]。
兩宋時期,川陜干道再次成為成都與外省貿易的陸路樞紐。“成都府之北部,當京蜀之孔道,車馬往來之沖”[7]。川陜道上,“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沿途“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群盜,悉皆屏跡”[8]。北路交通貿易的恢復,給川陜干道帶來了蓬勃生機。經北宋王朝多次對蜀道北段進行維修,路途比過去易行得多。蜀道南段成都至鳳州大驛路,已改為“自金牛入青陽驛至興州”,經鳳州而達鳳翔。[9]北宋以后,此路成為成都與西北貿易和官府綱運的重要交通線。
唐宋時期,成都經川陜北路與西北地區貿易的主要商品有茶葉、蜀錦、瓷器、布帛、藥材、蜀箋紙、蜀版書等,如西川茶葉經由北路的銷售數額很大,崔致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提出用北路商茶稅利作為軍費。“況舊謂西川富強,皆因北路商旅,托其茶葉,瞻彼軍儲”[10]。西川食鹽不足,唐王朝曾明令河中兩池鹽入川貿易,以彌補川鹽供應短缺,[11]西北池鹽因此大量輸川。直至北宋初,成都食鹽奇缺,仍準階州文州青白鹽、解州池鹽、峽路井鹽等輸川貿易,“勿收算”[12]。唐宋成都瓷器,由于質地優異,已作為寶貨輸往外省。唐代邛窯所產三彩人物水澄,為西域少婦形象。這顯然是適應蜀瓷遠銷西北及中亞而特意設計的。前蜀王建報后梁信物,也有成都青羊宮所產秘色青瓷碗。[13]
宋代成都和東西川所出產的各種絲織品,“負于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日輸月積,以衣被于天下。”[14]青泥指青泥嶺,大散即大散關,都在由四川北越秦嶺的陳倉道上,可見這條道路的重要。宋王朝在四川至陜、甘沿途設置水陸茶遞鋪,把四川所產的茶葉搬運鳳州以至熙河路出賣,總計水陸運每年達5—6萬馱之多。[15]隨著茶馬貿易的繁盛,運銷商貨規模日益增多,使這條交通線更為繁忙了。
除了上述對外主要路線外,成都與川中各屬也有大道可通。由成都東南經靈泉縣,越龍泉山達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大道上,“聚落市鎮,相為映帶”[16],而且“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17]可見四川盆地內部以成都為中心的商業交通的頻繁和發達。
(二)成渝地區的水上商貿、交通
由成都府河乘船東下,由岷江入長江,經渝州、入三峽到長江中下游的水道,歷來就是四川地區對外物資運輸的主要通道。劉禹錫《竹枝詞》(九首之一)說:“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欲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18]王建《江陵即事》詩說:“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驛賣山雞。”[19]宋代的這條水道交通線,自成都“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掛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逾千里,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20]可見這條水路交通的繁榮。以長江上游水道與長江三峽水路勾連形成的水上通道,是巴蜀地區與中原和長江流域地區交通運輸的主要路線。宋代“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自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為十綱。”[21]四川布帛、奇貨、茶葉、藥材等產品,通過它們運出,其他地區的各種產品也由此輸入。夔州地當荊楚貨運要沖,恰在渝州下游,“利走四方,吳蜀之貨,咸萃于此。”[22]
成都南郊的流江兩岸,萬里橋至合江亭一帶,由于是成都買舟東下三峽的水運碼頭,更是繁榮。唐代這里就已是“門泊東吳萬里船”[23]。宋代又在合江亭設立船官,以管理來往船只。呂大防《合江亭記》說合江亭:“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水,滄波修闊,渺然數里之遠……商舟漁艇,錯落游衍。”[24]范成大也說他離別成都時,“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25]由此可見,宋代成都的航運業是比較興盛的,沿江商船、漁舟錯落穿行,水上交通繁忙。
唐宋時期,成都與外省的水路貿易,主要是以岷江、沱江、嘉陵江為依托,長江為主渠道的水上交通貿易航道。這條貿易路線,以成都地區為起點,以長江中下游各地區為貿易輻射區,形成較為廣泛的通商貿易關系。成都物產豐富,其商品通過長江運道,順流而下,與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貿易聯系。生活在盛唐時期的陳子昂曾上書說:“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26]江浙等省,又以成都急需商品溯江而上,滿足了成都地區的需求。“水程通海貨,地利雜吳風”[27],就是對這種貿易關系的生動的描述。
根據唐宋時期的記載,巫峽、黔南、荊州、襄陽、金陵、廣州等地,均有商人遠至成都貿易。唐人李貽孫記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位于長江岸邊的云安,成為成都與東南地區貨物匯聚地,“商賈之蹤,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焉。”[28]唐咸通(公元860—874年)中,巫峽商人爾朱,“每歲賈于荊益”[29];唐代黔南采藥者黃萬祐“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賣藥”[30];唐代荊襄商船賈于蜀;[31]金陵商人西上貿易,入蜀經商;[32]廣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時寄錦官城”[33]。
前后蜀時,西川衛前將軍李思益參與下江商人貿易,與“江貨場勾當”[34]。蜀國東鄰南平(地當荊州、江陵一帶),“西通于蜀,利其供軍財貨。”[35]蜀中杜敬安鶴面佛像,擅長水墨丹青,“蜀偏霸時,江、吳商賈入蜀,多請其畫,將歸本道”[36]。由此可見,江南商人對杜敬安畫作的重視。“蜀廣政初,荊、湖商賈入蜀,競請(阮)惟德畫川樣美人卷簇,將歸本道,以為奇物。”[37]唐末五代時,成都市場廣銷香藥或稱海藥,當時李珣著有《海藥本草》,曾記其詳。據時人輯錄該書今存的124種海藥,絕大部分是從歐亞各國輸入的。它輸入成都的多種路線中,經嶺南、南漢、楚、南平入川,必然借助長江水路西上。[38]
兩宋時,成都通往東南各地區的水上貿易更為發達。成都等地區輸送中央政府的財帛,主要通過長江運道,再由湖北荊州等口岸轉運汴梁。[39]成都與東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貿易,亦暢行于長江水道,往來船舶極多,自成都順流而下,千里江面,動輒逾萬艘。[40]
宋代成都茶葉、蜀錦、布帛、藥材、各種土產,都有商人經水路運往全國各地。一些豪商巨賈,或與官府勾結,利用官船押運貨物,以私冒公,“影帶布帛”,或繞道“私路”,借以偷漏稅收,牟取暴利。[41]在宋代,由商而官,棄官經商,或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現象比較普遍。南宋中期,成都“士大夫之貪黷者,為之巨艘西下,船艫相銜,捆載客貨,安然如山”。他們還利用官僚的免稅特權,出售名分、索取商人重金,影庇商人。商人聚集夔門打聽某官出蜀日期,“爭為奔趨”;官僚得以“要索重價,一舟所獲,幾數千緡。經由場務,曲為復護免稅,懷刺納謁,懇囑干饒”。這種現象,“往時不過蜀人之赴舉者為之,既而蜀士之游宦江湖、召赴中都者,或未免循習。其后東南士大夫仕于蜀者,歸途亦多效之。而把揮持節者抑有甚焉”[42]。由于這種偷稅之風盛行,致使“沿江場務,所至蕭條,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43]。豪商大賈和官僚則在這種相互勾結利用中互惠互利,大發其財。
與此同時,頻繁的商品流通和水陸路長途貿易,增加了貨幣的使用量和流通頻率,催生了信用票據、紙質貨幣的產生。由于水上貿易的空前興盛,沿江要津,因其地利因素,發展為商業繁榮的城市。夔州地處長江要隘,是東西水上貿易必經口岸,為當時川東交通和貿易中心;渝州挾三巴之重,位于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二江之商販,舟楫旁午”[44],得以迅速發展;瀘州是沱江與長江會合處,成為“商賈輻輳,五方雜處”的重鎮;嘉州地處岷江隘口,當荊蜀渝瀘要道,是成都與東南地區水路貿易的集結地之一,商業、造船業因之興旺。
宋代四川沿江的州城,雖然仍是地區行政中樞,但城市的商業性、娛樂性的日益增強,逐漸改變著城市的基本面貌;經濟活動的突飛猛進、相應的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行使,使行政職能在發生變化。絕大部分州城都設立商稅務,征收商稅。在城市商業發展中,處于水陸交通樞紐位置的州城在這種變化里顯得十分突出。
1.梓州:唐代為劍南東道治所,商貿繁盛。宋代梓州仍是四川的大都會,梓州路治所,“南控瀘敘,西扼綿茂,江山形勝,水陸之沖,為劍外一都會,與成都相對”[45]。唐代興起的梓州藥市,原為九月一日至八日而散,宋代則增加三日,到十一日而罷。[46]熙寧十年(1077年)梓州州城商稅為55000貫,在四川州城的商稅收入中,僅次于成都府路的商稅收入。故政和年間(1111—1117年)升梓州為潼川府。
2.遂州:地處川中涪江中游,平川沃野,人物富庶,盛產甘蔗和糖霜,是中國最早制作冰糖之地。上游龍州、綿州各縣山區,均為藥材產地,尤以附子、麥冬等產量較高,歷代產銷不衰;綿州更以生絲和絲織品綾、錦等成為遠近暢銷商品,遂州也自然成為中轉口岸。熙寧十年,遂州的商稅額達48000貫,因其商業發達,北宋和南宋時期,梓州(潼川府)路轉運司曾一度設治所于此,主辦一路財政事宜。政和五年(1115年)亦由州升為遂寧府,領小溪、蓬溪、長江等五縣。
3.果州:地處嘉陵江中游,當水陸往來之沖,盛產柑橘、絹帛,每年供應河東、瀘南綾絹數十萬匹,故“其民喜商賈而怠穡事”。其政治地位雖亞于潼川府和遂寧府,經濟地位卻毫不遜色,是“士民所聚則過之”的川東北重鎮,“繁盛冠東川”,當時已是眾所周知;“蜀人喚作小成都”[47]。熙寧十年,果州城商稅額為32000貫,已發展成川東北的商業、貿易中心。
4.嘉州:嘉州是岷江進入長江的交匯口岸,宋代成為長江水上貿易的重要城鎮。岷江是成都通往長江中下游荊襄、江淮等商貿城市的交通干線,沿江彭山、眉山、嘉定成為重要樞紐城市,下行的蜀麻、茶葉、藥材等商品,上行的吳鹽、海貨,都是成都與長江中下游地區貿易的必經口岸。嘉州地當三江匯合處,水勢兇猛,來往舟楫失事者多。唐開元初年,才由海通和尚在三江口倡修大佛,以鎮水勢。因工程浩大,延續百年之久,到唐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才最終告竣。[48]
5.利州:地處四川北部交通孔道。其陸路北達秦陜,南過劍門而入兩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閬州、果州而達夔峽,上行而到興州、鳳州,實為舟車咽喉之地。雖然土地貧瘠,城廓矮小低下,居室簡陋,但是仍然發展成劍外一大都會,商業貿易相當發達。利州道上,“歲貢綱運,使命商賈,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群盜,悉皆屏跡。”[49]熙寧十年利州城商稅額43000貫,僅次于成都、梓州、遂州,居四川商稅收入第四位。商稅的數額,反映了當地商品的銷售量,因為商稅是按商品的價值或數量來征稅的。時人稱利州“為小益,對成都之為大益也”[50],足見利州在經濟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6.渝州:宋代以渝州為代表的巴渝城市比前代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是長江上游和中下游貿易快速發展,直接促進巴渝經濟的結果,也是伴隨著漢族居民的遷入和僚人等少數民族的漢化快速推進區域經濟進步而出現的城市化進程。巴渝經濟進步包括農業的進步、手工業的發展、商業的活躍、人口的增加等幾個方面。巴渝地區山區和丘陵區的開發,對山區、丘陵區農業梯田、塘堰工程的建設,改善了農業的落后局面。川東一帶沿岸臺地,地暖早熟,不少農田種植了早稻和中稻。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直到八月,中晚水稻才完成收割,因而“民食稻魚,兇年不憂,俗無愁苦”[51]。
工礦業中渝州、昌州、合州紡織、井鹽、瓷器以及綦江鐵礦業均得到快速發展,南平軍、合州均設置鑄鐵監。[52]宋代巴渝地區城市發展的一個首要標志,是巴渝商業比前代有所發展,并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商稅收入的具體記載,巴渝地區同鄰近各州相比,稅額處于中等水平。熙寧十年(1077年),渝州、合州、涪州商稅額都超過了3萬貫,南平軍因新置不久,商業尚不發達,僅3000余貫。巴渝地區商稅總額達到126826貫,這個數字雖然低于成都府(其時商稅總額為171631貫),但高于杭州府(82000余貫)。從戶均商稅看,巴渝五州軍戶均商稅為0.946貫;而川峽四路戶均商稅為0.768貫,全國戶均商稅為0.481貫。巴渝五州軍戶均商稅不僅高于川峽四路戶均商稅,而且幾近全國戶均商稅的兩倍。商稅收入主要集中在州城,部分縣雖也設稅務,但商稅收入大都偏低。交通條件是影響商稅收入的重要因素。合州、渝州都在長江沿岸,地處水陸交通要道,均比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而非交通要沖的昌州高出不少。江津縣亦因水運方便,稅額高于其他各縣,說明水陸交通要道對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對城市發展起著促進作用。[53]
渝州地處長江、嘉陵江匯合處,巴蜀各地運往東京汴梁、江淮和東南臨安(今杭州)的貨物或官物,都由長江干流或嘉陵江經渝州等沿江城市東下,“商賈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幾”[54]。渝州已成為四川東部的交通樞紐和商業貿易中心之一。合州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匯之處,農副業都相當發達,又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已發展成為嘉陵江流域的物資集散地,成為商業性城市。北宋早期,在昌州3縣各場鎮設有38個稅務;熙寧十年,因稅額過少,省并后僅在縣城置務。這表明除縣所在之場鎮外,其余場鎮商業貿易仍然是初步的。渝州成為成都與川東民族地區的轉運口岸,西去成都,出銅梁、過普州(今安岳縣)、簡州,道路雖然難行,但“商賈之往來冠蓋之,東西行者日不知其幾”[55]。官府在銅梁設置“勸農官”“酒稅官”,專“提私茶鹽礬,兼催綱就權”[56]。前述夔州路市鎮數據,證實渝州地區商品經濟的較快發展。有些交通不便、經濟落后的地區,場鎮市場很少,甚至還有個別空白地區。[57]地區發展不平衡顯而易見。
二、重慶開埠,帶動成都城市經濟轉型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煙臺條約續增專條》簽訂,使重慶成為對外開放的商埠。外商可在宜昌、重慶間雇傭華船或自備華船往來運貨,享受子口稅待遇。[58]根據這一專條,英、法、美、日、德等國先后在重慶設立領事館。光緒十七年,清政府正式勘定重慶南岸王家沱為商埠地址,[59]在重慶設立海關。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Hart)任命英人霍伯森(H·E·Hobson)為重慶稅務司,全面管理重慶進出口貿易。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使重慶府同沿海城市一樣,成為全面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規定新開通口岸任憑日本輪船自由行駛,允許“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制造;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或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60]。《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只承認開重慶為商埠,并未承認外輪可以進出川江;而《馬關條約》卻為國際資本取得了外輪直航重慶的權利,使四川與國際市場建立了直接聯系。值得注意的是,《馬關條約》規定:通商口岸準許外國商民自由貿易,開設工廠,“從事商業工藝制作”。其“為貿易、僑居、工業和制造業開辟了四個新的通商口岸;輪船在長江上游從宜昌到重慶的航行權,保證在內地設立批發和通商口岸、從事工業的權利。根據最惠國待遇,英國人民可以享受這一切特權”[61]。從此,清廷制止外資深入內地的防御戰略宣告徹底破產,外商從政治和法律上獲得了在四川投資的保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重慶海關又增設萬縣的通商口岸。實際上,整個川東地區已納入了對外開放的范圍。[62]
近代四川被迫對外開放地位的確立,使外商受到極大鼓舞。他們紛紛入川建立洋行、公司,選擇項目,準備在與同行的競爭中獲得最大的投資效益。但在現實中,他們又面對這樣一些棘手的實際問題。
(一)交通運輸問題
四川與外界的交通極其困難。陸路早有蜀道難之稱。川江水道受三峽險灘阻障,歷來只能行駛載貨量有限的小型木船,給大規模的中外經濟交流造成很大不便。自宜昌開埠后,外商“屢探峽江險阻”[63],以英商立德(Archibald J·Little)為代表的外國商人和以英國為代表的歐美政府,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探測川江行輪的可能性,并特制各種江輪、炮艇,上航重慶,試圖開辟入川貿易投資的航路,但未取得預期成效。[64]
川江輪運問題無法解決,外商在長時期內只好依賴川江的傳統運輸工具——木船。外商自備木船或租用木船,懸掛外國旗,同樣享受子口稅優待。但是,木船載重量很少,損失率高(在川江險灘報損率為10%),運輸周期長(從上海運貨至重慶需3~6個月)。這給外商擴大對四川的通商投資活動造成難以逾越的障礙。重慶海關稅務司華特森認為:“資本家們在四川省的進一步開拓,必須與四川以外的世界互相攜手,共同努力改善交通工具。”[65]
(二)市場問題
外商在宜昌開埠之初,對四川7000萬人口的消費潛力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他們把打開四川市場作為中國對外關系史的第三階段,“重要程度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條約”[66]。外商甚至把四川看作“僅次于上海、天津和漢口的第四位銷售中心”[67]。在經歷了進口貿易的最初增長以后,江貨的銷售出現了平緩曲折之勢,銷數“不如預期之好”。重慶開埠之后,外商發現,光緒十八年—二十七年(1892—1901年)10年間洋貨入川總值不如預期的理想:光緒十八年—二十一年洋貨入川總值呈現負增長。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三年雖比前段有明顯增長,但光緒二十四年又出現下降態勢;至光緒二十五年雖有迅速增長,光緒二十六年、光緒二十七年卻有顯著下降。[68]
出現這種曲線增長的原因,主要是外商過高估計四川市場的需求,因而陷入增長—過多進口—滯銷的循環圈,10年間年平均增長率為11.6%。從絕對增長數看,四川進口貿易出現兩位數的增長率似乎是十分可觀的。但是,如果考慮到四川外貿起步晚、基數低的實際狀況,這樣的增長形勢并非佳績。與全國洋貨進口總值比,其數額幾乎微乎其微。以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例,四川進口洋貨總值在全國進口洋貨總值16200萬海關兩中只占3%。[69]至20世紀初,四川進出口貿易額最高年份也沒有達到全國進出口貿易總值的5%。[70]這與四川人口占全國總人口10%以上的情況極不相稱。
四川進口洋貨總值遠遠低于全國水平的原因何在?外商在通商投資活動中發現:除了交通困難外,主要原因是四川居民消費水平太低,一般居民基本生活資料主要仰仗于自給性生產,需要由市場提供的商品非常稀少。比如光緒十八年—光緒二十七年外國棉織品在四川市場呈現滯銷趨勢:光緒十八年(1892年)四川進口棉織品總數為735109匹,而10年之后的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進口數反而降為643366匹。外商發現,四川居民對棉織品的消費情況是:“英國布匹主要是川省各大城市少數居民才使用,幾乎只有中產階級購買,……至于廣大農村人口則繼續穿著保暖耐用的土布。”[71]
這些土布都是農民自己生產的,他們“把棉花買來,在家庭里織成布匹自己使用,或者在村莊里出賣,或者借行商銷到遠地。”[72]四川居民對于非買不可的生活必需品,消費率也保持極低的水平。比如,外商觀察四川居民的火柴消費情況:“他在早晨用火柴生火(當他不能從鄰居借來一塊燃著的木柴時),此后一根紙捻或灶火就供應了他的許多次需要。”[73]在這樣低微的消費水平下,外商在四川的任何投入都受到低下的市場購買力的制約。
(三)投資環境的特殊性
外商經過周密考察,認定四川是一個自然條件良好、資源十分豐富的省區。華特生的重慶海關報告說明:“四川發現的礦產包括金、銀、銅、鐵、水銀、煤炭和石油,而輸出的主要物品則為鴉片、麻類、白蠟、蠶絲和250余種藥材。主要制造品是絲綢、刺繡、金漆家具用品、西藏羊毛毯和山羊皮、草席、草帽辮、篾器、蜜餞果品和酒類。”[74]
但是,四川在采礦和制造加工業方面生產力水平不高,生產技術落后,設備陳舊,普遍采用簡單協作方式維持效率低下的生產。比如煤礦開采,四川近代煤窯“采掘皆用舊法,無用機械者。礦區隧道深恒至數里,采者篝燈而入,作勞其間。”[75]挖匠采好之炭,即由拖匠伏地蛇行,拖負300余斤的炭簍,艱難出洞。又如冶鐵業,近代四川中小冶鐵作坊遍布全川,但冶鐵方法原始。豐都縣山區鐵廠每廠用工40~50名,“每日出礦十石或七八擔不等”,“燒礦煉鐵概用木炭。”[76]
以傳統技術著稱的巴蜀繅絲業于19世紀80年代仍在繼續增長,繅絲作坊超過2000家,分布于成都、嘉定、順慶、重慶等地。大部分生絲均由家庭生產。“成都大部分地區,每家居民都以紡、織、繡為業。在鄉間,甚至在冬天,繅絲、洗滌及漂白生絲都是很重要的工作”[77]。但是,四川生絲質量不高,在柔軟和光澤方面,比不上浙江生絲。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川絲無法進入國際市場。70年代初,由于國際生絲原料短缺,川絲開始出口,同治十年(1871年)有6000包川絲從上海輸往國外。此后,生絲一直作為四川重要出口商品,銷往海外市場。但是,由于質量不合國際標準,川絲大多作為廢絲出售,以低賤的價格招徠主顧。[78]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必然對引進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產生負效應,不能達到外商預期的經營目標。這是外商在四川投資中必然會遇到的現實問題。
近代長江對外開放以來,進出口貿易成倍增加,極大刺激了重慶加工出口業的增長。例如重慶的山貨業便起了巨大的變化。開埠前的山貨原由藥材字號附帶經營,并未獨立成幫;間有經營牛皮渣滓加工的膠幫附帶運銷牛羊皮出省,也有經銷洋貨的廣幫販運生豬鬃回廣東加工后出口,均屬小本經營,品種不多,數量有限。19世紀90年代初山貨出口品種和數量急劇上升,由原來的豬鬃、牛羊皮等數種迅速增加到30余種。到清末民初,除已有洋行10余家外,重慶專營山貨的字號已經發展到10余家,中路商20至30家,行棧10余家。[79]
19世紀末,重慶已成為洋貨輸入西南的轉口地。如進口洋布從重慶再遠銷到上游各地大中城市,如成都、嘉定、敘府、綿州、順慶等地,并初步向云貴浸銷。以經營洋布為業的重慶布匹字號隨之大為發展,廣貨鋪也應運而生,大小水客經常云集重慶。一般字號的資本額大多增至3000兩左右,而聚興祥字號已達萬兩。布匹字號也由漢口進貨改為上海進貨,獨資經營者也逐漸增多。光緒(1875—1908年)中重慶布匹業約有60家左右,甲午(1894年)戰后各種洋布充斥市場,重慶作為洋布西南轉運樞紐的作用也更為突出。那些獲得大利的各州縣水客,轉而在重慶開設字號,光、宣年間(1875—1911年)布匹業已增至90家左右。布匹商在資金周轉上較以前活泛得多,資本額一般增至6000兩左右。[80]
重慶系川東中心城市,也具有集散市場的性質。省內及陜甘、滇黔、西藏等省區大宗土產,如糧食、藥材、山貨、井鹽、蔗糖、桐油、生絲、川紙、木材等等,均將重慶作為重要的集散地。另外,湘、鄂、贛、粵等省藥材行銷西南各省者皆以重慶為分配地。清末重慶有20多家藥行、60多家藥棧、100多家字號、200多家鋪戶,有關藥材從業人員2000多人。[81]上游所產桐油也大量匯集重慶出口。進入重慶之桐油大體可分為川北、川江上游和川江下游三區。川北的閬中、江油、南充、鹽亭等地的桐油依靠巴河、渠江、涪江運輸之便,先匯于嘉陵江口之合州,再進入重慶市場。川江上游的井研、榮縣、樂山等州縣通過赤水河、綦江河、永寧河、岷江、沱江等為運道,匯于宜賓、瀘州、江津,再轉入重慶市場。川江下游的南川、酉陽、秀山等州縣借烏江集中于涪州,再運至重慶。同時,重慶也成為大批洋貨入川的集散口岸。[82]
重慶開埠后,借助其地利因素,迅速成為西南進出口貿易中心。成都僻處川西腹地,必須通過重慶口岸與國際市場聯系。有關商務調察報告說:“每年在一定的季節里,商人從僻遠和遼遠的城鎮如成都、保寧府、潼川府、遂寧縣、嘉定府、敘州府、綿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陸路,有的由水路來到重慶,運來他們的土產——鴉片、藥材、生絲等等,并運回土貨。”從事進出口貿易的重慶商人與上海和重慶的外國洋行建立了長期合同關系,負責向長江上游推銷洋貨和向洋行提供國際市場需要的土貨。例如,“重慶洋布進口貿易全部操在27家商號之手,他們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駐上海。”[83]這些商號把洋布從上海運回重慶后,首先批發給廣貨商人,廣貨商人隨即轉手批發給全城大小布莊、布店;布莊、布店除零售外,再將洋布轉售外埠大小水客,由水客將洋布運銷成都、嘉定、敘府、綿州、順慶等地。成都進出口貿易實際上只是重慶進出口貿易的一部分。
法國人馬尼愛于光緒年間考察了成都商業貿易狀況后認為:成都“為長江上流盡頭之埠,……此中商務之盛,一望可知,貨物充牣,民戶殷繁。自甘肅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間數千里內,林總者流,咸來懋遷取給”。他在成都所見“洋貨甚稀,各物皆中國自制。而細考之下,似有來自歐洲者,但大半掛日本牌記。出口貨有絲綢、布匹兩項,物既粗劣,價反加昂,惟耐久經用,行銷故廣。不特銷于四川,即毗鄰各省,亦爭相購致也。銷路之遠,可至廣西、云南,乃至北圻各埠。” 四川各屬所產草帽、藥材等土貨,積聚成都后,“能在各通商口岸覓得西國主顧,裝船后運赴漢口,以達上海。”如法國某洋行將草帽“發行歐洲,發約數千包也”;各種草藥“尤以成都為薈萃處。凡藥肆所售藥料,皆來自四川裝運。”[84]
成都的進出口貿易市場在20世紀初確已形成,傅崇榘《成都通覽》明確記述了成都客商中與進出口貿易有密切聯系的商幫,如 “出口貨幫”“棉紗幫”“匹頭幫”“布幫”“蘇貨幫”“傾銷幫”“藥材幫”“綢緞幫”“皮貨幫”“皮革幫”“絲幫”“書籍幫”“麻幫”“玻璃幫”“顏色幫”。大宗洋紗、洋布銷售成都市場,質地良好、價格低廉。成都郊縣行銷棉花、棉紗、洋貨、匹頭,郫縣“每年約值銀三十余萬兩”。他也記述了專門經銷洋貨的成都商號,如“公泰字號”(西東大街)、“從仁祥號”(科甲巷)、“光裕厚號”(總府街)、“正大裕號”(暑襪街)、“馬裕隆號”(西東大街)、“章洪源號”(東大街)、“大有征號”(總府街)、“元利生號”(西東大街)。這些商號經營的洋貨種類繁多,有鐘表、燈具、瓷器、玻璃、洋酒、洋煙、化妝品、衛生用品、染料、洋藥、時裝、皮具、眼鏡、文具、金屬用品等數百種商品。經營本地商品的成都商家,根據重慶洋行買辦的需求收購土貨。其收購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和藥材、土特產品,如豬鬃、鴨毛、赤金、人發、牛骨、牛皮、生絲、草帽、兔皮、破布、火麻、茶葉、五倍子、大黃、川芎等。[85]
根據本世紀初的資料統計:成都地區成都、華陽、雙流、溫江、新繁(今屬新都)、金堂、新都、郫縣、灌縣、彭縣、崇寧(今屬郫縣)、崇慶、新津、邛州(含今邛崍、蒲江、大邑縣)等16縣常年流通的商品共計251種,其中123種為本地生產,128種由外地輸入。本地生產的商品中,行銷上海、北京、廣東、外洋部分有:豬鬃、鴨毛、煙土、赤金、麝香、五倍子、牛骨、牛羊皮、兔皮、皮渣、人發、生絲、草帽、巴緞、破布、火麻、白木耳等20種,占本地流通商品1/6弱。外地輸入的商品中,屬于洋貨部分的主要有:洋紗、洋布、洋油,以及各種洋廣雜貨。由此可見,近代成都商業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的貿易關系十分薄弱,成都商品市場流通的主要商品仍然是傳統消費品。外商直接貿易投資的事例不多,真正獲得成效的商業經營業績更加有限。
綜上所述,19世紀下半葉,歐美國際資本向成渝地區傳統商貿市場進行了長時期的沖擊,由于強勢文化的優勢,取得了以重慶為開放口岸的戰略據點。90年代,隨著重慶商埠的對外開放,外商逐步控制了川江航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和歐美商人又取得在華設廠的特權,推動了外商對華投資的熱潮。外商入川投資,除由洋行、公司獨資經營部分土產加工企業外,還相繼與四川官方和私人簽署了第一批開發礦產資源的投資協議和合同。由于20世紀初四川反帝愛國運動的興起和辛亥革命中清王朝的覆滅,上述外商投資協議合同的多半未能付諸實施。但在重慶開埠的歷史進程中,成渝兩大經濟區仍共同擔負了經濟轉型期的時代重任,繼續起著經濟社會開放的互補作用。
注釋:
[1]唐·陳子昂:《上蜀川軍事》,《陳子昂集》卷八。
[2]《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三《王行言》。
[3]馮漢鏞:《唐代時期劍南道的交通路線考》,《文史》第14輯,1982年。
[4]唐·李蒲:《通泉縣靈鷲佛宇記》,《唐全文》卷八百一十八。
[5]《唐國史補》卷下《虜帳中烹茶》。
[6][8]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十二《虎盜屏跡》。
[7]宋·蹇汝明:《鈍庵記》,《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三。
[9]《宋會要輯稿·方域》十之三。
[10](新羅)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三。
[11]《唐會要》卷五《鹽鐵》。
[12]《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貨下五》。
[13]陳麗瓊:《試談四川古代瓷器的發展及其工藝》,四川史學會編《史學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頁。
[14]宋·呂大防:《錦官樓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四。
[15]賈大泉:《宋代四川地區的茶葉和茶政》,《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6]宋·蘇惲:《靈泉縣圣母堂記》,《蜀中廣記》卷八十一引。
[17]宋·袁輝:《通惠橋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中。
[18][19]《全唐詩》卷三百六十五,卷三百。
[20][40]宋·蘇德祥:《新修江瀆廟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七。
[21][39]《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貨志》。
[22]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八十一《大寧監·風俗形勝》。
[23]《杜詩詳注》卷十三《絕句四首》之三。
[24]清嘉慶《華陽縣志》卷三十九。
[25]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
[26]《新唐書》卷一百七《陳子昂傳》。
[27]《全唐詩》第10冊《盧綸》五。
[28]唐·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四下。
[29][30]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引《南楚新聞》,卷八十六引《錄異記》。
[31]《明倫匯·閨媛典》,《古今圖書集成》。
[32]唐·張籍:《賈客樂》,《全唐詩》第4冊。
[33]唐·杜甫:《送段工曹歸廣州詩》。
[34]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二附《李思益》。
[35]《新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高季興傳附子叢海傳》。
[36][37]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中《張玄傳》《阮惟德傳》。
[38]范行準:《李珣及其<海藥本草>的研究》,《廣東中醫》1958年第3卷第7、8期。
[41]《宋會要輯稿·食貨》十七之十八,《宋會要·方域》十二之三。
[42][43]《宋會要輯稿·食貨》十八之二十五。
[44][45][47][50][51]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七十五,卷一百五十四,卷一百五十六,卷一百八十四,卷一百六十五。
[46]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一百五十四。
[48]唐長壽:《嘉州山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72頁。
[49]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一《虎盜屏跡》。
[52]胡道修:《唐宋巴渝地區的經濟發展》,隗瀛濤主編《重慶城市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7頁。
[53]賈大泉:《四川通史》第4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1頁。
[54]宋·冉木:《心舟亭記》,清道光《重慶府志》卷一《輿地志》。
[55]宋·度正:《南峰黃氏第一峰修路記》,《性善堂稿》卷十一。
[56]清光緒《銅梁縣志》卷十六。
[57]胡昭曦、張茂澤:《兩宋時期的重慶》,《重慶城市研究》第82—89頁。
[58][60]黃月波:《中外條約匯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5—17頁,第151頁。
[59]民國《巴縣志》卷十二《工業》。
[61]《英國及外國政府公報》1894~1895年,卷八十七,第799—804頁。
[62]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7頁。
[63]清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五《論重慶通商》,《李文忠公全集》卷二十《譯署函稿》,第1頁。
[64]鄧少琴:《川江航運簡史》,重慶地方史資料組1982年編,第53—65,60—61頁。
[65][78]《重慶海關1892~1901年十年間調查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79年重印本,第174頁,第180—181頁。
[66](美)馬士(H·B·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頁。
[67]謝立三:《重慶洋貨貿易報告書》;英·史密斯:《重慶進口貿易備忘錄》,英國《藍皮書》,1883年。
[68]《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88頁。
[69][83]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91頁、第1549頁。
[70]《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3月15日,第112頁。
[71][73][74]《重慶海關1892~1901年十年調查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89頁、190頁,第170頁,第218頁。
[72]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0年,漢口,第216頁。
[75]民國《巴縣志》卷十二《工業》。
[76]《四川官報》甲辰第14冊《新聞》,第3頁。
[77]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0頁。
[79][80]重慶市工商聯等編《重慶工商史料》第1輯,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頁,第193—194頁。
[81]《四川衛生史料》總第4期,第2頁。
[82]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54~259頁。
[84](法)馬尼愛:《游歷四川成都記》,《渝報》第9冊,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
[85]分見清·傅崇榘:《成都通覽》,巴蜀書社1987年版,上冊第108—109頁、235—240頁,下冊第140頁、226—231頁。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