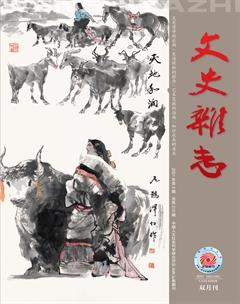古代著名的文人雅集
田旭中



清人張潮在《幽夢影》中寫道:“人莫樂于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閑則能撫琴,閑則能游名山,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茶,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莫大于是。”
古代文人雅士每當空閑之時,喜歡約三五知己,或徜徉綠郊山野,或臥聽松風竹月,或烹泉煮茗,或吟詩作對。這種以文會友的聚會古代稱之為“雅集”。文人們通過焚香、掛畫、瓶供、吟詠詩文、撫琴、禮茶等藝術形式陶冶情操,交流情感,切磋文藝,內容和形式有點類似于現代的文藝沙龍。
“雅集”既然是“集”,必須有雅人,有雅事,還要有雅興,這就是所謂的“雅集”。于是就出現了“或十日一會,或月一尋盟”的雅集現象。這既是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獨特景觀,又是中國文人階層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文化史上,先后出現過諸如蘭亭雅集、西園雅集、玉山雅集等,早已成為歷代文壇佳話。
傳統的文人雅集最重要的特征是隨意性和隨機性。“蓋無所謂門戶之章程,而以道義相契結。”而正是這種隨意性、隨機性與文學藝術家的自然本性相契合,在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中,才會很容易地激發創作靈感,從而催生出名垂千古的文學佳構和書畫精品。
雅集的雅,還在于茶席布置中體現的雅趣。古意茶壺、茶杯、桌旗、盆景、插花等,都是文人對于生活品質的獨特觀照。他們重視娛樂性靈,在推杯換盞中產生創作的欲望,一旦有感而發,便揮毫潑墨,落筆如風,氣貫長虹。中國傳統詩、書、畫中許多名篇佳作可以說大都是文人雅集的產物。
可知,文人雅集是中國古代文士的一種文化情結,也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藝形態。如果沒有這類雅集活動,中國文化史上就會失掉許多瑰麗的篇章。古代文人的雅集活動,既是農耕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與生活點綴。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雅集,隨便翻開一頁,都流光溢彩,令人神往。下面,讓我們隨著時間的脈絡,逐一敘述那些過往的歷史佳話,領略一下古代文士的精神世界。
梁苑之游
主持人:梁孝王劉武。參與名士:鄒陽、嚴忌、枚乘、司馬相如、公孫詭、羊勝等。時間:西漢,距今約2160年。現址:河南省商丘市梁園。
西漢很多王侯熱衷于延攬文士,尤以梁孝王劉武最為著名。他是漢景帝胞弟,最為竇太后疼愛。梁苑,也叫“梁園”,又名“兔園”,是劉武所建的一處私家園林。劉武雅好文翰,廣泛結交當時的文人名士,如司馬相如、枚乘、鄒陽等皆為其座上賓客。他們中的許多人長期居住園內,樂而忘返,“梁園”因此而聞名。唐朝詩人李白有詩云:“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用的就是這個典故。這在史上稱之為“梁苑之游”。
清人袁江畫過《梁園飛雪圖》,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畫上題款:“梁園飛雪,庚子徂暑,邗上袁江畫”。袁江將梁園安排在冬天的雪景中:豪華的宴筵,殿堂中燈火通明,人來人往,觥籌交錯,在雪片紛紛揚揚中,別有一番風味。而且,由于大雪的覆蓋,屋頂的瓦楞模糊地與細密的格窗、文飾等形成強烈的對比。色彩的敷著利用屋頂的白色,襯托出建筑物的絢麗斑斕的彩畫,同樣也別具風味。
西漢一些著名的文學作品如枚乘的《柳賦》、路喬如的《鶴賦》、公孫詭的《文鹿賦》、鄒陽的《酒賦》、公孫乘的《月賦》、羊勝的《屏風賦》、鄒陽的《幾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等都是在梁園完成的。其中尤以司馬相如《子虛賦》最為著名。
孟浩然的一句詩可以概括出梁苑之游的規模:“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不過,嚴格地講,梁苑之游還只能算文人聚集,不算真正的雅集活動。
鄴下之游
主持人:曹丕、曹植。參與名士:“建安七子”(王粲、劉楨、徐幹、陳琳、阮瑀、應玚,時已無孔融)、蔡文姬(蔡琰)等。時間:三國時期,距今約1800年。現址:河北臨漳。
三國時期,曹操定都鄴城。他與兒子曹丕、曹植都喜歡交游名士,因此文士麇集鄴下,經常集宴云游,詩酒酬唱。曹丕在《又與吳質書》中回憶當時的盛況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連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建安七子”之稱出自曹丕的《典論·論文》。而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長,且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被殺,因此實際上只有6人參加了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當時文風極盛,成一時風氣。所以后人評價說“詩酒唱和領群雄,文人雅集開風氣”。鄴下聚會,開創了文人雅集的先河。
明代畫家王問曾據此繪有《建安七子圖》絹本,生動地描繪了這次雅集活動。雖然畫面尺幅不大,但人物形象描繪得栩栩如生。
金谷園雅集
主持人:石崇。參與名士:“金谷二十四友”(包括石崇):潘岳、左思、陸機、陸云等。時間:西晉,距今1725年。現址:無跡可尋。據考證,其位置或在河南洛陽東北。
石崇,西晉時期有名的權臣,《世說新語》將其列入“汰侈”類,在歷史上以生活奢靡而留名。其實,當時他也是頗有文名的。他建有一座別墅,因金谷水貫注園中,故名之曰“金谷園”。金谷園隨地勢高低筑臺鑿池而成,酈道元《水經注》謂其:“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蔽翳”,是當時最美的花園。石崇曾在金谷園中召集文人聚會,與當時的文人左思、潘岳等23人結成詩社,史稱“金谷二十四友”。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將軍王翊從洛陽還長安,石崇在金谷園中為王翊設宴餞行。王翊一行及石崇親朋好友歡聚一堂,所有賓客賦詩述懷,宴后把所賦詩篇錄為一集,命名為《金谷集》。石崇親作《金谷詩序》(今已佚)以記其事。金谷園雅集遂被世人傳為佳話。后人稱這次聚會為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文人雅聚。
明代畫家仇英繪有《金谷園圖》,畫中園林奇花異木皆備,珍禽悠然自得。園主石崇與眾人娛樂,神態悠然。王詵則于《金谷園圖》上題款。清代華喦也創作過同名《金谷園圖軸》,紙本設色,178.7×94.4cm ,今藏于上海博物館。
蘭亭雅集
主持人:王羲之。參與名士:謝安、孫綽、王凝之、王徽之等41人。時間:晉穆帝永和九年,距今1668年,現址:浙江紹興城西南蘭渚山下。
金谷園雅集影響極大,據說后來的蘭亭集會完全比照這個模式來進行。《世說新語·企羨》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東晉王羲之曾與四十多個文人聚會,這便是有名的蘭亭之會。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在會稽山陰之蘭亭,會稽內史王羲之召集著名文士謝安、孫綽、王凝之、王徽之等41人,“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曲水流觴,詩文吟詠,成詩數十首。王羲之把大家所作的詩集在一起,乘興揮毫,寫下文辭與書法并絕千古的《蘭亭集序》。蘭亭集會也因此成為雅集史上的傳奇。這次雅集人數眾多,主持人又是真正的文人領袖而非權貴,并且出現了絕世書法《蘭亭序》,因此在文化史上尤為重要。
歷代書畫家對這次重要集會都有過表現或描繪,如唐代大書家褚遂良、馮承素、虞世南先后都摹寫過《蘭亭序》,今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而王羲之原作則被唐太宗李世民作為隨葬物陪葬。明代大畫家仇英曾據此作《蘭亭雅集圖》,唐寅 也繪制過《蘭亭雅集圖 》手卷。
滕王閣雅集
主持人:閻伯嶼(時任洪州牧)。參與名士:王勃等。時間:唐高宗上元二年,距今1346年。現址:江西省南昌市西北部沿江路贛江東岸。
滕王閣是滕王李元嬰任洪州都督時修建的。李元嬰是唐高祖李淵的幼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很有藝術才情。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洪州牧閻伯嶼于九月九日重陽節大會賓客,讓其婿吳子章作序以彰其名,在場文人很多,都假意謙讓,王勃卻提筆就作。其事《新唐書·文藝傳》有載:“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閻伯嶼初以“更衣”為名憤然離席,后來聽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句,大驚“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便出來站在王勃身邊觀看他寫完此序,并請入上席,極歡而罷。
王勃作此序時的年齡說法不一,《唐摭言》卷五說是14歲。 王勃《春思賦序》“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予春秋二十有二”,據此推算其 生年為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與會后便溺水驚悸而死,故寫此文時應為26歲。
韓愈在《新修滕王閣記》中說:“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
元代畫家唐棣、夏永相繼以《滕王閣圖》為題創作過畫卷,兩件作品都不大。唐棣畫作為紙本水墨 27.5×84.5cm,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夏永畫作更小,只有24.7×24cm,現存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香山九老會
主持人:白居易。參與名士:胡杲、吉玫、劉貞、鄭據、盧貞、張渾、李元爽和釋如滿。時間:唐代,距今約1176年。現址:河南洛陽。
白居易晚年對仕途心灰意冷。他居住在香山,自號“香山居士”,隱山遁水,坐禪談經。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暮春三月,白居易邀來六位老者,漫步山林,把酒言歡。這次聚會,加上白居易共計七人。座中最年長的是胡杲,已經89歲,依齒序排列,吉皎88歲,劉真87歲,鄭據85歲,盧真82歲,張渾77歲。主持人白居易年齡最小,也已經七十有四。白居易專門為這次七個退休老頭的聚會寫下一首《七老會詩》,詩的上半段是這樣的:“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須。手里無金莫嗟嘆,尊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壯,飲到三杯氣尚粗。”下半段寫了自己當時的感想。
這次雅集后,白居易意猶未盡,當年夏天,他又主持了一次雅集活動。這次參加者有些變化,增加了兩位高年不仕的人,一位是李元爽,時年136歲,是歷史上有記錄的最長壽的人。另一位是95歲的僧如滿,他是白居易的禪學老師。九位平均年齡在九十歲左右的老人詩酒唱酬,轟動一時。為了紀念這次盛會,白居易專門請人繪制了一幅九老圖,并著意突出兩位高壽者,寫下了《香山九老會詩序》:“雪做須眉云做衣,遼東華表鶴雙歸。當時一鶴猶稀有,何況今逢兩令威!”又過了十年,白居易駕鶴西去,但是九老會這種聚會形式卻未成絕唱。白居易在《香山寺》詩里這樣寫道:“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家釀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這首詩寫出了白居易等九位長者在居住香山寺期間的閑適生活。《香山雅集》的故事即由此而來,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深。
如今的香山寺內,還保存著九老堂建筑。據說白居易曾經把自己所作的八百多首詩稿存放在香山寺藏經堂內,供后人緬懷。
宋人馬興祖曾據此創作《香山九老圖卷》絹本水墨設色,現藏于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西園雅集
主持人:駙馬都尉王詵。參與名士: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李公麟、米芾、蔡肇等。時間:北宋元豐年間,距今900多年。現址:無跡可尋。據考證,位置或在河南開封解放大道北段。
西園是宋初“功臣”王全彬的后裔、“將門之子”王詵的宅第。王詵(1048—1104),北宋貴族、文人中的卓越畫家,字晉卿,太原人。王詵自幼天資聰穎,過目不忘,諸子百家無所不知,琴棋書畫無所不精,整日與文人雅士吟詩作畫。元豐年間(1078-1085年),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儀、鄭嘉會、張耒、王欽臣、劉涇、晁補之以及僧人圓通、道士陳碧虛等人會集于王詵府邸西園,故稱“西園雅集”。
這是一次影響僅次于蘭亭雅集的盛會。召集人王詵為當朝駙馬,名士則都是當時書畫界泰斗。后來被譽為“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者,其時就占了三家。秦觀是大名鼎鼎的詞人,李公麟是北宋首屈一指大畫家。王詵本人曾作《西園雅集圖》。李公麟亦據這次雅集作《西園雅集圖》。大書家米芾作《西園雅集圖記》以記其盛。“西園雅集”遂成為后世文人墨客追慕不已的一段佳話。
南宋著名畫家劉松年也據此創作過《西園雅集圖》。圖中蘇軾、黃庭堅、米芾、圓通大師等盛會于王詵西園。16人分四組:王詵、蔡肇和李之儀圍觀蘇軾寫書法;秦觀聽陳景元彈阮;王欽臣觀米芾題石;蘇轍、黃庭堅、晁補之、張耒、鄭靖老觀李公麟畫陶潛歸去來圖;劉涇與圓通大師談無生論。該畫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玉山雅集
主持人:顧瑛、楊維楨。參與名士:黃公望、倪瓚、王蒙、張渥、王冕、趙元等。時間:元末,距今600多年。現址:江蘇昆山巴城鎮。
顧瑛(1310—1369)是元后期江南名士,名瑛、一名仲瑛,字德輝,號金粟道人。顧瑛與倪云林、曹夢炎并稱為江南三大巨富。顧瑛好慕孟嘗君之為人,薄功名,購古書名畫、秘玩彝鼎并邀天下勝流相唱和,風流文采,鼎甲一時。據顧瑛《玉山草堂名勝集》記載,其大小雅集凡50多次。
玉山雅集雖以酬唱詩文為主,然而詩人多兼書畫,故書畫交流必在其中。從至正八年(1348年)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余年間,海內文人名士如張雨、黃溍、黃公望、倪瓚、楊維楨、王蒙、朱珪、楊基等均到過顧瑛的玉山草堂。《六硯齋筆記》記載《玉山草堂集》說,首次玉山雅集時在“至正戊子二月一十九日之會為諸集冠”。此次雅集,大畫家張渥用李公麟法作《玉山雅集圖》,楊維楨為之記,文中贊雅集:“稱美于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耳,金谷龍山而次弗論也。然而蘭亭過于清則隘,西園過于華而靡也,若今玉山之集非歟。”其將“玉山雅集”與王羲之的“蘭亭雅集”、王詵的“西園雅集”相提并論,可謂推崇至極。這也就確立了顧瑛“玉山雅集”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地位。
“元四家”中的黃公望、倪瓚、王蒙三家先后都出入過玉山草堂,元末江南文人畫家中的重要代表張渥、王冕、趙元都留下過詩書畫作合璧。元詩中,頗有一些寫于“玉山佳處”。清人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玉山雅集”:“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其賓客之佳,文詞之富,則未有過于是集者……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后,猶想見之”。
江亭雅集
主持人:鮑桂星。參與名士:錢儀吉、吳嵩梁、顧莼、朱為弼、張澍等。時間:清道光三年。距今198年。地點:在今北京西城區太平街。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監理黑窯廠。工作之余,他在慈悲庵西部構筑一座小亭,以供休憩,當年興建,翌年而成;又從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一詩末句“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拈出“陶然”二字為此亭命名,別稱“江亭”。
十年后,江藻長兄江蘩又對亭子進行了修改擴建。此地“流水半灣,潺潺沙渚,蒹葭聚生,綠波相蕩,居然有濠濮間意”。從此,陶然亭成為清代京城重要的風景游賞地和士大夫的雅集場所,被譽為“周侯藉卉之所,右軍修禊之地”“宣南士夫宴游屢集,宇內無不知有此亭者”。道光三年(1823年),內閣學士鮑桂星邀請了一批文士至此雅集。然而這次雅集似乎沒能留下什么重要的文藝成果,故而不為人所重。
縱觀古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文人雅集恐怕要數東晉的“蘭亭雅集”、北宋的“西園雅集”、元代的“玉山雅集”。“蘭亭雅集”催生出千古書法名篇《蘭亭序》,“西園雅集”誕生了一批書畫名作,而“玉山雅集”以持續時間長,參與文士多而著稱。
雅集這種形式之所以能夠把文人凝聚在一起,不僅因為它是自發和自由的,符合文人追求的理想人生,更因為這種形式背后有一種文化的力量。文人在其中所追尋的,正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所謂“同氣相應”“志同道合”都反映在其中。反觀今之各種名目飲食文化,烏煙瘴氣的飯局聚會,精心安排的品鮮嘗美,不少已淪為利益交換的場所。而古人的依山傍水、清膾疏筍、吟詩作畫則顯得瀟灑高潔,詩意暢快!撫今追昔,與其說逝去的是高人雅致,毋寧說失去的是一種文化傳統。
幸好,歷史為后人留下了那些美好的懷想和經典,讓我們能夠在浮躁中反求諸己,在閱讀與觀覽中去拾取心靈的那分寧靜。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家一級美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