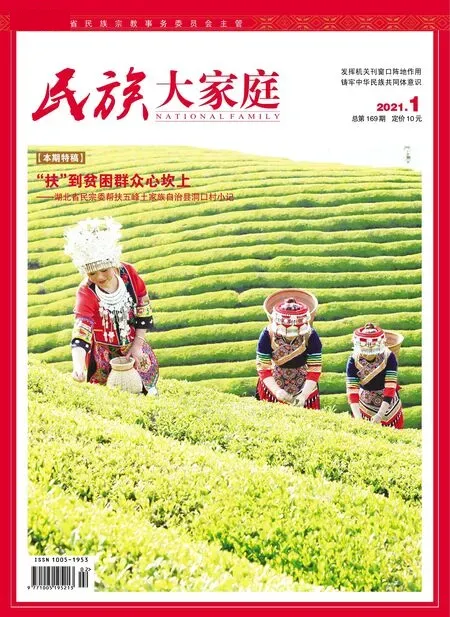那些年那些事
文/趙詩平
站在講臺上,看著孩子們那一張張燦爛的笑臉,一雙雙閃亮的眼睛,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
1973 年,我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鄉的一個小山村,有幸能夠親身經歷改革開放之前農村生活的艱辛,親身經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騰飛,綜合國力急劇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光輝歷程,見證改革開放40 年來農村生活和基礎教育的變遷,我倍感驕傲和自豪。
我的父親在大隊的小學教書,母親務農,過去稱為“半邊戶”。家里有姊妹五個,吃飯的人多、勞動力少,經常差工分,社員都說我們家像“五保戶”,靠他們養起的。
生產隊在分糧食的時候,把紅薯、洋芋當主糧,谷子、玉米當補糧,輪到分余糧的時候,我家就只能分到一些紅薯和洋芋。那時的物資非常匱乏,糧食十分緊缺。從記事起,家里來了客人要跟鄰居家借面條、借雞蛋,我是老幺還可以得到一小碗面條,哥哥、姐姐就只能用面湯煮點剩飯吃,他們都說我是“幺兒幺女命肝心”。
1982 年實行包產到戶,大隊改成了村,小隊改成了村民小組,家里分了五、六畝田土,還有七畝山林。母親是個堅強的女人。盡管自己不認識字,但是她仍覺得讀書才是孩子們的出路,堅持要送孩子們讀書,家里農活全部落在她的肩上。

湖北省恩施市第三實驗小學校內活動
父親的工資只有30 幾元錢,根本不夠家里開支。好幾次,我聽到父親在房里嘀咕,不想去教書了,要回家種田,都被母親數落了硬是要他到學校去。父親只得每天早去晚歸,盡力幫她減輕負擔。過了兩三年,大姐去讀高中,二姐不忍心母親一個人累死累活地做農活,讀了初中硬是不去上學了,被罰跪了好幾天。三姐帶著哥哥和我到村小學讀書。
村小學是原來隊里的集體保管室,兩棟一層的土坯房,場壩是用來曬糧食的,倒是不小,盡管隊里每年都要組織大家去夯實,但是還是坑坑洼洼的。教室里的黑板就是一塊木板子刷上黑漆,刷子印都可以看見。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粉筆灰直飛。剩余的粉筆頭經常被同學們珍藏,成為向小伙伴炫耀的資本。每天背著帆布書包,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忠于革命,忠于黨”,走起路來格外帶勁。
那時候,板泥巴、抓石子、跳皮筋、踢毽子是最好的游戲。一下課,本子、書都不管他的,跑到場壩里瘋玩。我記得最美的事就是到山上采黃構皮、鐵腳板,曬干扎把,送到供銷社賣錢后,花5 分錢買上一小杯葵花籽,揣在兜里慢慢地嗑。
村小學沒有小賣部,也沒有吃的賣。我們都是早上在家里熱點剩飯,一直管到放學。放學的時候,才走到老屋對門的山梁上,就朝在田里干活的母親喊:“媽,我餓了,快點給我弄飯吃。”隔壁王大嬸聽見我們喊,眼淚直流。從家里到村小學,上坡下坎要走五六里山路,天晴時還好,碰到下雨一身都要淋濕,鞋子上糊的泥巴讓人提不起腳。為此母親給我們各買了一雙短膠鞋,不管天晴下雨都穿。
過些年家里日子好些了,父親有事到區里和縣城里去,經常買些“娃娃書”帶回來,《地道戰》《鐵道游擊隊》,還有四大名著的連環畫,我愛不釋手,一看就是半天。我經常把書帶到學校借給同學們。可能是愛閱讀,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盡管國家在1986 年已經在推行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兩基”工作,但還是有部分家庭條件差的、成績差的農村孩子上不了初中,甚至有的連小學都讀不完,就早早地在家務農。
小學畢業的時候,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恩施市五中。那可是芭蕉最好的學校,整個村小學也就是我一個人考上了,成績差點的就只能在甘溪初中讀書。讀初中的學生們都是從家里帶米,在學校食堂的大蒸子里蒸。學生們輪流值班,用大籮筐把全班的飯盒抬到班上來吃,吃完了又抬去蒸。水少了吃生飯,米少了吃稀飯。有時飯盒放偏了,米撒了水潑了就沒有飯吃。調皮的學生自己沒有蒸飯就偷飯吃,學生們經常為吃飯的事扯皮。吃的菜要么在食堂里買,要么在村民那里買,三、五角不等。家里差錢的,就帶一罐頭瓶子榨廣椒、豆食或腌菜等等。每星期我從家里背五斤米、拿五塊錢,從來不敢買零食,攢點錢也只買些生活用品。
學生們睡的都是自己帶鋪板、棉絮、被單,一個寢室住20 來個人,陰暗潮濕。夏天窗戶四敞八開,蚊蟲飛繞,晚上睡覺只能用被單裹住頭。冬天在窗戶上蒙上一層薄膜膠紙,倒也暖和了幾多,如果有個破洞便感到十分寒冷。學生們大多來自農村,讀書比較勤奮,經常熄燈過后在教室里、寢室里點蠟燭、打手電看書,被值日老師罵了許多次。
初中畢業時已是1991 年,農村大多數人家不愁吃穿了,但是農村戶口和非農戶口仍有很大差別。中考放榜,我的成績上了重點分數線,可以讀恩施市一中,也可以讀中專。讀中專可以“農轉非”,包分配,從此就吃上“供應糧”,工作有了著落,成了國家干部,那可是農村家庭最盼望、最想成的大事,其誘惑力是難以抵擋的。但是讀了高中就還要考大學,如果考不上大學還是要回家務農。那時考上大學可是十分困難的,既然已經可以“跳出農門”了,何必去冒這個險。父母親絕對不想拿孩子的“前途”開玩笑。
得到建始師范錄取通知單的第二天,父親就挑了100 斤玉米、40 斤稻谷,帶著我到甘溪糧食收購站交了任務糧,領到了“供應糧”折子。從9 月1 日到建始師范報到起,每月就有30 斤糧食、29 元生活費,家里每月只需匯少量的生活費。第一學期,我把結余的55斤糧票兌成糯米帶回家,家里著實高興了好些天。就在第二年國家取消糧食統購統銷,吃“供應糧”成為歷史。
1994 年8 月,我被分配到芭蕉區黃泥塘小學教書。從家里到學校有20 幾里路,只有在黃泥塘逢場的日子才有一趟“趕場車”可以坐。到學校報到那天,我是一個人背著鋪蓋卷和行李去的,肩膀被背簍系勒出了血痕,背上也磨起了泡,很久我都覺得傷疼。學校對我很是器重,安排我擔任五年級住讀班語文老師,兼班主任。黃泥塘小學是王家村、青龍山村、二鳳巖村和黃泥塘村的中心小學,除黃泥塘村的學生外,其他幾個村都要在各村小學讀到四年級,然后到黃泥塘小學讀五、六年級。當時,黃泥塘小學有15 名教師、300 多個學生,新教學樓是一棟兩層樓的平房,是黃泥塘集鎮上最好的房子。
2001 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2003 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2004 年,國家教育部、財政部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地區“兩基”鞏固提高的意見》,農村教育投入明顯增長,辦學條件明顯改善,教育普及程度、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明顯提高,農村義務教育保障機制得到有效落實。
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改革開放40年,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長,教育不斷改革發展。如今,在義務教育實現全面普及和免費之后,進入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益的階段。恩施市實施了標準化學校建設,教室寬敞明亮,桌椅干凈結實,還配備了多媒體,學校里有平整、寬闊的操場,有球場、跑道,還有計算機教室、圖書室等等。兩免一補、營養午餐等政策有效實施。學校文化、體育和各類競賽活動經常開展,學生們快樂成長。校園文化氛圍濃厚,教育環境不斷優化。教師待遇大幅度提高,社會地位與日俱增。
我愛孩子們,孩子們也愛我。20 多年來,我不知道教過多少學生,有讀清華、北大的,有在家務農、在外地打工的,也有做了同行的。這些學生經常通過短信、QQ和微信向我表示問候和祝福,我十分欣慰。40 年改革,40 年風雨歷程,今天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局面來之不易,我們一定要時刻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推動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而奉獻智慧和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