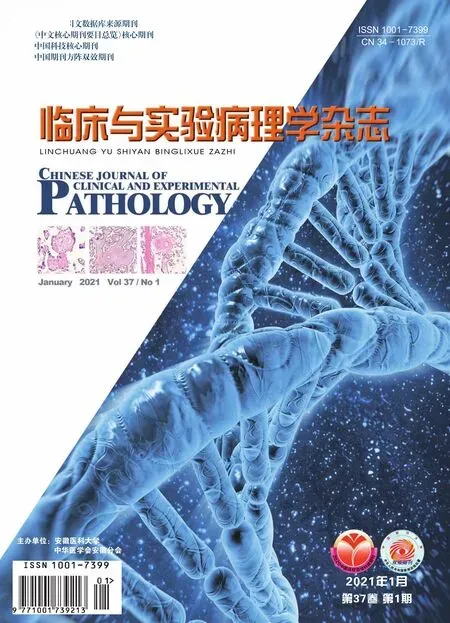卵巢Brenner腫瘤24例臨床病理分析
高巍松,趙 華,印永祥
卵巢Brenner腫瘤(Brenner tumor, BT)是一種罕見的上皮性卵巢腫瘤,占所有卵巢腫瘤的1%~2%,交界性BT及惡性BT尤其罕見。由于其發病率極低,患者多缺乏典型的臨床表現,目前尚無規范的診療方法。通常是絕經后婦女在其他手術過程中偶然發現卵巢BT。它們可以與其他卵巢疾病(如黏液性卵巢腫瘤)一起發現,并且可以與其他女性生殖器腫瘤共存[1]。為進一步了解BT,本文回顧性分析24例卵巢BT的臨床病理資料,探討其臨床病理學特征、免疫表型、治療及預后,并復習相關文獻,旨在提高臨床與病理醫師對其的認識水平。
1 材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收集2013年3月~2020年3月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婦幼保健院卵巢腫瘤11 875例,經病理確診為卵巢BT 24例。24例患者年齡27~72歲,平均54.95歲,中位年齡57歲,其中育齡期婦女6例(25%),絕經后婦女18例(75%)。24例BT中16例(66.7%)為良性BT,平均年齡為55.01歲;7例(29.2%)為交界性BT,平均年齡為55.85歲。1例(4.1%)為惡性BT,年齡為47歲。
1.2 方法標本均經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脫水浸蠟,包埋后切片,分別行HE和免疫組化EnVision法染色。即用型抗體CK7、CK20、p63、Ki-67、C-erbB-2、WT-1、PAX8、ER、PR均購自福州邁新公司,即用型抗體GATA3購自北京中杉金橋生物公司。
2 結果
2.1 臨床特點24例患者中,9例因體檢發現盆腔包塊就診,4例因陰道不規則出血就診,3例因腹脹、腹痛就診,2例因子宮肌瘤就診,2例因子宮頸病變就診,2例因子宮內膜癌放療就診,1例因體檢發現下腹增大就診,1例因剖宮產就診。24例中有3例合并黏液性囊腺瘤,2例合并卵巢單純性囊腫,4例合并子宮頸鱗狀細胞癌,1例合并子宮平滑肌瘤,1例合并卵巢子宮內膜囊腫,1例合并子宮肌腺病,1例合并淋巴管平滑肌瘤病,1例合并子宮內膜腺癌,1例合并子宮頸腺癌,5例無其他合并疾病(包括1例惡性BT)。其中有些病例合并兩種及以上疾病,如1例合并卵巢冠囊腫和平滑肌瘤,1例合并子宮肌瘤和乳腺癌,1例合并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腺癌,1例合并黏液性囊腺瘤和胃癌。24例BT患者均發生于單側卵巢,左側和右側相同,各12例。
2.2 術前檢查24例患者通過婦科雙合診檢查大部分可在腹部捫及腫塊,活動度中,無壓痛;B超提示附件區混合型包塊或低回聲團。1例惡性BT的B超檢查示子宮左側見一混合型包塊,大小11.8 cm×11.2 cm×9.0 cm,內回聲強弱不均,內見不規則回聲液性暗區,盆腔積液深4.5 cm,子宮膀胱凹積液深3.4 cm,子宮前壁肌層內見一低回聲區,大小3.7 cm×3.1 cm×3.6 cm,邊界欠清。CT檢查雖無特異性,但可以提示腫瘤的局部浸潤、淋巴結轉移情況,對腫瘤良惡性有一定的鑒別作用。1例惡性BT的CT檢查顯示腹主動脈周圍、髂血管周圍可見淋巴結影,最大者位于腹主動脈旁,大小1.2 cm×0.8 cm,境界尚清,增強掃描呈中度不均勻強化。盆腔內見巨大囊實性密度腫塊影,最大徑12.9 cm×10.8 cm,腫塊境界不清,形態不規則,內見多發粗糙纖維分隔影,增強掃描實性成分及纖維分隔呈明顯不均勻強化改變。考慮:(1)盆腔囊實性占位,伴腹主動脈旁淋巴結腫大,考慮卵巢惡性腫瘤。(2)大量腹水。
2.3 病理檢查
2.3.1眼觀 16例良性BT直徑達13.0 cm;7例交界性BT直徑3.0~26.0 cm,為灰紅色囊實性腫塊,切面灰黃色,略呈編織狀、質地稍韌。1例惡性BT為灰紅色囊腫,大小15 cm×14 cm×8 cm,局部已破,切面囊實性呈多彩狀,實性區灰黃色顆粒狀,囊性區內含血性液體。
2.3.2鏡檢 良性BT鏡下表現為致密的纖維間質內見增生的移行上皮巢,細胞未見明顯異型,核分裂象偶見(圖1)。交界性BT鏡下表現為囊腫壁及結節狀區域均內襯多層移行樣上皮,部分區見鱗狀上皮樣化生,部分上皮巢內見黏液腺樣結構,上皮細胞增生伴異型,細胞圓形至多角形,核卵圓形,核仁明顯,核分裂可見,局部卵巢間質內見腫瘤組織呈巢、團狀分布,可伴黏液性囊腺瘤(圖2)。惡性BT鏡下表現為乳頭狀、實性增生,細胞層次增多,核質比增大,伴異型,核仁明顯,核分裂易見,部分區伴出血、壞死(圖3、4)。
2.3.3免疫表型 24例中CK7(圖5)、GATA3(圖6)和p63(圖7)均陽性。CK20、PAX8和C-erbB-2均陰性。3例WT-1陽性。惡性BT中ER、PR均陽性,1例交界性BT中ER散在陽性、PR陰性;其他BT中ER、PR均陰性。惡性BT中Ki-67增殖指數為40%,交界性BT Ki-67增殖指數為10%~20%,良性BT Ki-67增殖指數<5%。
3 討論
3.1 臨床特點WHO(2014)女性卵巢腫瘤組織學分類中,卵巢BT分為良性BT、交界性BT和惡性BT,其發生率分別為95%、3%~4%和1%[2]。我院自2013年3月~2020年3月收治的卵巢腫瘤患者合計11 875例,其中24例為卵巢BT(0.2%)。24例BT中16例(66.7%)為良性BT,7例(29.2%)為交界性BT,1例(4.1%)為惡性BT。其組織學起源尚未明確,可能起源于輸卵管或Walthard細胞巢—陷于輸卵管旁組織內的化生性移行上皮形成的細胞巢[2-5]。
卵巢BT多發生于單側,雙側同時發病者僅占3%[6-7]。良性BT患者通常無明顯臨床癥狀,因其他疾病手術探查時偶然發現;極少數患者臨床表現為腹部不適或下腹疼痛、臨床上可觸及的腫塊[6,8]。惡性BT多見于50歲以上女性,臨床表現為腹部腫塊或疼痛[9]。本組24例患者均為單側卵巢病變,其中16例良性BT及7例交界性BT患者多為體檢偶然發現或伴其他疾病就診時被發現。1例惡性BT因腹部脹痛就診。BT通常與其他腫瘤共存,最常見的是黏液性囊腺瘤,其發生率為1.3%[10-11]。本組病例合并黏液性囊腺瘤占12.5%。Gaur等[12]發現1例伴平滑肌瘤和子宮內膜腺癌的BT。本組也同樣發現有1例BT伴有平滑肌瘤和子宮內膜腺癌。BT尚無特異性腫瘤標志物且缺乏特征性的影像學表現,術前一般無法做出明確診斷[13]。
3.2 病理特征良性或交界性BT通常表現為境界清楚、包膜完整的囊實性腫塊,切面灰白色或灰黃色,略呈編織狀。鏡下為致密的纖維間質中見境界清楚的移形細胞巢,上皮細胞巢為實心的或中央腔內可見嗜酸性或黏性物質。交界性BT的細胞形態與低級別非浸潤性乳頭狀異型腫瘤相似,偶爾可見細胞異型性和核分裂象,無間質浸潤及微浸潤。惡性BT大體表現為灰紅色囊實性腫塊,切面呈多彩狀,實性區灰黃色顆粒狀伴出血、壞死,囊性區含血性液體。鏡下見含有纖維血管軸心的粗乳頭結構或移形細胞巢不規則伴生長方式紊亂,細胞異型性明顯、核分裂象活躍可見病理性核分裂象,伴間質浸潤。本組1例惡性BT鏡下表現為腫瘤組織呈乳頭狀、實性增生,細胞層次增多,核質比增大,伴異型,核仁明顯,核分裂可見,部分區伴出血、壞死。周圍可見良性BT成分。免疫組化對BT具有鑒別診斷及指導診斷意義。Kondi-Pafti等[6]對30例卵巢BT進行免疫組化分析,發現所有病例中CK7均陽性,CK20均陰性,WT-1(5/30)局灶陽性。Roma等[14]對34例BT進行分析,免疫組化結果顯示CK7、GATA3和p63均呈陽性,CK20和PAX8均呈陰性。本組24例BT中CK7、p63和GATA3呈陽性,PAX8、CK20均呈陰性,與文獻報道基本一致。所有BT都有類似的尿路上皮腫瘤免疫表型,因此免疫組化標記CK7、GATA3和p63(在大多數情況下均顯示強而彌漫的染色)可輔助診斷。

①②③④⑤⑥⑦圖1 良性BT致密的纖維間質中見境界清楚的移形細胞巢,上皮細胞巢為實心的或中央腔內可見嗜酸性或黏性物質 圖2 交界性BT瘤伴黏液性囊腺瘤,局部卵巢間質內見腫瘤組織呈巢團狀分布 圖3 惡性BT瘤細胞層次增多,核質比增大,伴異型,核仁明顯,核分裂易見 圖4 惡性BT瘤部分區伴出血、壞死 圖5 交界性BT瘤細胞CK7呈陽性,EnVision法 圖6 交界性BT瘤細胞GATA3呈陽性,EnVision法 圖7 交界性BT瘤細胞p63呈陽性,EnVision法
3.3 術中快速病理診斷術前血清及影像學檢查無法對卵巢BT進行鑒別和確診,病理檢查可明確診斷,尤其是術中快速病理診斷尤為重要。良性卵巢BT在致密纖維間質內見境界清楚的上皮巢,而交界性BT常為囊性結構伴乳頭狀突起,多行腹腔鏡下患側卵巢腫瘤剔除術或患側附件切除術。由于快速冷凍切片受低溫影響,鏡下見腫瘤細胞密集擁擠、異型性增加,易造成過度診斷;惡性BT與移行細胞癌和低分化鱗狀細胞癌以及轉移性尿路上皮癌在快速病理診斷切片上難以鑒別,而且需有良性或交界性BT成分方可診斷為惡性BT。惡性BT多行全子宮+雙側附件根治術,是否行淋巴結清掃術仍存在爭議[9]。
3.4 分子病理學最新研究發現BT的分子機制可鑒別交界性和惡性BT。Kuhn等[3]通過熒光原位雜交分析了卵巢交界性和良性BT,發現所有交界性BT均存在純合缺失CDKN2A基因,而在良性BT中未發現;CDKN2A的丟失以及KRAS和PIK3CA體細胞突變的減少,在良性至交界性BT的進展中具有一定作用。
目前,交界性BT的發病機制仍不確定并有爭議。已有文獻報道表明,惡性BT通過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激活PI3K/Akt信號通路,證明在交界性和惡性BT中對EGFR和Ras具有中等至強的免疫反應性,而良性BT相反,提示增殖性標志物表達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惡性轉型[15]。現階段對p16表達缺失或減少的具體機制尚存爭議。p16的缺失可能除了EGFR-Ras-Raf信號通路失控外,還可能在病變從良性發展到交界性/惡性腫瘤的過程中起作用[16]。Cuatrecasas等[15]從新鮮冷凍標本中提取的DNA,證明了1例惡性BT中存在雜合性的喪失和p16基因的高度甲基化。
3.5 鑒別診斷
3.5.1卵巢移行細胞癌 卵巢移行細胞癌大體多為囊實性腫塊,伴出血、壞死,囊內可有乳頭或息肉樣質脆的結節。鏡下為卵巢內局灶上皮嗜酸性化生伴輕度異型,內見伴囊狀擴張的移行細胞巢及增生的Walthard細胞巢。局部見腫瘤組織呈實性、乳頭狀、片狀彌漫性生長,上皮層次增多,細胞核質比增大,異型明顯,核分裂可見。其屬于高級別漿液性癌,診斷需排除轉移腫瘤。
3.5.2卵巢顆粒細胞瘤 腫瘤細胞呈彌漫、小梁狀及綢帶狀分布,局部見Call-Exner小體樣結構,細胞短梭形,部分呈咖啡豆樣,可見核溝,核分裂偶見,局部細胞伴黃素化。免疫組化標記inhibin-α、CD99、CR等可資鑒別。
3.5.3轉移性尿路上皮癌 其無良性或交界性BT成分,有泌尿系統疾病病史和免疫組化檢測等均可鑒別。
3.6 治療及預后良性與交界性BT預后較好,多行腹腔鏡下患側卵巢腫瘤剔除術或患側附件切除術。16例良性BT患者行患側附件切除術。7例交界性BT患者行全子宮+雙側附件切除術,術后隨訪未見復發及轉移。惡性BT的預后與患者年齡、腫瘤分級和臨床分期相關,治療以手術切除為主,術后給予紫杉醇+卡鉑方案化療[17]。惡性BT是一種預后較差、局限于卵巢的高級別腫瘤,其復發性難以控制,可以選擇激素、生物療法和放療[18]。最新文獻報道4例惡性BT中有3例局部復發,2例有遠處轉移[19]。本組1例惡性BT行全子宮+雙側附件+大網膜+闌尾切除+腹主動脈旁淋巴結活檢術+道氏窩病灶切除術,診斷為左側卵巢惡性BT Ic期;術后33個月隨訪未見復發和轉移。
(本組有2例疑難病理切片經江蘇省人民醫院病理科范欽和教授會診,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