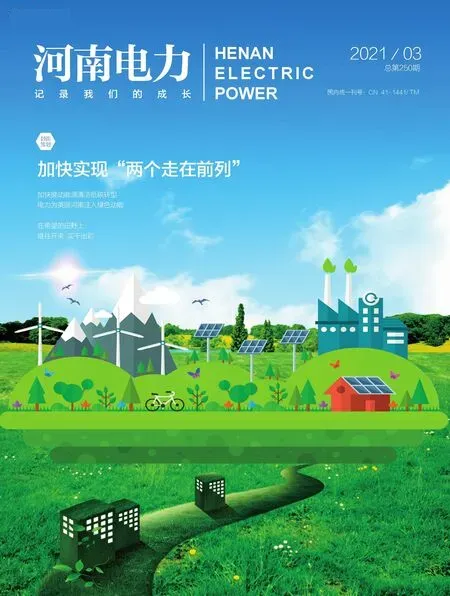歲月深處餃子香
文_李建國
老家堂屋北墻的相框內,有一張黑白底色的照片。盡管經過時光的浸染,它已有些泛黃,但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便想起30多年前的往事,那藏在歲月深處的濃濃溫馨,那飄在心底的餃子清香,令人心緒縈懷,無法忘卻。
照片上是我們一家人吃餃子的情景:矮矮的四方桌擠坐著六口人,父親、母親、姐姐、兩個哥哥,還有我。父親面前的粗瓷老碗里盛著小半碗餃子,他的筷子放在桌角,正微笑著看我們吃。母親則拿著筷子,正從她的碗中夾著一個餃子遞向緊挨著的我,消瘦的臉上滿是笑意。
這張照片攝于1981年的農歷小年。當時,在鄉村教書的父親有個學生在鎮上開了家小相館,因生意不太好,常下鄉到各村“兜攬”生意。那天正巧來到我們村,便給我家留下了這張“吃餃圖”。按照他的意愿,這張照片不收錢,執拗的父親說啥也不肯,硬讓母親從箱子里翻出3角錢作為酬勞。當時一個雞蛋才4分錢,母親心疼了好一陣子。這張飄著餃子香氣的照片,是我們家最早的一張照片,被當成“奢侈品”掛在堂屋保留下來。
“天長愛亦遠,歲深餃香濃。”這張照片中飄散的濃濃餃子香,未因時光變換、季節更替而消散,總能勾起我綿綿的思緒,讓我執念于它的溫情,沉醉于它的醇美,感奮于它的博愛。
我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小時候農村生活清苦,父親在離家三四千米的教學點教書,節假日方能回家。母親便挑起家庭重擔,既要拉扯我們姐弟4人,又要干農活,很不容易。小孩子正長身體,為讓我們吃得好一點,母親精打細算,想盡法子做各種“美食”,比如柿皮青菜糕、薯葉小米粥、蘿卜玉米餅等。其中,最難忘的是母親做的餃子。
母親通常將薺菜或灰菜放在開水中煮一陣子,去除野菜的澀味,添上一些干蘿卜絲切碎,攪拌均勻,加入調料炒制成餡。然后用黃豆、玉米、小麥磨成的雜面做成面皮,包成小小的餃子。煮好后,便成了我們的美味。看到我們吃得津津有味,母親很開心。其間,她吃得很慢、很少,臉上流露著滿足,掛著微笑。有時還輕輕唱起歌:一個餃子祝團圓,兩個餃子祝平安,三個餃子多美滿……
逢年過節,母親總會買來一點肉,加入蘿卜、粉條盤成餡,給我們包白面餃子。她和父親總是最后吃,不夠了就吃菜餅。父親說,當年我們家拍這張照片時,吃的就是白面餃子。每回到老家,談及過往的生活,父親總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這張照片,這份歲月深處的餃子香,分明也刻在他的記憶里。
時光推移,年輪流轉。后來,隨著改革開放深入,農村生活條件明顯改善。母親依然時常給我們包餃子吃,花樣也越來越多,雞蛋韭菜、羊肉蒜花、豬肉大蔥,在我們享受口福的同時,更體會到母愛的溫馨、深邃與博大。
母親認為,餃子代表團圓、平安和幸福。因此,她把餃子轉化為愛的寄托,也成為她追求美好生活、祈盼兒女美滿安康的一部分,讓餃子的清香、濃郁的親情交織成愛的樂章,延續著對未來的憧憬。至今我還記得,姐姐出嫁的前天晚上,我們家吃的是熱騰騰的餃子;大哥考上大學離開老家的早上,我們家吃的是飄著清香的餃子;二哥找到工作去報到的當天,我們家吃的是餃子;我背著行囊到城市打拼的那個早上,吃的也是母親親手包的餃子……
母親和父親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他們喜歡大山的幽靜、小河的清澈,不愿跟著兒女到城市生活。我們每次回家看望他們,母親給我們做的第一頓飯,依然是熱騰騰的餃子。幾年前的一個農歷二月初,臨近周末,我給母親打電話說準備第二天回老家看看她和父親。不料,當天夜里,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說母親身體情況不好。我匆匆趕到老家時,母親因突發心臟病,已經猝然離去。
在辦理母親后事期間,我無意中打開廚房的冰箱,里邊的冷藏室儲放著盤好的餃子餡。父親說,這是母親提前備好的,打算包我愛吃的羊肉餃子。聽到這話,我淚流滿面。
幾天前,遠在另一個城市工作的大哥打來電話,約我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穩定了回家看望父親。“咱爸老啦,性格又執拗,不愿離開老家。以后咱要常回家陪陪老人家。”大哥說著話,忽然話鋒一轉,“不知怎的,這幾天常想起老家的那張照片,想起瓷碗里的餃子,想起咱媽包餃子的樣子。”隨后一陣沉默,久久我倆都沒有說話,似乎在追思逝去的流年、追尋久遠的記憶,又似乎在心靈深處品味餃子的清香。
指尖白露凝霜,流年餃子飄香。時光如流,韶華漸去,唯有歲月深處的印痕,駐留心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