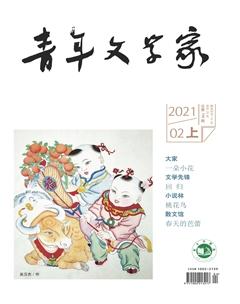惜糧
黃曉夢
關于珍惜糧食的句子信手拈來,“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珍惜糧食就是熱愛生命”“粒米雖小君莫扔,勤儉節約留美名”“倒下的是剩飯,流走的是血汗”……
我初中時學過王愿堅的《七根火柴》,文中寫盧進勇因小腿發炎而掉隊,本想日夜兼程趕上部隊卻遭遇暴雨,身上的衣服被澆透,手在衣服的口袋里意外摸到了一個面團,盡管他餓得發暈,為了不至于一口吞下去,希望這個面團“細水長流”,就將面團捏成了細長條……
糧食就是命啊!
我剛記事時,家里來了貴客,母親從鄰居家借來一盆麥面,給客人搟面條。煮好后讓我把面條從廚房端到堂屋給客人吃,我由于過于緊張,“砰”的一下摔到了地上,面條沾滿了泥,母親又氣又急,忍住沒發作,悄無聲息把面條拾起來,用清水洗凈,又回鍋煮,再端給客人。
在那個糧食匱乏、食不果腹的歲月,母親的淡定與惜糧就是這樣煉成的。
70年代吃的煎餅,是實至名歸的石磨煎餅。我家人口多,隔三岔五地推磨。天氣熱時磨膛里剩的殘渣容易酸腐,前幾圈推的糊子酸味撲鼻,烙成的煎餅又厚又黏,但是母親舍不得扔,在煎餅里撒點鹽,卷成卷,放進鏊窩里烤,改變了煎餅的味道,她自己吃了,每次皆如此。
現在不少人家里逢喜事,就在飯店里大操大辦,飯桌上吃剩的雞魚肉蛋、蔬菜水果、米飯饅頭等都倒掉了;許多家庭、單位食堂,也將吃剩的飯菜倒掉了……
殊不知倒下的是剩飯,流走的是血汗!
一個周末,在我家的餐桌上,先生看到孩子把吃剩的饅頭扔進了垃圾筐,說:“我小時候,父親去扒河,盡管很苦很累,也有危險,但是父親很樂意去,因為能吃到饅頭。父親的飯量很大,可是他每頓都不吃飽,將攢下的饅頭揣進懷里,帶回家分給我們幾個弟兄吃,那時我就眼巴巴地盼望父親回家……”
現在的孩子也許不知饑餓是何味,天天吃漢堡、披薩、意面……我的孩子聽他的父親講其親身經歷的故事,不以為然。
于是在一個麥香的時節,我帶孩子到老家的田野。廣袤的大地上風吹麥浪、香飄四野,我的家人在收割麥子。我也戴上草帽,左手抓麥子,右手用鐮刀割,割一把,放在身后,再割一把,放在身后,如此反復,夠一捆時,用麥秸捆住……兩個小時后,衣服已被汗漬透,口渴難忍,順手端起母親從家里帶來的一鍋溫開水,大口地飲。
孩子在我身后慢騰騰地拾麥穗,我把他喊過來,講道:“我四五歲時就跟在家人身后拾麥穗,稍大點就拿起鐮刀和家人一起割麥子。當時看著田地那么長、麥子那么多,心里發愁,嘴里嘟噥‘什么時候能割完,家人便安慰我‘眼是孬熊,手是好漢。有時不小心割破手,鮮血直流,我就地薅一把艾葉草,用它的葉子止血,繼續割。一把把地割完,一捆捆地捆好,一車車地運到場上,碼成垛,等陽光正好時,再一把把地往脫粒機的簸箕口不斷地塞麥子。打麥子時,機聲隆隆、麥穰橫飛,全身一會兒就布滿了灰塵,麥芒刺得皮膚難受,手上、臉上都黑乎乎的。那時候還用不起口罩,每次打麥子,鼻子、口腔中常常吸滿灰塵,鼻涕、痰都是黑色的。”
我似乎進入了角色,吐了口痰,看兒子聽得專注,繼續講:“打好的麥子還要分揀,用木杈挑走麥秸在旁邊垛起來,剩下的就是麥粒麥糠了。再迎風揚起,把麥糠分離,最后就是麥子。麥子需曬干才能顆粒歸倉。烙煎餅時,用瓢搲半桶,淘洗干凈,機器軋成糊,用鏊子烙成一張張煎餅。有時把麥子推到面粉廠,換成面,用來蒸饅頭、搟面條、包水餃等。兒子啊,當你吃上香噴噴的饅頭時,你想過由田地里的麥子到成為噴香可口的食物,經過多少工序,多少人力嗎?”
兒子若有所思……
恒念稼穡之艱,恒念“粒粒皆辛苦”,恒念做飯之繁瑣,恒念土地面積日益減少……惜糧,二字如此之重,當代代傳承,涌動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