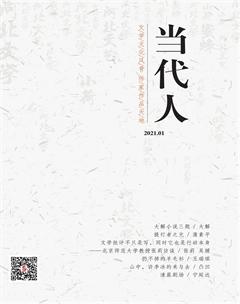山中,訪李冰的來與去
陽平山訪冰不遇
自成都城西北出,過彭州城,沿湔江旁側彭白公路行走,一個多小時后,就泊車在龍門山中了。
已不知多少次來陽平山地區。為丹景山的牡丹來過,為銀廠溝的幽涼來過,為海窩子的古風來過,為“5·12”抗震救災的援建工作來過。但這次,是專為冰而來。
這個冰,是司馬遷筆下“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里的冰,是后來者筆下的李冰的冰。你如果連李冰都不知道,沒關系,都江堰總知道吧,李冰就是那個生了眼鼻嘴、長了胳膊腿的都江堰的肉身。冰不在乎同類知不知道自己是個什么人,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冰只在乎他的都江堰工程是否對同類的生存與發展,實實在在硬硬邦邦有著天長地遠的澆灌作用。北京中華世紀壇雕塑有上下五千年四十尊中華文化名人,李冰位居第六,排在他前邊的是管仲、老子、孔子、孫子、屈原,緊挨在他后邊的五位,是司馬遷、張衡、蔡倫、王羲之、祖沖之。著名考古學家、生前任職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家祐研究員,針對太史公之述,在《李冰為蜀王之后》一文中講:“冰非中原人,不知其姓氏,若中原人,未有不記其姓氏之例。”
著名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書中明確指出:“李冰是蜀族陽平山地區生長的人。他的治水才能,只能是從蜀族柏灌氏和開明氏世代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再加以改進發展而取得的。”
但學界對李冰到底是哪里人卻各執一詞,多有爭議,蜀地說,巴東說,陜西說,山西說,甘肅說,不一而足。有清以來,持巴蜀本土說觀點的有陳懷仁、馬非百、任乃強、王家祐、劉少匆、郭發明、李誠等方家。
我專程到岷山山系龍門山中尋李冰足跡并桑梓地望,自是認同上述方家的觀點。必須承認,生于都江堰的我,對于冰有近乎偏執的熱愛——這也是我承接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湯湯水命——秦蜀郡守李冰》的初衷。
陽平山又名金城山。《新唐書·地理志》載,九隴縣有陽平山,山麓有陽平觀。九隴縣,今彭州市西北九隴鎮一帶。清光緒修《彭縣志》載,天彭門之東有陽平山。
這一地區,正處于古蜀文明的興盛區、岷山水系的發達區。三千多年前,魚鳧率蜀族離開滋養了蠶叢、柏灌部落的茂汶草原,沿河谷東進,翻越九峰山麓,順湔江、洛水,來到海窩子、虹口、湔堋、湔氐、章山等地區(今彭州、都江堰、什邡境內),首建了蜀國王朝。之后,經杜宇、開明兩朝開拓,進新都,迂廣都,定成都。
逆著清冽、激越的湔江,過天彭闕,過丹景山,再過海窩子,方向盤左打,上山,到了坐落于新興鎮陽平村陽平山麓的陽平觀。先秦時期,此處為蜀王祀祠之所。那天是2018年2月19日,正月初四,春節期間,游客、香客不多,也不少,特別適合順著自個兒的心思走。
在陽平山,我的腦屏幕上老是出現一群古蜀族人的行走,中有一張臉,冰的臉。
山西籍民族史學家馬長壽教授在《四川古代民族歷史考證》一文中,釋《魏書·薛辯傳》說:“蜀族原居成都平原,后有徙居山西者。河東、汾陰,及絳與晉城諸地皆有蜀族。”任乃強對“山西之蜀”發表意見道:“這些河東地區姓薛的蜀人,正如薛聰所說,只是魏晉以來從四川遷去的漢人。不過,可能有山西地區的古代蜀族人遺裔與他們聯結相附以度亂離之世而已,未必全是河東古代蜀族的后裔。”《四川上古史新探》按馬長壽、任乃強之說推斷,二千多年漫漫歷史長河中,山西河東一帶出現李冰后人,實屬正常,不足為異。
多年前游黃山,聞知其南麓徽州區潛口鎮東北部有個村叫蜀源村時,嚇了一跳。直到搞明白,其得名僅僅因為該村地形像極了四川盆地,才釋了然,松了口氣。蘇州籍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一書中有言:“綜合上面的記載,可知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其關系何等密切。……伏羲、女媧和神農都生在那邊,他們的子孫也建國在那邊。青陽和昌意都長期住在四川,昌意的妻還是從蜀山氏娶的。少昊和帝嚳早年都住在榮縣。顓頊是蜀山氏之女生在雅礱江上的。禹是生在汶川的石紐,娶于重慶的涂山……游宦者有老彭、萇弘,游學者有商瞿,都是一代的名流。” 擁有三星堆、金沙這種實錘硬核的古代蜀土,從來都是人才輸出之境,蜀源怎會發脈徽地,讓她反成了人流倒灌之域?時光是連續的,又是斷裂的,所以,道該村源頭為蜀人之流布,也未可知。
王家祐在《王家祐道教論稿》一書中對李冰的生平抽絲剝繭深研后指出:“綜觀以上引述,李冰是蜀王開明氏(鱉靈建國,來自楚)五斗米巫師(民族知識分子),蜀中‘李家道的神仙人物,秦改蜀侯為蜀郡守后任用的蜀人,故其歸魂葬所在今什邡縣。”他說:“老子實即彭祖(商周史傳格言編為《丹書》即《老子》)。乃虎族人,故稱‘李耳。”他的推論邏輯為,虎族出自巴蜀,李耳即貍耳,即虎也。又說:“‘李家道的許多神仙皆以‘李為姓,是四川秦漢道教或方士的特色。早于張家道流行于巴蜀的‘李家道,實際上就是原巴蜀氐人所崇奉的‘五斗米巫。”
按照任乃強、王家祐諸權威史家研究,李冰生養及魂歸之地,當在包括陽平山地區、三星堆在內的湔江、洛水流域。
除開出自都江堰水系的毗河、清白江,沱江的本源皆起水于九峰山,從北向南有三條:綿遠河、洛水、湔江。湔江先納洛水,又會綿遠河,再以北河之名在金堂縣趙鎮與毗河、中河(清白江)并流為沱江,最后于瀘州融滾滾長江。
來湔江流域前,已去過洛水流域。在與彭州相鄰的什邡市,除了拜謁章山李冰葬所,還踏勘了古瀑口、朱李火堰、后城山、升仙臺、川主廟、大王廟、李冰村、湔氐鎮等與李冰相關的遺跡。并據此撰三千言《章山謁李冰》作記。
從陽平觀下山,沿來路行駛,十幾分鐘,到了海窩子。
此行有彭州詩人、本土歷史文化田野考察者舟歌導陪,方便了許多。他不光給我介紹李冰與彭州有關信息,還向我引薦了魏新阜。魏新阜在海窩子古鎮開有農資鋪子,系對陽平山地區歷史文化頗有研究與心得的民間學者。在置有貨柜貨架、品種稀薄、約三十多平米的鋪子里,他如湔江一般滔滔不絕的講敘,道出了此處地脈堪輿對李冰一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古蜀國的文明中心,就在陽平山地區,還特別指出并闡解了此地的一些古蜀樹種,何以延續到今天。舟歌在一旁笑答,都江堰怎么延續到今天,古樹就怎么延續到今天。詩人的蹈空思維,雖說不算科學,但從道對萬物的推演看,似也不無東方人哲理。
舟歌指著陽平觀西側一座山說,那就是史料記載的古蜀“瞿上”。瞿上,乃高處之意,瞿上城即為筑在高地上的城。只有建在高地的城,才能既防洪水的沖襲,又防敵對勢力的攻略。瞿上城,是從蜀山西北高原逐漸遷徙而來的蜀族人,在成都附近建立的首座王城。我看見詩人指尖上的“瞿上城”,陡立在湔水南岸一個平地而起、形似狹長矩形山體的平臺上,動物糞便把草木支撐得那么葳蕤、嶙峋。
海窩子居于陽平山東南側,原是山谷中一塊大平壩,湔水急咆咆奔至此處后,被前邊的一道峽谷急彎所阻,湔水回漩,泥沙俱下,就在海窩子形成了一面數十平方里的過水湖海。
站于湔水北岸高山向南俯望,即可看見對岸群山大尺度地凸走過來,因湔水環繞山體流過,并形成過水湖海,竟使其成了一座標準的半島,而瞿上城、陽平觀、海窩子后山以及丹景山,則皆從西至東依次坐落半島之上。奇的是,整個畫面,竟儼然一幅陰陽太極圖。
出海窩子,去了杜甫、陸游詩詠過的盛產天彭牡丹的丹景山。在這里,沒尋到曾有的“李冰廟”,也沒尋到史載的“丹景山又東二里為玉女房”,卻聽到了一個傳說,曰“丹景山神”正是李冰次子李二郎。
在陽平山地區走得肚子咕咕直叫時,便就近在山下尋了一個叫通濟的場鎮晚餐。正食間,一抬頭,偌大石牌坊上的四字“天府原鄉”便罩了下來,弄得我的粗大竹筷老是夾不住一片薄薄的回鍋肉,更夾不住一塊比露珠還嫩的麻婆豆腐。
好一個天府原鄉!
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謹,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華陽國志》)。冰不就是“天府原鄉”嗎?可察天觀地,捉水捕影,冰的肌骨、血脈、呼吸以及來到人世的最初那聲啼哭,又在哪里?
章山謁李冰
身為河流愛好者,水利研究人,再或者身為川人,尤其生命成因與呼吸被成都平原的風吹拂過的人眾,似乎都應該去章山看看,看一個人,這個人叫李冰。
他是戰國末期秦國蜀郡太守,更是一名有著都江堰水利工程這件代表作的治水專家。
李冰陵在章山。古代名人的下葬地總是被時間弄得撲朔迷離,往往導致后世多地爭搶。但李冰的葬所只此一處。
我住在龍泉山脈長松山腳下,章山隸屬龍門山脈,中間隔的恰是成都平原,也就是川西壩子。上車,點火,導航。選了最近的,109公里,預計行程1小時46分。出小區,上沿山公路,在陽光城靠左入廈蓉高速,右轉繞城高速,繞小半個成都城后,右拐成萬高速,左轉洛小路。幾轉幾拐,就見到了左側的李冰路路牌。猶豫了下,還是順洛小路,進了已能一眼瞥見的洛水古鎮。目的地,必須放到最后,否則,拿什么來給此行壓軸?
吾國有多條洛水,但此地的這條,是《華陽國志》指認的被晚年李冰治過的洛水(今名石亭江):“又導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經什邡、雒,別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綿、洛為浸沃也。”
隸屬于什邡市的洛水鎮,渾身上下透出一襲古風。南和馬祖鎮相連,西與湔氐鎮相接。鎮西北的街子場,曾是秦漢時雒縣治所。僅與李冰相關的遺跡就有古瀑口、朱李火堰、后城山、升仙臺、李冰村等。還有供奉、祭祀李冰的場所川主廟,位于場鎮中心。
沿原路出洛水場鎮,右拐李冰路,開了不到兩公里,路邊粗大鐵欄下,有一面長長的、彎彎的、風景挺不錯的水泊,叫李冰陵水庫,從取名看,讓人聯想到的是北京十三陵水庫。一位孤獨的垂釣者,盯著水體入神,似被魚釣住。返程時方知,李公湖,公墓治湖,道的也是這座水庫。一水三名,乃為尋陵者設些周章,以試虔誠焉?過水庫不久,導航提示,目的地李冰陵到了。下車,看見不遠處山腳下,有座色彩鮮艷的古建。走近,發現是座寺院,名大鵬寺。問一背著柴薪快步如飛的鄉婦,方知走錯。于是,調頭,過小石橋,左拐,順溪,沿一條窄得不能會車的鄉道進山。
終于見到一座沒有題名的古建。
空空如也的院壩中,見有位道士模樣的人在掃落葉,問過,方知這就是李冰陵園。看來,古建是陵園門庭。
抬頭,依山一面的平臺上,九龍壁正對的方向,矗立著一尊雄巍的古人雕塑。走近,上石梯,看見了陰刻在雕塑底座上的“李冰”兩個大字,以及大字下方的“約公元前302年—前235年”“第三任蜀郡守”兩排小字。石像黃石琢成,高8.3米,像主左手捋須,右腰佩劍。顯然,雕塑家呈現的是李太守中晚年風采。從都江堰出土的漢代李冰石像看,壯年李太守無胡須。并且,雕塑家突出的是像主的太守身份,而非治水大師,否則隨身的器件似應為探水鐵杖,而不是一柄佩劍。
古代,各色人等的亡故和下葬地是有不同稱謂的。帝王“駕崩”后葬所為“陵”。諸侯“薨”后葬所為“冢”,大夫“卒”后葬所為“墓”,平頭百姓“死”后葬所為“墳”。李冰的葬所稱陵,我想,蓋因他是王吧:宋被冊封為廣濟王,元被加封為圣德廣裕英惠王,清被封為敷澤興濟通佑王。
以為此處就是陵了,但不是,說陵在山上。遂踩著石像旁側的石階上山。
石階繞過石像后,變為陵園中軸線,很陡,路邊間有小亭。在濃密得不透光也仿佛不透氣的古樹中穿行,感覺走了很久,石階還是一望無際筆筆直直向天上通去,與天梯無二。
半山有一平臺,平臺上有一四角墻柱支撐的兩層建筑。以為到了,但還是沒有。設在此處的是頌德壇。正中一道綠色花崗石碑,上鐫:“創科學治水之先例,建華夏文明之瑰寶。”源于江南的水,與李冰的蜀水在章山合龍。
前幾年用登山鍛煉身體,卻將膝蓋鍛煉出了毛病,之后基本不登山,但這是李冰的山,不能不登。是下午,卻有黃昏的幽暗氣場,森嚴如禁衛軍如亡靈的偌大陵地森林中,只有我一人在躬背爬行。居然生發了一種怕和悚的感覺,立馬羞愧于這感覺。熱透胸口、涼透背心的汗,只能是汗顏的汗。此行,妻子伴陪,膝蓋更困難的她,走了一段石梯后,吃不住,說在山下石像處等我。此行是2018年早春二月,乍暖還寒。李冰陵1993年重建,汶川地震嚴重受損,七年后修復。擅治水災的李冰,卻對震災無奈。處身幾近空無一人的360畝陵區,內心的天氣急遽降溫,抵達極寒。要知道,成都平原文化中心天府廣場,距李冰陵僅84公里。安心來的話,市區堵車那點時間,就夠了。沒安心來,一輩子的時間都不夠。事實上,出了什邡地界,知道章山、知道李冰陵的人,很少。遂想起山下陵園門庭院壩,支立的易拉寶上,噴繪有公告《李冰陵道院化募緣啟》,落款為:什邡市李冰陵道院住持鐘道長。陵園的清寡,可想而知。
終于到頂。頂是一面平地,更高的山在側后的山谷那邊。
一眼就看見了秦漢建筑風格與形制的陵,一座圓形的小丘。
明代《蜀中名勝記》載:“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按《開山記》云:什邡公墓治上有升仙臺,為李冰飛升之處。古《蜀記》謂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藏衣冠章山冢中矣。”洛水鎮那座始建于唐朝的大王廟,明代時覓得宋時碑刻,亦詳細記載了李冰晚年“導洛通山”,在后城山遇羽衣人飛升成仙的故事。
史料和傳說,旨在說明,李冰晚年在沱江上游治水時,肉身升了天,成了仙,而衣冠就埋在了當地。如果拋開道家仙說成分,李冰則是病累交加,逝于章山。著名考古學家王家祐在《李冰導洛卒于什邡》一文中指出:“李冰是生于斯,而又殉職于斯,所以歸葬于章山,是符合當時習俗的。”
自1979年內蒙古挖出刻在一件戈上的“上郡守冰造”五字后,一些專家就據此推論,李冰離開蜀郡,履新上郡,卒在上郡任上,而葬骨處成謎。一個冰字,用凍結的方式,將一個人的斷代史與歸屬,鎖定為了一個人的北遷。這里似可提出兩點疑問,一是上郡守冰,就是蜀守冰嗎?二是李冰建了都江堰渠首及灌區,鑿了鹽井,導了岷江中下游和沱江的綿、洛二水,至少也是六十來歲了吧,古代的這個壽數可是高齡。讓一名治水大師、擅抓經濟的老邁官員,遠調戰事頻仍、兵戈鐵馬的邊地上郡,又無半點事功留世,可能不?再則,唐《北堂書鈔》引東漢《風俗通》說:“秦昭王聽田貴之議,以李冰為蜀守,穿成都兩江,造興田萬頃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按這個說法,秦始皇統一之戰因蜀水之功為李冰立有專祠,而這樣的專祠應該是立在蜀地川西壩子,最有可能是都江堰玉壘山,總之邏輯上與上郡無關。
當然,肉身消亡之地,與魂歸之所,不在一處,也未嘗不可。
所以,退一萬步講,即便眼前的陵是衣冠冢,那又有什么呢?畢竟是貼過李冰肌膚、納過李冰氣息的衣冠,是袍,是澤。
為了環境、消防計,上墳香火被禁。見到了陵,除對著一丘土石躬身,默立,什么也不能做,做不了。奇怪的是,默立中,腦海中反復閃回的卻是一段燃燒著亂世戰火的詩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繞陵一周的圍石上,刻有陵主治水立下水功的壁畫。正前方護陵的是四只遠古神獸:水犀、狻猊、蛟龍和巨龜。
陵山所在處為李家山,系章山的一部分。李家山不知何時得名,望文生義,當地土著心中,當為李冰家山。觀景臺附近,竟意外發現有一條汽車道是通上山的,正待后悔自己的粗心,想想是見李冰,歷些艱難,傷點膝骨,應該,立馬釋然。山階九百九十九級,跟我多年前登的張家界天門洞一個級數,不同的是,后者梯面寬展,一目透頂,前者曲徑通幽,蜀霧繚繞。
下山返程時,去了被譽為“小都江堰”的朱李火堰。此處的朱家橋村洪水溝,有一片上千畝的百年棗林。棗是我的最愛,但我來早了,更來晚了。
(凸凹,本名魏平。詩人、小說家、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散文學會特邀會長,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蚯蚓之舞》《甑子場》《大三線》《湯湯水命》《花兒與手槍》等書20余部,其中,獲獎圖書6部。編劇有30集電視連續劇《滾滾血脈》等。獲有中國2018“名人堂·年度十大詩人”、中國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作家”等榮譽。)
編輯:尉遲克冰